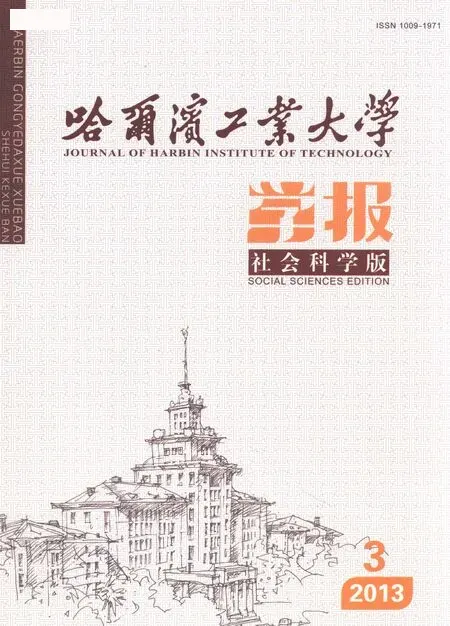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析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中关于V与R的论证
周 力
(1.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2.山东大学 法学院,济南250100)
对当代法学研究而言,德沃金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人物。迄今为止,德沃金的论题都是围绕“正确答案”论题展开:他各个时代的作品大都是对“正确答案”论题的解答。对于“正确答案”命题本身,最早的表述是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他认为“在疑难案件中,唯有一个正确答案”[1]279。而后在《原则问题》中,德沃金强调这一命题并在书中的第五章对否认“正确答案”命题的各种理论进行了批判[2]5。在之后的《法律帝国》中,德沃金强调“法官可以以先前的实践和政治道德原则,将法律运用到最合适的方式来判断疑难案件”[3]226。当然,这样的阐释还有很多。直到今天,德沃金依然捍卫他的观念,并且认为法官“需要宪法哲学来确定法律是什么”[4]。
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是否是其理论的重心曾有过争论。科尔曼(Jules Coleman)认为,“德沃金已经放弃了正确答案论题,取代这个论题的是他在《法律帝国》中的合法权力的政治理论。”尽管科尔曼认为德沃金的观点在于“联系的共同体展现出来的政治优点和理想,并非依赖于法律争议中的正确答案理论”[5],但德沃金经常重复他的“正确答案”论题,这种实践化的努力使得司法与合法性理论产生了某种联系。
德沃金在其著作《原则问题》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证,其关键在于回应对“正确答案”论题的质疑,他假设了两个对手——对手V与对手R。其中,德沃金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策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观念,得出结论:在法律规则出现某种不确定的状况时,也存在唯一正确答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结论理解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
一、关于对手V与对手R的论证
(一)凯卡波尔塔之门的超越
在法律思想史上,自洛克伊始就力图奠定基于个人权利的宪政,但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论述仅仅给出了权利作为基础性的原则以及为保障权利而形成的权力分立[6]。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共同体却不能仅仅通过基本的权利原则来进行保障,法官作为裁判者被认为应当依照法律来进行判断。可是,洛克的工作却留下一个不足:他反复强调法官的判决依据只能是法律,但又在法治原则里论述“法律应当有适当的灵活性”。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法官的裁判权可能成为某种“无法律的专断”。在洛克之后,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怎样使洛克论述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共同体有生命力,历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法律实证主义来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实证主义的前提是保障基于个人自由而形成的共同体中的个人免于法官任意的危险。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是一种事实,法律的有效性来源于某种社会事实的功能,法的应当与法的实际应当是分离的。确定这样一种分离是因为道德的强制是一种不确定的强制,而作为事实的法律却是一种确定性的强制。在追寻确定性的努力中,实证主义者们留下了一个悬疑:法律排除了道德,但法律可能出现“开放结构”[7]121-126。当一个特定案件诉诸法院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确定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规则[7]128,并且即使客观存在某一特定的法律规则,也会面临用以表述该规则的语言出现“阴影地带”的难题[7]123。在法律实证主义者哈特看来,法律规则运用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个案件落入规则的“开放结构”,那么在客观上就不存在可以确定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规则,这一案件的裁判就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法官在规则的“开放结构”的情形下进行实质上的“缝中立法”(interstitial legislation)[8]。“缝中立法”意味着“法律的很多东西将交由法官去发展,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在相互竞争的从一个案件到另一案件分量不等的利益之间作出权衡”[7]132,然后“将该新法溯及既往地适用于该案件中的当事人”[7]135。
法律实证主义通过确认法律是一种事实来维系法律的确定性,然而当一个具体的案件落入规则的空缺结构,案件的当事人就不再是基于一致同意的规则的强制,他们的命运就完全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在裁判此种案件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受任何既有法律的约束——他处于规则之外。这一判断几乎让人难以接受,“缝中立法”将使理性的个人处于他人的专断意志之下,这是一个基于自由的政治共同体所不能接受的。
哈特坚持认为规则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不确定性会发生,法律存在这个突出的事实依然真实。这一判断几乎是在宣称:尽管凯克波尔塔之门开着,但君士坦丁堡依然固若金汤。其实,法律实证主义所留下的不确定的疑难类似凯卡波尔塔之门所造成的灾难:他们在寻求确定性的同时却放弃了确定性,他们在维系法律权威的同时又放弃了法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在捍卫自由的同时又在一个微小的区域中放弃了自由。所以,实证主义对于法律是什么的回答或许是错误的,这也正是德沃金理论开始的地方——他需要超越实证主义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
德沃金认为,在规则可能处于“开放结构”的疑难案件中,将当事人的命运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是不公正的。当事人仍然具有确定的法律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被任意处置[2]151。德沃金指出,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对于法律实践的描述是错误的,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实践[3]33-35。法律的存在绝不是一个事实问题,恰恰相反,法律就是从争议开始的[3]123。既然是争议,那么正确答案则是我们必须寻求的。
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律规则中出现了模糊语言,那么将规则运用到案件之中将不会有正确答案,这就意味着某一个特定的表述“非真非假”。德沃金力图捍卫“正确答案”理论,并在《原则问题》第五章作了“不确定的模糊语言并不导致正确答案缺失”的解释工作。德沃金力图捍卫“司法的二值性”,并认为“模糊性的法律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2]130。
(二)对手V与对手R
1.德沃金的对手V
在《原则问题》第五章的开篇,德沃金首先预设了对手V。这里的V在某种程度上意指哈特。
V可能这样进行判断:如果α是一个模糊表达,那么“X是α”则可能为真、为假或非真非假。V认为最后一个判断即“X是α”非真非假使法律呈现出不确定性。这里的含义是如果α本身作为一个模糊表达,那么存在“X是α”是不用怀疑的,存在“X不是α”也是不用怀疑的。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案件,有一部分合同显失公平是毫无疑虑的,有一部分合同并未构成显失公平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的α则是“显失公平”,某一特定的合同则是X。哈特认为有一部分的X是无法判定的,这是属于α表达的“开放结构”,需要进行“缝中立法”。
哈特认为,开放结构的产生是由于“语言固有的提供指引的限度是客观存在的”[7]123,而在边界上的不确定是“有关事实问题的任何传递形式中使用一般分类词语都需付出的代价”[7]124。哈特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很“蛮横”的论证:“我们是人而非神……这是人类立法无法摆脱的困境。”[7]125这主要源于“我们对事实的相对无知或是我们对目的的相对模糊”[7]125。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只能“通过在竞争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来解决问题”[7]130。
德沃金认为,这种情况下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并不产生,法官在这里也不能拥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德沃金提出,可以运用“法律原则”来对“X是α”进行判定,“法律原则”可以要求“X是α”这样的表达为真或者为假[2]130,而不必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当“X是α”出现哈特所说的“非真非假”,依据法律原则完全可以判定为“真”或“假”,因为建构解释的要求本身就排除了V所宣称的不确定性。
德沃金所论证的“法律原则”可以抵抗这样的不确定性,而运用法律原则所作的“建构性”解释实质是法律本身的展现过程。由此,对于特定的“X是α”而言,是不可能出现或然状况的。
2.德沃金的对手R
德沃金论证的第二个对手是R,这里R或许是在意指拉兹。拉兹认为,并不存在清晰案件和不清晰案件的截然区分,在模糊的主要形式中,“不确定性”是“持续的”[9]73。
R这样进行判断:在清晰案件和疑难案件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的界线,所以V所运用的论证中,可能出现的“‘X是α’为真”可能非真非假。如果用P来代表“X是α”,我们可以不停地把这个不确定性延续下去。我们将继续探讨T(P)、TT(P)……按照拉兹运用的真值谓词理论,这可以无限制地推论下去[9]73。
德沃金的关键一步在于拒斥这种宣称。他认为,如果“X是 α”非真非假,那么“‘X是 α’为真”则为假。德沃金的建构规则依然在起作用,并不存在“‘X是α’为真”非真非假的案件。
这个论证给我们的印象是V使得R的判断变得艰难。德沃金说:“R似乎是V自身演绎其论证的牺牲品。”[2]130
德沃金继续论证:“读者可能感受到R上了这个论证的当。R所要求注重的问题是可能产生的。比如,某人说如果‘契约是渎神的’为非真的一个判断,他将认为契约是非渎神的,但他仍然有迷惑,他将不确定契约渎神是否为真。我同意这样的一个论证,但是这是V的问题,绝非R的问题。”[2]405
德沃金指出,R 的问题是由 V 预设的[2]130。在这个场景中,R所要求的“‘X是α’为真”或者“‘X是α’为假”,都是不确定的。V的三值论题(“X是α”为真、为假、或非真非假)预示着“‘X是α’为真”是一个二值论题,即“‘X是α’为真”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模糊的三值特征挫败了V也迷惑了R。这其中的结论就是R的问题是V整体进路的困境[2]405。如此人们就不能像 V一样断言,对于在临界案件中模糊语言的运用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因此,德沃金反对模糊论题仅仅依赖于V的这种形式性论证。
V可能作出这样的区分:“P非真”和“‘P为真’非真”。“P非真”说明断言的标准(P)没有遇到,这并非说明断言(~P)的标准遇到了。德沃金认为,对于断言(P)的标准而言,“‘P为真’非真”并没有说明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这个问题的可能回答是:第一个判断是断言的标准(P)没有遇到,V认为“P为真”仅在(P)处于清晰状况中,当然后续的R就会想到“‘P为真’为真”仅在(P)为真的清晰状况中。R只需简单的主张:将判断“真”附加在这个断言之上。V的论点支持了这个主张,事实上,V依赖于这个主张。
德沃金认为这样反复回答一个问题是荒谬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德沃金将断言(P)的标准视同为断言“(P)为真”的标准。通过反对R,德沃金展开了判断:对于一个判断加上一个“真”的判断并非给这个判断加上什么[2]405。德沃金的这个判断或许对V是有效的,但对R则不一定有效。如果我们允许V区分(P)的判断和“(P)为真”的判断,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真值谓词。我们已经区分了(P)和“(P)为真”,那么就是已经在(P)和“(P)为真”之间插入了一个逻辑空间,而且没有办法使得R停止在两个命题之间不断地插入这样的逻辑空间。
德沃金允许V对P与T(P)作出区分,但不允许R区分TT(P)与T(P)。他同意对一个命题加上“……为真”的判断,但仅限一次,于是“……为真为真为真”与“……为真”同义。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来理解这段论述。如果一个命题“苹果是红的”(可以认为是前述的断言P),那么V可能有三种判断:这个命题是假的,这个命题是真的,这个命题非真非假。德沃金会认为这是个关乎实践的断定命题的事情,“红”的标准取决于我们的实践而非去定义“红”,通过我们在实践中关于“红”的规则和“红”的原则,我们可以得出并不存在第三种情况。对于R而言,R可以对“‘苹果是红的’为真”(当然判断项是可以替换的)作出更进一步的真值判断,这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德沃金会认为,不停地加入逻辑谓词是荒谬的,换言之,“‘苹果是红的’为真”是否存在“为真、为假或非真非假”,在逻辑上有意义,但对于实践而言没有意义,因为实践考虑的是命题“苹果是红的”本身,而不是考虑某个命题。
(三)法律实证主义对V的重构
恩迪克特对《原则问题》中的对手V进行了反思,并认为如果模糊主张不犯V这样的错误,那么德沃金的理论似乎就要陷入困境,而且将很难去反对模糊性论题。恩迪克特认为,V的错误源于“开放结构”的案件,“X是α”是既非真也非假。如果我们提取V的论题的积极方面的要点,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阐释模糊性论题。
V的主张是否定性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重构它。每一个方式都将给予V的否定性一个新的空间。第一个是使V的否定性外在于“‘X是α’为真”这样一个论题,第二个是使V的否定性内在于这个判断。
1.外在否定性重构
外在否定可以描述为:在叙说“‘X是α’非真非假”,V倾向于认为“X是α”为真,也倾向于认为“X是α”为假。
外在否定使用日常的一般语言,从而使得V的观点有意义。这并非通过其文字含义,或通过其字面解释来论证,这里意味着V在说“我不愿意说‘X是α’是真,也不愿意说它为假”。他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在开放结构中,一个有能力的语言的使用者将不知道如何判断“X是α”。在这种情况之下,V的判断其实是对于“X是否是α”的一个怀疑的简单表达。
如果我们这样接受V的观点,德沃金的建构规则或许将存在困境。当一个有言说能力的言说者在怀疑“‘X是α’是真”的时候,德沃金直接就把“X是α”当作假。建构规则在这种情形之中将直接决定案件的结果。这样一个案件对于一个熟悉语言的人来说是充满疑虑的。例如在合同显失公平的论题上,这是对于一个合同有效性的模糊检验,就是“某个合同是一个显失公平的合同”的一个模糊检验。对于这样一个规则的运用,是肯定存在临界状况的,并且,如果一个胜任的言说者毫无疑虑地说明某个合同显失公平,也不会使得问题变得简单,不仅因为不同的胜任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还包括这个人将不确定他的怀疑从何处产生。
如果我们沿用上文给出的“苹果是红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么V的外在否定可以叙述为我们无法认识到苹果是否是红的。这类似于将逻辑问题交给认识,是我们的认识让我们无法判断,而并不是命题没有真假。如果我们把语词的使用当成语词的意义的来源,那么这种“怀疑”将变得可疑,我们在使用“红”的时候,我们自然是对“红”没有怀疑的,当然可以用另外一个符号来代替“红”,但这分属不同的语言体系。
外在否定不是一个逻辑运算,而是一种日常用语的描绘,但是这个日常语言的描绘不仅没有消除德沃金的理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攻击了哈特。按照哈特的理解,我们遵守规则是因为我们处于共同接受的承认规则所确定的规则之中[7]110,这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意味着大家对于规则已经形成了“一致认识”,如果大家对如何游戏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其实就没有在同一体系来探讨问题。所以,这种日常语言的描绘是不同共同体的描绘,而非同一共同体对于规则的描绘。德沃金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就同一法律问题当然可以出现不同的答案,但这不是我的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德沃金认为这样去回答一个问题显得毫无意义。
2.内在否定性重构
内在否定可以描述为:在叙说“‘X是α’非真非假”,V认为“X是α”非真同时“X是α”非假[10]。内在否定是一种类似经典逻辑的否定。经典逻辑并没有给外在否定留有位置。这个论断仅有的否定就是├P是├~P,不存在式子~├P,论断的符号“├”属于元语言,否定的符号“~”属于对象语言。
德沃金在反对V的论点中,运用了逻辑否定形式来定义V的无正确答案命题。德沃金认为,~P是对P的逻辑否定。如果P为假,那么~P就为真;如果~P为假,那么P就为真。沃德金认为,V的观点“在一部分案件中P与~P都不为真”,也就意味着在这些案件中,两种观点都没有。
但是如果V的主张运用于内在否定,V将有比德沃金的建构规则更为麻烦的问题。V主张在某些案件中P非真,~P也非真,如果我们接受逻辑学中的去引号规则,那么V的主张将陷入矛盾,即X是和不是α[11]96。V应当做的是要么拒绝这个推理中的某些原则,要么接受这个自相矛盾的结论[11]190,或许这样的一个结论在逻辑学家看来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推理,使得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说:“模糊性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相矛盾,所以描绘模糊性连贯的唯一正确方式是使我们自相矛盾。”[11]189
如果用前述的例子来表达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是“苹果是红的”为真和为假同时存在,这是在逻辑上的悖论。
恩迪克特论证道:对德沃金的理论而言,因为V的主张不能被达到并且自相矛盾,那么从内在否定的观点来看,德沃金的建构规则就不能运行。德沃金的论点中假定V的论断可以按照建构规则来处理,从而以“真”或“假”来对待,但是他如何面对这个在逻辑上混乱的V?德沃金的建构规则可以面对一个矛盾来运行吗?
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太阳西下,V可能说黄昏与夜交换的那一刻是不确定的,那个时候既非黄昏也非黑夜。
德沃金的可能回答方式是:这第三种情况视为假,我们不需要一个三元的判断来宣称不存在黄昏的最后一刻。如果参与到规则中的人处于某种自相矛盾之中,他感到的是无所适从,判断也感到艰难,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非一个法律实践问题。认识论问题需要回答“陷于矛盾的认识如何可能”,而德沃金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实践”。德沃金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认识论问题,因为他构建了一个“帝国”而且有一个非凡的“赫拉克勒斯”。
二、司法的二值与正确答案
德沃金对于V与R的反对其实是在捍卫他的一个基本观念:司法只有二值而无三值,某个复杂而全面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对同一案件有两套不同的解答[2]151。
在重新审视德沃金的建构规则或法律原则时,我们需要追问这样一个结果:是支持还是反对德沃金的正确答案论题。
其一,如果德沃金的建构规则消除了模糊性,德沃金的论点可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法律的模糊性来源并不是由于立法时采用了模糊语言。德沃金在论证语言的模糊性并不导致法律的模糊性这个问题时,要求有一个规则去消除模糊。如此,建构规则中的模糊性是处于这个论题之外的,建构规则本身并不能消解自身的模糊性。德沃金断言法律规则的模糊和建构规则的模糊“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如同我们依赖于对渎神一词的理解,我们怀疑没有正确答案的东西根本没有说出来”[2]131。
其二,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是他法律理论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建构性解释本身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法律实践,法官都有责任继续进行已经置身于此的实践[3]87。这并不需要对法律模糊性进行讨论,相反,可以看出,德沃金关于模糊的讨论是把它作为可以牺牲的话题而进行的,而且他理论的中心要素是把语言的模糊性排除在外。
德沃金在其所有的作品中都强调法律的要求不能通过对语言的追问来确定。语言如何在其运用中展现出意义也不是德沃金论述的主旨。因此,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讨论的法律原则并不是简单地给法律方法增添一种类型。德沃金认为,在法律的本质中,人们并不能通过对法律语言的运用来确定权利和义务。他认为,规则本身就是代表一种“可适用”的特征,规则规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形,保证了种种情况,叙述了如何适用[1]24。另一方面,原则“阐释了原因”,“指明”了一个方向,也应当被考虑,陈述原则并非说它们如何使用[1]28。更为重要的是,德沃金认为,某人说一个规则具有约束力其实就暗示着原则将支持它的使用[1]38。因此,没有人可能纯粹通过立法者的意图陈述法律之要求,更不可能重申立法的要求。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所提出的解释理论,主张法律表达混入了“前解释”的阶段,即与政治共同体的法律史相联系。任何人试图陈述法律的要求仅仅只能从这个阶段开始,而且必须继续为政治美德成为法律提出依据,继而去考虑用何种标准来描述法律才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扩大。换言之,陈述法律之要求并非陈述构成法律之语言的运用。德沃金这样阐释道:模糊语言可以呈现出在运用时的真实的困难,概念允许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并不需要各种含义都使用,除非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需要人们参予到解释的实践中来[3]128。因此,德沃金警告某种可能的混乱,“在立法中运用一个模糊语汇与在不同情况下阐释一个概念是不同的”[1]136。在《法律帝国》中,德沃金坚持把语言的模糊视作“语义学之刺”[3]17,而且允许概念有多种含义。
德沃金更关心法律的实践。他认为,判决本身是二值的,如同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总是在讨论当事人的罪与非罪,应当承担责任或是不存在责任,法院也要在二者中作出选择。这二者的确定性是必然的,换言之,对手V与对手R的问题都可以用二值模式来解释的。
德沃金的论证创造了一个假设的界限去阻挡模糊性。这个假定是“帝国”,或者可以说是赫拉克勒斯,也可以认为是建构规则抑或是法律原则或政策。对于这个假定,如果要怀疑那就是怀疑“法律帝国”本身。德沃金需要的不是去挑战这个怀疑,而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法律中并以此为生活之据。”[3]1怀疑本身在神话的内部是无法产生的,除非我们跳出神话,去一个法律并非居于高位的地方,但是现代的人如何能脱离法律来生活?德沃金的这个假定促使我们只能接受,这是一种对“生活形式”的接受。
结 语
关于德沃金的对手V与R,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分析法学的理论。在分析法学发展到20世纪之时,法学家们纷纷举起维特根斯坦的大旗,这不仅因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开创者。当20世纪的分析法学试图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与观念的时候,他们忽略了维特根斯坦的“实践哲学转向”,从而使得20世纪的分析法学陷入停滞。
我们可以用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来理解:没有明确划界的表达是有用的[12]61。当维特根斯坦探讨不确定性的时候,他厘清的是我们在使用中的误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应当停止追问无意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回应到法学上则会产生问题,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低限度的显失公平?”“什么是我们公司的最大权限?”“什么是最低限度的犯罪构成?”这些问题都是不确定性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维特根斯坦说:“理想的精确性是不可能规定的。”[12]88判断这些问题的“真或者假”,仅在于“生活形式上的一致”[12]43。
“法律”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仅仅包含了形式化的规则本身还是包含了对规则的超越呢?德沃金在完成了对实证主义的评判后给出了某种法哲学的洞见。这个问题似乎在于打破“我们”与“法律”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在先前的思维态度中,我们总是把法律当成对象,这可能是一种错误。法律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我们自身的实践本身。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所意指的法律仅仅是文字以及它的含义而已。德沃金或许更想说的是:我赞赏你的态度,但我确有不知的是,脱离了人类对文字的“使用实践”,你将如何获得它们的含义?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重述了生活形式。当然对于特定的生活形式而言,我们总要去追寻一致,这种一致也就是德沃金所认为的“唯一正确答案”。如果我们把法律当作实践,那么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德沃金的那句名言:“法律是一种实践、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它可能由于其缺陷而无效,乃至于完全无效,但这绝非是一种荒唐的玩笑。”[3]44
[1]DWORKIN R.Taking Rights Seriously[M].London:Duckworth,1977.
[2]DWORKIN R.A Matter of Principl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3]DWORKIN R.Law's Empir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DWORKIN R .Justice Sotomayor:The Unjust Hearings[J].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9 -09 -24.
[5]COLEMAN J.Truth and Objectivity in Law[J].Legal Theory,1995,(1):49 -50.
[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7 -80.
[7]HART H L A.The Concept of Law[M].BULLOCH P and RAZED J.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8]HART H L A.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7.
[9]RAZ J.The Authority of Law[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
[10]ENDICOTT T.Vagueness in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70 -72.
[11]WILLIAMSON T.Vagueness[M].London:Routledge,1994.
[12]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ANSCOMBE G E 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