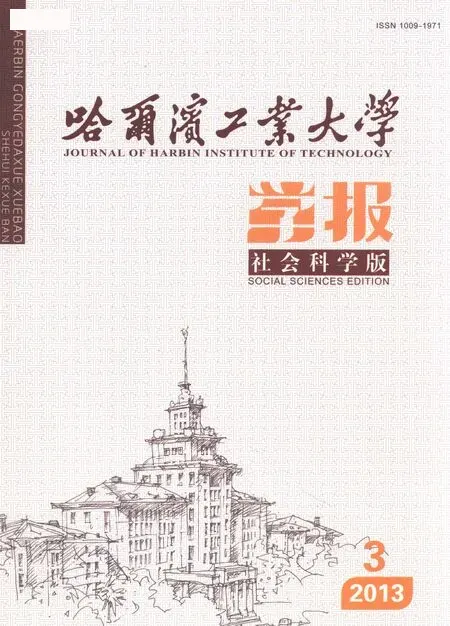国家构建与制度建设:转型国家的分析框架
曹海军,霍伟桦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国家构建与制度建设:转型国家的分析框架
曹海军,霍伟桦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随着国家学派的崛起和“国家中心论”的复兴,国家构建与制度建设逐渐成为研究国家转型的分析框架。与传统的理论视角不同,国家自主性理论重新将国家视为政治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和分析变量,强调国家可以依其意愿偏好与能力来制定政策或设定国家目标。由此,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主要是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相联系的,进而影响国家构建的成功与否。从财政视角出发,财政汲取能力是影响国家构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制度的强弱和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体现在财政汲取能力的水平上。最后,制度主义范式指出国家可以被视为制度结构或制度机器,因此不同要素的制度变革对国家形成和国家转型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国家构建;制度建设;转型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制度变革
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对国家和国家构建的理论有着全方位的论述和比较分析,政治学对国家理论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这两个学科的方法论知识,以扩大对国家问题的分析视野和增强国家理论的解释力。本文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以上理论资源建立起来的,首先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上述广阔的理论脉络基础之上,进而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前提。
一、国家与国家构建:定义与争论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在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从欧洲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到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再到第三世界的“脆弱国家”、“失败国家”,还有处于各类转型时期的国家,国家性的呈现方式不一而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论认为,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的全球化力量会消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性逻辑;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会加速国际一体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虽然国家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但其基础作用仍然重大,特别是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推翻了新自由主义的范式。而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地区冲突、弱国家和失败国家的例子(如阿富汗、伊拉克)比比皆是,这就对建立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国家产生了实际需求,国家构建的命题应运而生。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家构建过程更多地是以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反恐”合法性理由,通过占领(特别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来按照西方的国家制度模式进行移植的过程。福山(Fukuyama)将这一轮国家构建称为“构建一个国家”(building of a state),国家构建亦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建设,“国家建设就是建立新型的政府机构,并强化现有的政府机构”。具体参见Francis Fukuyama,F.State-Building:Governanceand World Order in the21st Century[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Francis Fukuyama(ed.).Nation-building: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Francis Fukuyama.Liberalism Versus State-Building[J].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8,Number 3,July 2007,pp.10-13.
有关“后共产主义”东欧和苏联国家的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主要集中于民主化、经济转型(即所谓的双重转型)和民族认同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则集中于国家构建即国家的形成和转型问题,这一问题源自因腐败等造成虚弱和功能失调的国家的出现。
有关国家构建问题的文献主要是对欧洲早期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的反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给国家概念下了两个经典的定义。韦伯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1]梯利认为“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控制人口的组织,因为(1)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在同一领土内运作的其他组织;(2)它具有自主性;(3)它是集权化的;(4)其组成部分形式上是相互协作的。”[2]显然,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国家的结构性和组织性。除了韦伯在定义中指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以外,他们都没有提到国家的功能。而两个定义的一个重要差别是韦伯着力强调合法性,即人民对权威的接受。
(一)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与社会关系
梯利的定义主要是将国家自主性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面向。这一面向引起了学界对国家自主性、国家嵌入性和国家俘获的广泛争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论复兴的重要标志,在古典政治学的研究中,国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占据着政治理论“皇冠”的位置。而二战以后,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滥觞,大大推动了实证科学和经验研究的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个体行为和集团行动的研究逐渐取代了国家而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焦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源自欧洲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在政治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的概念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推动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进一步成长。
除了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外,国家研究的衰落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学术界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构想和哲学观。西方社会居于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看待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立场上采取了“社会中心论”(society-centered)的研究路径。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是作为人类集体生活的必要的恶,其职能应该尽可能减少,仅仅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尽可能减少对社会的渗透以及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干预。基于这样一种国家定位,各种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纷纷从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国家及其结构功能。其中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观是这种社会中心论的典范。
直到20世纪80年代,彼特·埃文斯(Peter B.Evans)、迪特里希·鲁斯奇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西达·斯科切波(Theda Skocpol)的《找回国家》[3]7(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出版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一股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研究范式转换,大有“国家回归”(return to state)之势。一时间,以国家学派(statist)、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强或弱国家(strong or weak state)、国家自主(state autonomy)、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国家制度建设(state institution-building)为核心术语的“国家学派”理论浪潮席卷整个西方政治学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分别从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等不同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出发,讨论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以及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各类相关问题。国家中心论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将国家视为政治过程的行为主体和分析变量,从而一改社会中心论者将社会现象视为自变量、而将国家视为因应社会因素而变动的因变量的方法论趋势。与强调个人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微观视角不同,在国家中心论和国家学派理论的分析过程中,国家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其更注重历史与制度的研究路径和宏观层次的视野。
在国家学派理论中,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来自国家学派理论的国家观。根据斯科切波的观点,“国家被视为对其领土范围与人民具有控制权力,可以形成并推行其政策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反映社会团体、阶级或社会利益或需要的组织。”[3]7-8也就是说,国家自主性成为国家的重要内涵,国家若缺乏独立自主形成政策并执行政策目标的力量,就无法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根据这一概念,国家自主可以定义为,国家依其意愿偏好与能力来制定政策或设定国家目标,而非单纯地反映社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依据国家决策反映社会诸利益集团的程度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国家自主大体上可以分为绝对自主(absolute autonomy)、相对自主(relative autonomy)和嵌入自主(embedded autonomy)。
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一书中从类型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是如何通过转换社会偏好来实现自身自主的。他将国家相对于社会自主的模式分为三类,在第一类和第二类中,国家与社会的偏好趋异,国家利用策略和权威改变社会偏好,甚至将国家偏好强加于社会之上。在第三类中,国家与社会的偏好趋同,国家可以运用政策宣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具来强化政策偏好的强度,削弱潜在的反对力量[4]。最后,国家自主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换言之,国家自主的决策未必能够保障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共同实现。国家的决策可能存在失误,也会出现执行偏差,这些因素都会促使国家自主产生国家非理性行动的后果。而且,实际上,国家的行动无法确保结果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其结果必然是有利于部分社会阶层,而不利于另一部分社会团体。国家行动的合理性在于充分了解国家在何时、为何以及如何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决策,而并非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自主。
就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论,早期强大而后羸弱的国家正是由于深受腐败的积弊而出现了“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的现象。国家俘获的概念正是对应于(嵌入性)自主的概念而作为分析框架的。被俘获的国家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提供服务,不是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当然,国家俘获的问题并不是后共产主义国家所独有的,也不是后共产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唯一的国家性问题。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针对国家权力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而又有区分的两个概念,即“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s)和“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s)。专制性权力是随意且自主地作出决策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早期现代国家(包括传统封建时代的中国)的专制性权力都是强大的。基础性权力指的是国家官僚机构以及国家主持的规划(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对社会的实际渗透。曼发现国家权力的历史演变趋势是“基础性权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原来完全与社会隔离的“专制性权力”所具有的专制性越来越弱,逐渐演变为受社会问责约束进而与社会协同的嵌入性自主。
对于后苏联国家来说,基础性权力和连续的专制性权力相互交织。与许多战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相比较,后苏联国家向国家渗透的基础性权力较强,许多现代国家的基础性职能相对完备,诸如国防安全、公共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同时,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专制性权力接近于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制性权力有所减弱,而且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中央政令向下传导和执行的功能大大弱化。这种持续的专制但却碎片化的权力为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苏联时期的基础性权力也得到维系。
按照韦伯主义的视角,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机器,是国家构建的一项重要目标。要分析后苏联国家在国家构建特别是国家能力构建方面的差异性问题,首先要分析国家构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同时考察在现有制度架构下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国家的作用:规范意义上的争论
国家规模是在国家理论中最初引发争论的问题,其中包括描述分析和规范研究两个思路。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思潮的影响下,“国家瘦身”(downsizing the state)的讨论大行其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对19世纪以来、特别是战后国家极度扩张的一次理论反动,同时也是对东亚以外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失败的一种理论回应。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通过私有化、合同外包等手段实现国家瘦身,是解决发达国家经济滞胀、防范发展中国家出现“掠夺性政府”和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不过,国家瘦身的尝试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正面效果,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①“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总结,基本上是一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其中产权基础设施(比如运行正常的司法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熟的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强大的风险管理水平)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是经济学家们就误以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改革的政治意愿,再加上他们的好建议,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标的实现简直易如反掌。但是,“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有路径依赖,必须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要比理论假设慢得多、难得多。一旦理论假设错误,其推导出的结论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议就失去立足之本。此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应该是华盛顿共识过度市场化的一大失败例证。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国家》[5]1,25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以不同方式来改善发展成果的经验:一是提供一种为有效的经济活动设定正确刺激机制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二是提供如财产权、和平、法律与秩序以及规则等能够保护和促进长期投资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三是确保提供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以及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并保护自然环境。显然,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不是国家的规模问题,而是国家或政府的有效性问题。该报告关于国家或政府角色的结论揭示了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关键性因素,国家或政府的有效性起到绝对的作用。报告强调:“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经济的、社会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5]2。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规模大大超越了过去。作为工业国家类型的福利国家不断增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纳了以政府主导为主的发展战略,世界各国政府的规模和功能职责全面扩张。“正是这种政府影响的极大增长,使得问题的重点……从政府的规模及其干预措施的范围转向它们在满足人民需求的有效性上来了”[5]39。
新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理论主张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行为规则,反对国家实施再分配的职能。满足人民需求的再分配职能必然要求国家不仅在规模上增长,而且具有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自此,国家能力的命题引入到国家构建这一总命题的范畴之中。
(三)国家与治理的有效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能力的讨论一般都与“善治”(good governance)联系起来。当代有关善治的学术探讨主要关注国家形成和国家转型的问题。在了解善治之前,首先讨论一下治理的概念。治理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共同使用的核心概念,其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无所不包。就国家能力而言,治理的作用恰恰在于它在结构和行为者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新定位。换言之,治理的概念强调应该超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将重心放在了政治游戏规则的塑造以及在塑造和变革规则的连续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行为者上”[6]。不过,国内外学界自始至终都未能对“治理”的确切定义达成共识。
皮埃尔(Pierre)和彼得斯(Peters)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换言之,治理就是政府驾驭社会的能力。”[7]世界银行认为,“治理乃是在一定资源约束下,公共组织应一国公民或其他代表的要求,按照一种有效的、透明的、公正的、负责的方式,提供公共和其他物品的制度能力。”[8]上述有关治理的定义大体上等同于本文对国家能力的界定,主要是指塑造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在定性的意义上,这两个定义是有所差别的,它们强调超越公与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界,因此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影响公共政策塑造及其后果的个人和集团网络。
就苏联国家构建问题而言,许多问题涉及治理的有效性,比如严重的腐败问题、漠视法治等。不过,治理这一术语的运用有时会将症状和肇因混为一谈。此外,许多治理方面的研究要么是描述性的,即对跨个案和跨时段的治理有效性的测量,要么是规范性的,探讨诸如自由主义市场体制这类特定治理模式的规定性。
这两种研究路径都需要补充说明为何有些政权比另外一些政权治理得好,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治理的发展演变。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的关系是本研究的核心目标,这些国家在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方面存在着区别。为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探讨后苏联国家接近或背离研究目标的因果关系。
(四)国家构建问题的兴起
本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国家构建的差别具有时空性和权变性。类比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国家构建也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趋势和差别。传统的国家学派包括韦伯和梯利等人主要关心的是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state-formation)或(state-making)国家缔造问题。霍尔(Hall)则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发现,后发国家的国家构建模式存在差别与先在的模式有关,而且关键的“大转型”只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兴起只发生一次,其他国家都是模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成可能与欧洲核心地带的经历有所不同。”[9]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亚非拉国家为摆脱殖民地地位、争取独立的斗争历程构成从战后到90年代国家构建浪潮的第一波。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家构建的第二波浪潮由两个次级波构成,一是苏东解体后的国家构建,二是以阿富汗、伊拉克等为代表的“失败国家”或“后冲突国家”的国家构建。问题在于,战后的“两波”国家构建都是以西方的国家和制度模式为模板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包括资本、政治样式、民主模式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输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国家模式的供给并不能构成国家构建后成功运转的充分条件,国家能力也无法自动得到完善和提升。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进行的纸上谈兵式的制度建设甚至成为国家构建的障碍和阻力。国家构建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国内的主客观条件,这也构成了诸多案例差异化的主要根源。
作为“第二波”国家构建的次级波,后苏联国家的国家构建与其他“第二波”国家有共同之处:共同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发展潮流。一是伴随广泛传播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强化了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优越性,二是实践上由市场化向国家能力构建的转移。当然,苏联时期人民对国家作用的体验促成了后苏联国家的政治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后苏联国家的国家构建过程是以和平而非冲突的方式启动的。
二、国家构建的财政视角
财政问题是国家形成和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按照查尔斯·梯利的观点,国家构建就是国家渗透、汲取和协调能力的建构。米格达尔也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深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等四大能力[10]。新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构建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学习预算与决算的编制、控制公共资金的使用。财政问题之所以构成国家构建的核心,是因为岁入汲取和财政支出问题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与运行过程。此外,财政问题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二重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和问题的产生根源。经济学家熊彼特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财政问题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塑造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和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分析思路和研究路径。
列维认为,统治者始终要实现岁入最大化,不过是在政治和经济约束下运行的。据此,列维指出,历史上,当统治者提高(自愿的)税收而得到服从时,规则制定(议会)的共识形式越多,越容易导致更高的税收水平[11]。奥尔森认为,与追求长期岁入最大化的独裁者不同,民主政治下的汲取要少得多,因为前者的政治领导人多数情况下感兴趣的是提供有限的公共物品,同时将钱放入自己的腰包。
沿着这一财政社会学的传统,公共财政专家和经济史学家针对税收和财政支出制度的发展提出三个解释框架:经济解释、制度解释和政治解释。经济解释认为,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限制和塑造了汲取的机会。由此,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中,税收汲取相对于GDP的份额一般明显小于工业社会。按照财政学家威尔达夫斯基的观点[12],处于经济波动之中的贫困国家会因资源和储备匮乏等问题而遇到预决算方面的困境。此外,对财政制度与汲取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从制度的效能和制度变革的动力两个方面展开。最后,政治因素的影响无疑取决于各国或地区的特定背景。斯坦摩(Steinmo)研究了社会联盟和税收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的国家里,税收特权和预算补贴是统治者收买关键性小圈子政治支持的手段之一[13]。
在有关转型国家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俄罗斯和东、中欧国家,而对后苏联国家的关注较少。财政的视角遵循了财政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将财政制度视为国家的核心。这一研究路径的优势在于可以对因变量进行详细的经验分析,而且对诸如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重要性这类普遍认可的命题加以检验和探索。
后苏联国家的案例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如何运转、建立、变革、崩溃和巩固的研究。同时,这一研究对于从波黑到阿富汗、伊拉克这类“失败国家”和“脆弱国家”的国家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后苏联国家的案例为探讨国家能力与民主的、权威主义的和各种混合型政体的不同组合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遇。虽然国家的形成(stateformation)极为罕见,但制度建设和制度变革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根据制度主义的术语设定后苏联国家形成和转型的研究框架,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就会涉及非渐进性的制度变革、遗产的作用,以及制度和制度体系是如何建立、维持和削弱的。尤其重要的是,后苏联国家的案例提醒人们注意:国家构建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即使是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也会出现“脱轨”现象。
以方法论的观点看,后苏联国家的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场所,15个国家都是从一个形式上具有同质性的制度内同时启动国家构建历程的,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通过其可以检验诸多假设,并在诸如共同的遗产、相同的国际环境前提下,解释发展水平、精英结构以及精英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因此,本文并不旨在提供一个普适性的国家构建的构想,而是运用新的材料对制度变革和创建的比较政治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而言之,对该地区转型过程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究国家能力弱化的原因,并找到克服这一难题的钥匙。
在转型国家的学术探讨方面,强弱问题是国家讨论中最常见的特征。有人认为,转型国家特别是后苏联国家的案例显示这些国家过于软弱无力。而有人则认为,后苏联国家都是相对强大却治理糟糕的国家,而且有些糟糕的政府举措实际上支撑了国家的权力。按照米格达尔的观点,这只是说明后苏联国家权力分布不均衡,有些领域强,有些领域弱。如果从财政发展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后苏联国家的规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贯穿整个后苏联时期。
三、国家构建与制度变革
除了上述静态的视角之外,制度主义范式的出现转向了对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和国家转型(state transformation)的动态分析。
按照制度主义的观点,国家可以被视为制度结构或制度机器。起初,制度主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话语论证制度的重要性和制度的产出效果。关于制度起源和变革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主要来自诺斯和罗伯特·贝茨等人的研究成果[14][15][16]。制度主义学家西伦(Thelen)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制度变革概念化的基础。同时,谢德勒(Schedler)指出,有关制度起源的研究已经逐渐淡出当前制度主义的主流文献。
制度主义的研究基本上是将国家制度相对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把这一方法和视角引入到后苏联国家研究会在制度特征和发展水平上存在适用性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国家构建与制度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国家构建历程不同,后苏联国家的国家构建始于先前结构的零碎改革,既涉及制度破坏,也涉及制度变革。因此,在这一脉络下可以区分制度破坏(去制度化)、制度转型(改变现有制度)和制度创建(建立新的制度)三种制度变革的不同要素。此外,许多前苏联时期曾经衰朽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又重新焕发活力。制度衰朽涉及两方面因素:苏联的解体一方面破坏了联盟层面的制度架构,对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都构成破坏;另一方面,苏联解体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从根本上摧毁了可以提供整合、协作、控制的关键制度,最终大大降低了国家的有效性。苏联共产党的解体对整个制度体系构成毁灭性的打击。苏联后期,由于政府的诚信和执政合法性持续下降,党和国家的治理机构遭到严重削弱,国家原有的职能甚至转给了经济和社会中介组织。这对独立初期的国家构建产生不良影响,独立之时,制度化程度或说治理水平严重衰朽。后苏联国家构建过程涉及制度衰朽、重建和恢复多种制度变革形式。
按照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和制度体系可以制造一种激励结构,并刺激特定体系的投资。此外,制度变革往往很艰难而且具有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根据诺斯的观点,“稳定是通过系列复杂的制约来实现的,它们包括在一个等级下的各种正规规则(在这里,每一层次的变革比原先变革的难度更高)”[17]。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整个制度架构的转型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可能面临着运转不良的风险。当一个旧秩序遭到彻底毁灭而解体时,新兴的社会是否能够代之以更好的运转机制,尚需拭目以待。可怕的是,制度变革的成本问题起初并没有得到重视。波波夫(Popov)指出,“戈尔巴乔夫1985年到1991年改革的失败并不在于改革是渐进式的,而是由于国家制度能力的弱化导致了政府无力控制事态的发展。类似地,叶利钦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改革付出如此代价并不是由于休克疗法,而是由于用来执行法律和秩序以及实施可控转型的制度崩溃了”[18]。
同样,联合国开发署1997年关于转型国家的报告认为[5]1,这并不是要否定宏观经济与财政稳定、公共财政调整与改革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这类改革因政府丧失了掌控转型和市场建设的能力而付出沉重代价。在缺乏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效支持下,急速的财政金融政策改革可能会降低政府的有效性,因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需要在市场建设和市场监管方面发挥新型而复杂的职能。
由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所限,本文并不试图评估各种制度变革路径的成本,只是提醒关注制度变革可能产生的成本和风险,比如在制度变革路径的选择与转型衰退期GDP损失规模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些选择恢复到原有制度下的国家最初仍然比其他国家保持着较高的GDP水平。由于新制度的建立需要调适等原因,至少从短期来看回到原有的制度要比建立新的制度成本低。此外,由于新制度建立涉及在全新的未知模式上达成共识,这条道路势必比旧制度的复辟更具有挑战性。观察经验可知,有时次优的制度可能后来会得到改进,有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地踏步。
制度变革的成本和收益在整个社会中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般来说,制度衰朽势必会因再分配机制的减少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由于私有化等因素,转型初期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分配促进了财富和收入的落差,对逐渐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体系的类型产生深远影响。
制度变革包括制度衰朽的过程和重建的过程。制度变革可以分为有意为之的变革和无意为之的变革、渐进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等不同类型。激进式的变革又被称为“大跃进式”(big leap)①这里所指的“大跃进”不同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脱离现实的“大跃进”运动。变革,是指一种重大的非渐进性的制度改进。在此意义上,“大跃进”是与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相对的反向运动。
“大跃进式”的制度构建指的是大规模改革,比如行政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等。在此意义上,“大跃进式”的变革必然是有意为之的,虽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变革必然是建立在广泛社会联盟的共识基础之上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大跃进式”的制度变革涉及重大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大跃进式”的变革不是线性的或者可以预期的。此外,“大跃进式”的变革要求强有力的决策能力。而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相对难度较小,常常依赖于学习过程,并且不需要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联盟和一致共识的基础之上,很多情况下也并非特定行为者有意为之。此外,由于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绝少涉及分配问题,前期成本会比较小。
在转型的早期阶段,如解除价格控制、取缔外贸审批体制等制度分拆摆在突出的位置上。“休克疗法”的倡议者们建议在转型初期尽可能地实施“大爆炸式”的制度变革,以便迅速拆除旧制度。这种建议的关键设想是出于改变经济主体立足新基础作出迅速反应进而重建经济的动机。
在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一设计获得成功。其成功的前提是旧制度解体、伴随着国家驾驭制度变革以及针对弱势群体实施再分配政策等基本能力的提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苏联,“大爆炸式的”制度变革使国家陷入长期而深层次的制度衰朽,使国家消化制度变革和创建新制度结构的能力弱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运作都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两种规则形式。在常态的发展情况下,非正式规则一般都是支撑正式规则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当二者发生分歧甚至是冲突之时,制度能力就处于衰朽和腐化之中,从而导致国家的功能失调。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发生背离或出现偏差最终会导致国家能力丧失,同时为了维系权力的分配也会出现公共行政权力的滥用。
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非正式制度对于任何正式规则体系的正常运转都是至关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推动正式制度的运转。“非正式约束的主要作用是修订、补充或扩展正式规则。因此,正式规则或其实施的变迁将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19]在苏联时期,非正式规则支撑了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而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黑市经济流行),抑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背离,从而滋生潜规则的盛行。这预示着对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和正式规则的失效。
恢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一致性,就需要恢复国家的自主性或独立性,确立市场的自主性,同时建立起民主的治理体系。对于国家能力弱的国家来说,情况可能未必如此,政府内部产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防守”逻辑会对正式制度体系滥用。这一状况往往会维系甚至加剧这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背离趋势。
[1][德]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5-56.
[2]TILLY C(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Western Europ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70.
[3]EVANS P,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eds.).Bring the State Back i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7-8.
[4]NORDLINGER E A.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56.
[5]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6]FEENY D.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u[G]//OSTROM V,et al.(eds.).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ssues,Alternatives and Choices.San Fransisco:ICS Press,1988:159-209.
[7]PIERRE J,PETERS B G.Governance,Politics and the State[M].London:St.Martin’s Press,2000:1.
[8]World Bank.Can Africa Claim the 21st Century?[M].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0:48.
[9]HALL J(ed.).The State:Critical Concepts,vols.I and II[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II:217.
[10][美]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
[11]LEVIM.Of Rule and Revenu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10-41.
[12]WILDAVSKY and CAIDEN.Prologue to Planning and Budgeting in Poor Countrie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1:199-213.
[13]STEINMO S.Taxation and Democracy:Swedish,British,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he Modern Stat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35-36.
[14]WALDNER D.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5.
[15]BATES R H.Macro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G]//ALT JE and SHEPSLE A(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48.
[16]KNIGHT Jand NORTH D.Explaining the Complexit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G]//WEIMER D L(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349-354.
[17]NORTH 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83.
[18]POPOV V.Stro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peed of Reforms[G]//CUDDY M and GEKKER R(ed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Aldershot:Ashgate,2002:65.
[19][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0.
State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CAO Hai-jun,HUOWei-hu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With the rise of the State School and the revival of the"State-centrism",the state-building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has been gradually becom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tate transformation.Unlik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e theory of state autonomy regards states as behavior agents and variables of analysi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emphasizing that the states can formulate policy and set their goals depending on their preferences and abilities.Thus,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tates play different roles,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te governance,thereby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state-building.From the fiscal perspective,the financial extractive capacity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to affect the state-building.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generally reflected i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extractive capacity.Finally,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points out that states can be regarded a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r system ofmachines.Therefore,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 with different elementswill ha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n states formation and states transition.
state-building;institution building;transition countries;financial extractive capacity;institutional change
D03
A
1009-1971(2013)03-0019-08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3-03-05
曹海军(1975—),男,吉林长春人,副教授,从事政治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研究;霍伟桦(1989—),男,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