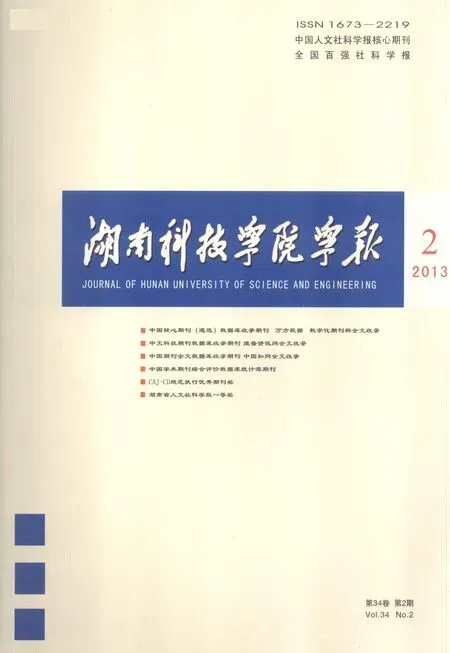论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场对文学场的介入:以“作协奖”为例
范国英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艺自身具有的商品属性在整个社会场域中获得了普遍认同,文艺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面向。因而那些体现市场逻辑的文学活动在社会场域中已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并在文学场域中拥有一定的资本和权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对文艺商品属性的发现,并没有也不可能遮蔽文艺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200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消息,次日又刊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认真学习这一文件的通知,中宣部在通知中说,“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把两者统一到文化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中”[1]。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文艺既具有商品的属性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当经济资本在一定层面上成为影响和制约文学场逻辑的强势资本时,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引导的文学评奖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
应该说,体现权力场对文学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的奖项,主要包括政府奖和中国作协框架下的文学评奖(简称“作协奖”)。政府奖主要是指政府“三大奖”,也既是由新闻出版署主持的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图书奖、以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在这三大奖下又包括了众多的子项。作协奖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中国作协的四大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二是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作协(文联)举办的各种文学评奖。如四川省作协举办的“四川文学奖”;海南省作协举办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奖”;等等。这类奖项主要用于奖励本省或本市的作家和在这一省市刊物上发表的优秀作品。目前较有影响的奖项主要有:由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主办的“老舍文学奖”,此奖项成立于1999年,并于2000年6月颁奖;以及山西省作协于2004年重新恢复的中断了20年的“赵树理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设立于1985年,后来主要因为资金的缘故,评奖很快就中断了);等等。三是由中国作协下属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各种奖项,如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等。在这里需要对中华文学基金会做一点说明,中华文学基金会是直属于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成立于1986年,国家财政部曾给予一次性拨款二百万元人民币的支助,这一机构还接受个人、企业等单位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的帮助。
由于中国作协在社会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可以说,中国作协本身就是权力场对文学场发生作用的一个中介。因而,中国作协框架下的文学评奖必然会在一定的层面上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性和导向性。这一点通过作协奖与政府奖之间的关系就能清楚地见出。实际上,作协奖与政府奖的获得者之间是存在相当的重叠的。毋庸置疑,评奖的运作机制必然会受到此类评奖在文学场中所处位置的制约和限制,或者说,此类评奖在文学场中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其运作机制上的基本特点。下面我们就主要以鲁迅文学奖为例,对作协奖的运作机制做一简单的说明。
鲁迅文学奖设立于1997年(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该奖项设置了除长篇外的针对各种体裁的 7个单项奖。包括:由《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小说选刊》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由《中国作家》主办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由《诗刊》承办的全国优秀诗歌奖、由《文艺报》主办的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和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2]。此奖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中出现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的一种恢复。鲁迅文学奖的评奖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三步:首先是经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后,由中国作协向各团体会员单位征集作品,报送各奖项承办单位备选。然而由初选小组推荐供评委会审读的备选篇目。并且,经三名以上评委联名提议,就可在审读小组推荐的篇目外,增加备选篇目。最后由评选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获奖作品[3]。而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程序也大致如此。可以确定的是,这类奖项的评选委员必然被那些代表纯粹美学原则的学院派批评家指称为“前文学工作者”[4]。布迪厄的“惯习”打破了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间的对立关系,“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5]。也就是说,这些老一代的在传统现实主义氛围中熏陶成长的所谓“前文学工作者”,其心智结构就与体现国家意识形态需要的文学规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与此相应,作协奖就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学评价标准和评价尺度,也就是寻求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并且,这类奖项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阐释也是基本一致的。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骏马奖”的评奖条例指出,在要求作品符合基本的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同时,强调“对于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6]。正是在此基础上,邵燕君指出,1997年设立的鲁迅文学奖与设立于1978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学观念上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7]。
这样一来,这类评奖在文学场中占据的位置及具有的作用,一方面就受到其所置身的文学场的结构的制约,同时,更受到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所占比例以及政治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转换率的规约。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逐步完成和完善,文学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部类的作用被弱化。与此相应,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政治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化率必然逐渐降低。这一点可以从政治资本在作家身份认同中具有的不同作用清楚地看出,如果我们将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刘心武的获奖感言,与2000年对他的采访做一番对比的话,就能清楚地见出这之间的差异:因《班主任》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刘心武,在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讲了话,“我们要把党和人民给予的奖励,当作前进的动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积极地投身到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代激流中去。我们要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社会生活,更刻苦努力地提高艺术修养和协作技巧,争取写出更能传达时代脉搏、表达人民愿望的新作品来,更好地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8];而因为《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刘心武,在面对当今记者的采访时说:“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大关心......至于上次获奖,那是某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的,至于怎么评的,我不知道。我一个电话没打过,一个人也没问过”[9]。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在对建国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反思的基础上,将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就成为建立自主性文学场的重要诉求。这样一来,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具有的作用就被弱化,同时政治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换率也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经济资本从过去的弱势资本一跃而为在社会场和文学场中具有相当作用的强势资本。那么,这类与政治资本具有较为密切关系的奖项在社会场和文学场中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必然也被弱化,不过,弱化并非是消失。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就指出“权力场”作为“元场域”,拥有在整个社会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以及颁发某种文化资本的权利(布迪厄将社会场域中的各种资本类型大致上划分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因而,权力场对文学场的作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如湖南省委宣传部就建立了“五个一工程”专项经费,每年拿出100万元左右支持“五个一工程”的实施,并且湖南省委确立,在“五个一工程”评选中的获奖作品,作为该省新闻出版奖、文学艺术奖、社科理论奖的当然获奖对象,予以重奖;凡有一项精神产品在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奖的省直厅局、地州市委宣传部,则成为该省一年一度的“五个一工程”组织奖的当然获奖单位[10]。因而,在权力场逻辑的介入下,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活动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拥有一定的资本和权力,以此来巩固其已掌握的“文化领导权”。而权力场对文学场的作用的方式以及作用的能力无疑与文学场的自主程度紧密相关。实际上,文学场每时每刻都是两条原则——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而“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关系状况取决于场总体上掌握的自主权,也就是场自身的律令和制约在多大程度上加诸全体文化财富生产者和暂时(临时)在文化生产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以及有待占据统治地位的人”[11]。
就政府奖和作协奖来看,它们作为文学场中特定位置的占据者,其策略的选取必然是其占据的位置与文学场逻辑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政府奖和作协奖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必然使此类奖项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在与政治对立基础上的自主性文学场的逐步形成,并且经济资本已成为文学场中的强势资本,在这几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必然使政府奖和作协奖的评奖策略出现某种变化。在我看来,政府奖和作协奖评奖策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政府奖和作协奖的获奖作品来看,在以思想性取胜的同时,获奖作品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也体现了目前对“主旋律”作品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没有艺术性或艺术性过弱的话,作品包含的思想性如何转换为现实性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作品的社会效益就难以有效地实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此类评奖与体现文学场逻辑的所谓的“民间奖”相比来看,其获奖作品在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美的属性的同时,其意识形态性依然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二,此类评奖的奖金额也呈上升趋势,以中国作协框架下的评奖来看,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奖金额从2000元上升至1万元。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的单项最高奖金达到3万元,总奖金额上升至16万元。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此类评奖与体现市场逻辑的文学评奖相对照来看,其奖金的增长幅度和奖金额必然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应该说,这也应证了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所指出的,文学场中一定位置的占据者的策略选取是其所处的位置与文学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实际上,经济资本在文学场中所起作用的增大不仅仅体现在,以政治资本为依托的文学奖项奖金额度的攀升,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作用的不断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言,消费才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价值。那么,随着文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文学产品消费者的读者在实现文学生产的经济价值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看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相当的层面上就体现了读者对评奖介入能力和作用的增强。
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起,网络成为评奖活动展开的一个重要媒介。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由新浪读书频道与中国作家网共同合作报道评选活动。新浪网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网站之一,其受众的数量和质量已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作为中国作协框架下的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场自主逻辑的作用下,其影响力及经典化能力不断下降,并且其影响幅度和辐射的范围也日渐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12],这些都成了茅盾文学奖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对媒体影响力的借重,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那么,就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来说,当受众成为文学场中占主要地位的逻辑时,受众的介入是如何改变茅盾文学奖与文学场的张力关系的?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当代表知识分子资本的审读小组推荐的23部“入围作品”名单刚一在新浪网公布,就遭到了网友的猛烈围攻。而这23部“入围作品”的艺术水准,“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如果不是最高的,至少也可说是最整齐的”[13]。并且,在这些推荐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获得过“民间奖”。就是这些体现了文学场自主逻辑的作品(这些作品被认为在技术上或形式上极其成熟),却受到了网友义正辞严的指责。指责的重心不是作品不够艺术,而是作品不够现实。并由此引发对茅盾文学奖的主旨、意义和价值的质疑。并且,在读者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北京青年报》,在《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的文章中,直接以“莫言作品全票当选直面现实之作落选备受争议”为副题,集中指出了网友对 23部入围作品的批评和责问:“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桃李》等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准,大众爱读的现实作品却榜上无名,所以这个评委会是令人质疑的。中国的文学之路该怎样走,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水准奖项的评委们,难道就没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吗?”[14]在评选的第二阶段,按《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由三名或三名以上的评委共同提名增补了进入终评的六部作品,这六部作品全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且包括了最终获奖的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对读者力量的一种回应。并且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对评奖条例做出了修正,《条例》修改稿规定,为了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在终评开始前一个月,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向社会公布入围名单,读者的意见可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反馈到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并作为评选委员会评选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基本准则——坚持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被替换为“导向性、群众性、公正性”,也就是用评奖的“群众性”代替评奖的“权威性”。
应该说,“群众性”是1978年文学评奖运作机制的基本特点。那么,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构成,以及评选机制上的改变,是否就是对1978年文学评奖的一种回归,或者说就是对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简单的回归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第一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大众、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彼此呼应的[15]。而就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来看,一方面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与大众的阅读习惯之间是具有一定的亲和性的。“实际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直是畅销的,说明读者还是欢迎的”[16]。这样一来,借助读者对文学场的作用,茅盾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精英原则(文学场自主原则)相抗衡的新资本。在这些力量的张力作用下,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必然会向符合更多读者阅读习惯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偏移。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茅盾文学奖评奖标准的趋同性的同时,也不能就此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毕竟读者推崇的现实题材作品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等,所建构的现实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现实题材作品为我们构想的现实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因而,在我看来,茅盾文学奖如何定位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在一定层面上就决定了该奖项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具有的作用能力的大小。
最后要强调的是,由于权力场的逻辑,使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活动必然在文学场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总是偏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17]。但是,我们说的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活动会在文学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非唯一的位置。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文坛,新一代领导集体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写入了宪法,这本身就说明了文学场本身就是各种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场所,而这无疑才是文学存在的常态。“我们在强调高扬主旋律的同时,还必须提倡在题材、形式、风格、表现方法上的多样化,这才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的实践的辩证的观点”[18]。应该说,对那些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的倡导,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不过是使其占有某种主导地位,而非唯一地位。
[1]中宣部通知要求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6-01-14.
[2]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全面启动载[N].文艺报,1997-11-20.
[3]全国性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正式启动[N].文艺报,1997-08-19.
[4]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2.
[6]关于开展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工作通知[N].文艺报,2005-01-11.
[7]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15.
[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1979-03-27.
[9]思思.茅盾文学奖:人文话题知多少[N].北京日报,2000-10-25.
[10]湖南省每年资助“五个一”一百万[N].文艺报,1994-10-08.
[11]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5.
[12]唐韧,黎超然,吕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J].广西大学学报,1999,(10).
[13]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处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J].粤海风,2004,(2).
[14]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N].北京青年报,2003-11-17.
[15]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6]徐林正.茅盾文学奖背后的矛盾[N].陕西日报,2000-06-23.
[17]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卷[M].王荫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3.
[18]刘忠德.高扬主旋律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学习《邓小平文选》,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思考[N].人民日报,1993-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