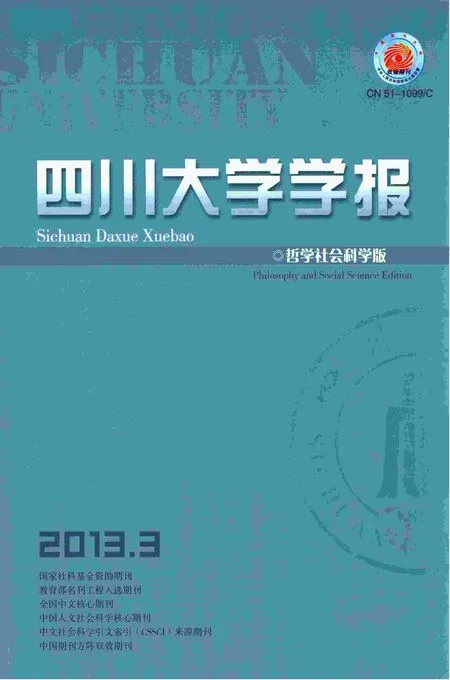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同文馆唱和诗》虽然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辩证》以及《宋人总集叙录》等重要的“提要”与“叙录”,但其诗集之编纂体例与其锁院的时间、地点、人物、性质、意义都还有尚待探讨、值得考论之处,下文就这些问题一一探析。
一、《同文馆唱和诗》的编集
附录在张耒诗文集中的《同文馆唱和诗》有两个版本,一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柯山集》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凡四卷;一在四部丛刊本《张右史文集》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凡五卷。
《柯山集》之四卷本,前两卷为古体,五古在前,一组(以韵分组)四首;七古与柏梁体在后,两组分别十九、十三首;后两卷为近体,五律在前,五组一百零六首;七律随后,四组五十五首;最后是七绝,七组二十二首。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点校本《张耒集》采用的是这个版本,只是放在卷六十二到卷六十五,作为别集收尾。
《张右史文集》之五卷本,前三卷为近体,后二卷为古体,与《柯山集》恰好相反。有两首五律混到卷三十九的七绝中,有四首五古不在卷四十的七古前,却在卷四十一的柏梁体前。署名邓忠臣等撰、收录在《四库全书》总集类的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虽分为十卷,但排列顺序却与《张右史文集》没有区别,正如《四库提要辨证》曰:“此书之有单行本,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绐藏书家耳。《提要》不加深考,以为宋时果有此书,遂以舛漏讥《宋志》,岂其然乎?”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61 页。
首先从分体编集的顺序看,宋诗别集很少将近体放在古体之前,因此四卷本的《柯山集》与《张耒集》更符合宋人体例;其次从各体内唱和诗排列顺序看,《柯山集》与《张右史文集》大同小异,但后者却有两处如前所说的不当,所以四卷本系统也更合理;再从卷次上看,单行本根据《张右史文集》而“分一卷为两卷”时,将同一组诗歌分割到不同卷次,也不符合古人编集习惯,甚至不如《张右史文集》。因此本文选择《柯山集》与《张耒集》的四卷本系统作为论述主要依据,个别字句会参校《张右史文集》与四库单行本。
《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时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为试院,因录同舍唱和之作,汇为一编”,固然如《四库提要辨证》所说是误以为后世抄书为宋人编集,但这里有个问题是:宋代《同文馆唱和诗》有无单行本?余氏云:“然吾尝考之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家书目,及《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亦皆无其书。且不闻有元、明刻本,直至厉鹗作《宋诗纪事》始选其诗,《四库》据鲍士恭家藏本,始著于录。”的确,前人目录学著作中没有著录《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总集,但并非其他文献没有著录。
张表臣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所写的《张右史文集序》,云其从汪藻、王鈇、何若、秦熺四公处得到张耒诗文“凡百余卷”后,“亟加考订,去其重复,正其讹谬,补其缺漏,定取七十卷,号《张右史集》”,①《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附录《东湖丛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21 页。以下所引《同文馆唱和诗》的诗句,均以此集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不一一写出诗题。他分体罗列了诗文分体篇目数量,结末列“同文馆唱和六卷”。这“六卷”当时是否是单行本?因张表臣语焉不详,他所编的《张右史集》原貌也不可考,所以很难得知。只是从其单独列出“同文馆唱和六卷”看,似乎这“六卷”就是当时的一个单行本。张表臣将其附录在《张右史集》中,从此就变成了别集附录本,而不再是单行之总集。“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家”可能就因此而没再关注此事。
当时“六卷”若非单行本,那《张右史集》中所录,则可能就是张表臣所编,若是他编集,也定有个底本。他的底本从“四公”得来,而“四公”又从何而得?无从考证。定是参与唱和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编集而成,或是张耒,或是邓忠臣,或是其他人。唱和集按体分卷、按韵分组排列,并未突出某个个人。但无论如何,张表臣之前或从张表臣开始,已有“同文馆唱和六卷”存在。
无论是别集附录本,还是总集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都没有得到后世太多的关注。有关同文馆这次锁院的其他文献记载也十分罕见,连具体到年月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次考试锁院也只字未提,这使得此次锁院显得十分隐秘,影响到我们对整个锁院唱和的认知度。
二、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时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同文馆唱和诗》之提要已经考证出此次锁院在元祐二年,《四库提要辩证》更进一步考证其在此年秋天。具体的起止日期是否能够考察?
几乎没有什么集外资料可以说明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日期,而《同文馆唱和诗》的大量诗歌却具有极为突出的自证性和互证性,可以提供今人所需的信息量。
从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所云“了无一事犹深锁,辜负东篱菊品浓”看,九月九日试官们已经较艺完毕,但尚未开院。耿南仲的和诗云“贡珍已选茂良充,犹被拘縻类缚钟”,也是说较艺工作已经完成,而试官犹被“拘縻”在同文馆。晁补之觉得天已寒而开院之日似乎仍遥遥无期,甚至向家人索要御寒之衣:“更促寄衣真似旅,晓堂初怯露寒浓。”邓忠臣悲观到要通过打卦问卜以求确切日期:“归期专欲问龟从。”余幹则比较乐观地说“开门预计无多日”。而张耒,则比其他人更早得到开院确切时间:“十日飞腾过眼疾,万签甲乙定谁从。”且注云:“时去开院十日。”我们据此可知,开院当在九月十九日。而蔡肇在和邓忠臣《与文潜无咎对榻夜话达旦》时云:“穷秋天气少晴明,雨叶风窗夜夜声。应为幽人听未足,不教骢马出重城。”且注云:“时已奏号,而御史不至,遂留一夕。”这样看来,预定九月十九日的开院,可能推迟到二十日。
蔡肇《漫兴成章屡蒙子方宠和更辱赠句辄用奉酬》云“礼闱联事几三月,词客悲秋共一音”,此诗写于重九之后、开院之前不久。由“几三月”上推,则锁院当在六月十九日或其后,亦即在六月中下旬之间。邓忠臣“忆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农家苦”,之所以谈到前三年的“六月”,自是从眼前之“六月”生发出感想来的。
六月中下旬锁院之说,从诸公有关“初伏大雨”的唱和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能够推论得更为精确。由张耒首唱的《初伏大雨戏呈无咎》,应该是《同文馆唱和诗》中最早的一组诗歌。张之首唱与晁补之、曹辅、邓忠臣、蔡肇四人之和诗,共八首,当均作于入试院前后。从晁补之“蓬山西邻九轨路,三月街晴叶吹土。直庐凿牖面宫垣,青壁崭崭看垂雨”,说明这场大雨来时,他还在秘书省①元丰五年将崇文院与秘阁合并称秘书省,在左升龙门里,其变化迁移情况,详参陈元锋:《北宋翰苑馆阁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 页。值班。这首和诗在他的《鸡肋集》中题为《次韵文潜馆中作》,②晁诗以及当时唱和者称秘书省为“馆中”,同文馆为“试院”。更能说明大雨时尚未入锁院。
初伏第一天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元祐二年五月十三甲子是夏至,经过庚午(五月十九)、庚辰(五月二十九),六月辛巳朔(六月初一),第三个庚日是庚寅即六月初十,亦即初伏第一天。初伏第十天,便是第四个庚日即庚子(六月二十),这天又是中伏的开始,即中伏日。晁补之诗结尾云“但忧伏日细君须,割肉无缘俟归俎”,则说明到中伏日时,诸人已经得到锁院通知、业已入试院,无法回家过节了。由此可以确定锁院在大雨之后、六月二十之前。③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零二云:元祐二年六月“甲午(十四日)诏以大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又补充云:“《御集》六月十三日。”可知在十三、四日前后尚大热无雨。那么,大雨当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
张耒“快洗晩空作晴碧,三更月华清万户”,说明初伏的那场大雨在傍晚时即下即停,是典型的夏日阵雨。而诸公的入院时间和情状是:“东门骢马止行行,被诏秋闱阅俊英。三岛隔云天北极,万灯明路国西城”(邓忠臣);“天街落日走鸣珂,咫尺衡门不许过。催去据鞍犹鹤望,争观夹道已云罗”(张耒);“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东华走马过” (晁补之);“午门钥入断人行,禁漏稀微出迩英。齐拜敕书期老仗,并驱驺御出西城。喧哗灯火看如梦,关锁官曹只寄声”(蔡肇);“云龙九阙晨书诏,灯火千门夜出城。潇洒庭除当月色,稠重幕帘断人声”(孔武仲)。五人的描述,都说明他们是在日落天黑、华灯初上时进入锁院的,他们均未提到雨后,则说明他们入锁院不是在下雨后的那个傍晚,而是在另一个傍晚。结合晁补之诗中那句无法回家吃伏日肉的尾联,可以推断是十九日傍晚下雨,二十日一早,他们上朝接到诏书,傍晚入锁院。蔡肇所云“昨朝东门同拜敕,玉齿犹残道中语”,即说明他与张、晁、邓等人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尚未结束,就接到锁院之诏书,因此他们在道路上还在谈论着唱和诗歌。
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从蔡肇的“次韵文潜丈”始及其以下的十一首同韵诗,才明显是锁院后所写,蔡肇所云“闭门十日无一事,坐对空庭秋叶舞”,则可见他们进入锁院之后最初十天都无事可做,才继续步韵和诗再续前缘。将“初伏大雨”一组唱和收录其中,其实也证明大雨在入院前一天傍晚,而有关大雨的唱和诗歌在第二天入院后还在继续。这样说来,《四库提要辩证》的“秋天”说,不够准确。锁院是盛夏中伏日就开始了。
元祐二年七月庚戌,是朔日又是立秋日,中伏日后的第十天便是秋后末伏的开始,所以张耒④此诗作者,《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本与《坡门酬唱集》卷二十二均作“张耒”,而《柯山集》与《张耒集》作“曹辅”。当作张耒,因为曹辅锁院前不在秘书省。有“忽惊秋近梧桐落”之语,曹辅《呈邓张晁蔡》云“九人同日锁重闱,一夜涛声卷秋雨”,都谈到“秋”,与中伏日前下雨而中伏时间较短有关。柳子文“重闱几日锁清秋,酬唱新篇乱如雨”,以“秋日同文馆”为题为首句的多首诗歌,似乎都强调此次锁院在秋天,但实际上,是在立秋前十天。
张耒“来时汗流今雨霜,重门事严御史章”,可知此次锁院的时间漫长。科考锁院一般是五六十天,而此次锁院“几三月”近九十天,在科举史上怕是少见。或许是因为元祐更化初期,旧党内部对科场“更化”的意见还不统一造成的。当时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主张沿袭熙宁元丰以来的经义考试,只是不再使用《三经新义》、《字说》,而苏轼、孔文仲、刘挚等人建议加上熙宁元丰废除的诗赋,一时争议纷起,①详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 页。尚无定论,锁院正在等待朝廷的决策,引试日期也推迟。②参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元祐三年)十一月庚申,三省奏检会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指挥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四月十二日指挥仍罢律义;六月十二日指挥将来科场程序不得用《字说》,并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已见,即不许引用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不得于老、列、庄子内出题。”可以看出科场规则内容一直在变化之中。余幹写在蔡肇《次韵文潜丈》之后的次韵诗云“后朝便足阅英才,为指帡幪设千俎”,说明入院十三四天后才引试。
三、同文馆承载的对外政策“更化”消息
同文馆在汴京城西,本是招待高丽使节的场所,元祐二年临时用作试院。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七十二熙宁同文馆云:“在延秋坊,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七年正月,以内臣掌之。”“以待高丽使”后有注“舍宇一百七十八间”,可知其规模之大,而如此多的房间也足够一场大型考试使用。
邓忠臣“馆阊阖外西城隍,书槖迫遽不及装”,描述了同文馆所在具体的位置以及他们匆忙赴馆的情状。同文馆在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比只说延秋坊还精确细致。柳子文在试院期间,写道“庭木何年植,窗尘异域题”,并自注云:“高丽人馆此,书字尚在。”呈现了同文馆当时的环境与曾经的历史。邓忠臣“人闲聊假诗书乐,地远还闻市井声”以及商倚“图书堆枕畔,歌吹隔墙隈”,都说在馆内仍能听见“市井”、“歌吹”之声,可见同文馆并未远离“人境”,是个热闹的所在,只是锁院中的人不能享受那份热闹而已。
《四库提要辩证》认为“高丽使不常至,其地空闲,故借以为试院”。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560 页。而事实上,“高丽使”并非不常至,同文馆也并非一直“空闲”。同文馆此次被用作试院,其实透漏出元祐更化时期朝廷对待高丽政策的变化。蔡肇诗“万里夷王子,曾听若木鸡。泛舟沧海外,授馆国门西。琛币来重译,车书想旧题。苍梧弓剑冷,云雨泣芝泥”,涉及到的便是朝廷与高丽关系今昔变化。
宋神宗变法时期,十分注重对外特别是对高丽的政策,所以熙宁中专修同文馆以厚待高丽使节。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蛮。元丰待高丽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络绎不绝的高丽使节时常到达京师,同文馆在元丰间门庭若市的情状可以想见。
元祐更化初期,旧党不少人都认为神宗时期待高丽人过厚而引起不少弊端,因此提议改变对高丽的政策,苏轼、苏辙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多次上奏朝廷,如《栾城集》卷四十六《再乞禁止高丽下节出入札子》云“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例”即是其中之一。所以元祐时期,朝廷不再厚待高丽使节,同文馆也因此风光不再,才被用作试院。蔡肇在元丰期间积极追随王安石,支持变法,所以他在诗歌尾联通过高丽人对神宗的哀悼,表达了他自己对神宗的思念,也传达出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的深厚感情。其他考官几乎不提及同文馆这段相距并不太遥远历史,或许是在有意回避,或许是并无感情,因为张耒、晁补之都才做了苏门学士不久。
同文馆后来似乎像是巧合地成为旧党的一个符号,“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哲宗元符元年。就将这个地方与元祐党人更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四、参与及未参与锁院唱和的试官
据柳子文“毛遂未至空连房”句注:“同舍十九人,余独后入。”则知相继入锁院的试官有十九人。参与唱和的十三人中,邓忠臣(?—1106 或1107?⑤《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其“崇观间卒”。)、蔡肇(?—1119)、晁补之 (1053—1110)、张耒(1054—1114)四人唱和最多,在二十首以上;余幹(生卒不详)、曹辅(生卒不详)、李公麟(1049?—1106)、柳子文(?—1099?)、商倚(生卒不详)、耿南仲(?—1129)六人居中,在十首以上;孔武仲(1041—1097)、温益(1038—1103)、向(生卒不详)三人唱和不多,孔二首,益、向均一首。①对十三人的详细研究,另撰《同文馆唱和诗人事迹考补》一文,此处不详谈。
十三人外,还有三名未参与唱和的试官姓名可考。据邓忠臣“喜陪群彦集,通籍在金闺”自注云:“属彦常、彦思、元忠、器之、文潜、无咎。”其中彦常即孔武仲,文潜、无咎即张耒、晁补之,而彦思、元忠、器之当为十九人之三。彦思当是赵睿,②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跋鱼计亭赋》云:“又明年二月,(宇文黄中)为荥阳赵公睿作《鱼计亭赋》,引物连类,开阖古今,深得东坡、颍滨之笔势。适有天幸,出入侍从、身名俱荣者,俱好文之主也。赵公字彦思,熙宁六年进士,当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首,与孙逢吉彦同作《职官分纪序》。”熙宁六年进士。元忠当是孙朴,为孙固之子,郑州管城人。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注云:“孙朴,固子。”孙固字和父,《宋史》三百四十一有传。孔凡礼《苏轼年谱》第749 页有孙朴相关资料。器之当为刘安世,亦是熙宁六年进士。④据《宋史》卷三百五十六、《东都事略》卷九十四以及《郡斋读书志》卷五下可知: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师事司马光,熙宁六年登进士第。哲宗立,司马光举安世充馆阁之选,除秘书省正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初七),朝奉郎毕仲游、赵挺之并为集贤校理,承议郎行军器监丞孙朴、承议郎行太学博士梅灏、奉议郎张舜民、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赵睿,并为秘阁校理;宣德郎详定役法所管勾文字李籲、承议郎盛次仲并为校书郎;试太学录张耒、试太学正晁补之,河南府左军廵判官礼部编修贡籍刘安世、和州防御推官知常州晋陵县丞李昭玘、宣德郎陈察并为正字,仍今后除校理已上职,并出告。仲游等十三人,并以学士院召,诏充选也。”赵睿、孙朴、刘安世与张耒、晁补之同时被召试充馆职。此次所授馆职为此次秋闱锁院试官的主力军,所以商倚才有这样的诗句:“宝玉荆山尽,文星禁掖稀。”并自注云“馆阁诸公多集于此”。由此段话可知,入锁院时,赵睿、孙朴为秘阁校理,张耒、晁补之与刘安世均为秘书省正字。
五、此次锁院性质:吏部选人还是发解试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认为此次“同文馆所试乃吏部文武选人”。⑤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560 页。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58 页同意此说。其根据有二:一是晁补之《鸡肋集》卷十五《试院次韵呈兵部叶员外端礼并呈祠部陈员外元舆太学博士黄冕仲》“文武中铨集,丹铅百卷堆。豚鱼聊可辨,皮弁不应恢”之自注“左选试经义,右选试兵策”,且云:“此诗之后,才隔九首,即《次韵邓正字慎思秋日同文馆诗》,明系作于同时。”既然“才隔九首”,为何不收录唱和集中?不收入唱和集中,如何敢判定其“明系作于同时”?若“才隔九首”便为同时作,那么其间的八首当亦是同时作?显然不是。“才隔九首”而不在唱和集中的诗歌,当然没有唱和集中的诗歌更靠得住。而且此诗诗题所言之叶端礼、陈元舆(轩)、黄冕仲(裳),均不在同文馆唱和的十三人之列,也无其他材料说明他们参与了这次锁院,所以很难确定此诗说的是此次考试。⑥似是元祐三年春闱锁院,叶端礼不可考,陈轩与黄裳都在其中,当时也有武举。二是“若所试者为进士,纵贡院未成,亦当就太学为试院,不当借同文馆也”。事实上,进士科(诸科常与进士科同时考)的省试一般不会借用同文馆,但若是国子监或是开封府的进士科之发解试则很可能会借用同文馆。因为“各地发解试的考试,都集中在州府治地举行,但在宋代,州府却长期没有专用的考试场所,多是临时借学宫或佛寺为之。州郡贡院(又称试院),到北宋末方才建立”。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133 页。既然是借用,国子监或开封府的发解试当然也可以借用“学宫或佛寺”以外的同文馆。
其实关于此次锁院所试之性质,《同文馆唱和诗》中有相当多的诗句可以证明其并非是“吏部”铨选“文武选人”,而是“秋闱”。邓忠臣“被诏秋闱阅俊英”、“秋闱深锁觉愁多”,张耒“秋闱何幸相握手”以及 柳子文“秋闱得暂依”,都明确说他们这次锁院是发解试,因为“秋闱”是全国性科考三级试之发解试的专用术语。据柳子文“万户争看榜,三年此一开。异时千载遇,此日四方来”看,此试为英宗治平二年所定三年一开科的科举常例考试。①《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引《宋登科记》云:“英宗治平二年,始诏三岁一贡举。”
耿南仲“由来京邑贡,正合冠多方”,是说京畿之地解试所贡的举子,其水平历来是全国各地解试之冠,正说明此次考试就是开封府的发解试。②柳子文“槐花举子促书囊,成均贡士贤登乡”,所云“成均”,是国子监别称。据《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344 页):“元丰新制后,国子监执掌国子、太学、律学、武学、算学五学之政令与训导事,以及刻印书籍等。”并不单独进行“五学”的发解试,这里可能指国子监执掌的“五学”士子也参与了开封府的发解试或别头试。李公麟有几首诗云“雍畿兹吁俊,元祐看新魁”、“门通三级峻,桂露一年香。庆及飞龙旦,同歌庶事康”、“吁俊天畿合辟雍,……龟列春庭先壤奠,龙飞天路得云从”,反复明确地强调,这次秋闱是哲宗登基后的第一次科考,即龙飞榜的初级考试,也即元祐三年省试(春闱)、殿试之前的解试。
与此次秋闱相关的是同时锁院而开院更早的别头试,黄庭坚参与了这场于武成宫举行的别头试的考校工作。③见《山谷年谱》卷二十二《次韵徐文将至国门见寄》注云:“诗中有‘槐催举子着花黄’之句,盖是岁秋试。……已上皆武成宫试闱所作。”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诗注云“是日别试榜出,亲友亦有预荐者”,可知别头试九月九日已经开院,而发解试之试官尚在锁院中。作为同文馆试官的蔡肇与晁补之,其弟均在此次避亲嫌的别头试中及第,二人闻知后有诗,蔡肇有《家弟别试预荐,特蒙慎思学士赠诗致庆,感荷不已,次韵酬谢》,其弟即蔡载,字天任;晁补之有《八弟预荐,慎思兄以诗为庆,复次韵并寄八弟》其八弟即晁将之,字无斁,第二年即元祐三年进士及第,④晁补之有《送八弟无斁宰宝应》等与八弟相关的诗歌。详参张剑:《晁说之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8 页。邓忠臣也写了《九日考试罢,闻无咎、天启二弟荐名,因用前韵,以纾同庆之怀》,这些诗题与诗歌都可以从侧面证明同文馆锁院是进士及诸科的发解试性质。
六、此次发解试之更化意义及试官们的态度
作为哲宗登基后的首次开封府发解试,具有科场更化尝试意义,参与唱和的试官们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柳子文《初入試院》即云“上国擢材初改辙”,他很直白地指出这次“上国”即首善之区的解试,承载着科场更弦改辙的意义,要更改的是神宗时期的考试内容以及方向。旧党从元丰末元祐初就已经开始全面改变“新法”,而且势头猛烈,科场涉及到人才选拔与培养,当然是其更化的首选重点,因此尽管旧党内部改革的意见尚未统一,士子的学习内容方法尚未改变,但“更化”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推行了。柳子文作为苏轼、苏辙的堂侄女婿,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关的信息,而张耒、晁补之也早在入馆阁前就熟知了二苏的主张。孔武仲更是科场改革的急先锋。商倚云“盛世文章由此变,坐看风俗反醇浓”,更指出这次解试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只是科场的更化,而且还是文坛风气、社会风俗的更化。晁补之“搜才赖公等,要助俗成康”,也将这次为国“搜才”,看成是促使民风民俗焕然一新的行为。
既有如此的认识,多数试官都充满信心,决心为“更化”贡献个人的力量,如柳子文“上国擢材初改辙,众心督战亦乘城”,就愿意为其尽心尽力,他还说“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圣主开明堂”,表现出激情狂烈的精神。邓忠臣“逢辰强思报,矫首咏明康”,也表达了明时感恩图报之情。孔武仲最为坚定,他说“欲把尘埃补山岳,宁辞羽翮寄罝罗”,为了这场科场革新,他自愿牺牲个人自由。诸人之中,蔡肇的态度较为特别。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考试是“奎壁重开照,琳琅尽得归”、“诸彦联翩入,斯文迤逦回”,但他另一诗也云“明时勤选擢,间设誉髦场。该学添《三传》,微能及《九章》。静无桃叶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忧病,惟应赖杜康”。既然一切都顺理成章、完美无缺,他何以“幽忧”呢?作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年间的进士,蔡肇实际上对这次科考改革抱着忧虑且审慎的态度。事实上,参与唱和的十三名试官,除了孔武仲是嘉祐八年进士,曹辅未中进士,温益、向及第年限状况不可考外,其余九人也都是熙宁、元丰间的进士,他们虽然能够认识此次解试的意义,但若全盘否定熙宁元丰,就等于说全盘否定他们自己的教育,所以他们也都不像孔武仲那样激进,而较为保守审慎。
蔡肇云“该学添《三传》,微能及《九章》”与“即今文学科卜商,赤刀大训在西房”,透露出一点考试信息,熙宁元丰间废弃的《春秋三传》与《九章》所代指的诗赋及“文学”都可能在这场考试中加入了。作为王安石的弟子,蔡肇对此种变化比其他人敏感。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到卷四百零五所载,元祐元年元月到二年九月,正是旧党积极废除新法、旧党内部洛蜀朔党争渐起且激烈之时,而来自不同阵营的邓蔡张晁等十三人,封闭于锁院,能悠游唱和,实在是难得的和谐。
处于元祐更化时期的开封府发解试,被赋予了科场更化的尝试性质,为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之春闱改革奠定了基础。有关同文馆锁院唱和的文献很少,但唱和诗具有超过独吟诗很多的自证性与互证性功能:一题多首唱和诗歌提供的信息量显然大于一题一首,多题多首唱和诗之间提供的信息互相参照,这一优势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唱和诗,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唱和诗这个显而易见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