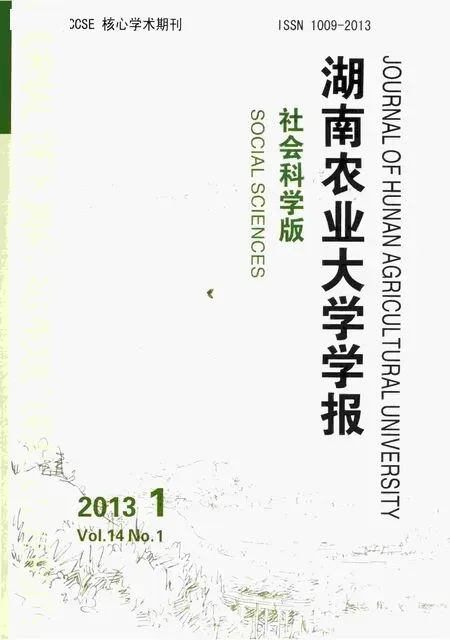诉讼欺诈的定性与刑法规制
周扬帆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诉讼的原本含义就是双方抱着共同的意愿期待法院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 无论双方争讼的原因如何,想要合理地解决矛盾就必须受到诚信的约束,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公正的基础是诚信”,[1]否则充满了欺诈谎言的诉讼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甚至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司法的权威。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据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和维护权益的现象越来越多,这说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我国民众开始懂得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由于民众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现行司法制度的缺陷,滥用诉权进行虚假诉讼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在 200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民事案件诉讼欺诈防范惩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在存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通过对100起民事二审改判案件进行抽样分析,发现有超过 20% 的案件存在诉讼欺诈行为。[2]这不仅侵害了公民、集体和国家的财产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司法秩序,给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阻碍。因此,有必要借鉴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关成果,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危害、定性争议以及规制措施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诉讼欺诈的社会危害
诉讼欺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诉讼欺诈,也即侵财类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做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或者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物或财产上不法利益的行为。广义的诉讼欺诈则不仅限于提起诉讼骗取财物这种情形,还包括基于其他动机目的而在诉讼活动中实施的形形色色的欺骗行为。[3]诉讼欺诈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既包括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
1.严重侵害相对人的权益
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诉讼欺诈被识破而遭到败诉的结果,一种是通过一审或者二审从而获得胜诉达到诉讼欺诈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诉讼结果如何,相对人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被卷入到虚假的诉讼之中,并且为此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精神上的痛苦。换言之,即使诉讼欺诈行为人的目的没有达成,但相对人仍然无端地遭受到了诉讼的一系列“麻烦”,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自古就有着厌讼传统的国度,诉讼程序的进行本身对于相对人来说就是一种“飞来横祸”。更不用说一旦诉讼欺诈行为人的目的达成,相对人的标的财产会进一步遭受损失,明显肆意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将非常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形成不良价值导向
因为诉讼欺诈的实质是法院被行为人欺骗而陷入认识错误,并依职权以判决方式对被害人的财产进行处分。一旦法院裁判做出有效的判决,这种隐藏着诉讼欺诈行为的判决书是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诉讼欺诈行为人能够由此而获得利益,形成“恶人得势”的错误的价值导向。对社会甚至会起到反面导向作用,会让更多心怀不劳而获想法的人看到所谓的“希望”,进而去钻法律的空子,引发诉讼欺诈愈演愈烈之势,造成法律不公的现象。
3.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
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诉讼欺诈不是真正的争讼关系,而只是行为人获得非法利益所利用的途径,这种诉讼行为根本不能实现诉讼原本的价值,而只是利用司法机关的职能和职责来达到自己非法的目的。所有的司法程序都只是行为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和过场,庭审程序以及各项工作的进行都是完全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其行为无疑会严重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
4.损害法院的公正与权威
由于法院的判决能够产生法律效果,诉讼欺诈行为人达到非法目的后,会由藐视法律、利用法律到挑战司法的权威与公正,法院成为行为人非法交易甚至犯罪的场所。与此同时,相对人由于收到法院具有执行力的裁判文书而不得不执行或遭到强制执行,导致自己的合法财产被转让给诉讼欺诈行为人,心生愤慨进而怀疑法院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权威性。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公众对国家的司法权威以及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的同时,潜在的犯罪人更加看到犯罪成功的可能性,会试图不断效仿通过诉讼欺诈的行为达到自己非法获取权益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诉讼欺诈定性的争议评析
对于诉讼欺诈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德、日刑法学界通说和审判实践均认为构成诈骗罪,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欺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在这种场合下,法院是被骗者,同时也是交付者,而且法院具有将财物交付给原告的权限,因此构成诈骗罪。”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激烈的争议,现对主要观点评议如下:
1.以诈骗罪论处
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例如张明楷认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成立诈骗罪。[4]主张构成诈骗罪的学者主要引进了三角诈骗的理论,认为诉讼欺诈的本质与诈骗罪相同,都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并且被骗者与被害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由于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有依法对公私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进行处分的权力。所以在诉讼欺诈中,法院基于这一特殊地位和职能而成为被骗人,被害人是民事案件中的被告甚或案外人,两者不是同一人。
笔者认为,把诉讼欺诈行为归结到诈骗罪中不能解决如下问题:首先,从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法益侵犯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更破坏了司法公正与权威。通常,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区分此罪和彼罪的重要标准,行为相似但侵犯的客体不同,就构成不同犯罪,故将侵犯复杂客体的诉讼诈骗行为直接归入诈骗罪,就会产生矛盾。其次,根据前文所提到的诉讼欺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后果,诉讼欺诈人胜诉则得到不法利益,并且所得非法收益也能成为判定诈骗罪既遂与否的标准。但若诉讼欺诈人败诉,或者被法院识破则没有非法利益的所得,那么依据诈骗罪定罪则为未遂,但事实上其行为已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从保护司法秩序的角度来看其行为已经既遂了。
2.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王作富认为虚假诉讼行为就是借助法院裁决的强制力来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或者使行为人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点。[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看到了法院判决的强制性特征,认为敲诈勒索罪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由于强迫他人交付财物,所采用的威胁、要挟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将借助法院判决的强制力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归结于威胁、要挟的方法之一,而不是骗取被告的财物,从而认定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方法,勒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这里被害人交出财物并不是出于恐惧心理,而是迫于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因此与敲诈勒索的交出财物的缘由还是不同的。
3.以其他犯罪论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2002]高检研发第 18 号)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280 条第 2 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307 条第 1 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诉讼欺诈如果不成立诈骗罪,但其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以其他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对于整体行为无法评价为犯罪,而方法手段行为又确实造成了一定社会危害时,对其进行处罚,确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主要靠伪造证据而成就的诉讼欺诈行为的数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个答复依然存在问题:这样的规定确实是对手段方法行为作出了规制,但也只是考虑到了手段方法的危害,而没有对整体进行全面的评价。直接给予除罪化规定,忽视了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危害。而且刑法第 307 条第 1 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的是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即无论是诉讼当事人指使他人作伪证还是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都为刑法所评价,而本人的伪造证据却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这对诉讼欺诈的定性造成了逻辑上的矛盾。[6]
4.以无罪论处
也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行为不构成犯罪,在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均不同于诈骗罪,现行刑法也没有相应条款对其予以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只能按无罪处理。[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的当事人伪造证据行为确实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损失,扰乱诉讼的正常秩序,其危害程度也显而易见,但由于没有相应条款加以规定,没有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要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按照无罪处理。这种观点看似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实则是机械地理解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含义,有教条主义的痕迹。由于虚假诉讼对法益的侵害的危害日益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不能以刑法没有规定为由而忽略该问题。
综合以上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分析,笔者认为诉讼欺诈的行为必定是对法益造成了侵害,具备社会危害性,应当为刑法所规制。
三、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规制
考虑到现行刑法罪名以及最高院的答复都无法全面保护诉讼欺诈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尤其是对司法秩序破坏这一方面,所以可以在妨害司法罪一章节中新增“诉讼欺诈罪”这一新罪名,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诈骗罪侵犯的只是财产权这一单一的客体,而侵犯双重客体的诉讼欺诈行为是不能被评价到诈骗罪中的,因为它还破坏了司法秩序。
其次,刑法第305条对发生的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民事诉讼中的作伪证的行为同样侵害对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并且扰乱了司法公正,也应该给予规制。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伪证罪就贯彻到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所以在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为伪证罪却不能解决民事诉讼中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其归入到诉讼欺诈罪的范围中。
再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对于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情形规定为妨害作证罪,将当事人自己作伪证的情形作了除罪化处理。笔者认为这里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其没有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差异。根据刑法期待性的理论,在刑事诉讼中很难期待被告人“自证其罪”,所以被告人为了脱罪而作有利于自己的证明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但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涉及到了对方的权益,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作伪证的行为完全是损人利己,其行为应当受到处罚。
因此,诉讼欺诈罪的犯罪构成应当具有以下内容: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 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利益的目的。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又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性利益。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向法院提起了虚假的诉讼,破坏人民法院正常审判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当然,在适用诉讼欺诈罪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罪与非罪的问题,对于实施本罪中的行为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该作除罪化处理,不以犯罪论处,但应定追究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责任,行为构成侵权的应当进行民事赔偿。在这里的情节严重与否应当综合考量其行为对司法秩序的破坏程度以及试图侵占财产利益的大小;关于既遂问题,由于诉讼欺诈罪属于行为犯,即只要行为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进而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情节严重就达到诉讼欺诈罪的既遂,这样才能体现对司法秩序的保护。但行为人如果还未提起虚假诉讼,则无任何法益侵犯无需承担责任;关于一罪与数罪的问题,鉴于本罪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司法秩序,所以被规定在妨害司法罪一章中。那么在诉讼欺诈的行为过程中又有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行为构罪以及妨害作证、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构罪的,按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不实施数罪并罚。
[1]西塞罗.论义务[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3.
[2]黄 剑,张秀娟.浅谈诉讼欺诈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11(5):34.
[3]吴玉萍.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4):47.
[4]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2):93-106.
[5]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J].检察日报,2003-02-10(3).
[6]李 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案件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6):29.
[7]潘晓甫.伪造民事证据是否构成犯罪[J].检察日报,200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