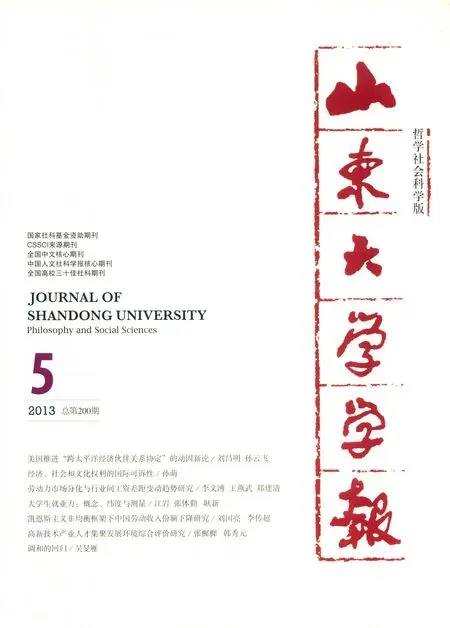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混沌学思想阐释
梁爱民 陈 艳
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混沌学思想阐释
梁爱民 陈 艳
在维果斯基创立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理论是研究人类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强调在不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心理机能的发展。从混沌学视角来解读社会文化理论,可以发现:人类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思维与语言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动态的非线性关系;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是影响最近发展区的奇异吸引子;语言工具在个体认知发展系统中具有蝴蝶效应。
社会文化理论; 混沌学; 开放的动态系统; 非线性; 奇异吸引子; 蝴蝶效应
一、前言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可以追溯到 18、19 世纪的德国哲学(特别是Kant和Hegel)、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学、经济学,但主要和直接来自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 (Vygotsky) 创立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它不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层面或文化层面的理论,而是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High Psychological Function)发展的理论,该理论强调“在不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研究人类认知和心理机能的发展,因为人类认知与心理机能的起源和发展包含在社会文化的互动中”*Lantolf, J. P. & Thorne, S. L.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维果斯基早在19世纪20年代,在批评人类心理及其发展生物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发展“文化历史理论”,认为人类认知与心理机能的起源和发展融合了动物生物进化和人类历史发展两个过程。他撰写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1931)和《思维与语言》(1934)两部巨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翻译出版后,给国内外心理学和教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儿童心理学家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 还有一些教育心理学家把他的理论应用到教育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应用语言学家又创造性地将社会文化理论引入了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并力求使之本土化。至此,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
混沌学(Chaos Theory)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它发端于物理学,随后很快被应用到生物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近年来,混沌学理论逐渐被应用到语言学研究领域,因为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系统, 而是一个多维开放的体系, 语言现象与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纠缠, 其中存在许多动态的、不稳定的、随机性的因素。*张公瑾、丁石庆:《混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进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可以说,混沌学的出现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从混沌学视角对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进行探讨和解读。
二、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涵
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确切地说,“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心理从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的实现是通过语言符号的中介和调节、知识的内化、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最近发展区的跨越为条件的。”*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10.因此,中介论(又译为调节论)(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构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中介论。中介论或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其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机能(比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是以社会文化的产物——语言符号为中介,通过调节的作用发展而成的。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被称作调节,语言作为最基本的调节工具,在调节人的活动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从而形成了人类特有的高级的、被调节的心理机能——认知发展。*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3页。但获取和维持对复杂心理活动的调控需要个体逐步实现,因此,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了从物体调控(Object Regulation)到他人调控(Other Regulation)再到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作用经历了从外部的社会语言(Social Speech)到自我中心语言(Egocentric Speech)再到内在语言(Inner Speech)的发展过程。*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53页。内部语言的形成是个体思维与语言走向统一的标志,是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最后阶段。
2.内化论。如何定义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之间的关系曾是心理学中常见的难题之一,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失败已经成为心理学与哲学中许多理论走向死胡同的原因。笛卡尔假设心理学研究的唯一真实领域是内部心理活动,这一假设促使后继研究者只关注天生素质等问题,忽视了社会和物质环境对个体内部心理过程的影响。相反,行为主义者假设外部行为是心理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使后继研究者忽视了内部心理过程的复杂性。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就即在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之间的整体关系,他用内化概念描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所有高级的社会历史的心理活动形式,首先都是作为外部活动的形式,而后内化为在头脑中进行的内部活动。”*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20.这种从外部、人际间的活动形式向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变就是“内化”。“个体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是社会关系的内化,正是这些内化了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个性的社会结构。”*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22.
3.活动理论。活动理论是维果斯基有关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是同样的”*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32.。维果斯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观,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后指出:“人的高级认知功能是在社会活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王光荣:《文化的诠释——维果斯基学派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20页。活动理论把人的行动视为社会和个体相互影响的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个体生来就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在与他人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发展起新的行为系统(高级心理机能)。个体行为心理起源并受制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交往活动,个体发展的社会源泉是他们参与的各种共同活动,这些共同活动将各种不同的影响融入了学习者新颖的理解与参与方式之中。
4.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源于维果斯基的文化发展遗传规律(Genetic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该遗传规律的核心观点为,“高级思维在人的认知发展中出现两次,先在社会层面,然后在心理层面”*Vygotsky, L.S. Mind i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33.,在此基础上,维果斯基提出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或同伴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维果斯基:《维果斯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维果斯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发展与教学的关系,强调了教学在发展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阐释了“合理的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头,并引导发展,教学应唤醒或促进一系列位于最近发展区内处于成熟状态的机能”*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22页。的深刻内涵,从而驳斥了当时出现的两种观点:一是教育与发展是一个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过程,发展遵循的是内部自然规律,而教学从外部利用了发展的潜能;二是教学与发展是同一回事,教学即是发展。
社会文化理论与其它心理学及教育学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观、巴赫金的对话论、Peirce的符号理论、Mead 的符号互动论等多种理论,既强调了社会活动、语言符号在人类由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过渡中重要的中介作用, 又强调了在此过程中学习者主体间互动的重要性, 还强调了个体发展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要作用,即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可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在内部心理和外部环境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融合了自然主义取向心理学研究和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研究产生的对立局面。*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为此,1994年,美国语言学家James Lantolf编辑了《现代语言》杂志,将该理论科学地引入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2007年起,我国学者文秋芳、高一虹、刘永兵等注意到社会文化理论的独特之处,撰写了大量文章,从哲学倾向、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二语习得等视角对其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和分析。
三、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混沌学思想

(一)人类心理机能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
混沌学理论关注的是开放的动态性系统(Opening Dynamic System)的表现。开放的动态系统中既包含有确定性系统,又包含有不确定性系统。两种子系统在系统运行中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影响,通过自身的重组和调整反作用于产生无序的力量,产生新的秩序,从而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必须区分两种心理机能,一种是自然的、直接的低级生物性机能,如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意注意以及形象思维、情绪等。另一种是社会的、间接的高级心理机能,如随意注意、逻辑记忆、抽象思维、高级情感和意志等。然而,“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这两种不同的心理机能既是独立的,又是互动的。”*维果斯基:《维果斯基儿童心理与教育论著选》,龚浩然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确切地说,个体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生物种系的发展又有历史文化的发展,该过程既包含了确定性、又包含了不确定性,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开放的动态系统。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所谓随意机能,就是指相应的外界刺激没有出现,或没有发生较强作用,或在无关刺激不断干扰的情况下,人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努力把它呈现在自己的头脑中。例如,学生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注意听教师讲课,思考问题、回忆事情等等。随意性越强,心理水平就越高。
2.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儿童能够通过概括抽象形成各种级别的概念,并且能够运用它们来进行判断和推理,以掌握各种知识体系。维果斯基指出儿童概括抽象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依靠各种语言符号(主要是词)系统为中介来实现的。随着儿童知识经验的不断增长,词的概括作用不断扩大和深入,儿童的心理机能逐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最后形成了最高级的意识系统。
3.各种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并重新组合,形成高级心理结构。例如,知觉在3岁前的儿童意识系统中起着优势的中心作用。儿童大多是以再认的形式来进行回忆的,而且,这时儿童的思维主要带有直接性。到了学龄前期,儿童的意识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机能系统,记忆处于意识的中心。由于记忆的发展,儿童思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儿童不像先前那样只能分析可见的联系,还能够分析自己的一般表象即概括性的回忆,这种一般表象乃是儿童思维由直接性质向抽象概念过渡的标志。在学龄期,随着言语的发展和交往活动的增加,儿童各个心理机能发生更多的质变。这样,各个心理机能间便重新组合起来形成新质的更高级的意识系统。
总之,无论是随意机能还是概括抽象机能,都是个体在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人类社会文化构建工具的调节逐步发展起来。随意机能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随机性;概括抽象机能既不断变化又不断增长;各种心理机能通过变化、重组、从有序到无序,形成了高级心理结构。因此,个体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
(二)思维与语言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非线性关系

1.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具有并行交叉的关系。维果斯基既不赞成沃尔夫(B.L.Whorf)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也不赞赏皮亚杰(J.Piaget)思维决定语言的理论,它认为思维和言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它们有时犹两条曲线不断交叉, 有时又似两条直线各自前行, 有时汇成一条直线重合而后又分叉”*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0页。,而这种复杂的非线性规律无论在种系发生学还是在个体发生学上都可以体现出来。从种系发展来看, 思维和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 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但有时交叉。在类人猿身上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与语言之间非常接近的一致性, 其思维发展至前语言阶段, 语言发展至前智力阶段而止步。从个体发展来看, 思维与语言也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 在儿童最初的语言发展中存在前智力阶段, 在思维发展中存在前语言阶段。大约在2岁之前二者沿不同路线发展, 彼此独立。大约2岁左右甚至更大一些两条曲线汇合,这表明儿童在与成人较长时间的交互过程中,实现了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的转化以及思维与语言的统一。
2.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的转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外部语言是“儿童最初的语言,是‘对别人’的语言”*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53页。,是社会性的;自我中心语言是“从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过渡的形式,或者说是连接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的中间环节”*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54页。,内部语言 “起源于自我中心语言,它是‘对自己’的语言,是思维与语言相融合,并形成语言思维的阶段,也是语言和思维走向统一的阶段。”*维果斯基:《思维与语言》,第153页。维果斯基认为从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转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原始或自然阶段, 这一阶段与思维发展中的前语言和语言发展中的前智力相一致;第二个阶段为幼稚的心理阶段, 即在某种愿望驱使下通过交往被儿童掌握而变为个体的外部语言阶段;第三阶段为外部符号阶段, 即儿童在活动中把个体的外部语言转变成自我中心语言的阶段; 第四阶段为内部生长阶段,即通过内化转换将外部语言转化为内部语言的阶段。具体的路径是: 外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内部语言。在语言交际活动中, 说话者(表达过程)的语言是由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而听话者 (理解过程)的语言是由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转化。由此可见,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经历了由外→内→外的循环的、动态、非线性的过程。
(三)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是影响“最近发展区”的奇异吸引子
混沌论认为:“动力系统中有三种不同的吸引子(点吸引子、极限环吸引子和奇异吸引子)控制和限制物体的运动程度。前两种吸引子起限制的作用,以便系统的性态呈现出静态的、平衡性特征,而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则使系统偏离而导向不同的性态,它通过诱发系统的活力,使其变为非预设模式,从而创造了不可预测性”*宋宏:《混沌理论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解释力刍议》,《中国外语》2009年第6期。。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个体从现有发展水平发展到潜在发展水平需要跨越一个区域——最近发展区。也就是说,个体的认知发展、学习的进步、知识的获得是通过最近发展区跨越完成的,而跨越最近发展区最好的方法是利用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可以说,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构成了使最近发展区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奇异吸引子。
1.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通常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接触而产生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一出生就进入了人际交往的世界,学习与发展则发生在他们与其他人的交往与互动中。互动的过程是有序和无序的统一,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交往中,学习者以语言为调节工具不断接触到知识和经验,并在教师和同伴的指引下把外在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从社会层面内化为个人的心理层面,从而实现最近发展跨越和认知水平的发展。
2.支架(Scaffolding)本意是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教学支架就是在儿童试图解决超过他们当前知识水平的问题时教师或同伴所给予的支持和指导。提供教学支架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最终能够独立完成任务、顺利通过最近发展区。在操作上,教学支架应该考虑学生的需要:当学生需要较少的帮助时,教师就撤销“支架”,以便学生能独立完成任务。“支架”具有6个基本的功能:即吸引注意力、 简化任务、 维持目标、 确定已完成任务和理想方案间的差距、控制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挫折和演示将执行的理性行动。
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通过综合运动,可以诱发 “最近发展区”系统的活力,使之不断发生变化,变为一个非预设模式,从而使学生的潜能得以发掘和发展,创造出一系列不可预测性。
(四)语言工具在个体认知发展中具有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又称为对初始值敏感性, 是混沌运动的基本特点之一。该概念指的是:“在系统的长期行为中,初始值的微小变化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被扩大,导致轨道发生巨大偏差,以致在空间中的相对距离越来越远”*张公瑾、丁石庆:《混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进展》, 第284页。。在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语言被认为是个体认知发展的核心,它的发展和使用会影响和决定个体认知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因此,可以说语言在个体认知发展系统中具有蝴蝶效应或对初始值的敏感性。
1.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中介工具。语言高度发展的人,可以完成那些文盲所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这是因为人们在学习语言时,不仅仅在学习语词,同时还在学习与这些语词相连的思想。语言使得人们能够向其他人学习,并提供了获得其他人已有知识的途径。语言为学习者提供了认知工具,使得他们能够对世界进行思考并解决问题。因此,语言是个体认识与理解世界的一种中介工具。
2.语言是社会交往与活动的工具。语言在认知发展中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使得儿童能与他人进行交往,从而开始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或观念交换。维果斯基认为,文化在认知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交往是文化得以分享并传递的主要途径。活动这一概念意指儿童在“做”中学,即通过与更有能力的人一起进行有意义活动来学习。活动提供了使对话可能发生的情境,通过活动来进行对话,在个体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个体便得以发展。
3.语言是自我调控与反思的工具。语言在认知发展中还有第三个作用,即为人们提供了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与调控的工具。所有的人都会自言自语,但维果斯基认为,这种“自言自语式”的外在言语是个人言语内化的先兆,是内部言语的开端。个人言语是自我调控、引导个体思维与行为的自我谈话,它从最初自言自语,逐渐被内化,进而发展成为复杂认知技能的基础。
综上,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交流和调控工具,它的发展变化能够引起个体认知发展的巨大变化,这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蝴蝶效应。
五、结语
总之,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对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思维与言语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语言、教育等因素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科学诠释,从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该理论也充分体现了混沌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因为个体心理发展的过程,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以各种逐步掌握的心理工具为中介,在各种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高级心理机能的过程,而该过程是从一个无序到有序、开放的动态系统。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并不对应,它们的关系犹如两条发展曲线是交叉的非线性的;外部语言通过自我中心语言转化为内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社会互动和教学支架是帮助个体跨越最近发展区、发展认知水平、获得知识的奇异吸引子;语言作为认知发展、社会交往和自我调节的中介工具,在个体认知发展中具有蝴蝶效应。
[责任编辑:林舒]
The Interpretation of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 in Perspective of Chaos Theory
LIANG Ai-min CHEN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P.R.China)
The Socio-cultural Theory,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created by Vygotsky,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high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Thi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should be studied under the socio-cultural surroun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os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Socio-cultural Theory there exist some chaotic properties: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is an opening and dynamic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shows mutual dependent and restrictive nonlinearity;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eaching scaffoldings are the strange attractors which can affect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language has butterfly effects on people’s cognitive developments.
the socio-cultural theory; chaos theory; opening and dynamic system; nonlinearity; strange attractor; butterfly effect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CWXJ11)和“话语分析视角下的课堂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0CWXJ13)的阶段性成果。
梁爱民,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22);陈艳,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济南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