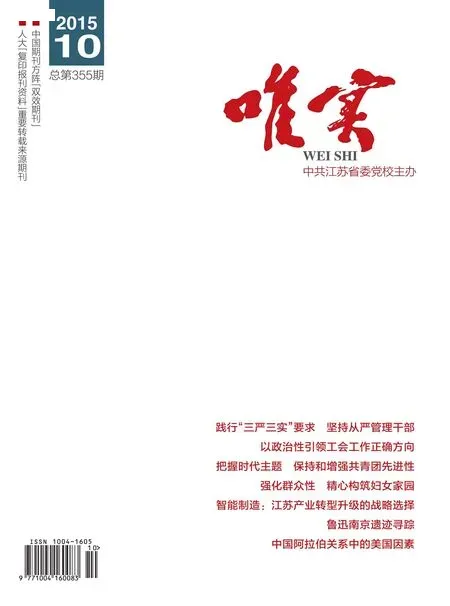那地、那人、那魂——南通先民文化中的海洋元素
庄安正
那地、那人、那魂——南通先民文化中的海洋元素
庄安正
南通南临长江,东濒黄海,系长江顺流而下的泥沙在海流与江流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冲积平原,境内县乡地名蕴含着浓郁的海洋气息。新石器时代的青墩人傍海而居,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早一批居民,随后的居民是各地迁徙于此的“流人”。他们既围堰造田,煮盐为业,又改造盐碱地,谱写了绵延千年的农耕创业史。流人群体的奋斗精神、反抗精神与协作精神,均与大海有着密切关联。
南通位于苏北平原,南临长江,东濒黄海,既与江心的崇明岛以及上海隔江相望,又日夜感受着海风激荡,潮流涨落。南通先民世代傍海而居,形成了具有丰富海洋元素的区域文化。
一
远古时代,南通所在的地理位置一片汪洋。长江从上中游奔腾东下,在此注入大海。由于海流与江流的交互作用,江流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南通这片海域沉淀,日积月累,形成了诸如“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许多沙洲,沙洲不断扩大并互相接近,又与西北的古大陆连接,最终形成了南通这块陆地。南通陆地海拔较低,东西宽、南北窄,呈草鞋状,面积约0.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206公里,所辖海安、如皋、如东、通州、海门与启东六个市区县中,除如皋外,其他五个均面对海洋。位于西北的海安县在南通境内最早成陆。1973年后,考古学者在海安青墩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以及骨镞、贝壳等遗物,表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安青墩一带临海,在此居住的青墩人既在陆地从事狩猎与原始农业,还经常下海捕捞贝类与鱼类,从陆、海两个方面获取食物,显示出与北方裴李岗人与半坡人不同的特色。海安最早成陆后,南通陆地由西北向东南继续推进,大约到唐末宋初,除启东外,南通主体部分连成一片,并大致形成了现在的模样。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称,故文化亦可简称为人化。如果说,南通成陆是一个江海联动,自然造化的过程,与文化无涉,那么自青墩人开始的南通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并给家乡烙下了人的鲜明印记后,即与南通的区域文化相关联了。
鸟瞰现今南通大地,一马平川,除工业发达,环境宜人的城市错落分布外,广大农村则良田万顷,成了江苏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每到金秋时节,但见稻穗沉甸,玉米吐絮,棉花盛开,一派丰收景象。但是,南通成陆后很长时期,脚下这片土地则是环境恶劣,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宋元后归并淮南盐场,包括南通在内的淮南盐场与淮北盐场曾在国内盐业中占重要地位。直到上世纪初,实业家张謇仍如此描绘淮南盐场的景象:“凫雁成群,飞鸣于侧,獐兔纵横,决起于前,终日不见一人。夏夜则见照螃蜞之火,若繁星点而已。”既然是临海盐场,土壤中盐分极高,南通先民只能靠海吃海,“煮盐为业”。但“煮盐业”体力消耗极大,收入极低,加之“灶民”原本往往是农民,不甘受制于此,故在从事盐业同时,又开始了废灶兴垦的尝试。对盐碱地的改造极其艰难,时间长达几百年甚至一千多年。每当临海原先的盐场终于成为了农田,海岸线却往往东移,老盐场以东又出现了大片新的盐场,自然也会开始新的废灶兴垦的尝试。南通海岸线的东移一天不停止,这种废灶兴垦的改造就一天也不会停止。结果南通境内农田面积越来越大,而沿海盐碱地依然不断形成。考察南通成陆以及连接成片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南通盐碱地逐渐改造成农耕地的历史。
南通先民日日临海而居,劳作于斯,他们给家乡取的地名饶有兴味。先就市名、区名、县名而言,“海安”,寄寓大海安宁,造福桑梓之意。“如皋”,“如”,往;“皋”,高地也。告诫一旦发生海难,大祸临头,高地即为逃生之地。“通州”,宣示家乡虽然四面临水,却也四通八达,无远不届。“海门”,此地临海,是拱卫南通的门户。“启东”,蕴含此地乃“启我东疆”,向大海索要疆土而成。至于南通乡村地名,一二十个常用字更是随处可见,镶嵌其间。例如,场(指海边盐场)、灶(指盐场必须设灶煮海水为盐)、港(指临海港汊)、圩(指海滩新成的陆地)、坎(指沿海低洼地)、墩(指沿海躲避海潮所筑土墩)、匡、堤(指沿海新垦土地,以匡、堤为单位计算)、堡、垛(指沿海堆土为堡,防卫海盗侵扰),等等。浏览使用至今的上述地名,发现除蕴含南通先民对生活安宁的期盼与家乡特色的概括外,更含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苏北腹地的盐城与南通相邻,地理环境相仿,且直接以“盐城”命名,独一无二,特色鲜明,给人留下极深印象。南通地名无一处带盐字,但处处尝得海潮咸味,见得海盐如雪,可谓异曲同工,尽得风流。深入分析,上述南通乡村地名形成的年代在时间上有早晚,如将相同年代的乡村地名彼此间用一根曲线串连,会大致勾勒那个年代南通海岸线的实际走向。如再将不同年代南通海岸线的实际走向加以比较,还可发现南通陆地面积不断扩大,海岸线不断东移的大致趋势。
二
南通最早的先民,据考古发现,当数上述新石器时代的青墩人。他们栖身海边,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远古文化。但时至四千年前左右,由于地壳运动等复杂的原因,长江口大片陆地重新被海洋淹没。海潮倒灌时,青墩人不知所终,消失在了历史深处。当海洋逐渐消退,沉没的南通陆地重新浮现时,发现并登上这片陆地的人们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他们是否是原先青墩人的子孙,具有血脉上的承继关系,已不可考且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南通历史上继青墩人之后的又一批先民。这批先民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流人”。他们来自大江南北,四面八方,主体是在各原籍地家贫如洗,无法生存,流浪到南通来谋生的“流民”;也有因种种罪名为当时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经长途押送发配到这块土地上服刑的“流犯”。一个“流”字,写尽了南通先民浪迹天涯的苦难人生。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倒也用不着攀比门第职位的尊卑高下,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搀扶,携手开发这片临海的土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海陵县》记载:“胡豆洲在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这段史料,大致反映了唐代以前,南通先民的主要身份以及他们从事的主要职业。不管这批“流人”原先有无与海洋打交道的生活体验,一旦到南通落脚谋生,他们必须面对海洋,了解海洋禀性,掌握“靠海吃海”的本领。因此,“流人”除下海捕鱼外,很快因地制宜学会了从海水中晒盐、煮盐的技能,并获得了“盐民”或“灶民”的新身份或新称谓。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居住在海滩“滚地龙”、“环筒舍”一类简易住房,不仅经常食不果腹,而且饮食极其粗陋,“菜是卤菜和蟛蜞酱,长了蛆子还吃”。有些人衣不遮体,“夏天不穿裤子,已成为习惯”,“大小便不分场合”。他们皮肤黝黑,体形健壮,性格强悍,“弄不好就要打架”。自然,他们没有条件上学,世代皆文盲。
事实上,这种外来移民涌入南通谋生的情况自唐宋至近代,绵延一千多年没有停止过。如果说,较早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不能一概而论;那么,明清时期,移居南通的先民则主要来自太仓、苏州、常熟、江阴等苏南州县(甚至还有少部分来自距离较远的浙江北部)。移民主要来自苏南的原因为苏南人口在明清时期较其他地方更为密集,苏南封建地主又占有了其中大部分土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亦更为尖锐,故贫穷农民被迫外流现象十分普遍。南通与苏南仅一江之隔,距离不远,临海有那么多空旷的盐碱地,其吸引力之大足以使他们成群渡江,捷足先登。农耕社会,人口从密集地区向稀少地区迁移是一个长久现象。很多苏南农民往往先迁移到崇明岛,以此为跳板北渡海门,然后分散到南通沿海各处,充当“盐民”、“灶民”或改造盐碱地的劳力。由于迁移时间有一千多年,那些较早迁移到南通充当盐民”、“灶民”的先民,在完成了栖息地废灶兴垦的任务后,即安土重迁,以农为本,其身份也逐渐转化为农民。久而久之,他们甚至淡化了对原籍地的思念,开始以南通本地人自居。明清时期那些较晚到南通充当“盐民”、“灶民”的先民,一般必须先栖身沿海新生成的沙地上,从事盐业或废灶兴垦业。沙地环境比较恶劣,他们的生活更为窘迫。较早迁移的先民,往往称其为“沙里人”或“崇明人”。相反,这一时期来自苏南州县的先民,移居时间尚短,比较清晰了解家族根系所在,虽人居长江北,并傍海而居,仍自视为苏南人,而称对方为“江北人”,互示区别。两种先民除迁移南通时间有早晚外,彼此语言不同,也是一个明显的区别。南通地方语言相当复杂,其中唐代较早来到“胡豆洲”的“流人”,因居住地四面环水,与外界隔绝,各种原籍地语言在一个封闭环境中长期交流,最终形成一种即使在苏北亦非常独特的南通方言。而较晚来自苏南州县的先民,保留了属于吴语系的语言,与南通方言形成极大的差别。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原有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不同等因素,两部分先民间会出现各种利益上的“土客之争”,因某个导火线引爆甚至造成局部冲突甚至械斗。但是,两部分先民毕竟共居一块地,同傍海之畔,都属沦落人,何必分早晚!较早迁移到南通的先民,固然对海洋盐业以及改造盐碱地方面的经验掌握较多,而较晚来自苏南州县的先民,也带来了精耕细作的务农技能和耕读文化的传统。双方在嗑嗑碰碰中互相发现了对方的长处,学习和融合逐渐成为了双方相处的主旋律。历史证明,明清时期苏南州县农民移居南通后,南通盐业继续长足发展,农业发展尤其显著,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一批耕读人家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下的近百名进士绝大多数诞生在这一时期。
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孕育一方经济,也塑造了一方魂魄。南通先民的魂魄,同样与海洋密切关联。魂魄,此处特寓意南通先民的精神也。
首先,南通先民身上洋溢着一种矢志不移,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们在与海洋争田,改造自然过程中培育成的。尽管南通现在的环境非常优越,但这块陆地形成初期,却是一块极不适合人居的蛮荒之地,大自然对于南通先民显得特别苛刻。除所处盐碱地不宜务农,废灶兴垦极其艰辛外,南通因临海每年夏秋易受季风袭击,季风与海潮经常交相为灾。查阅南通各县地方志,有关此类灾害的记载不绝于书。以通州、海门为例,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海潮横溢,冲坏堤堰,吕四场灶民被溺死三万余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海门遭季风与海潮袭击,县治危殆,县令被迫率百姓转移,一度迁入通州金沙。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因遭遇海啸,辖区大片土地坍陷,被迫废县为乡,迁入通州兴仁。一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经奏请清政府同意,海门借通州一块沙地得以重设,并延续至今。时至上世纪初,实业家张謇为发展棉纺织工业,在通州、如皋(今如东)、海门境内建立盐垦公司围海造田,种植棉花。因季风与海潮施暴,公司多次遭遇海堤损坏、田毁人亡的惨剧。事实上,南通境内每个以场、灶、墩等命名的乡村,初期都有过类似的历史。但是,南通先民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每次灾后都重修堤岸,收拾旧山河。查阅南通各县地方志,有关南通先民抵御海潮,保卫家园的记载同样不绝于书。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南通先民在范仲淹领导下,修筑“范公堤”。嗣后,庆历年间(1041~1048年),修筑“狄(遵礼)公堤”;至和年间(1054~1055年),修筑“沈(起)公堤”;明隆庆三年(1569年),修筑“包(柽芳)公堤”。至于近代在张謇领导下,南通先民修筑的盐垦公司堤岸工程量,更超过了以往的总和。总之,南通先民是在与海洋争田的长期较量中,塑造了越挫越坚的拼搏精神。
其次,南通先民身上充满着不畏强暴、抵御侵略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们在与自海上来犯的异族抗争中培育成的。南通因地处长江、黄海交汇的海防前沿,历史上屡遭异族海上入侵。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南通系江苏重灾区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自吴淞口由海上入长江,犯太仓,逼近南通,南通震动。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又自吴淞口入长江,乘潮于南通狼山乘陆,烧杀掳掠,屠杀老幼数千人。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自海上在如皋掘港登陆,犯丁捻折向南侵入平潮,一路烧杀掳掠,再次逼近南通,南通戒严。晚清以来,南通又受英军严重威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鸦片战争第三阶段中,英军自吴淞口入长江犯南京,军舰经过南通时炮口对准狼山准备轰击,南通戒严,唯因英军急于兵临南京城下,南通躲过了屠城一劫。光绪二十一年春(1895年),在甲午战争后期,日军欲犯苏北沿海,南通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在与海洋争田中表现出顽强拼搏精神的南通先民,清醒认识到南通最大的外患来自海上,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旦遭遇异族自海上来犯,绝对奋不顾身,保卫家园。嘉靖年间南通抗倭英雄曹顶,即是突出一例。曹顶原本是余西场一极普通“灶民”,面对倭寇来犯,毅然应募入伍。每次交战,战功卓著。终因一次战斗中奋勇追敌,马蹶堑壕,为倭寇所害,成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一个罕见的草根英雄,南通先民为之树碑建祠,长久纪念。近代张謇在曹公祠内书挽联两幅:“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北郭留名单家店,南山增气曹公坟”,对曹顶英勇业绩给予了极高评价。光绪二十一年春,日军欲犯苏北沿海,南通沿海到处组织“民团”、“民军”,彼此互相激励:“死人者人之所必有也……若能执干戈以卫乡里,则是堂堂丈夫,可谓重于泰山矣。”可见布衣曹顶事迹,在南通世代相传,融入了南通先民的血脉,一个曹顶化为了千百个曹顶。
再次,南通先民身上还反映出一种团结互助,友好相处的协作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们在与海洋争田以及抵御异族侵略过程中培育成的。南通历史上除最早的青墩人算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外,不同时期的先民都来自四面八方,先民的主体是移民,南通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虽然各自身份与离开原籍地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先民肯定都是当时社会的草根一族,且为各自家乡所不容,背井离乡来到南通傍海而居的。因此,尽管他们有籍贯、移居早晚、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但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自从来到南通这块陆地那一刻,先民已各自将他们善良、同情、互助等共同的草根特性带到了南通。这是帮助他们解决彼此冲突,进而团结互助,友好相处的族群原因。此外,南通蛮荒之地的环境,异族自海上侵略的威胁,也明白无误地告诫南通先民,如果热衷于彼此冲突,结果会两败俱伤,大大削弱他们挑战恶劣环境与抵御异族自海上侵略的力量,只有团结互助,友好相处,彼此才有可能在南通立足,并进而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帮助他们培育协作精神的现实原因。千百年来,南通先民被称为“一团和气”,最讲义气,信奉“通州好,礼俗海滨饶”、“邻居好,赛金宝”,等等,成为南通世代相传的乡风乡俗。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