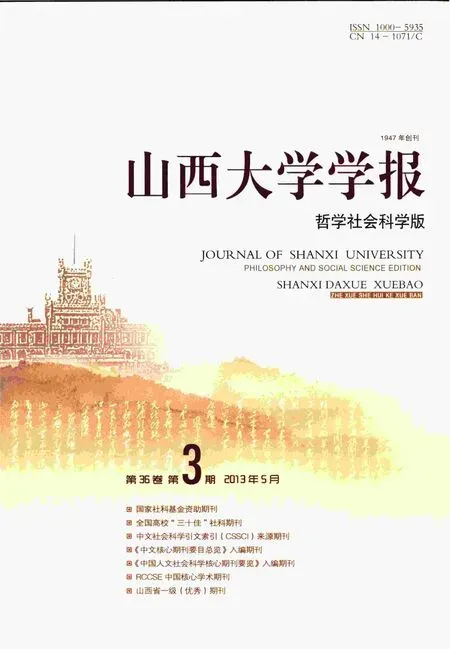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变迁及作用
薛剑文
(1.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2.青岛大学 新闻中心,山东青岛266071)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重要内容的慈善救济事业,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事业更是成为学者们研究关注的焦点,慈善救济史研究也取得了新突破。纵观古代的慈善救济事业,就其主办者来说,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慈善救济,二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慈善救济。学术界往往更加侧重于政府慈善救济行为的研究,而忽略了民间慈善救济的作用。实际上,古代民间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兴盛,有效弥补了官方救助的不足,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梳理出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脉络、主要特征及其发挥的社会作用。
一 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一直有民间自救的传统,乐善好施、敬老助孤、济困扶贫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早在原始社会,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已出现了互助的习惯,如鄂伦春族在狩猎后,一般采取平均分配猎物的办法,凡“参加的人,不分男女,每人一分。对于虽未参加劳动,但为鲜寡孤独或有其他困难的户,也分给一些皮张和肉类”。[1]285这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就是后世慈善救济的最初萌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个人性质的慈善救济,不过此时慈善救济更多的是在生产和生活中结成的互助共济行为,属于临时行为,并未形成专门的慈善救助组织。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始自汉唐时期。
(一)汉唐时期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初步形成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慈善思想中的“福报”、“修福”的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活动开始活跃,佛教寺院凭借着雄厚的寺院经济,开展了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等慈善救济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济事业进一步发展,至唐代时达到鼎盛。唐代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为慈善事业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唐代,开始在寺院内建立起有固定场所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容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的慈善机构。[2]悲田养病坊在武则天统治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不但在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且设置机构派出官员参与管理活动。唐玄宗时继续给予悲田养病坊经费补贴。唐武宗时“会昌废佛”,毁佛寺,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原先依赖佛教根基存在的悲田养病坊也受到连累,陷入困境。即使如此,悲田养病坊也没有被彻底废止,在长安、洛阳及地方各州道的佛寺中仍然广设。唐末五代,北方地区又出现了一种带有佛教色彩的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社邑,它多由僧人和民间的佛教信徒自愿结合而设,社邑经常开展一些诸如互助丧葬、嫁娶等慈善活动。盛唐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民间私人赈济活动也开始涌现。
(二)宋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壮大
宋代官办慈善救济事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先后出现了居养院、安济坊、婴儿局、慈幼局、举子仓、举子田、安养院、漏泽圆、慈济局等机构,建立了庞大慈善救济体系,“其计划之详尽、规模之宏大、设施之齐全、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2]
同时,宋代民间慈善救济也趋于活跃。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远远超越了前代。从形式上看,宋代民间慈善活动包括赈饥救荒、济贫恤穷、扶弱解困、公益事业等不同形式;从结构上看,包括宗亲慈善、社区慈善、周朋恤旧、民间互助等不同内容;从主体上看,包括士人官员、乡绅富民、佛道群体、妇女群体等。慈善活动内容涉及赈粜施粥、施医赠药、济婚助丧、养老慈幼、助学济士、筑桥修路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3]267
宋代民间慈善活动一大特点是宗族性的慈善救济比较活跃,出现了带有宗族性的慈善组织——义庄(义田),这使得原本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中国最早的义庄是范仲淹在苏州吴县、长州设立的“范氏义庄”,该义庄对周恤宗亲,凝聚族人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其救助范围主要限于宗族成员,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作用。继范仲淹创立义庄之后,士绅们纷纷仿效,一时义庄遍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宋代就有义庄义田79个。[3]163直到民国期间,仍然保留着。除宗族性慈善组织义庄、义田外,宋代有些地方还建立了资助贫困学子和士人的义学庄田,如朱熹的考亭书院,四明地方士人的四明义田等。唐宋时期还建立了一些有影响的民间互助组织,如敦煌私社和新安之社,对其成员进行生活周济、疾病治疗、婚丧嫁娶等救济活动。士人之间也出现了互助组织,如万桂社是建立于福建等地的士人间的经济互助组织、黑金社则是白鹿洞书院学生间的经济互助组织。宋代个人有组织的慈善活动也比较活跃,如富弼青州赈济流民、刘宰金坛三赈饥民、黄震改革慈幼之政、真德秀广办慈善等等。
宋代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虽趋于活跃,但多属民间自发性的、松散的个体行为,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制度约束,因此,民间慈善行为只是官办慈善事业的补充而已。
(三)明清时期民间的慈善救济事业日臻完善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办及民间的慈善救济事业都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此时民间的慈善事业无论是在组织的数量上,还是功能、经费、参与的社会阶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和影响。[4]不仅个别善人的慈善活动比较活跃,而且各类民间社会力量举办的有组织的慈善机构日益增多,民间社会慈善出现了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趋向。尤其是到了清代,各类慈善组织团体数量急剧增加,功能渐趋齐全,救助内容多样,经费相对充裕,活动频繁,参与的社会阶层包括地方乡绅、工商业者、百姓等各层次人群,民间慈善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官督民办慈善救济事业兴盛。普济堂和育婴堂是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官督民办慈善组织。普济堂初创时期多系民间力量筹资兴办,依赖地方绅士、商贾的鼎力支持。后来,随着其救济功效远远超出官办的养济院,且无需政府出资,才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普济堂因此盛行一时。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统计,有清一代,河南省109个州县共建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01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131所普济堂。[5]500而且各州县的普济堂“纤毫不需公顷”,完全是用民间资金建立。仅仅一、两年时间,河南省官绅士商百姓捐银78 912两1钱、义田11 164亩、麦豆谷23 912石;山东省官绅士商百姓捐银84 246两7钱、义田15 238亩、麦米谷4122石余。[5]502又如嘉庆年间所建的杭州的普济堂,每年收入超过一万两白银,“列号舍二百五十间”。[6]至乾隆中后期,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普济堂遂逐步由纯粹的民间慈善组织变为官督民办、官民合办的慈善组织。
明清时期的育婴事业比较发达,育婴堂的数量很多,遍布全国各地。据梁其姿先生统计,全国育婴堂类共973个,仅1850年以前建立的就有579个。[7]328至清代,育婴堂的普及率仅次于官办的养济院,在民间慈善机构中位居第一。[7]256其中以江南地区的育婴慈善事业最为突出,育婴机构扩展至县级城市,甚至延伸到乡村一级。形成由保婴局、留婴堂、接婴所、育婴堂等构成的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至康熙末年,全国共有育婴堂96所,江、浙两省为50所;两省中属江南地区的为28所,占全国总数的29%。[8]福建在清代设育婴堂达79所。[9]有些育婴堂规模还相当可观,比如苏州育婴堂,建筑宏伟,仅雇佣的乳母就有300余人。所需经费,皆“士大夫助之”。[6]至乾隆年间江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不低于62.5%。[8]清朝中后期,育婴堂逐渐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演变成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
混合臂高空作业车工作斗模糊PID调平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7。调平控制系统在运行中,不断检测e和ec,根据模糊控制原理对3个参数在线修改以满足不同e和ec时对控制参数的要求,从而使得混合臂高空作业车工作斗在满足该调平控制系统要求的精度下平稳,快速的调平。
第二,会馆的兴起。会馆是明清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依一定的地缘和业缘关系联结而成,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为宗旨,在对同乡、同业者的救助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现知最早的会馆为明朝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建立的芜湖会馆,入清以后,由于流官制度的实行及经济的繁荣,会馆更加兴盛,清中叶以后,主要市镇基本上已是会馆林立了。[10]13许多会馆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同乡、同业者的基本生活救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与宗族组织类似的作用,如康熙年间山、陕商人在汉口创立的“山陕会馆”,其宗旨即为“结合团体,维持公益”,乾隆年间设立的“咸宁会馆”,“以联络同乡,维持公益为宗旨”。[11]从初创时勒碑的条程规章及其刊印的征信录等资料来看,会馆举办的慈善活动主要有助学、助丧、施医、济贫等四个方面。救助内容包括施棺助瘗、恤孤赈穷、延医给药、发给回乡川资、购置义所、兴办义学等各个方面。
其三,宗族义庄的兴盛。自北宋范仲淹首设义庄之后,各地设义庄置族田渐成风气。据统计,明代大约设置了200个,清代设置的义庄更是数以千计。仅以苏州为例,宋代设有4个义庄,明代有8个,清代高达185个。[12]明清义庄的发展,表现在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许多义庄所置田亩面积累年不断增多。如著名的范氏义庄,起初仅置田1 000余亩,而至清末已达到5 300余亩。其他义庄的土地规模百余亩至千余亩不等,除了灾荒的救济外,也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济贫、恤病、助婚丧、养老、劝学、救急等项内容。值得指出的是,清嘉、道以降,一些宗族义庄的救助对象不再局限于族人,出现了面向社会的救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州的丰豫义庄。作为一种带宗族性质的慈善机构,义庄对救助贫病疾困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四,善堂、善会的盛行。宋明以降,儒、释、道三教渐趋合流,善书广为流布。受此影响,明朝中后期以后,各类民间社会力量发起的有组织的慈善机构日渐增多。这类慈善组织的滥觞就是万历十八年(1590)建立的同善会,此后,类似的善堂善会组织纷纷兴起,并蔚然成风。入清后,特别乾隆中后期以来,善会、善堂的种类日益增多,数量日益扩大,分布和活动范围日广,其中有对患者施医给药的医药局,有对死者施棺代葬的施棺会、义冢,有打捞和赈济落水者的救生局,有笃疾孤老的普济堂、安济堂,有收容流民的栖流所,有抚恤节烈妇女的儒寡会、清节堂,有收养遗弃婴孩的育婴堂、恤孤局、留婴社,还有恤及生灵万物的放生局、惜字会等等。这些慈善组织多由民间社会力量独立主持和运作,管理也日趋规范,设有专门的规程条约,而且大多数组织还定期刊刻征信录,记录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以及运营状况。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育婴组织先后成立了至少973个,普济堂399个,清节堂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13]江南地区善堂善会组织更为发达,在清代江南各县设立善堂少则十多个,多至五六十,并开始从大中城市向市镇普及,救助面延伸到广大乡村地区。[14]众多善会、善堂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亦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在苏州碑刻中即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非有诸善举绵延不绝,阴为补救,曷由开悔祸之机,以挽回气数?”[15]
二 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同官方的慈善救济事业相比,中国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相对滞后。与西方慈善救济不同,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很早就介入了慈善救济事务,承担起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政府的慈善救济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主流,即使是在民间慈善事业相对活跃的明清时期,民间慈善救济活动也只是起到补官赈之不足的作用,其影响远未能超越政府。而在西方,民间和宗教的慈善救济远早于政府的救济,其影响也较政府大得多。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有很大的排斥性。在早期儒家传统中就已经有了“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提供者的想法”,所谓“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责令官司收养,可谓仁政矣”。[7]32在儒家看来,个人的慈善救济活动与政府的仁政是相悖的。因为个人慈善活动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政府的不“仁”,这正违背了“天地之大无弃物,王政之大无弃民”的“仁政”原则。由此导致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这就决定了民间慈善组织,尤其是大规模慈善组织的形成非常困难。即使在国家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的时候,往往也是一鼓励就导致官僚化,民间慈善救济又以“官督民办”的形式绕回到了“国家救助”的模式上来。二是中国自秦以来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皇权至高无上是历代统治者恪守的法则,他们均不愿看到一个超乎其外的在国家事务中发生作用的力量,对皇权的抗衡通常只是服从前提下一种牵制或对抗。[11]而在西方,世俗王权之上尚有教权,教会的权力曾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尤其是与社会救助相关的事务,一直是主导者,直到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才逐渐得以改变。
第二,政治性与民间性共存。在中国特定体制下,民间慈善救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是民间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保持着极紧密的联系。传统民间慈善活动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许或认可才能进行,或是充当政府的代言人,受其委托实施慈善救济,或是需要政府支持才得以发展。二是从慈善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看,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往往是当时的士人、官员、乡绅富商、已取得出仕资格者,他们大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当见到社会秩序混乱、人心道德败坏、民不聊生时,总是身先士卒、匡世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正是他们政治人的角色才需要适当的媒介来发抒其政治抱负,民间慈善组织因之成为其政治性策略工具。[16]三是从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行为及价值取向来看,它们完全担当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政治性责任,如灾荒赈济、济贫养孤、养老慈幼、乡约教化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承担和履行着政府的部分职能。正鉴于此,即使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进一步加强的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也能容忍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第三,具有很强的宗族性、地域性和业缘性。依血缘联结而成的家庭、宗族、姻亲,以地缘联结而成的邻里乡党,依业缘联结而成的行业关系是中国古代慈善救济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大多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以地方精英分子为主要实施者的民间慈善救济深受儒家思想中“施由亲始”观念的影响,始终无法超越自我-家庭-国家的框架。慈善始于家就成了慈善救济行为的最高法则,这也就使古代慈善救济事业打上了深深的宗族烙印,如范仲淹的“义田”,宋熹的“社仓”都是为族人而设,对族外之人一般不予赈济。另外民间慈善救济活动深受地域的限制,一般由当地人组织领导,在当地筹集善款,最终也以当地人为施济对象。跨流域、跨地区的慈善活动极其罕见。依业缘而结成的会馆、公所对同乡、同业者的救助也深受地域和行业关系的限制。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的民间慈善救济具有很强的内敛性和封闭性。
三 古代民间慈善救济的社会作用和影响
就政府社会救济与民间慈善救济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政府的社会救济始终是社会救助的主体,但古代名目繁多、规模各异、形式多样的民间社会救济毕竟对国家社会救济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育,其意义不容低估。
(一)补官方救济之不足
从中国古代社会社会救济的整体情况看,政府性的社会救济虽然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政府性的社会救济也有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在王朝更迭或是社会动荡时期,政府性社会救助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无法进行,即使在社会升平稳定时期,由于灾荒、财政压力以及胥吏腐败等问题也使得官方救济力不从心。以宋朝乾道五年(1169)饶州赈济为例,当年朝廷拨付义仓米6800余硕,“不了一月赈粜之数”。又从上供米中拨付10 000硕,仍微不足济。而同时从上户①在宋代第一等户大致是占有土地三、四顷到几十顷、上百顷的大地主,第二、三等户是土地较少的中、小地主,三等户中也有自耕农。上三等户习惯上称为上户。处“劝谕”所得即为196 000余硕。[3]276可见民间救助已经成为这次赈济的主要经费来源。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极为频繁,几乎是无年不荒、无年不灾,民间慈善救济在赈灾济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宣德末年,江西普遍出现饥荒,“义民鲁希恭及新淦郑宗鲁各出粟二千石助赈济,吉水胡有初千五百石”。[18]卷5清乾隆七年,扬州府属淫雨成涝,官府紧急劝募在扬州的盐商捐钱助赈,歙县人汪应庚一次性捐银六万两,使灾民受惠。
从救济范围上看,以国家政府力量创建的慈善救济组织一般都设立在城镇,其救济活动也多集中于此,而对广大的乡村救济则涉及较少。以士绅阶层为主的社会力量举办的各慈善救济组织,多是建立在乡村,可以有效地弥补官方救济之不足,从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发挥慈善救济的社会作用。如宋代的刘宰在发生灾荒之际三次大规模赈济灾民,最多时日就食者达15 000人。[3]225又如宋人李发在乾道四年(1168)大灾荒时,“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万人。明年,流通未复,而荒政已罢,民愈困敝,数百里间,扶老携幼,挚釜束薪,而以李为归者,其众又倍于前”。[19]卷3据此推算,最高日食人数可多达七八万人之众,远超刘宰粥局救济人数。至明清时期,赈灾甚至不假胥吏之手,而由当时素有威望的士绅来总理赈务,比如,明崇祯三年(1630),江浙等地发生饥荒,在嘉善,民间的灾荒赈济就由正在家乡的著名绅士陈龙正主持,他要求地方富室必须自救其地方贫民,嘉善共有20个区,他就组织乡民,每区推选一名深孚众望的乡绅主持救荒活动。清代道光三年(1823)江南水灾,江苏的大吏就明确指示,“举公正绅董,自为经理,不假吏胥之手”。[6]
此外,与官府所行救济措施相比,民间慈善更为灵活深入,士绅多生活于民间,较为了解民间的疾苦,也更清楚灾民的实际需要,因此能根据实际需要施行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救济,在赈灾救荒、收养弃孩、医疗救济、掩埋尸体、照顾产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太仓的闻少谷等六人见当时“城乡辄有抛弃婴儿者”,就各出资六百千文,开设收婴局,共收婴三百余名,到第二年麦收时,送还其父母,“并给以钱”。常熟的绅民根据灾后的实际需要,将原来施棺掩埋的宁善堂扩建为“夏施药,冬施衣,平时施棺”等多种功能的凝善堂。[6]这样民间慈善对于官方救济而言,有效弥补了官赈之不足,其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乡村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二)推动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从古代民间慈善救济发展历程看,这是一个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借助慈善救济活动扩大其影响进而广泛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民间慈善救济事业正是士绅大显身手的领域,士绅等地方精英分子对地方权力的接管,往往是从接管地方赈济事务开始的。如清初的善堂组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顺理成章地接管了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权力:近代基督教会势力的扩展,也是从慈善事务开始的。[3]279士绅不仅是慈善救济活动资金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慈善救济活动具体事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处于基层社会的顶端,熟悉下层民众的要求,并有效地凝聚和控制着下层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中介。士绅通过对慈善救济事务的参与扩大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或巩固士绅在国家和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如这些人通过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形成了覆盖面极广、关系复杂、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并由此控制基层社会,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郝秉键将其归结为两大“辐射区”,即“家庭辐射区”和“社会辐射区”。“在家庭辐射区内,以血缘、姻戚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宗族、姻戚成员;以人身依附关系连接着主子和奴才们;以契约关系为纽带连接着东家和清客们。在社会辐射区内,以师生、同学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宗师、门生、同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连接着同乡绅士;以互利关系为纽带,连接着绅士与州县官、幕友、吏胥、保甲、流氓等。而这些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又纵横交错,多向联络,形成一系列‘亚关系’,从而使绅权权利结构更加复杂化。”[20]
虽然依托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发展起来的地方精英在地方事务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可能会分享官方的部分权力,但这并没有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因为作为民间慈善事业领导者的士绅首先必须被认为是符合官方道德规范的“义民”,能遵循儒家思想原则。其次又能为民间社会所接受,能够为民间社会谋利益,或能够为稳定社会秩序作贡献。这样,他活动的空间才能够被认可或得以扩展。实际上,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权力来源,士绅总是将地方社会纳入国家权力的正统规范,士绅在举办慈善事业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政府的器重以便在地方社会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组织从来都是持警惕态度,唯独对地方的慈善救济持支持态度的原因,这也使得民间慈善救济成为各种地方精英和各类民间组织扩大其影响,进而取得地方社会控制权力的主要途径。
在具体的实践中,尤其是明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国家权力不断扩张,但并未割断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社会救济事业的传统。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去而已,而非以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来压缩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6]实际上,这“并非是官、民之间的分立或对峙,而是官民之间的合作,系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力量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共同起作用的领域”。[21]224到了清代后期,官办民助、官民合办性质的慈善救济组织已经占据很大份额,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区赈济行为在江南越来越普遍,出现了“邻里乡里模式;村社模式;以‘庄’为单位的赈济模式;乡、都区模式;图(里)模式”以及以圩和市镇等为基础的赈济模式等,但这些模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地方事务完全是脱离官方的社会管理行为,而“实际上是响应官府的号召代为管理地方事务”。[22]这种官方和民间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官民合力”模式,对今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杨 堃.原始社会发展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J].史学月刊,2000(3):95-102.
[3]张 文.宋代民间慈善活动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谢忠强,李 云.试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J].延边大学学报,2010(2):126-130.
[5][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伍 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余新忠.遗失的传统:明清民间社会救济[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08 - 6 - 2/HTML_YY91K7R9S07O_7.html.
[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中国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8]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J].清史研究,2000(1):75-85.
[9]徐文彬.清代福建育婴事业试探[J].福建史志,2006(4):36-40.
[10]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M].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66.
[11]周 荣.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探[M]//张建民.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二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2]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J].中国史研究,1995(3):56-68.
[13]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J].社会学研究,1998(1):86-99.
[14]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J].学习与探索,2007(1):232-236.
[15]唐力行,王国平.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序[M]//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
[16]靳环宇.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J].中州学刊,2006(2):111-114.
[17]赵 倩.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历程与特点[J].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7(1):50-52.
[18]陈龙正.救荒策会[M].崇祯十五年刊本.
[19](宋)董 煟.救荒活民书[M].丛书集成本.
[20]郝秉键.试论绅权[J].清史研究,1997(2):22-35.
[21]马 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2]吴 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1(4):18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