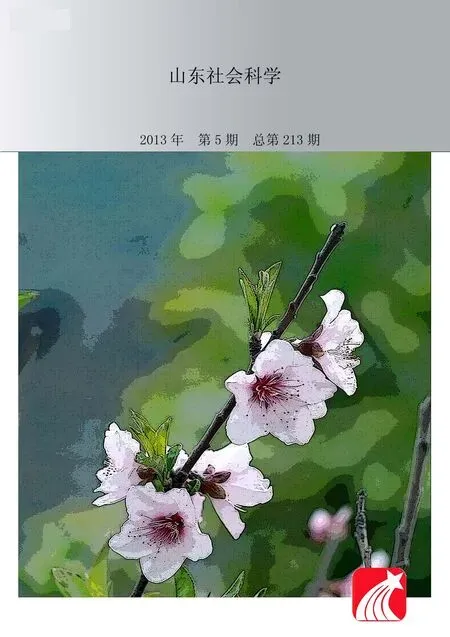语言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国家形象
——基于主体认知的分析视角
哈嘉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北京 100029)
当语言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时,其所产生的功能价值往往会超越语言本身。在一国内部使用共同的语言,能够使整个国族在心理上形成认同感,从而达到凝聚国族内部意志,巩固国族民族性的重要作用。将本国族语言在不同国族之间传播,通过对他国公众的心理认知施加影响,从而减少彼此间的误解与偏见,增进不同国族之间的善意与好感,最终在国际上构建起本国的良好形象,也是语言能够超越语言价值,实现国家利益的功能所在。对外构建国家形象,谋求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从国家形象认知者的主观认知这一微观层面入手,探求国家形象的形成,是有的放矢制定具体策略的重要基础。
一、主体认知与国家形象的形成
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其中牵涉到一国自身的真实存在、现实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等所提供的认知资源,也牵涉到由于认知者自身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尽相同的认知视角。但国家形象的最终形成仍取决于认知主体自身的主观态度与评价。考察与国家形象相关的理论,我们可以获得认知者的主观意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支新流派:“认知—心理(perceptual-psychological或congnitive-psychological)学派”。不同于以往以关注物质力量、物质结构以及由前两者外化而产生的制度和规范,“认知—心理学派”关注的是人的认识和形象以及和这两者有关的各种变量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该学派较早研究国家形象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开创者当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他在《形象:社会与生活中的知识》(The Images: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1956)一书中将形象定义为:“决定着人们行为的对世界的主观认识”。而他在《国家形象与国际体系》(National Ima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一文中的论述最为经典。在这篇文章中,博尔丁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些人的决策足以影响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对于真实情形的反应,而是对于他们对真实情形的想象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脑海里对世界的认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情况……事实是‘国家形象’基本上是一个谎言。或者至少是从某个角度对事实的歪曲,它可能导致易于为野蛮和罪恶来辩护……”①Kenneth Ewart Boulding.1959.“National Ima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3,p120.。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生成、流变与传播。考察比较文学形象学给出的关于“形象”的定义,我们发现这一学科研究的线索并不在于“形象”本身,而是“形象”背后的东西。因为“形象”只是主体主观心理活动所带来的结果。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一文中认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在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现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①[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2页。而布吕奈尔等在《形象与人民心理学》中认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②[法]布吕奈尔等:《形象与人民心理学》,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这些都是在强调“形象”是一种主观的产物,文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描述反映的是认识主体通过想象制造出来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与客观的历史现实并不相符。
纵观国内研究者对于国家形象的界定,虽然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侧重不同,因此所给出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但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可国家形象是认知者对一国客观真实存在的主观认知、态度与评价。③如刘继南认为:“国家形象是指一国在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综合评价和印象,主要体现在别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刘小燕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汤光鸿对国家形象的定义是:“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汤光鸿:《论国家形象》,《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杨伟芬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等。因此,在对外传播领域,研究什么样的传播方式能够对主体的主观认知施加影响并加以引导,是一国对外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根据。
二、语言的国际传播对国家形象形成的认知影响作用
(一)语言的国际传播与群际间深度接触:突破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概括。为了简化世界,我们概括出:英国人保守;美国人开朗……”④[美]戴维·迈尔斯:《迈尔斯心理学》,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影响人的认知过程,人们往往会依据自己原有的刻板印象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判断并决定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认知现象也体现于不同国族之间的相互认知上,由于缺乏直接接触的条件,不同国族公众之间的认知大多依据原有刻板印象,而作为一般大众的世俗刻板印象,常常是来自于诸如大众传播媒介或人们口耳相传的间接信息源,并非得自直接经验。而负面的刻板印象则形成偏见,是跨文化交流的重大障碍。在对外自我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中,通过影响对方的心理认知,从而突破对本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形成公正的态度与评价,是自我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心理学上,奥波特(Allport)于1954年提出的“群际接触假说”(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被认为是突破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奥波特(Allport)提出的“群际接触假说”的主要内容是:减少群际偏见的主要方式是与外群体在最佳条件下进行接触。群际接触对于消除刻板印象的认知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获取新的信息方面。“假说”认为,刻板印象和态度的形成源于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接触情境为获得新的信息,澄清感知错误,以及再学习提供了机会。JohnF.Dovidio等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群际接触理论:过去、现状和未来》中提到“(通过群际接触)增多对他者的了解,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起到减少偏见的作用。首先,只有拥有关于他者更多的信息,人们才有可能以更为个性化和私人化的方式去看待他者,当有机会与其他群体成员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时,群际之间的接触会使原来的刻板印象逐渐减弱。第二,更多的对他者的了解可以减少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时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增进与其他群体成员的接触并减少接触时的不适感。第三,就更好地提供历史背景和增加对异文化敏感度而言,对他者更多的了解可以提升跨文化理解,并可能通过对以往不公正评价的再认知来降低偏见。”⑤John F.Dovidio 等 Intergroup contact:The Past,Present,and the Future,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20036:5.
今天,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各国开放程度空前提升,以旅游、贸易、体育、艺术、教育等形式展开的国际公众交往逐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各国公众直接获取对象国信息的机会。其中,语言的国际传播由于交往的内容为学习对方语言,因此在群际接触的层次上有别于其他国际公众交往形式,语言的国际传播是更深层次的一种交往形式。由于群际间接触层次的不同,决定了通过群际接触所获取对方信息也有表层、深层的区别。表层信息的获取相对容易,在短时间内可通过纯粹接触完成,但表层信息往往只停留在对方的物质文化层面,难以触及到对方文化的深层内容。深层信息包括对对方历史、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等的了解,涉及对方精神文化层面,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破除以往刻板印象、重新认识对方形象的有价值的新信息。而对对方精神文化的获取不仅在时间上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还要能够深入到对方文化的内部。因为“从外部来理解文化是极其困难的。习惯和信仰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孤立地理解。要依据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观来研究文化,……人类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因此来自某一文化的人经常会发现难以设身处地地去理解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观念或行为”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阎书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语言的国际传播在获取对方深层信息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由于语言的起源、形成、发展及使用都紧密依存于社会,对于语言来说,社会与文化不仅是一个存在的环境,还渗透到了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文化属性是可以通过一些语言本体要素,如词汇、语法、语音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学习对方语言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对方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其次,语言学习为群际交往提供了必要的交流媒介,掌握对方语言对于群际间的接触频次及交流质量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使用语言这一交流媒介与对方群体深度接触,是培养善意、建立好感,降低由于群际间偏差而产生负面刻板印象重要渠道。笔者曾对来华留学生的中国形象认知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在来华前后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方面,对来华前的负面刻板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甚至消除。②哈嘉莹:《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自我构建》,《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二)语言的国际传播与群际间态度的改善:通过学习语言增进彼此认同
Gardner提出的二语习得社会教育模式主要聚焦于有关二语习得的四个因素,即:社会环境、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语言学习环境和二语习得所取得的结果。其中把二语习得取得的结果分为语言方面的和非语言方面的。③G ardner,R.C.,Soci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H.Giles and R.St.Clair(eds),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Oxford:Basil Blackwell.非语言方面的结果包括学习者通过二语学习而产生的使用该种语言的意愿,整体上对语言的兴趣,通过语言学习对其他文化群体的态度改善,对使用其他语言的群体形成更为赞赏的态度等。根据这一“二语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R.C.Gardner和R.N.Lalonde在《二语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使用LISREL因果模式的调查研究》中对生活在加拿大单语英语城的140名大学生学习法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二语习得过程的18个变量,对学习结果的调查中有“对法裔加拿大人的态度”(AFC)一项,“这项测量包括对法裔加拿大人的五个正面评价的词汇选项和五个负面评价的词汇选项,所获高分(maximum=70)反应出的是正面的态度(α =0.79)”④R.C.Gardner and R.N.Lalonde,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n Investigation Using Lisrel Causal Modeling,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2,1 -15.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对于群际之间态度改善的研究还有Stephen C.Wright在1995年的文章《教室中的身份与语言:对遗产语言、二语教育在提升个人自尊和集体自尊中影响的调查》,分别对居住于次北极地区的因纽特儿童,白人儿童,白人儿童和因纽特儿童的混合群体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接受了自己本族遗产语言教育的群体在个人自尊方面会得到逐渐提升,而接受二语教育的儿童群体则没有这样的表现。在因纽特人中,因纽特语言教育与对因纽特自群体的积极尊重态度提升有直接的联系,而在因纽特人中进行英语、法语的二语教育则与对白人外群体的好感有直接的联系。⑤Stephen C.Wright:Identity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Heritage Versus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o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elf- Esteem,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5,Vol.87,No.2,241 -252Wrigh和Tropp在2005年发表了《语言与群际接触:双语教育对儿童群际态度影响的调查研究》,将课堂双语教育和英语单语教育作了对比,检验了这样的假说,即:在课堂上教授少数族裔的语言(西班牙语)有利于构建不同族群之间积极接触的条件。使得只讲英语的白人儿童:(1)能够感觉到他们与拉丁族裔儿童有更多的相似性;(2)更愿意与拉丁裔儿童发展友谊;(3)对拉丁族裔儿童持有更为友善的态度。通过研究,Wrigh和Tropp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语言不仅仅是群际差异的区别性标志,而且也是能够用来消除/增强身份上的不平等,提升/削弱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的有力工具。”①Stephen C.Wright& LindaR.Tropp:Language and Intergroup Contact: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Bilingual Instruction on Children’s Intergroup Attitudes,Group Processes&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5Vol8(3)309 –328.
这说明语言在不同族群之间的传播在改善群际关系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模式将直接影响正面群际接触的认知条件。语言传播对群际关系改善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是心理学家Tajfel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Tajfel采用最简群体实验(Minimail-Groupparadigm),创造了一个微型“群体世界”。他先请被测试者对一张卡片进行“点估计”的作业,并以此为理由随机地将被测试者分为两组——高估组与低估组。接着要求被测试者进行资源分配的工作。结果显示,这些被测试者虽然与同组成员互不相识而且从未有过谋面和实际的互动,但还是分配给自己所在组别成员较多的资源。最简群体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因此,Tajfel等人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会对自己所在的群体产生认同,进而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偏见(out-group derogation)。在此基础上,Turner于1985年进一步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对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Turner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因此在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区分出内群体和外群体。Tajfel与Turner在1986年的经典论文《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中分析了群际差异与社会分类之间的关系:“对分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这种感知,足以引发有利于内群体(凝聚)的群际间歧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实质上就是社会分类的结果。换句话说,对内群体来说,意识到外群体存在的这种意识本身就足以引发群际之间竞争性或歧视性的反应。”②Henri Tajfel and John C.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tergroup Behavior”in Worchel S,Austin W(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p13.
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群体间的差异意识与群体成员的社会分类有直接的关系,而群际之间的这种差别意识是引发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冲突的重要心理基础。进行社会分类的依据很多,其中,语言作为族群成员身份的重要标志,是用来分类“我族群”与“他族群”的重要分类依据。用“学习与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社会分类,完全模糊了“我族群”与“他族群”之间的界限,使不同族群成员之间因为共同语的使用而生成一种积极的态度,促进族群之间认同感的形成,从而改善群际间的关系。
(三)语言的国际传播对主体认知的引导作用
语言的国际传播是一种国际公众交往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通行的国际教育模式。考察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以及中国的孔子学院等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对外传播本民族语言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语言教学,有配套的师资、教材以及相应的考试研发。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模式,语言的国际传播在引导他国公众认知方面具有诸多优势。
首先,语言的国际传播对象以年轻人居多,与上一代人相比,生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新生代不受“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更为开放,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对年轻人的认知进行引导,有利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长远发展。
其次,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模式,语言的国际传播与其他国际公众交往方式相比较,是有组织的集中教学,学习者是可管理可控制的群体。以语言为教学内容的国际教育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上具有极强的自主性,教育者是课堂信息的把关人,可以决定哪些内容传达给学习者,哪些内容不能传达给学习者,哪些内容要强化放大,哪些内容要淡化缩小,对于接受对象的认知是可控的。这种可控性来自于有组织的课堂教学环境与师资以及教材编排的自主性特征。美籍学者Guangqiu Xu在《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影响:1979—1989》一文中曾提到,第一批来华的富布赖特学者在英语教学中成功地将美国历史与美国文化作为教学补充或背景知识提供给中国学生。许多美国学者为能够在教授中国学生的同时提供新课程、介绍新知识和运用新方法而感到高兴。“首先,他们提供了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课程,而这些在中国自1949年之后是没有的……其次,中国人开始更好地理解一些政治观念了……第三,富布赖特学者们相信,对于他们的中国学生和同事来说,他们扮演了密友和顾问的重要角色。”③Guangqiu Xu,“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U.S Fulbrighters on Chinese Students:1979 -1989”,Asian Affairs,Fall 1999,Vol.26 Issue 3,146 -148.文章还提到,在教学之外,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做讲座,从美国大使馆借来美国电影、录音和书籍与中国学生一起分享。
语言的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慢媒介”,以文化浸润和正面引导塑造着学习者的主观认知,从而使学习者逐渐对一国形成心理、情感上的向往以及理性上的认同,同时这些语言的学习者作为“意见领袖”,又把他们对于一国的认知传递给他们周围的人。
三、对汉语国际传播构建中国形象的启示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了汉语作为一门“外语”的学习价值。目前,汉语的国际传播已成规模,至2010年底,全球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来华留学的人数逐年攀升,到2011年,来华留学的总人数已将近30万。①数据来源:国家汉办官方网站:http://www.hanban.edu.cn/,2012 -10 -16。作为中国进行对外传播可资利用的巨大资源,从语言国际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角度分析,目前在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与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对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路径有待拓展
目前,国内对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仍集中于汉语国际传播的教学层面。其中,对汉语教材的研究、对汉语教学法的研究、对汉语师资建设等领域的研究仍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而对汉语教学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超越教学层面的功能关注不够。随着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逐渐深入,对汉语国际传播内涵的理解也应逐步拓宽。
(二)重视对来华留学生认知的培养
我们在提到汉语国际传播构建中国形象的作用时所关注的仍是汉语传播的“走出去”,而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引进来”重视不够。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海外汉语传播在引导他国公众认知、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对他国公众来说,在自己的国家认知中国,是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了解中国,因此对于中国文化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部分接受起来相对容易,而对于精神文化部分理解起来仍有隔膜。来华留学生在中国亲身体会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民情,亲眼所见中国本土的实际变化,能够设身处地地依据中国文化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观来理解认识中国形象,有利于消除先前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
(三)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践研究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策略性研究,目前仍偏重于宏观性研究,偏重理论阐述而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策略指导。从语言国际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角度而言,具体的传播策略的出台应该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践研究基础之上。但由于进行大范围的实践性研究难度较大,不易操作,往往不是个人行为所能完成,这个层次上的研究,还须借助国家力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