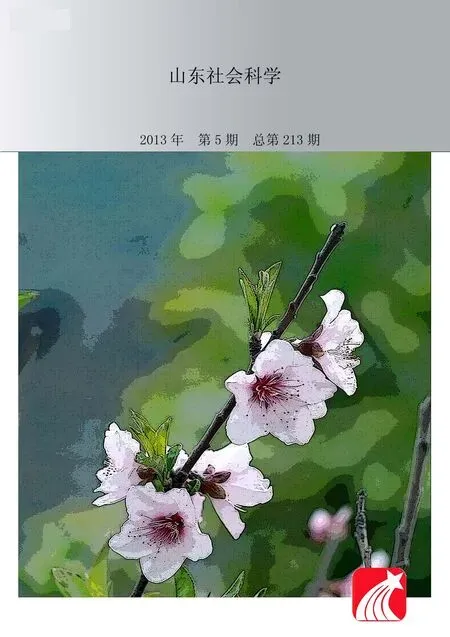《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
——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魏淑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学研究部,上海 201204)
一、从洋务运动到《公司律》出台: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的渐进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次遭遇战,传统中国在西方现代性挑战面前第一次败下阵来。晚清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则是前现代性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后,伴随一次次的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那个古老、庞大而羸弱的清王朝的“天朝上国”梦幻被击碎,同时中国传统精神世界中的华夏中心世界观也逐渐彻底崩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逐步丧失,古老中国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器物”、制度和文化。为实现富国强兵,清政府开始接受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武器”,于1860年代开始创办洋务运动。早期的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军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清政府虽然也希望振兴工商、求富图强,但已经无力出资大规模兴建民用企业,若要振兴商务,就不得不向民间商人筹资以设立公司企业。但出于不希望放弃对社会经济控制权的心理,以及对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一经发展起来难以控制的担心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晚清政府便重拾历代王朝惯用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发展经济之手段,并将该种手段直接嫁接到股份公司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上,从而创造出 “官督商办”公司。官督商办的实质其实是不承认民间自由从事新式工商生产的权利,是现有传统体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希望接受西方现代性“器物”,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全新的现代性工商制度,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意图实现王朝“中兴”的重要举措。
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和“官督商办”公司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也是清王朝面对现代性挑战作出的一次应对尝试(这是一种希图固守“中体”,仅在器物层面尝试现代化的尝试)的失败。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开始将其经济政策调整为“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注徐卫国:《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原载《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8年第5期。。政府放宽了对民间投资办厂的限制,一部分地主、商人、官僚受资本利润的吸引,又痛感民族危机深重和国家力量贫弱,提出了“设厂自救”、“回收利权”和“商战”的呼吁,使甲午战后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高潮,民族资本创办公司有了较大的发展。1898年是晚清政府最终决心促进现代商业的发展的关键之年[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1898年8月,清廷在北京设农工商总局,该局虽不具备统一管理全国农工商事务的权力,但却是清政府第一次设立的新型经济部门,是在政府机构层面因应现代性挑战的创举。总体来看,甲午战后之初清政府采取过某些振兴工商的措施,但基本上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层面上,尚没有一个全面制度性的变革。
社会经济发展到20世纪初期,中国境内已经在包括航运、纺织、机械制造、化工、矿业、铁路等新型的工商领域中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公司企业,清王朝的传统经济生活中已经较多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经济因素,但晚清的传统法律架构没有为20世纪初国内工商经济的发展提供任何有效的制度空间。无论是国内华商公司,还是外商在华的公司都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的法律架构为其明确法律地位、厘清交易关系、提供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其时,商办公司企业的设立仍旧需要“拟定章程,奏准开办”[注]史际春:《企业、公司溯源》,载《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才能获得“合法”的地位。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民用企业虽然称之为“公司”,但由于没有公司法,公司赖以生存壮大的一些基本因素依然缺失。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始终没有在晚清早期的公司实践中得到贯彻。这种局面严重阻碍了晚清新式工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晚清财政收入的增加。为了适应时局需要,赢得商战,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晚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实行新政。1902年3月光绪帝颁布“修律”诏书;1904年1月21日,晚清修律运动中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两个部分)获谕允,并正式颁布实施。可见,《公司律》等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的颁布,一如当初晚清开始接受并生产枪炮等现代武器,是在被动应对西方各种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实质是落后的前现代性在先进的现代性挑战面前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之策。但不管怎样,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传统中国还是突破了仅在“器物”层面作出应对的局限,开始在法律制度层面作出应对,并向现代性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注]许世英:《 论清末商法的实施及其效果》,《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
需要明确的是,为了收回被西方褫夺的法律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是晚清《公司律》等一批现代意义上法律制度出台的直接历史动因。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列强明确要求清政府引入公司法等西式商事法律制度的正式提出。随后,美国和日本都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晚清政府通过商约谈判,与西方列强达成了以中国整顿律例为条件,列强放弃其在华治外法权的交易。可见,《公司律》等一批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的推出,也是晚清政府因应西方现代性挑战,在法律层面上作出的重要举措。
二、晚清《公司律》的颁布及实施情况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1903年4月22日),光绪帝发布先行编订商律的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急应加意讲求,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业,鼓励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注]《大清新法令·法律》,转引自帅天龙:《清末的商事立法》,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1904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商律》获谕允,并正式颁布实施。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大清《商律》的主体——《公司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公司法,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篇之作。
(一)晚清政府对《公司律》的态度和执行情况
《公司律》出台后,晚清商部(后改组为农工商部)在对公司注册审查时,总起来讲还是能够按照《公司律》和《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进行的[注]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徐立志:《清末商事立法研究》,http://flwh.znufe.edu.cn/article_show.asp?id=3070,访问日期:2010年3月30日。。根据《商务官报》第一期至第十期的记载统计,1906年5月至1908年5月两年间,因为以下原因未能注册者达到118家。这些原因包括:未按法律规定备其注册所需手续;所报公司性质与《公司律》不符;未按《公司律》规定将股本落实;所订章程与《公司律》不符等。[注]有关实际例证参见徐立志:《清末商事立法研究》,http://flwh.znufe.edu.cn/article_show.asp?id=3070,(访问日期:2010年3月30日)。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公司呈请登记中,除了予以正式注册的以外,还有一类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只能作为“先行准予立案”的情况,并在完备有关手续和材料后,即可正式注册。[注]参见《批职商孙钟伟请注册呈》,载《商务官报》1906年第2期。晚清政府工商部曾于1908年和1909年分别编订过《农工商部统计表》,分别就《公司律》规定的四种公司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这充分说明了农工商部非常重视公司注册登记制度和《公司律》的实施情况。另有实例表明,晚清商部也较为重视敦促商人对《公司律》的执行。如1907年,杨宗翰发起创办的无锡业勤纱厂,经营卓有成效,“惟积习相沿,并未按商律办事”,“经理人从未报告账目”,因此引起许多股东的不满,上诉到商部。商部为维护股东利益,责令该厂另立章程,公布账目,按《公司律》行事。[注]参见《商务官报》1907年第24期。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晚清政府虽然认识到变法新政的重要性,但是一部《公司律》的颁布并不代表晚清政府已经真正走上了法治之路,真正的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公司律》实施中虽然有注册严格、按律办事的实例,但也有各级官僚抛开“依法维护”于不顾,屡屡对商办公司进行“官督”,直接干预公司内部事务。“据统计,在1903至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立了18个铁路公司。……各省铁路公司的总理或总办,即主持人,除广东潮汕、新宁、粤汉三路公司是由股东推选的外,其余都是由各省绅、商公举,由商部奏派的。[注]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在路政问题上,清政府更是屡屡违背自己出台的法律。1906年,湖南绅商奏请自办湘境铁路,商部认为“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注]《清实录·德宗》卷561,第6页。1910年9月,邮传部更以“铁路决非寻常商业公司可比,不能将普通《公司律》附会牵合”[注]《大清宣统新法令》,第20册,第3页。为借口公然将《公司律》弃置一边。1911年,清政府进一步自行否定前律,擅自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其以前批准各案一律取消。”[注]《宣统政纪》卷52,宣统3年4月11日上谕。清政府这一强制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既违反了《公司律》和《铁路简明章程》,同时又公然与民众对立,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和晚清覆灭的直接原因。
(二)商界对于《公司律》的态度、认知和执行情况
《公司律》给予商办公司以合法地位,因此,各商办公司希望通过依律注册公司,获取法律之保护。《公司律》和《公司注册试办章程》颁布后,不仅新设立的公司陆续呈文到商部呈请注册给照开办,一些先已设立的公司也开始纷纷要求注册。1904年《公司律》出台后,《申报》上经常出现商办公司的招股广告,每每打着“根据《公司律》”或“根据商部核准”等旗号公开招股,这说明,时人已经认识到法律所具有的保护和权威功效。商办公司经注册登记,获得合法的地位后,已经出现能够按律设立内部组织机构,召开股东会议,通过公司内部决策机制解决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的新气象。自《公司律》颁行后,新创办的公司一般已经能够按照《公司律》的要求在创办之时即及时召开股东大会。不少公司在股东会议召开前都能在一些主流报纸(如《申报》等)事先刊登股东会广告,有些还事先发布进行股东权利挂号(股权登记)广告。[注]如1909年7月31日《申报》刊登《招商局股东挂号处第六次报告》:“上次报告挂号书目25244股。此7日来续又挂号1500股,连前共计26744股。公议股东大会定期月30日。外埠挂号于6月15日截止。过期不挂,自弃权利。发起人不担责任。谨此报告”;1909年11月2日《申报》同时登载两家公司的股东会广告:《汉镇积极水电公司开第二次股东会广告》、《中国图书公司定于9月20日开股东常会广告》等。还有一些公司能够依据《公司律》提供的制度规则,解决经营中碰到的问题。如1909年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积亏192300两,董事会便依据《公司律》第76条的规定,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讨论并制订出解决方案,待各项措施实施后,该公司逐渐度过了难关[注]详细内容参见:《申报》1909年4月12日、5月30日。。
但是,在《公司律》颁行后,商界对《公司律》在认知和遵守仍存在较大的缺陷。经济史专家们认为当时社会还存在已经比照公司组织运营,但是未经呈报注册的公司,而且这些公司数量要远远大于业经正式登记注册的公司数。[注]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公司律》颁行后,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现了公司注册的热潮。事实上,“并未有蜂拥前往注册公司的情况发生,一些最大的商人还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及其家庭的资金,同时也得到一小群合伙人的资助。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筹集资金的概念还需要凝固。直至进入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注]科大卫:《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中国经济社会史》2002年第3期。同时,公司运行中漠视《公司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学公会等于1909年编成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就列举了一些当时商人不遵守《公司律》的现象,特别是《公司律》关于新式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在当时更是少有执行[注]张家镇等编著:《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载《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王志华编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可见一种制度的引进颁行,远比颁行人和商人们真正能理解这种制度并将这种制度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要简单得多。制度移植到本土以后,要真正变成本土的商业惯行,还需要长期的实践积淀。对于《公司律》颁行后公司运作的情况,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进行了总结归纳。其中特别谈到了“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注]梁启超:《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事实上,这是梁启超对晚清政府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商办公司股东缺乏股权意识的深刻认识。
三、《公司律》的时代效用
(一)《公司律》及有关奖励工商法规的相继出台,大大提高了晚清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19世纪中国早期现代工商业是在无现代法律可依的状态下运行的。洋务运动中的工商企业的设立和运作全依赖清政府的特许和洋务官僚的意旨,毫无规则可言。其时,中国工商业者没有自由设厂、开办公司的权利,他们只能或“附股洋商”,或委身“官督”得以特许设厂,因此,当时的工商业者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以一种“依附”的状态艰难生存。20世纪初,清政府不仅再三谕令各级官吏保护和鼓励华商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而且制订了《公司律》,第一次确立了华商从事工矿交通运输业等现代工商业的合法性;第一次确立了华商自由设立现代工商企业的自由;第一次赋予华商投资设立的公司企业以合法地位。《公司律》还确立了两项平等权利:商办公司与官办公司享受“一体保护之利益”(即《公司律》面前各类公司一律平等);无论官股还是商股,各项利益与权利“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即股权平等原则),这是晚清政府从限制官股和官办公司特权的角度体现了对一般商股权利和商办公司的保障。晚清《公司律》给予商办公司和工商业者明确的合法地位,为现代工商业者独立品格的形成打下了制度性的基础。同时晚清政府在“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思想的推动下,大力推行“重商”国策,从“抑商、困商”到“奖商、恤商”,甚至连续发布奖商章程,以“封官加爵”来奖励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工商业者,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重商、尊商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提高。
有了法律保护的工商业者,还获得了政府承认的“结社权”。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劝谕成立商会。商部还专门设立了商会处,拟订了《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商会处专为商会而设……冀通声气之路”。“各业中如有体面巨商,欲进谒本部堂宪而面陈议论者,即自行来署。先赴商会处呈明来意,由商会处随时回堂接见,绝无阻碍。”[注]《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1期。不久,各省及通商大埠的工商业者纷纷成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纷设商务分会。商会的成立,一般是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然后由商部颁发关防钤记,从而得到官府承认和保护。商会为“众商业之代表”,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从此之后,工商业者有了真正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组织机构。通过商会,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工商业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绝对不可忽视的社会集合力。1907至1909年期间,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学公会的倡导和组织下,工商业者召开了两次商法大会,并拟订了《商法总则草案》和《公司律草案》,呈请清政府在修改公司律时予以采纳。清廷农工商部将该两草案稍作修改后,即定名为《改订大清商律草案》,呈资政院审议,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该草案被搁置。但在民国初年,尘封不久的该草案又被北洋政府稍作修改以《商人条例》和《公司条例》的面目问世,并就此成就了中国法制史上卓有功效的一部公司法。晚清两次商法大会以及商法草案的拟订,标志着中国工商业者开始以团体的力量参与国家的商事立法和法律改革。在这场政府与商会的商事立法互动中,工商业者以及商会的集体性立法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认可。
(二)《公司律》的颁行事实上宣告了“官督”公司管理模式的终结
《公司律》的颁行事实上宣告了“官督商办”这一商办公司运作形式的出局,以及“官督”公司管理模式的历史终结。1904年的《公司律》并未提及“官督商办”,在规定各种类型的公司均一律平等时,该律的提法为:“无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各项公司及各局(凡经营商业者皆是)均应一体遵守商部定例办理。”可见,在清政府的官方语言中,“官督商办”已经没有了地位。而同时,公司法对公司的法律地位、股东权利以及公司运作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的存在,启发和推动了洋务民用企业中商股股东的公司化思维,开启了他们摆脱“官督”、自由经营的“商办”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为商股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抵抗官权的干预、主张商办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司律》第44条规定:“附股人不论职官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他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这一规定,有助于增进官商之间的经济合作。许多官商合办公司的章程中,都有“官股、商股一律享受利益,不稍歧异”的规定。[注]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公司律》第30条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各项公司及各局(凡经营商业者皆是)均应一体遵守商部定例办理。”该条规定事实上也确认了当时存在的三种公司类型(以股东身份为标准进行区分的):官办、商办、官商合办。有研究表明,《公司律》颁布后,“官款以股份形式同商股合作的事例较前增加了”[注]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这一方面与清政府振兴商务、以资金支持工商企业设立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公司律》明确了官股、商股一律平等,以及“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各项公司及各局(凡经营商业者皆是)均应一体遵守商部定例办理”等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
《公司律》施行后,“官督商办”公司纷纷依律转归商办公司。如“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等三厂在盛宣怀的推动下,完成了商办注册。事实上,1904年《公司律》出台后,“原来的官督商办企业也逐渐地或收归国有,或改归商办,宣告了官督商办形式上的终结。”[注]豆建民:《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三)《公司律》的颁行推动了晚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公司律》的颁行以及晚清政府保商、奖商等重商政策的推行,在举国“振兴商务”热潮的大背景下,继洋务民用公司热之后,中国近代又一次出现了“公司热”[注]当时的报纸曾这样描写:“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见《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载《国风报》第1期第1号。,中国民族工商业在20世纪之初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次“公司热”的浪潮中,到晚清政府工商部办理注册、申请给照营业的新设公司数量增长较快。据经济史专家统计,到1911年全国约有各种华资近代企业2300多个,资本总额约在3亿2000万元左右,大约相当于1900年华资掌握的企业数额和资本总额的四倍半,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五。[注]樊百川:《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概况与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1904至1911年间,真正以公司名义注册登记的企业应该是410家左右”[注]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而事实上“社会上总是存在一些虽已经创办或已经营业,但是并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公司”。[注]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商人向来注重保密,崇尚“商业神秘主义”,因此,《公司律》颁行后,虽未办理注册登记,但事实上从事现代工商业经营的企业,应不在少数。
四、《公司律》的颁行是中国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椎轮筚路、厥功至巨”
晚清《公司律》“草创之始,难语完备。”[注]张家镇等编著:《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载《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王志华编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该律虽然存在体裁不齐、结构混乱;内容简略,不适于用;缺乏对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调查、融合及改造,“致多拂逆商情”等诸多缺陷,但《公司律》的颁行“椎轮筚路、厥功至巨”,其在中国近现代立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公司律》是晚清修律推出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是中国因应现代性挑战作出的最具现代意义上的因对措施之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中国开始了政治、法律、经济以及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中国现代化进程自此真正开始。就连20世纪初期的商人也认为《公司律》的出台是“由事实而渐进于法律,椎轮筚路,厥功至巨。”[注]张家镇等编著:《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载《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王志华编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1904年之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努力从未停歇,
(二)《公司律》以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法律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肇端于政府将经济活动自由归还给社会民众。1904年初,以《公司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法律的相继出台,宣告了公司设立的“特许主义”制度开始被“准则主义”制度所替代,经济自由、平等的理念和制度开始走入中国经济社会。首先,《商人通例》正式宣告国人有从商的权利。该通例第二条规定:“凡男子自十六岁成丁后可为商(按年月计足十六岁)”。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国人以“商事权利”,是中国人享有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其次,《公司律》的出台标志着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标志着商办企业取得了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华商从此可以自由设立自己的公司。在此之前,清政府一直未在法律上确立华商自由投资兴办工矿交通等近代化企业的权利,更谈不上给予切实保护了;再次,《公司律》及其配套经济法律的出台,确立了经济平等的观念和制度。《公司律》第30条规定:“无论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各项公司及各局均应一体遵守商部定例办理。”1904年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规定:“无论现在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注]《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5期。《公司律》还确立了股权平等原则,该律第44条规定:“附股人不论官职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上述规定,确立了商办企业同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官股与商股平等原则。
(三)《公司律》第一次将公司法律制度引进国内,并推动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权利意识的形成
《公司律》的出台,第一次在中国确立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现代法制理念和制度:公司是国家认可的法定工商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类型法定主义;公司设立准则主义;公司自由注册制度;公司的有限责任;以股东会、董事会和查账人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构;现代财务会计制度;迥异于我国传统商业神秘主义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司解散与清算制度等,这些制度基本上涵盖了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主要方面。《公司律》开启了中国新式工商企业制度的新时代。
《公司律》确立了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个私法性质的权利——股东权利。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股东权利意识很快在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商人中形成,甚至出现为维护股东权利不断抗争的实例。如1910年清政府为了出卖路权,革去了立宪派代表人物汤寿潜的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之职,浙路公司众商股股东为挽留“公举”的总理汤寿潜,以《公司律》和保护股东权利为依据与清政府邮传部进行斗争,认为浙路总理的任替,须由股东会公决,不应由朝廷定进退,以“剥夺人民应享之权利”[注]《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后余闻》,《东方杂志》1910年第9期。。可见,虽然出于挽回时局的需要,晚清政府被迫出台了《公司律》,但其对商办公司或官商合办公司的股东权利从来没有真正地尊重过,及至1911年,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违背了自己颁行的《公司律》,严重侵害了铁路公司的商股股东权利,激发了商股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激起影响全国的“保路运动”,并最终引发辛亥革命,导致清廷覆灭。
综上所述,晚清《公司律》虽然还是相当粗糙的一部法律,但这部法律第一次承认了商人自由设立公司企业的权利,极大激发了国人发展工商经济的热情,同时一个代表现代性的工商阶层开始出现,商会作为这个阶层的重要组织力量起到了联纵工商人士、通达晚清政府的积极作用,这是千百年来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最具积极意义的群体组织,对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人是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力量,现代中国30年改革开放,首先是赋予了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极大激发了国人发展经济的热情,从而取得了重大经济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几代人共同追求的“求富”、“求强”的梦想。但我们的现代化还在路上,我们从百年之前的前现代性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现代性积累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还远未完成,我们须完成这一转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