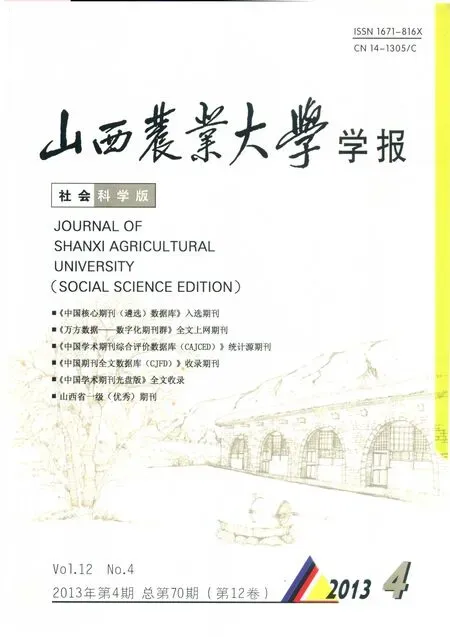从符号学角度谈文学作品中陌生化手法的翻译
张敏,胡艳
(太原科技大学 外语系,山西 太原030027)
“陌生化”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常见的技巧,自古以来就被文学大家们不自觉地使用。自十九世纪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提出之后,这个概念便被文学界所认可,代表着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成为实现文学性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文学性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文学翻译中,陌生化手法也引起了翻译家们的重视。较早的有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翻译研究派,其代表人物米科 (Frantisek Miko),波 波 维 奇 (Anton Popovic)分别提出了诗歌翻译中应注意 “表现特征”和 “转换表达”,换而言之就是陌生化手法。之后,希尼 (Seamus Heaney)提出译者应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标语的表达变的陌生。[1]根茨勒 (Edwin Gentzler)也指出“译文应该保留源语文本的陌生化表现手法,如果源语文本中的表现手法在第二语言中已经存在,译者就要构想出新的表现手法”。[2]国内学者郑海凌、王东风、金兵等人也在其论文或著作中强调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充分意识到原作的陌生化手法,并予以再现;甚至陈琳还提出 “陌生化翻译”应被视为一种翻译策略,[3]从而使译入语变得陌生而有吸引力。然而,“陌生化”这种逆常规的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再现陌生化手法时会遇到哪些障碍?遇到陌生化手法时,译者可采用哪些具体的翻译方法?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似乎都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把陌生化手法的翻译研究建立在符号学这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符号学分析 “陌生化”之本质
“陌生化”在文学作品中被视为 “在创作中不落俗套,将习以为常的,陈旧的语言和文本经验通过变形处理,使之成为独特的、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4]要研究 “独特的、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来自何处,必须弄明白意义如何产生、传递以及如何被接受者阐释的问题。这便是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将 “陌生化”的研究建立在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对于符号的研究,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却始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渊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范式,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C.S.Peirce)的逻辑学范式,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范式。[5]本文主要采用皮尔斯的理论。皮尔斯将符号进行了三分法:代表项 (sign vehicle)、 对 象 (object)和 解 释 项 (interpretant)。[5]代表项是指符号的物质形式,如玫瑰的发音或文字序列;对象就是代表项所指向的 “事物”,如一朵或几朵玫瑰花本身;解释项是指接受者做出的解释,即意义,如玫瑰这一类植物或由玫瑰引起的示爱的联想。他们三者具有以下关系:客体对象是符号的形成的原因;而解释项则是符号所产生的结果,是对符号的诠释:这一诠释可以和客体对象对等,如玫瑰花本身;也可以是进一步发展了的、与客体对象相关联的意义,如示爱的联想。这些相关联的、发展了的内涵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呢?符号的使用是建立在规约性的基础上的,即最初用哪个符号来代表哪类客观对象是任意的、无法论证的、具有一定偶然性的,如玫瑰这个发音或文字序列并不比其他发音或文字序列更具备代表玫瑰这种植物的优势,只是第一个人恰巧那么用,被社会成员所接受,进而建立起规约性,被广泛使用而已。但是,符号释义的神奇之处也恰恰在于这种规约性可以被打破,进而发展出新的意义。如当第一个人用玫瑰来象征爱情时,就已经打破了规约,消解了 “玫瑰”这一符号代表项所承载的 “一种蔷薇属的、茎通常有皮刺、叶互生的植物”的解释项,并在与这一解释项相关联的基础上通过隐喻的方式产生了新的解释项,即爱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内涵意义在使用的初期,都是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因为接受者必须花费力气找到爱情和玫瑰花之间的相关之处,才能在语境中阐释出示爱的含义,也就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 “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延长了感受的时间”。[6]但是,随着这一新的解释项被反复沿用,也会逐渐建立起一种规约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不需要思考,便可以自动化、机械化地获得的意义,这时便不再拥有 “陌生化”的效果了。
从以上的符号学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陌生化”就是作者有意识地打破现实符号的代表项与解释项之间规约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扭曲、变形、拉长或颠倒,从而产生诗学效果。第二,“陌生化”在剥离现实符号的内容,强化形式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向纯形式化,而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产生了新的解释项,即新的意义。第三,“陌生化”并非唯陌生而陌生,而是希望对事物达到更高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并不是一切陌生的语言都能构成诗,因为符号在延伸过程中,新的解释项和代表项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任意性,而是有根据的,体现在新的解释项与前一个解释项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这种联系接受者经过努力才能够发现,才能在一定的语境中阐释出新的意义。第四,“陌生化”是动态的。陌生化的语言一开始出现时对于接受者来讲是新鲜的,没有见过的,但久而久之,这一符号代表项与解释项经过重复使用,就变成了常规化的,自动化的现实语言。因此,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曾这样讲:“普希金的诗,如今显然在被人们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已经在石化了。”[7]这里所谓石化,就是自动化,机械化。
二、从符号学分析翻译中再现 “陌生化”之障碍
皮尔斯认为,人作为符号主体,在对符号进行释义时,既有其发挥的自由,从而推动符号的成长,同时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限制来自于符号使用者所处的社会规范,就具体的符号使用者来说,则是内化为知识或经验的一种习惯。在语际翻译中,穿梭于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译者,必然会受到两套 “规范”限制。而这两套“规范”的差异性,必然会给译者带来达意方面的困难。具体来讲,这两套 “规范”的差异性体现在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 “异”以及这两种语言符号所反映的各个社会文化子系统之 “异”。而 “陌生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于源语言读者已经是陌生的,是一种 “异”质成分,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讲,就很有可能变成 “异”上加 “异”,给译者造成莫大的困难。下面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一)语言符号系统之异带来的障碍
“陌生化”讲究的是破坏日常语言的常规性、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实现标新立异。在同种语言符号系统中,对其进行转述都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更何况要跨越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英汉两门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各个方面都差异巨大,译者们常常能感觉到这些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难。这一点在诗歌这种特别强调语言的文学形式中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了:节奏、韵律、意象、内容,译者很难面面俱到,十全十美,有时甚至只能做到解释说明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8]卡明斯 (E.E.Cumings)有一首著名的视图诗:
L(a
le
af
fa
ll
s)
One
L
Iness
该诗将a leaf falls放在括号里且插在loneliness一词之间,构成:L(a leaf falls)oneliness的形式。诗人将这些词拆散竖排,形成 “一片落叶渐渐下降”的视觉形象来烘托 “寂寞如落叶飘零”的意境。乍看起来,这并不象一首诗,而是一种文字游戏,但仔细品味便可发现诗人是以图示诗,想让读者去看诗,去看诗的绘画性,看到一片落叶飘飘而下。这样,“寂寞飘零”的抽象概念就被落叶的具体形象烘托出来。而这种艺术效果对于汉语这种方块字来讲,想要得到再现,真可谓是难于登天。
(二)社会文化子系统之异带来的障碍
英汉两种语言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子系统,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环境等之间的 “共核”部分,构成了翻译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也给译者们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再现 “陌生化”手法时,这一点尤为突出:如若译入语读者连符号的惯常化意义都不明了,又何以去打破常规,获得审美体验呢?如 《水浒传》第四十七回中杜兴向杨雄、石秀介绍祝家庄时,有这样的一句:“又有一个教师,唤作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
此处使用成语 “万夫不当之勇”,巧妙地对栾廷玉的勇猛进行了夸张的描述,使人物刻画更加形象、生动。然而想要再现这种夸张的手法,却由于文化差异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在汉语的许多表达中,千、万等词语用来泛指数目之大,并没有明确的算术含义。这里如若将 “万”译成“ten thousand”,大多数西方人会当成确切的数目来对待,产生疑惑:一万个人都抵挡不住,难以信服。于是译者杰克逊 (J.H.Jackson)在翻译时也选择舍弃形式,将本句译为:"They had a drill instructor named Luan Ying-yu,nick-named Iron Stuff,who was invincible."
三、文学作品中翻译 “陌生化”手段的方法
从符号学来看,翻译的过程可分为译者在源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解码过程,以及在目标语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编码过程。通过上文的分析可得出,译者在源语言符号系统解码时应当分析作者使用语言符号时,是否有意识地打破了符号的惯常化、机械化用法,而对符号代表项与解释项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形、扭曲,从而在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在译入语符号系统编码时,译者应对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差异进行分析,在考虑可读性的同时,尽力再现这样一种非常规的关系,从而给译文读者带来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那么译者可以采用哪些翻译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呢?具体说来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一)移植法
如果原文符号的代表项与解释项的关系打破后在语境中产生的新的意义,在译入语中能够通过相对应的符号得以实现时,适用移植的方法。如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中有这样的句子:
“Stephen,still trembling at his soul's cry,heard warm running sunlight,and in the air behind him friendly words.
仍在为心灵的呐喊而颤抖的斯蒂芬,听到了身后有温熙的阳光在流动,空气中有好友说话的声音。(金隄译)
灵魂的呼唤依然使斯蒂芬浑身发颤,但他感到倾泻而下的阳光的温熙,并听见了从背后传来的友善的话语。(萧乾,文洁若译)”[9]
从原文来看,sunlight和hear,并不搭配。但恰恰是这一个 “听”字,让人直接感觉到了倾泻而下的阳光,耐人寻味。这种通感的手法,在汉语作品中也常常使用,汉语读者具有接受的基础。因此,此处适用移植法,把原文的陌生化手法照搬入译文即可,如金隄的译文。萧乾,文洁若的译文把原作的陌生化手法过滤掉,看起来是逻辑通顺了,但反而丢掉了作者的苦心和读者应获得的乐趣了。
(二)模仿法
如果原文符号的代表项与解释项的关系打破后在语境中产生的新意义,由于语言及社会文化的差异,照搬后译入语读者无法阐释出新的解释项,会造成意义丢失时,适用模仿法:即译者努力在译入语中寻找其他符号来模仿原作符号代表项与解释项之间的陌生化关系,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如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一段:
贾母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念道:
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
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也得了贾母的东西。
霍克斯译为:
"Of course,"said Grandmother Jia."the monkey's tail reaches from tree-top to ground.It's the name of a fruit."
Jia Zheng knew that the answer to this hoary old chestnut was"a longan" (long'un),but pretended not to,and made all kinds of ab-surd guesses,each time incurring the obligation to pay his mother a forfeit,before finally giving the right answer and receiving the old lady's prize.[10]
此处贾母出的谜面是猴子 “立枝”,读者在释义时需要把 “立枝”这一符号与其解释项 “站立枝头”的关系打破,只剩下符号代表项本身,即 “立枝”的发音,之后再通过谐音的联系,得到新的解释项 “荔枝”。作为译者,应当关注并模仿此处的这种关系,而不是将其表面意思进行直译。霍克斯的译文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妙,乍一看似乎谜底从荔枝 (litchi)变成了龙眼 (longan),但这恰恰说明他充分地意识到了作者此处语言与常规化语言的相异之处,并利用longan与long'un(long one)的谐音,在英语中再造了同样的逻辑关系,再现了原作的精妙之处。
(三)补偿法
英汉之间的语言及社会文化差异造成的再现“陌生化”效果的障碍,有时能够因译者的聪明才智而巧妙地避开,有时却无法逾越,即便勉强译出,也未能曲尽原文之妙。出现这种情况时,比较好的做法是采用补偿手段。这里所说的 “补偿”是指由于不可形意兼备,译者应对损失的方面通过加注的方式来传达。如萨克雷的 《名利场》中有以下一段:
"What have we for dinner,Betsy?"said the baronet.
"Mutton broth,I believe,Sir Pitt,"answered Lady Crawley.
"Mouton aux navets,"added the butler gravely (pronounce,if you please,moutongonavvy);"and the soup is potage de mouton a L'Ecossaise.The side dishes contain pommes de terre au naturel and choufleur a l'eau."
杨必译为:
管酒的板着正经脸说:“今天吃Mouton aux navets,”(他读得很像 “木头窝囊废”); “汤是potage de mouton a L'Ecossaise,外加 pommes de terre au naturel和choufleur a l'eau。”
[注]法国是著名讲究饭菜的国家,因此用法文菜名,显得名贵,实际上吃的菜不过是羊肉胡萝卜,苏格兰式羊肉汤,添的菜是白马铃薯和菜花。[11]
此处,划线部分为法语,萨克雷为了刻画人物性格采用了语码转换这一陌生化手段,使管酒的端着架子,自视高贵的形象跃然纸上。杨必在翻译时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保留了不同语码。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这几句法语会让汉语读者备感吃力,因此加注成为必要的补偿手段。但是,如若译者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将不同语码译成同一语码,文学性就有所损失了。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上,“陌生化”的本质得到了清晰的透视,译者在对源语言符号系统进行解码时应充分分析符号的释义过程,对这种超乎常规的语言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译入语符号系统进行编码时,应当考虑到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差异性,以及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分别采用移植、模仿以及补偿的方法尽力再现 “陌生化”效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的限制条件是动态的,现在看起来无法得到再现,不能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因而只能通过补偿手段翻译的 “陌生化”语言,若干年后,随着目标语文化的发展,及读者素质的提高,很有可能变得容易再现了。因此,译者要遵循重视而适度的原则处理文学翻译时遇到的 “陌生化”手法。
[1]Heaney,Seamus.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M].London:Faber and Faber,1989:36.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Rev 2nd 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80.
[3]陈琳.论陌生化翻译 [J].中国翻译,2010,31 (1):13-20.
[4]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4.
[5]翟丽霞,梁爱民.解读现代符号学的三大理论来源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6(11):64-66.
[6]什克洛夫斯基著.王薇生译.俄国形式主义文选 [C].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226.
[7]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8.
[8]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77.
[9]金兵.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 [D].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冯庆华.红译艺坛—— 《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82.
[11]萨克雷著.杨必译.名利场 [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