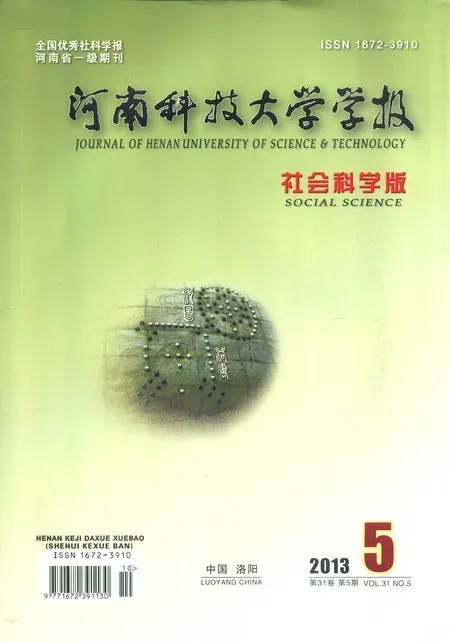“重复”:从“词”到“篇”
——《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张素丽
(防灾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北 三河 065201)
【艺文寻珠】
“重复”:从“词”到“篇”
——《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张素丽
(防灾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北 三河 065201)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鲁迅;《故事新编》;小说结构;重复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多次重复性地使用一些降格性的“时间”表述方式,比如“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功夫”(《采薇》)、“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功夫”(《铸剑》)等,把圣贤、英雄的威严行为消融于日常生活的世俗情境中。单个的语词不构成现象,但当某个或某种语词在文本中执拗性地重复出现时,它就不再拘囿于自身内涵外延的意义权限,有时甚至会上升为某种结构性事实。本文聚焦《故事新编》的诸种“重复”现象,旨在对这部小说集的对称性结构特征作出深入阐释。
一、《故事新编》中的语词重复
在《故事新编》之小说《采薇》中多处出现了特殊的时间意象重复,文中用烙饼所做的三处时间修辞分别是这样的:
……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
……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
……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
从行文语言来看,这三处时间表述方式非常相像,即在降格的文辞处理中为小说造成一种戏谑化效果。从小说内部逻辑出发,鲁迅之所以用烙饼来做度量时间长短的单位,是因为伯夷、叔齐在西周养老堂时曾抱怨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对这两位礼仪气节胜于一切的圣贤世子,再没有比用果腹的烙饼来衡量“时间之于他们的意义”更为讽刺的事情了。这种重复的时间意象带来的行文效果,与小说结末中阿金姐诋毁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喝鹿奶吃鹿肉的荒诞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采薇》中的这种时间用法在《铸剑》中也有体现:
……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
……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
第一处时间表述出现在眉间尺复仇途中,眉间尺复仇心切,却被无聊闲人纠缠,脱身不得,作者用“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来衬托他为琐事困扰的焦躁;第二处时间表述出现在复仇行动结束后,王后弄臣们为打捞王头商议对策,耗时良久但依然未果。这种重复手法一方面把王后弄臣们的滑稽愚蠢进行了夸张化处理,同时也把威严悲壮的复仇大义消解于“煮小米”这等世俗意象中。
与《采薇》、《铸剑》相比,《起死》中重复性手法的运用构成文本的一种“对话性”隐喻特征,该小说从语词到场景说明、结构设置等都有这方面的表现。庄子拱手向天念诵的咒语在小说中两次出现:“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陈宿列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1]491这段混杂《千字文》《百家姓》的语词在小说中的重复性设置,既有语言上的戏拟效果,又是小说完成情节突转的重要关捩点:第一次设置让庄子“起死”汉子成为可能,第二次设置让庄子陷入困境成为必然。《起死》原典本为《庄子·至乐》篇中的一则寓言。在寓言中,庄子与汉子的形而上对话是在庄子“梦”中完成的,“起死”行为并未发生;在鲁迅小说中,“起死”虽成为事实,但依然应该解作一种隐喻象征,是作者为实现庄子与汉子对话从“形而上”转为“形而下”的艺术构思使然。从文本戏剧冲突的走向来看,《起死》主要为完成对庄子故作超脱的虚伪哲学的声讨。顺着这个逻辑,庄子逃离后小说对巡士和汉子对话的叙写可能会给人画蛇添足之感,因为在那段结局式叙写中,任何矛盾都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从巡士和庄子都狂吹警笛的动作设置来看,小说结局的叙写大概并非闲笔。
二、《故事新编》中的句段重复
鲁迅小说结构安排上的精当一向为研究者所称道,美国学者威廉·莱尔在《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一文中曾特别谈到鲁迅“民谣式地反复使用同一词汇、道具、以至人物,建立起故事的基本框架”[2]334的“重复”特征。在《故事新编》中,这种“重复”性在词汇之外,甚至还延伸到了段落、篇章。关于《补天》中人物语言前后呼应的重复性特征,笔者曾撰文《鲁迅〈补天〉的“对话”诗学》作过探讨。[3]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在描写女娲造人之前,曾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1]357
这些色彩浓烈(石绿色、血红)的描写犹如一曲激情赞歌,为女娲将要展开的一场伟大瑰丽的创作行动作出预示。然而,几乎还是这段描写,在女娲补天耗尽全身力气时又重复出现: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1]365
石绿色的浮云不再有,忽明忽灭的星也已隐退,只剩下一个冷而且白的月亮映衬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女娲由“不理会”周遭环境的变换,到“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完成了自身命运的周转。事实上,那“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在第一段描写中的出现,即是一种不祥预兆,这也使得作者用近乎相同的笔墨完成一曲庄严哀歌成为可能。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说:“的确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种幸福的辩证法:一是赞歌形式,一是挽歌形式。一是前所未有的极乐的高峰;一是永恒的轮回,无尽的回归太初,回归最初的幸福。”[4]在鲁迅的这两段描写里,赞歌与挽歌因素交相混融,文本的“重复”行为制造出一种近乎悖论的美学效果。另外,就小说形式因素而言,“重复”在文本内部造成明显的“对话”性。对《补天》来说,这两段环境描写意味着一个故事的完结,这种结构上的“对话”呼应性张大了文本的意蕴空间,鲁迅寄寓其中的复杂情感也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见。
另外,《铸剑》中也出现了诸如《补天》中的那种片断式重复用法:
笑声即刻散步在杉树林中,深处随着有一群燐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最先头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扑过来。他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1]441
在这里,段落间的重复描写烘托出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为复仇行为的悲壮性定下基调。作者对饿狼吞食肉体的惨烈状貌的两次摹写,也反衬出眉间尺为父报仇的果敢与坚决。另外,正像威廉·莱尔所注意到的,鲁迅极善在“对比”情境下结构故事,比如“音响和寂静相对比:音响在寂静中爆发,表示故事开始;由音响再回到寂静,表示故事结束;静止和行动相对比:故事开始时,种种人和事纷至沓来,进入行动;故事结束时,又回到原来的静止状态”。[2]334同样的,悲、喜剧因素的交相运用亦属此类“对比”性描写。在《铸剑》中,上述那种阴森恐怖的悲剧氛围与小说结局部分的讽喻性喜剧空间形成“对比”,“对比”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文本内诸种“对话”因素的交相呼应,在小说中构筑成一种独特的美学格调。
张箭飞曾对鲁迅小说的音乐性做过专门研究,她借用音乐中的“节奏”、“和声”等来分析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认为“节奏是某种形式的重复。所有重复都是三种基本方式的演化——对比、对称和序列……重复往往形成规律性的节奏,但是规律并不意味着封闭”。[5]依照这种看法,《故事新编》小说中的“重复”可能正是文本节奏的体现。
三、《故事新编》中的结构重复
在《故事新编》中,《出关》和《起死》两篇小说中“重复”手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词句片断、而直接参与到文本布局的构架中来。从文本叙事特征入手探究小说的意蕴指向,研究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不过此种视角往往能发现一些被表层叙事遮掩的裂痕,为文本解读找到重要突破口。
对《故事新编》小说诗学作过整体研究的郑家建,就在《理水》篇中作者对“大禹治水”事件的叙写上发现了问题:“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大禹治水的事迹在整个的叙述中是被‘虚写化’了,而把大禹如何地被身边的小人们包围、纠缠这一困境最大限度地在文本的叙述中‘前置化’,这从文本的语言上可以看出:关于大禹的叙述语言是在文本戏拟的众声喧哗中,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漂浮着。”[6]这种由“语言”而“叙述”而“结构”的分析方法对讲究文体自觉的鲁迅小说有时非常有效。从小说叙述视点的游移走向来探寻作者的隐含意图,而不为故事的表层叙述所拘囿,一般情况下有益于我们把文本解读引向深入。
在《故事新编》的《出关》中,小说开篇的两部分重复性对称描写,如同发生于老子、孔子之间的两场独幕剧,道具场景不变,时间相隔三个月,人物的对话语言也只在内容上略作调整,句式口吻均未有明显更换,这就从语言的戏拟而上升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描摹。小说关于老子和孔子见面的第二次叙写是这样的:
一过就是三个月。老子仍旧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老子,孔丘来了哩!”他的学生庚桑楚,诧异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他不是长久没来了吗?这的来,不知道是怎的?……”
“请……”老子照例只说了这一个字。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
“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长久不看见了,一定是躲在寓里用功罢?”
……
大家都从此没有话,好像两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孔子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
……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1]455-456
在这部分叙写中,“一过就是三个月”作为衔接两场独幕剧的时间道白,既有承上之“意”,亦有启下之“图”。作者用“仍旧”、“照例”等词语来暗示人物动作序列上的呼应性,并以段落式的机械模仿表明这种呼应并非偶然,本文把这种呼应现象称作结构性重复。“在历史中,海登·怀特说,是尾巴摇狗;是叙事成规决定着一个被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实’。”[7]而在关于“历史”叙事的小说《出关》中,鲁迅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两次叙写,虽也有《庄子·天运》篇中所载故事的大致轮廓,但这种场景性戏剧化处理显然属于海登·怀特的“尾巴摇狗”行为。
这两段重复性描写在小说中的叙事职能,即为完成老子出关原因的叙写。在《〈出关〉的“关”》一文中,鲁迅说:“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8]在《出关》的两部分对称性描写中,鲁迅的这种“孔”“老”观就表现在孔子老子的两段对话里。事实上,这也几乎构成了两场独幕剧的唯一叙事内容。也就是说,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的结构性重复,一则出于文本整体戏拟化效果的考虑,二则是为便于完成孔、老之间两次对话内容的“对话”。另外,在这两部分重复性叙写中,作者重在人物动作、状貌的描摹,如“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大约过了八分钟,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等,人物言谈对话的内容倒在其次,关键是让孔、老观念对话的两次内容宛如镶嵌在套路模式下的动态因素,既成为支撑叙事行程的关键内容,又与文本的整体戏拟性氛围显得不那么和谐。此种创作方法可能是作者历史观念支配的产物。鲁迅说过:“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9]这种循环论式的历史观念使得鲁迅的小说常常借“历史”对“现实”发言,表现在创作手法上,即带有一定程度的隐喻性。以《出关》的前两部分描写为例,鲁迅不像郭沫若历史小说中常常表现的那样,让历史人物代自己立言,借他人之酒浇自家心中块垒,他是直接与历史人物对话,在重复性的戏拟摹写中“抑老”而“扬孔”。“出关”,作为老子思想观念退避的行动选择,也并非良善之策,就像小说结末中关尹喜所说的:“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外面这里来的。”[1]463因此,从隐喻层面来讲,“出关”更像作者放逐老子思想的象征摹写,这与小说开篇的戏仿式重复一起,共同构成文本意义空间的复杂呈现。
鲁迅是一位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重视语词的运用、结构篇章的设置,在他的小说中,“对位”性的戏剧现象经常出现,这是文学家鲁迅对世界发言的独特方式。“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这种手法在《故事新编》中的频繁出现,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不止于文本内部的相互生发,更在小说文本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自由出入。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美]威廉·莱尔.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M]//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3]张素丽.鲁迅《补天》的“对话”诗学[J].名作欣赏,2011,(1):77-79.
[4][德]瓦尔特·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J].张旭东,译.天涯,1998,(5):147.
[5]张箭飞.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43-50.
[6]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41.
[7][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0.
[8]鲁迅.且界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0-521.
[9]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9.
“Repetition”from“W ords”to“Discourse”——Structural Feature of Old Tales Retold
ZHANG Su-l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Sanhe 065201,China)
Lu Xun’s Old Tales Retold indicates a vital textual phenomenon repetition,which can be shown by word repetition and paragraph repetition.Repetition is a kind of contraposition,which contributes to Old Tales Retol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dialogue.This technique is not confined to the internalmeaning of the short stories but symbolizes a kind of structural facts in the story text.
Lu Xun;Old Tales Retold;story structure;repetition
I210.6
:A
:1672-3910(2013)05-0053-04
2013-05-10
中国地震局2012年度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20115);防灾科技学院第三批重点建设课程资助项目
张素丽(1982-),女,河南平顶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