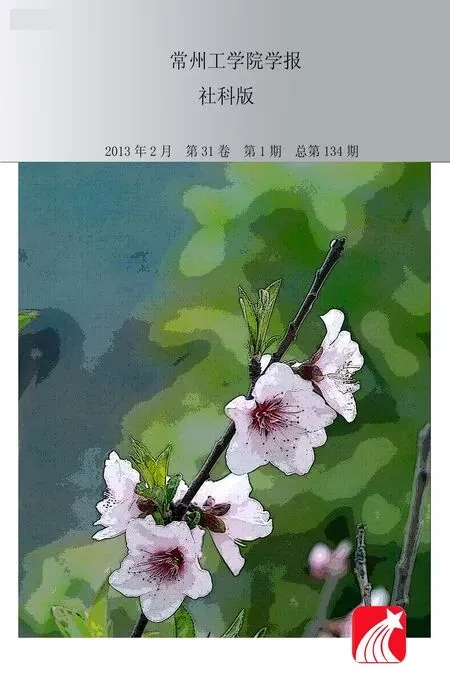中西合译中的变通性研究
——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译介为例
毕婷婷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泰西新史揽要》(以下简称《揽要》)是一部由西人李提摩太口述,华人蔡尔康笔录的外国历史性著作,叙述了19 世纪欧美各国的发展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此书由英人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1823—1881)原著,原名《19 世纪——一部历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1880年在伦敦出版),被断语为“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1]163,然而其中译本却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2]3。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译界的注意,深思翻译过程中的功过。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对其进行点评,却都忽略了本书最大的特点——合译。合译,古已有之,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讲究变通,即适应与选择。本文将以《揽要》在晚清社会的译介为例,通过对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译中的翻译思想与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来反观变通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从而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方面的重视,为当前基于互联网的集体分工翻译提供借鉴。
一、矛盾主体间的变通与译本的选择
变通,即为满足某种需求而不断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译者首先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才能在这个环境中得以生存,逐步实现自己的需求,否则就有可能被翻译生态环境淘汰。”[3]3
作为一个虔诚的福音传布者,李提摩太来到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教徒,传播教义。他学习中文,投身赈灾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底层百姓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然而这条下层路线却未使其在华事业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传教依旧徒有虚名。李鸿章曾指出:“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2]467这席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反省,开始将重心放在中国的读书人身上,尝试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上层精英路线。时值晚清时期,国家由强变弱,国民苦不堪言。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倾向。蔡尔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拥有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报国无门,只好另辟它径,投身报界,企图通过引进西学改变国家命运,实现自身鸿鹄之志。
为适应晚清特殊的翻译环境,合译主体已开始改变各自的初衷,本能地另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李提摩太放弃原有的下层传教路线,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蔡尔康亦弃科举,转而投身报业,引进西学知识。然而,合译主体间依旧矛盾众多。一方面,“晚清来华传教士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夸救世之口,兼有不平等条约保护,造成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心理距离较大,文化传播的阻力也大”[2]13,中国文人排斥宗教书籍,李提摩太的事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西语言本源自不同语系,文化间差异甚大,加之长久隔阂,通晓者寥寥无几,翻译更着实不易,西学输入也因此困难重重。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适应另一种文化,适应另一种语言,适应不同的编辑和出版商,最后还要适应读者群”[3]35。此时,中西合译主体为适应对方的文化、语言已各自做出让步,然而在“读者群”问题上,二者的需求却难以满足,必定要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方法来解决矛盾。甲午战后,摆在民众面前的是关乎国家生死的前途问题,有识之士希望借鉴西方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改革经验挽救国家命运,因此西学输入刻不容缓,中国文人不得不与西人合作,采取西译中述的合译形式。这期间中国文人选译的必定是那些进步人士感兴趣的科学书籍,而对宗教书籍予以排斥,这种强烈的排斥感给传教士的传教事业造成了巨大的阻碍,然而,李提摩太为实现上层传教路线不得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只好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既含有基督教思想,同时又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科学社会书籍,然后再通过这些书籍感化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得到他们的支持,实现在华传教。
《揽要》就是这种本能适应与有意识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它在西方史学界价值不高,但所传递的信息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犹如“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4]序1。强烈的经世致用、以史为鉴色彩,使它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二、文化碰撞在翻译中的变通处理
随着晚清政府社会地位的不断下滑,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也因国家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而遭受质疑。强烈的文化地位冲突必定会给中西合译带来巨大的阻碍。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合译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中西国家地位问题,而这在书名的翻译中尤其突出。
此书原名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被译作《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介绍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详情,后更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西例以耶稣降世后每百年为一周,今适在十九周中也”[4]序3,故翻译为《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更为贴切,为何要以“新史”代替“第十九周大事”呢?除了所译史书有别于中国旧史书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西文化地位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人心里更是根深蒂固,这些知识分子心中始终印有“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然而所译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以西历为标准,忽略了中国沿用数千年的历法,无形之中会产生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自然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满,造成文化冲突。李提摩太的最终目的是“布道”,因此他不得不更改译名,采用“以西顺中”的策略,在不损害中国文化尊严的前提下传播西学知识,从而为进一步的“布道”铺平道路。
类似的翻译变通处理在书中比比皆是,例如开篇第一卷的标题,原文为“Europe at the opening of the century”,即“创世纪/周之初的欧洲”,而《揽要》以中历为准,译为“欧洲百年前情形”;又如在翻译标题“Louis ⅩⅤ”及“French nobles”时,以中国传统纪传体小说标题的形式变通原文,译为文人业已熟悉的“法国鲁意王第十五小传”以及“法国世家小传”。为了满足各自的需求、避免文化冲撞,李提摩太与蔡尔康不断适应对方文化传统,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既顺应中国人思维方式,又暗含传教动机的译法,甚至出现了不少“误译”。
在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麦肯齐原作中多次提到“revolution(革命)”一词,李、蔡译本中均灵活处理为“乱”或“整顿”“变易”,避免提及有关暴力推翻统治阶级的事迹。这一方面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学目的,即以西方教民、养民、新民、安民的经验为中国改革推波助澜,提供借鉴;另一方面,这样的变通也彰显了李提摩太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消极态度,企图通过美化西方历史来赢得中国文人的信赖,从而使上层学术传教路线得以进行下去。
李提摩太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进行“布道”,然而文人对此极为反感,他只好有意识地将基督教的知识糅合进《揽要》中,无形中向这些读书人宣扬教义,因此《揽要》中也出现了不少“增译”,例如:
“Over this constituency the king of Austria exercised the authority of emperor,representing in a shadowy way the old Caesars,whose dignities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inherited.Each of the petty states might be required to contribute troop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empire.”[5]69
“其自主之通商镇集亦颇与意大利相似,而奥地利阿国、普鲁士国迭为雄长,有时奥王更俨称为皇帝之尊,以辖治日耳曼,自言其权势位望皆罗马教皇之所给予,遇有战事可檄召诸小国抽调额兵以为臂助。”[4]47
在翻译奥王地位时,李以“皇帝之尊”翻译原文的“the old Caesars”,方便中国文人了解西方权势,而紧随其后,李又增译“自言其权势位望皆罗马教皇之所给予”,以此便在无形中将教皇地位驾驭在中国皇帝之上,从而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基督教的重要性,方便在华传教事业的拓展。
晚清社会,中西文化矛盾尖锐,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合译中不断变通,灵活处理,最终完成这部影响深刻的译作。
三、史书翻译策略的变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海战,是中国史学从封建旧史学中脱胎出来,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6]4这一时期,摆在人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社会现实,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调适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接受心态,随时迎接外来世界的挑战。
《揽要》是一部西方历史学著作,翻译之时正逢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变,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翻译时试图以史学做武器,通过借鉴西方改革历史,以抵御侵略、拯救国家,因此,译作中有机融合了许多旧学新知,从而将史书编写体例推向新境界。
在史书叙述结构方面,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接受环境,李、蔡二人采取中西合璧的特殊史学形式,即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纪传本末体与西方卷、章、节合成的史书体例相糅合。两者合二为一的卷节体不仅能分篇综述纵横交错的各种政治事件,而且能清楚地表述纷繁复杂的历史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前因后果。
在史书翻译的具体形式上,李提摩太与蔡尔康亦创制了新体例。首先,“是书所纪全系西事,在西人之习闻掌故者自各开卷了然,及传译华文,华人不免有隔膜处,故间采华事以相印证,原书则无是文也”[4]5。为方便中国人阅读,李、蔡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在西历后辅以中国历法,便于印证岁月。中西历对照,既避免了中国人产生迷惑,又形成了强烈的中西社会现状对比,鞭策着中国人加快改革的步伐。其次,“是书以国为经,以事为纬”[4]5,在内容的编排上,李、蔡突出各国世系,清晰的脉络更加有助于中国人了解泰西各国的状况和发展历程。再次,“读他国书莫苦于人地诸名记忆不清”[4]6,因此,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完成译作后又分章节作人地诸名表一卷,使初次涉及此书或对外国历史不甚了解的人能初步熟悉地名、人名及各种事件的性质,从而便于理解原文。最后,书中随处可见各种注释、按语,以中国人所熟悉的事物解释原文抽象陌生的名词、句子。例如,“国家选练”后辅以小字“如今中国旗绿经制额兵之类”;“况相争至二十五年,其杀戮而死亡者生灵不下数百万”后又缀以按语“中国近年遘发捻诸逆之乱,兵民与贼之惨遭浩劫者,乃不下数千万”。中国人所熟知的概念、情况与原文形成对比,更便于他们了解泰西各国情况。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揽要》中创造的史书翻译新条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原文丰富的知识,加上译文清晰易懂的脉络,拓宽了史书的阅读市场。这种体例,此后的史学翻译家们纷纷效仿,一直沿用至今。
四、结语
传统译学注重原文与译者的关系问题,译者的翻译必须紧紧依据原文,受限于原文;《揽要》的成功取决于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在合译中的灵活变通,将译者从原文中解放出来,在本能的适应与有意识的选择中找出最实际的翻译方法。这种变通性在当前基于互联网的集体分工翻译中极具实践意义,但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如果不很好地把握译者解放的度,就会与原文背道而驰,合译个体间更难以谋和一致。至于如何把握译者解放的度,不妨跳出传统,从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去深入研究。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M].(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Mackenzie Robert.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M].Chicago:Fairbanks,Palmer & Co,1881:69.
[6]李洪岩.中国史学的近代化[J].学术研究,1999(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