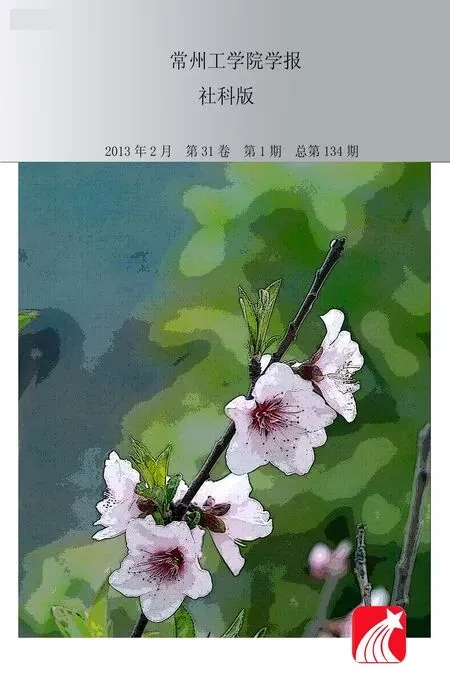融汇前沿知识 凸显创新品质
——评古远清先生《当代台港文学概论》
张益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古远清先生的《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于2012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刚出炉的教材,它凝聚着古先生多年来的研究心血,显示着他开阔的学术视域与精雕细琢的文学品鉴能力。就教材而言,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台湾文学史或香港文学史倒是不少,然而,将台港文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分两段撰写,目前尚不多见。古先生在后记中说这样的体例安排“确实有一个长久积累和思考的过程”①,显然,这不是轻举妄动或者一时兴起的产物,而是经过长久性的沉潜和打磨的结晶。在此基础上,教材必然会承载着古先生独特的“发现”和“发掘”,给人们带来惊喜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台湾、香港自古就是中华民族行政区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被殖民主义者觊觎的主要对象。1894年中日战争后,台湾一度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阶下囚,这成为整个华夏民族史上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光复后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虽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有新的发展,但是与大陆的一度隔绝也引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无限思念与怅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互通以后,有着游子身份的台湾人的“乡愁”情愫才略有释解。而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香港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此,香港不得不听命于大英帝国白人的殖民统治。但是意识形态的迥异不能改变中国是台湾、香港等中华儿女的华夏之根的事实,台湾人、香港人身上自然涌动的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不会被殖民统治切断的,华夏文化——这一根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华夏子女的心灵深处。可以说,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精神已成为包括台港在内的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便日本执政者或港英政府推行种种“民族分裂”“语言同化”政策,都不能斩断台港人的“华夏情结”。另一方面,台港在近代经受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遭际与文化语境。从地理学上看,台港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处于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前沿,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历史的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在这两个区域较早地得以运演。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社会和市场的繁荣给台港带来了从外(社会层面)到内(精神层面)的冲击。“5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呈现出西化的发展趋势。”②而在香港,商品经济“激发了与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相抵牾的商品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迥异于玄学清流的经世致用作风和区别于禁欲主义的讲求实惠的享乐精神。这一切并不以理性见长地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却以实际行为渗透在市井小民感性的世俗生活里的文化特征,无不在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中,获得充分的发挥。这是香港文化最基本的内核”③。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多元化的特点在此得以准确地表述和流露,再加上“香港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或少受两岸主流话语的干扰,才真正做到了人才来去自由”④。很明显,正是基于历史多种文化政治的合力推演,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中的香港文化姿态才有着不同于大陆、台湾的脉络走向。由是观之,与内陆相比较,当代台港人在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情感诉求等层面显然有着较大的反差,甚至是趋向不同的两极。这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自然不能无动于衷,由文化这一大语境所衍生出来的台港文学的样态和姿彩必然呈示着诸多“异质性”元素,台港人独特的社会心态和心理欲求、曲折的命运走向和历史冥思、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价值追认必然在文学这一形式之中得以命名和敞显。
而古先生的《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便给我们描摹出这一繁富庞杂的台港文学风貌。本教材可谓汇通了前沿知识,凸显了学术创新的品格。下面笔者欲从三个层面谈谈这部教材的创新之处。
一、视域的开阔性
文学“作为写作集体的文学和作为时间系列的历史之间”⑤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也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⑥可见,文学本身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对文学之外的事物的关注与体察,与台港文学相联系的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时代风尚等大环境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自身裹挟的文类演变、艺术创新、思想承继等也是编史者理应关注的重心所在。此外,作家的艺术取向、个人经验、身份诉求等极富个人性的艺术内蕴也是文学史叙事中的必然要义。本教材将时间限定在1949~2010年之间,系统钩沉60年来台港文学的发展历程,显示着古先生开阔的学术视域。
首先,教材从宏观层面时而进行全局性的厘定,时而从微观方面开展细致入微的论证分析,在作家作品分析的一些章节,则将宏观审察和微观评述有机地结合起来,资料翔实,视界开放。
教材分为八章,“导论”部分概述了台港文学60年的历程,在总述中,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紧密结合时代、政治、思想的变迁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进行阐述。教材针对各种文学类型和文艺现象的演变,各种文艺思潮的兴起和衰退及其背后的缘由,给出了清晰的描述和切实中肯的评价。这其中,“台港文学的交迭与冲突”、“台港文学的特殊经验与问题”两节显示着教材的特殊视界。在纵向梳理文学史基础上,对台港文学进行横向的比较,并在与大陆文学相对照的视域中凸显台港文学的“特殊性”经验。教材在指出“台湾文学的贡献”时讲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文论有着大陆文论家没有的理论深度”、“填补了当代文学的大片空白”、“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关系处理”⑦等,这些观点显然既客观又实事求是,可谓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切实把台湾文学的特质和“异质性”以及在中国文学地图上的重要位置给点了出来,从而彰显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香港文学的特色。在“香港文学经验”的论述中,著者也敏锐地指出了具有“自由身份”“本土立场”特征的港式写作所呈现的“香港造”的区域特色,秉承几代香港人的本土情怀和港人独特的家国情愫,香港独特的文学坐标体系便在教材全方位(宏观视角)的观照中展现出来,别开生面。
在第一章“文学思潮”中,著者除了采用宏观叙事的模式之外,也恰如其分地进行一些微观分析,让文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小“事件”浮出水面,对这些“事件”或作渊源式的考据分析,或作客观性的评定鉴赏,或把事实公布呈现,留给读者继续思考,或将已有的争议暂时搁置,显示着教材直面纷繁复杂的台港文学流变时的敏锐掌控能力和自觉意识。比如:就台湾50年代的“战斗文艺”功用而言,教材讲到:“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兵文学’”⑧,这样的文学写作宗旨显然“要求作家牺牲个人的自由,放弃个人单独的行动和写作主张为政治服务”⑨。论者自觉而醒目的辨别意识可见一斑。而读者有了对此种文学创作动机、旨归的了解,就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进行总体性的体认。接着,论者便以纪弦的一首“反共诗歌”《革命!革命!》为例剖析这一文艺思潮的创作动机,显然,细致(微观视角)的评点比宏观的叙事在此更显得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教材也没有一味地受意识形态的拘囿,而是从更高的立场和文学本身出发,对于台湾文学中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化分离创作行为、政治干预等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解剖。教材指出:“一是它具有动乱年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二是作者们常常把反共与怀乡联系在一起,在思念故土故乡时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三是在内容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⑩显然,这些论述都是建立于著者对文学文献的认真解读基础之上的,是论者不带任何阶级偏见品质的体现,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于这时期的文艺进行新的审视。这不能不说是该教材的一个亮点所在。
教材从第二章到第八章都以微观剖析为主,宏观叙事为辅。古先生多年来从事台港文学的教育和研究,他既重视文学学科的自由性、审美性、创新性等特性,又不忽略文学的教育性、指导性等社会功能。在“现代小说”一节,编者注意到了小说在现代报刊和杂志以及市场化运作下的牵引作用,也关注到西化风气影响下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事实也证明,正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才形成了台湾6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的高潮。教材也正是精准地把握住中西文化碰撞、异质文化植入这一大的趋势,因此,一批作家的创作风貌以及现代小说的特质都被教材给予精准阐析。以白先勇为例,教材设置专节介绍了他的现代小说成就,从创作历程的分段描述到小说主题的分点概括,从小说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归纳到小说风格的独特品位的阐发,显示着古先生扎实的学术能力和细致入微的艺术品鉴力。
其次,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80年代后文学商业化、文化工业化大潮的来临,教材也紧紧抓住市场和受众两个重要因素,从接受者和市场运作的角度客观评判台港文学的复杂运演态势。今天大陆网络文学的繁荣昌盛以当年的“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肇始,一时间在数字与市场同谋运作下滋生出大批畅销书作家和“网络作家”。针对这一文学发展态势和一场大众语言、思想的狂欢,论者指出了网络文学的优势:“增加文学阅读人口”,“为通俗文学的流行开路”,“降低了平面媒体的垄断力”等,都给人启发和思考,能够让人看穿“网络狂欢化”背景下的文学运作规律、生成方式的变革及其隐藏着的利与弊。
二、体例的创新性
在台港文学史的编纂过程中,有人采用时间线索,有人以主流名家名作为线索,还有人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演变视角切入以突出与大陆文学的相似性、继承性,而消弭了异质性和变异性。不同于以上的编写传统,古远清教授采用的是按照时间上的历时性发展为脉,突出共时性背景下的台港文学发展演变的复杂风貌,一横一纵形成时间上的一个坐标系。在此基础上,他按照文类对台港文学进行细致的爬梳和论述。
首先是历时性的梳理。教材以时间的纵轴为序,“导论”部分抓住了台湾文学发展的“竹节式”特征,从50年代的“战斗文艺”开始展开论述,到60年代的现代文学思潮,至70年代的乡土文学、80年代的后现代文学、90年代的女性文学和后殖民书写,最后到新世纪五花八门的“文学乱象”。第一章到第八章则细致勾勒和甄别台湾文学每个阶段的思潮特征、作家、作品、文艺批评,从文类上讲,台港小说、散文、新诗、话剧、通俗文学、评论等基本上涵盖了当代台港文学的所有类型,这样,台港文学60年历程按照章节的顺序一一获得呈现。
其次是将学术见解和观点融汇于文学史的客观叙事中。韦勒克在论及“文学史”的书写时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显然是无意义的事件系列分离成本质的因素和非本质的因素。”因此,文学史的编写一方面应将文学置于彼时彼地的语境中进行观照,另一方面,文学史又不同于还原历史本身的元叙事,它应该加进去历代编史者对文学事件和作品的批评甚至对于这种批评的再批评。可以说,以上两方面制约着编写者的视界取舍,也决定着文学范畴和类别的厘定。能否做到前二者的兼顾和交融,甚至决定着一部文学史撰写的好与坏。古先生的这部教材做到了这两个层面的很好的结合。在论述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时,他总是将文学产生的演变缘由以及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交代清楚,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轮廓,让受众对作家的生存环境和语境以及文学的外部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从社会的、美学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种种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进行极富个人性又不失客观性的学术赏鉴。可以说,古先生抓住了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内部环境之间的交融和链接,真正遵循着文学发展的规律,将叙事和批评的运行置于这一规律的体系之内。
再次,在每一节的最后,教材还增加了两个板块:其一“思考题”,其二“延伸阅读”。“思考题”或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或具有抽象的思辨性,或测试读者的概括能力,或具备比较视域的超越意识。问题的提出建立在对文学史主体描述的基础之上,可以指引读者对文学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甚至做下一步的延伸性研究和琢磨。由此,相对直观化、平面化的文学史描述被引向了深度思考和理性认知层面,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现象和规律共链接的契机和平台。“延伸阅读”板块链接的有他种文学史、作家传记、难度较深的理论专著,也有较为通俗的记述性报刊文献,这些都会引领读者做下一步的“延伸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于作家和文学现象的更广领域的认知,带动他们进入更深层次的阅读实践。
最后,本教材在编写上配置了插图,有作家照片、电影预告、书影、作家漫画。版面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有利于读者从文字中走出来,在视觉上对于作家和创作进行品味和联想,直观而又形象。这一点打破了以往教材的单调性,增强了教材的视觉刺激和美学效果。
三、论证的严密性
古先生的此部教材追求学术上的客观性,论证上的严密性。首先表现在教材所具备的客观的文学史观。
“历史过程会不断地产生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的而且是不可预言的新价值形式。”正像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文学史撰写的一个任务就是编史者对于历史价值的挖掘和发现。这样必然要求论者除了具有高屋建瓴的视域之外,还要具备严谨严密的论证能力,在史料的描述上实事求是,在论证上要做到有理有据,恰如其分。只有这样,文学史的编写体系才会显得科学,每一个观点的下定和结论的落脚才会显得平实、可靠。古先生说:“故写台湾文学时尽可能有包容性:不能只写‘外省作家’而不写本土作家,或只写‘统派’而完全忽略‘独派’的存在。”有着强烈学术敏锐度的古先生一向追求学术上的客观真实。还原历史,就是要打破意识形态营建的种种壁垒,冲破历史延伸出的重重迷障,给文学现象和作品价值以客观的剖析和评价。所以教材尽可能挖掘原先囿于意识形态而被遮蔽的文学资源。“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教材显然暗合了这样的史学认知理路,将以往文学史因为各种原因省去略去的文学现象和作家重新召唤回来,将那些原先被埋藏在角落里面却闪耀着文学之光的宝石拉回到“日光灯”下,给其新的平台,让人们对于此类文学事件进行重新认识和合乎逻辑的评判,从而也还之以原貌,让那些逸出历史的“边缘文学”重新发光发热,凸显着教材的客观历史主义立场。这其中,比如“后遗民写作”问题、乡土文学论战的问题、“张腔胡调”的内涵都是以往文学史中较少论及或者根本不提的一些概念,但是古先生在本教材中尽力“除蔽”,尽量将更可能多的知识汇入其中,让人们对于这些曾经发生过的文学经验事实进行阅读和认知。
其次,教材显示着相对自觉的台港意识。古先生多年从事台港文学研究,他每年都要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购买大量的书籍资料,搜集珍贵的研究资料。可以说,这些资料和信息开阔了他的研究视野,不断更新着他的文学观念,也树立其相对独立自觉的台港文学史编纂意识。针对台港文学类型的演变和文学样态的发展,教材都能够从台港文学特殊发展背景上进行权衡,如“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到王德威”一节。教材对三位批评家的成就和贡献的论述,都能够从他们自身所处的不同于大陆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语境出发,抓到了批评家学术品格上的自由性和文学意识的独立性特征,这样,评定就显得中肯全面。教材中自觉的台港意识避免了将台港文学仅仅定位为中国大陆文学的陪衬和补充,从而引起读者重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辟性和独创性意义,让读者对这种相对“异质性”的文学形态有了新的认知和评判。
再次,在材料的援引上,古先生力争做到全面而又实证,细致而又确凿。以“白先勇:台湾现代小说的旗手”为例,引用的资料从欧阳子著名的《王谢堂前的燕子》(1976年,台北,尔雅出版社)到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再到张旭鹏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脉络中的同性恋》(北京,《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资料与时俱进,显示着不同时段不同论者对于白先勇小说的跟进性关注。因此,古先生教材的观点也显示着资料和信息的丰富性,知识的不断延伸性和新颖性,不会给人以陈旧过时、走套路的感觉,而是凸显着他的创新资质。
最后,教材在对于文学现象的解释和语言风格的把握上,显示着严密而又睿智的特征。“最具香港特色的框框杂文”一节中,教材关注到香港报刊专栏文学的繁荣现象,这种“怪论”文学被余光中称为“贩文认可区”,教材将这种框框杂文的八大特征给予总结,让人认识到香港杂文和大陆、台湾杂文在书写、形式层面的差异。其中的很多“总结”和“命名”本身极富“智性”色彩,显示着论者思维的缜密、逻辑的有序。不仅如此,教材还详细分析了香港专栏文章繁盛的原因,“不单是经济繁荣促成,也有言论自由、教育、政治等制度的配合”。台港的通俗文学十分发达,在上世纪两岸互通后大量涌入内地,武侠、言情以小说、剧本、影视剧的形式冲击着几代人的神经,这不能不归功于金庸、琼瑶、三毛等人的小说的异质性和自由性等特质。在第六章“通俗文学”一章中,教材分析了这些特质,从作家艺术创作特征和受众心理需求两个方面论证了通俗文学在民间受欢迎的原因,教材也对作家之死(如三毛)及后世的品评给予客观的分析,“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猎奇的综合反应”。显然,对于这位才女的死亡缘由,确实不能归于一种单一的解释。这样,教材对于“度”的把握和对于“界”的指涉既有概念上的科学性,又有着范围上的明确性,显示着文学史应有的缜密与严谨的属性。
陈平原说:“‘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此言不虚。古远清先生的教材因为具备了视域开阔、体例创新、论证客观等特征,必然会成为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的案头藏书。当然,作为一本当代文学教材,也必然会在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课堂实践中留下好的口碑。
注释:
③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⑤帕特逊:《文学史》,收入《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⑥(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