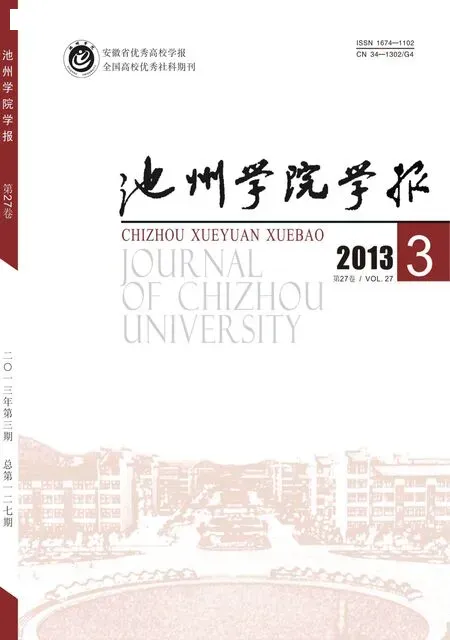“多向主体”教学模式初探
王翠薇
(池州学院 现代传媒系,安徽 池州247000)
大凡世界上所有的旧事物和旧模式,乃至新事物和新技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两面性。教学新技术和新模式也不例外。最近十余年来,随着多维化、智能化、广域化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不断引发人类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教育新技术对提升教学变革的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它已经或正在成为新的教学变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但是另一方面,教学过程大量引入新技术,教学模式发生新旧变迁,也潜伏着某种负能量的可能因子。我们通过大量的教学反馈发现,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各有所长,不能一概而论。在现代教育新技术降临之初,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常常被人诟病,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非一优百优,无懈可击。有人认为,只要教育技术先进了,教学观念和方式也自然先进。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对于现代教育新技术,过度崇拜和极力回避都走向两个极端,都不是对待它们的正确态度。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对新技术、新模式扬长避短,进而在新的界域中承旧创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多向主体”教学模式,正是基于对新技术时代教学变革的得与失进行反思与再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1 “单向主体”教学模式的缺陷
所谓“单向主体”教学模式,是指以施教者为主体或者以受教者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也可以称为以“教”为中心或者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共同的表征皆为“单向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还表现出下述缺陷:
其一,“单向主体”教学模式中的教师与学生处在非平等的地位。这里的平等不是指人格意义上的,而是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主体不处在对等地位。以“教”为中心,课堂教学是只见教师不见学生的,类似于“见树不见林”。因为它主要凸显教学系统三要素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例如,解放初期从苏联传入我国的凯洛夫五段教学法,便是这一教学模式的范型[1]。其特征是教师占据绝对的制高点,学生成了向下“俯冲”的开阔地。教师的任务是端起知识之“壶”,向渴求知识的众多“瓶子”一味地灌输——不管“瓶塞”是否打开,打开多少,反正就是往里面灌注。不能不承认,这种通过高位差造成压力来传输知识是有效的,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而以“学”为中心,师生双方的主体也不完全处于对等地位,类似“见林不见树”。新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媒介的丰富,也使得教师的主导不断弱化和淡化,学生自主猎取、自我控制。
其二,在“单向主体”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的互动性比较少的,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互动。在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提问,学生被动回答;即便教师说错了,也不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被忽视,认知主体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成为被动的外部刺激的接受者。在新技术条件下,多媒体课件控制了课堂教学,教学过程完全技术化,教师的作用往往退居次席,甚至成了放映员和操作员,那种神采飞扬的讲解已鲜见。与此同时,因材施教的针对性受到削弱,学生也很难打破课件限制,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
其三,在“单向主体”教学模式中,师生双方难以达到双向激活状态。当人的主体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由此引发另一主体的高度亢奋状态,我们称之为激活状态。教学过程是最佳状态是双向激活,这时的教与学的主体如同齿轮配合默契,课堂气氛热烈,双方都开动脑筋,心灵间撞出智慧的火花,对教材的理解常常“逸”出预先设计。最好的教学是教师对学生的心智给予启迪,而学生的妙想灵思也打破了教师的设计,使对教材的理解更丰富,教学的思路得到大大的拓展。
从“单向主体”教学模式的诸种缺陷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传统教学模式还是新潮教学模式,检验它们的重要尺度在于,主体间的平等性、互动性和激活性是否达到基本的指数。在我看来,并非教育新技术使用得越多,教学效果就越好,或者教学手段先进了,就意味着教学观念必然先进。归根结蒂,教育的人文主义是永远不可忽略或轻视的。对于抱残守缺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我们都必须加以抵制。
2 建构“多向主体”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我们发现,“单向主体”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病,并不在于主张发挥教师或学生的主导作用,而在于把教师或学生的单向主体作用任意夸大,并达到绝对化,类似于“单边主义”。与此同时,最近十年来,教育界也有提出“双主模式”,即介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之间,它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两者的长处吸收过来,而把两者的消极因素加以避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但这一“双主模式”主要是建立在静态的基础之上,没有提出主体间的平等性、互动性和激活性,作为这一模式的必要的限制和指数。
在这些教学模式中,教学系统三要素中学生与教师被视作主体,成为能动的双方。但这里忽略了一个潜在的重要主体:即教学要素中的教学内容(知识对象)也是一种主体存在。而这一存在正是“多向主体”建构的基础。
其一,教学内容的主体性,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种主体间性。教与学的关系,不完全是认知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也是各个认知主体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教学过程仅仅是解决学生与科学、人文等知识对象的问题。其实不然,教学过程还应包括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学生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也包括教师和学生共同面对某一作家(或科学家)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认知对象并非纯客观,在很多情形下也是一个主体。例如,讲解一篇莫言的文章,师生必须共同面对在这篇文章中呈现的作者主体。
其二,教学内容的主体性,体现在知识创造的主体意志在知识中的沉淀。例如,当我们面对核物理这一科学知识时,我们同样要面对科学家的主体意志,即核能是一把双刃剑。任何知识的发明与产生都是主体行为,尽管知识是用来反映客观世界,但是知识最初产生的那个主体意志并未消失。
其三,教学内容的主体性,体现在知识再加工时所叠加的主体意志。当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可能面对的不再是知识最初的原貌,而是经过教师、教材编制者、各种媒体信息编制者再次加工后的知识,它们打上了强烈的主体意志的烙印。例如,对《红楼梦》的解释已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红学”,而且还分成不同的流派。在新技术广泛用于教学的今天,这种经过再加工的知识随处可见。例如,对某一软件的创造性使用,可能会超出原软件的设计。说到底,教育是一个不断加工、阐释知识的过程。孔子的思想便是他的弟子一代代加工的过程,《论语》并非孔子的原著。
由此可见,教学系统三要素的关系不是主客体之关系,而是主体间之关系。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忽视了知识主体这一“第三主体”。笔者提出“多向主体”教学模式的构想,其宗旨是建立一种主体间多向流动的相对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特征,除了上述平等性、互动性和激活性等要素以外,这里重点阐述在动态条件下教学要素间的 “多向主体”的运动。
首先,建构“多向主体”教学模式,必须认识和确立作为教学结构要素的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和知识主体的多种关系。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认知对象并非纯客观,在很多情形下也是一种主体存在。教师最初是与知识主体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这才使施教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互动成为可能。而学习主体在接受过程中,也必然要与知识主体发生联系,并与施教主体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互动成为可能,也使双向或多向的激活成为可能。例如,一篇课文的潜在意蕴未被教师发现,经过课堂激烈的讨论与争论,教师发现备课中的理解有偏差,没有与作者主体形成真正的理解互动,于是及时地加以修正,并在课后对这一问题加以思考,至少使这篇课文的讲解水平得到提升。在传统教学中,尤其是文科教育,受到社会体制和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对象存在单向理解的问题。正如鲁迅论述《红楼梦》所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也是存在的[2]。因为政治需要,一篇包含多种意蕴的文章被解读成为单一指向,说得严重点,这是一种“强奸”作者主体的行为。
其次,建构“多向主体”教学模式,必须在各个主体间建立一种能动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知的多向主体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某一方被压制了而已。“双主模式”只注重二者的静态确立,却并没有让主体间的关系建立在动态的基础上。只有教学过程中的主体间出现积极的互动与激活,教与学的主体才称得上真正确立。也就是说,认证多向主体之确立的唯一指数,是课堂教学中的良性互动和彼此激活。与此同时,这种“多向”,还指向动态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主体间的自由状态:在不同的某个时间段,教师主体占据主动,或者学生主体占据主动,而他们都受到知识主体的制约。例如,在教师讲授课文的时段,施教主体占据主动导引位置,这时传统教学的长处尽可以吸收之。在传统教学中,优秀教师可以尽情发挥他的主体性,个人风格可以淋漓展现,学生直接面对老师的熏陶和启发,枯燥的知识传输染上了人性的色彩,师生之间眼神交接直至心灵交流、情感交融。综观二十世纪中国各学科大师的成长轨迹,都可以看到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优秀教师的垂范和熏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三,建构“多向主体”教学模式,还必须树立相对开放、自由的教学理念。也就是说,“多向”含有“异向”之义。所谓“异向”,是指现代教育突出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即对不同见解的宽容与尊重。这种思想并非现代才有,其实在古代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韩愈在《师说》中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但是从孔子到韩愈的这一思想并没有真正延续下来,而是在封建集权的体制下中断了。因此在“单向主体”教学模式中,出现“一言堂”也并不奇怪。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单向主体”教学模式也是封闭的、单向流动的。有人作过调查,在美国,学生上课时可以随时打断老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争论,教师并不占据任何话语权优势;而且教师还乐于听到学生刁钻提问和不同见解,因为它对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都有启发。而在中国,除非老师主动提问,学生是不许、不敢或不愿主动提问的,更遑论与老师争辨的;偶然也有个别大胆的学生提出异议,教师会老羞成怒,认为这是扫他的面子,出他的洋相,并以师道尊严加以压制。据相关调查,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与美国的同类学生相比,从总体上说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都明显不如对方,尽管前者的基础知识水平略占上风。这暴露了“单向主体”教学模式的内在缺陷。
近几年来,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颠倒的教室”的新教法,可以作为“多向主体”教学模式的重要例证之一。英特尔全球教育总监Brian Gonzalez指出:颠倒的教室,是指教育者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把知识传授的过程放在教室外,让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接受新知识;而把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教室内,以便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在我看来,“颠倒的教室”恰好体现了多向主体间的关系。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诠释,它们产生于主体因而也带有主体性。学生的知识并非全由老师直接传授,而是学生与这些知识主体进行互动,通过选择自己最易接受的形式来完成。教师与学生在对知识占有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相互激活,达成对知识主体的认同,直至形成新的知识主体。在这其中,还隐含了另一个环节,即教师与知识主体间的互动,对知识主体的全面理解。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与知识主体的互动体现在备课中,学生与知识主体的互动体现在课堂学习中。譬如对一篇课文的理解,学生的疑问往往改变和丰富了教师的理解。在颠倒的教室中,作为教学结构要素而存在的多向主体得以能动地互动起来,可以说是对“多向主体”教学模式的有益探索,尽管它并没有作出这一命名。
3 辩证认识教育新技术之利弊
教育新技术不仅带来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也带来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然而,如何正确地辩证地认识新技术的利弊,对于构建“多向主体”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教育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结构和过程,带来高信息量、多媒体化、网络化的教学手段,能传送语言、文字、图像和活动视频,将教学内容生动、具体、形象地传达给学生,把形、声、色、光,情、意融为一体,通过新技术处理和各种教学辅助课件,创造一个融知识性、立体性、娱乐性为一体的有声有色的教学环境,使动与静、快与慢、远与近、大与小、整体与部分、表象与内质之间相互转化,加速学生的感知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记忆和应用的能力,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无庸讳言,现代科技手段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既带来正效应,也会带来某种负效应。一方面,正如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言:“数字不再是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3]。人类生活(包括教育)已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数字化也容易导致实体教学被抽空,教学内容的课件化和模块化,使独具风格和个性的教学越来越少。事实上,教师对现代教育手段有过度依赖之嫌,忽视了教学过程的人性设计,甚至出现了以“多媒体”为中心的误区,教师临场发挥能力受到压制。这样一来,既不利于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育新技术呢?
在我看来,应当将教育新技术纳入到认识论的高度来审视。现代认识论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使得传统认识论出现重要的转向:把人类认知的对象世界,特别是精神现象不再看作客体,而是看作主体,将认知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由 “主体—客体”关系,转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存在共生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可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行为[4]。由此看来,教师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则是主体间关系。课堂教学其实是“多向主体”的共时并存,也即主体间的共在——教育新技术运用得当,可以使这种共在得到强化。
由此观之,既然教师与教育新技术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那么教师对待新技术的态度理所应当地是“以我为主”,而不是相反。教育新技术作为客体,我们可以作冷静的分析:其一,应该将现代教育技术与这种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加以区分。负效应不一定是教育技术出现问题,而可能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理二者的关系出现问题。其二,现代教育技术本身也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对这种不完善持有清醒的认识,有助于减少它的负效应。其三,现代教育技术只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元素,它与体制、教材、模式、教师、学生等因素,共时构成了一个完整运作的体系。只有这个体系的每一个元素处在相互激活、相互促进的效能中,才能使教学效果最优化。一句话,关键在于操控它的人(包括老师和学生)如何辩证地使用它。因为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是挖掘和激活人之潜能的教育,而这都将关涉如何处理和协调多向主体间的关系,关涉新技术条件下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进一步研究,“多向主体”教学模式的实验与实践将有赖于此。
[1]凯洛夫,冈察洛夫.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20-98.
[2]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6.
[3]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30.
[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