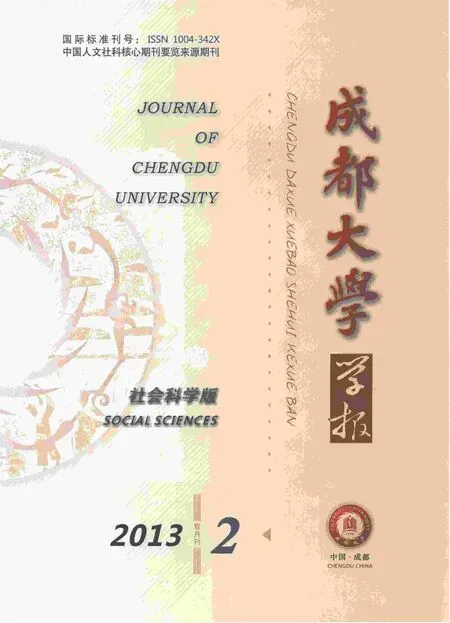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与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
罗曼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红色抒情”,指的是作家将其理想追求寄托在其书写当中,意以抒发左翼情怀,并期望这种情怀成为一种感染群体的力量。
陈映真作品中左翼情感的抒发,经历了一个由隐藏到显露、从曲折到直接、从只言片语到直抒胸臆的过程。在早期它只是小说中抑郁而死的青年,《将军族》中一面在风中摇撼的红旗;到后期开始对白色恐怖时期的书写,《山路》和《赵南栋》对革命的失落直接发出疑问;他对革命承继和台湾出路的思考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的《忠孝公园》。
作品内的陈映真有着丰沛的情感,作品外的他所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陈映真作品中充满了阴郁敏感、自戕而死的人物,绝望气息中带有微弱的希望;而现实中的他则执信于左翼理想,愈挫愈勇。作品的抒情与现实中作家的区别,使人在阅读和理解陈映真过程中产生微妙的差异感。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似乎总有一种无法避免的错位。
出生于战后、成长在1970年代步入社会的台湾知识青年,是对台湾社会政治转折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代,他们在青年时期对陈映真的阅读和接受是值得考量的一个现象。陈映真的红色抒情对成长在197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起到什么作用,是思考陈映真在台湾的当下意义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 徘徊于绝望和希望之间——陈映真红色抒情的变化
早在1960年代初,台湾社会尚在白色恐怖阴影下的时候,陈映真便透过他笔下阴郁故事中堕落的青年,那些带有朴素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物,隐晦地、暗自抒发了其左翼思想被压抑的苦闷,以及对历史真相和当下现实被掩盖的焦虑。
《乡村的教师》(1960年)中的青年吴锦翔自南洋战场回归后,看到破败却仍不失生命的家乡,对重拾曾经的理想生起了热望。出身贫苦佃农的他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而“由于读书”,他秘密参加过抗日活动,以至因此被日本殖民者投到婆罗洲前线。此时他想起改变农民现状的方法,便是从这些农民后代的教育做起,“他觉得甚至自己在尊敬着这些小小的农民的儿女们……务要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1]但是他归来次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①却使他不禁为中国的内乱感到悲哀,为改革这样的中国感到无力。吴锦翔曾“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1937年7月台湾人组成的军队开始被送上战场,因此可以猜想到吴锦翔所读到的正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甚至还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正是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他才参加了抗日活动。此时他为改革的无力痛骂自己“幼稚病”,然而真正让他变成一个“堕落了的改革者”的,是接下来进入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同之前提及的“二·二八”事件一样,此处陈映真并没有明写白色恐怖这一背景,但从“过了三十岁的吴锦翔”可推断出年份(吴锦翔1946年归国时是二十六岁),他现在读的是租回来的日文杂志上的通俗小说,也暗示了书禁下对大陆文学作品的封杀。因此吴锦翔是堕落于现实对其左翼理想的摧毁,死于他在战争中犯下的背反人性的罪责。
同年发表的《故乡》里描写的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执意在焦炭厂里做着保健医师,为工人的健康热情奉献,而后在“相连不辍的风暴”下,在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后堕落成一名赌徒。这名被陈映真赋予宗教式形容的,“变成了一个由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2],他所经历的“相连不辍的风暴”,从时间上推断(“我”从初中升入高中),也恰好进入了1950年代,那么他的堕落便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家道中落,而必须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冷战和白色恐怖,这些并未出现在文中的字眼,却强烈地影响了人物的命运。文末崇拜着哥哥的“我”迫切地想逃离,发出“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的呼喊,其实是陈映真为理想烛火的熄灭所发出的悲呼,而“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也喻指了戒严时期精神压抑的台湾社会。
《乡村的教师》中暗含的从太平洋战争到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再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轨迹,直到1983年写作的《铃珰花》才得到呼应。《铃珰花》开篇即点出背景“1950年”,这在《乡村的教师》的写作年代是不可能的。但是陈映真仍要写作,他必须通过写作来宣泄他因思想情感日益激进而积累的焦虑和孤独。正如陈映真自己所说,创作“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3],他自身的左翼理想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在艺术化的掩饰下得到抒发,小说中无不堕落死亡的青年,支撑了现实中的陈映真继续固守他的思想。
陈映真出狱后的创作,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愈加具有现实主义的风貌,甚至具备了报告文学的特点。197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面向的是受资本主义和美国文化侵蚀的台湾跨国企业中的中国人的处境。《云》(1980年)中工会组织和女工斗争的描绘带有新闻深度报导的色彩,《万商帝君》(1982年)中更有大段的严谨如社会经济学论著的分析。写实的笔调增强了这一系列小说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陈映真对于台湾缺乏对资本主义问题思考的焦虑,因此他要在作品中揭露现实的同时达到“传道授业”的目的。而那辆开往南方故乡的夜行货车(《夜行货车》1978年),记录着年轻梦想和爱恋的录影带(《上班族的一日》1978年),摇曳在空中的由不同劳动部门的帽子组成的花朵(《云》1980年),却像鲁迅放置在夏瑜墓上的花,为通篇冷静刻画的作品平添上一笔暖色。这几篇作品与陈映真前期的小说相比艺术色彩减少了许多,更为贴合社会解剖刀的目的,所以那一笔暖色可以说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投射,是陈映真内心希望的抒发。
由于台湾的戒严状况,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不得不经过艺术的加工和转化。对比早期作品的隐晦暗示,发表于1980年代的“铃珰花”系列,艺术化的目的不在于掩饰,而是为了更好地达到传播的目的。陈映真曾回忆道:
我要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指《铃珰花》),是1983年,还没有解严,远远还没有解严,我的顾虑很大,可是心里面的写作的呼唤很强。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我写《山路》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个故事太理想化了。……于是我第一次考虑到艺术性的问题,尽量地把它写得艺术一点。艺术一点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越是艺术性高,它的歧义性越大,它解释的空间越多。哪一天有人来找,说你哪一段这一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可以解释得更多一点。第二个是艺术性越高,它就变成一种糖衣——这个听起来很工于心计——让人家能够接受这故事。[4]
在整整三十八年的戒严期内,国民党政府对左翼的清扫造成一大段历史被掩盖,又通过国民教育的导向,战后出生的台湾人对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无所知,甚至对于台湾岛内发生过的反帝抗日活动也知之甚少。因此当陈映真为补偿这种缺陷,同时也是抒发他内心的感动情绪,想要把他在狱中直接接触早期政治犯们所听到的真实故事告知于众时,他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故事怎样写才能更好地让读者接受?
陈映真无惧于承认自己是“主题先行的作家”,是“文学工具论者”[5],他认为小说和论文、杂文一样,是表达自己思想的、发表自身言说的方式。他关注的主题,从堕落的理想主义者、大陆来台族群,到越战、跨国企业,以及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内战和冷战造成的民族分裂,他的思考路线贴合着从光复初期到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的台湾历史脉络,也是台湾社会和政治从紧张压抑的戒严到各种思想充溢复杂的1970代、到逐渐放松以至解严的过程。
同时,陈映真也认为小说写作不能忽视其艺术性和审美功能,他说“像三十年代的‘恋爱+革命’的那种文学,是行不通的”,“我不写那样的文学,是因为那样不能达到我的目的”[6]。将艺术性作为糖衣,包裹内里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左翼思想,即使宣传的力度可能因此减弱,但对于当时的陈映真而言尚是一种折中的可取之法。于是《铃珰花》(1983年)的故事是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的,童稚中流动着左翼知识青年被捕杀的恐惧和哀伤;《山路》(1983年)中因愧疚而放弃生命的蔡千惠似乎接续了早期的康雄们,为革命赴死的大哥和过着安逸生活的中产阶级的弟弟之间横亘着距离,对革命失落的质问之外,让人印象更深的却是飞驰着运煤车的长长的山路。陈映真的早期隐晦表达红色情感时的压抑灰暗,此时变成了温暖平和的抒情,带有更为普世的人道主义色彩,即使隐去其左翼成分不提,也是触动人心的。因此《铃珰花》和《山路》收到陈映真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本担心读者看不懂,却发现有人为之感动流泪。而这感动流泪是否因为陈映真真正想要传达的红色情感,则不一而论了。
比起之前的作品中零星的侧面描写,解严后写作的《赵南栋》(1987年)直接描写了白色恐怖时期牢狱中残酷的刑讯,对所刻画的几名革命者参加左翼运动和被捕的经过都有详细描述,“二·二八”和“左翼”也不再是禁语。没有了长年的束缚,陈映真对革命和白色恐怖的述说是从未有过的直陈,他的红色抒情也是从未有过的激烈汹涌。这集中体现在赵庆云临死前梦境的描写:他梦见曾经一同系狱的逝去的战友们,把他的理想和思想都通过人物的口说出:“认识中国,先认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民族内部相互仇视,国家分断,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7],这些积攒在内心数十年的话在“《劳动节》交响曲”的终场合唱中达到高潮。这一部分文字虽显直白,但因为与梦境和音乐的结合而得到艺术的提升。
“铃珰花”系列写作时,正值共产主义阵营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大陆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陈映真一直关注着大陆的“文革”,而且从未全盘否定“文革”[8]。《山路》中蔡千惠的话“如果中国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9]也是陈映真对自己的反问。大陆的变故对陈映真的打击可说不小——大陆尚不能为,何况台湾?对于革命承继问题的悲观,以及对台湾未来出路的思考,明显地展现在这三篇小说中,以至于停笔十二年后,在世纪之交陈映真再度提笔写下《归乡》(1999年)、《夜雾》(2000年)和《忠孝公园》(2001年)时仍在继续。
而陈映真最后的这三部作品,抒情色彩比之前的“铃珰花”系列有所减弱,讨论的是国家、民族分断,戒严体制的反思,另外还涉及台籍日本兵的历史遗留问题。光从标题阐释,这三部小说的标题即显示出主题的象征意义:“归乡”象征国家统一和民族精神回归,“夜雾”象征戒严体制造成的集体恐惧和社会扭曲,而“忠孝公园”则象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纠葛。20世纪末民进党代替国民党获得执政权,在台湾岛内是一件“变天换日”的重要事件。昔日的众多盟友都倒戈转向,但陈映真和少数统派仍在坚守。白描是这三篇作品的共同特点,陈映真如此选择对历史复述的方式,为的是更直接的、更无障碍地揭示真实,因此也更可见出他内心的焦虑。现实不如人愿,陈映真在冷静剖析和沉淀思考之时,还是不禁表达出他的期望,使得《归乡》出现了过于直白的理想化的语调,《夜雾》和《忠孝公园》则似乎有点自我安慰的意味。
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陈映真的作品往往体现出绝望色彩,这是他的真实感受的投射,但他仍流露出一丝希望的成分;现实世界中他也宁可抱持希望,不然他的左翼理想将无法继续。从隐秘暗示到艺术加工,从曲折慎言到直抒胸臆,由始至终,陈映真并没有放弃在作品中传达左翼的思想信息,也没有停止他的红色抒情。
二 有意而为与无奈之举——陈映真红色抒情的错位
戒严末期,政治环境有了更多松动,党外运动高涨。左翼分裂后,“本土派”积极争夺政治权力,“台湾意识”逐渐掌握话语主导权,以至于在1984年初发生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论战,其导火索便是宋冬阳(即陈芳明)发表的《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台湾文艺》第八十六期,1984年1月15日),对陈映真的以中国观点论台湾文学发起批判。
在这样的情势下,陈映真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他需要在这时通过更明确的语言来披露历史真相,将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掩盖、现在又即将被“本土派”偷换概念②的左翼存在告知于众。经过了《乡村的教师》时期不敢言说的忧郁,在狱中七年获得对台湾三十年代左翼的直接真实的认知,陈映真重返人间时首先冷静地对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状进行解剖。但是到“铃珰花”他的笔调又发生了改变,小说艺术性加大的背后,可以看出这是陈映真为红色抒情目的做出的一种选择。政治环境的放松使他能够更显露地进行表达,因此“铃珰花”系列可说是陈映真红色抒情的一个高峰。
但是从结果看,不免会对陈映真的这种努力发出叹息。在书写中,抒情与作家的追求并不是一体并行的,抒情的审美性使作品的呈现与作家的意愿发生错位,即如陈映真的《山路》所表现出的美学氛围更多引起的是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感动,却没有接收到作者想要的对革命意志的传播。
早在《乡村的教师》时,陈映真便借左翼青年吴锦翔之口,对红色抒情的错位发出过悲叹:“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10]这种对自己作品被审美化阅读、自己的思想被艺术替换的担忧,延续到《山路》的写作。
作品体现出的抒情性大于目的性,其实仍是作家主体意识外化作用的体现。作家会因为意识的变化而改变书写,以合乎其情感抒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家虽带有某种目的去进行写作,但作品自身产生的运作机制使其不能完全遵从于作者的目的,这便发生了抒情与写作目的之间的错位。再在从接受方(读者)的角度看,接受方的思想基础与作家并不一致,也是导致两者错位的一个原因。左翼在台湾长期的戒严体制下被强行排除了,没有这种思想储备的读者、尤其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如何体会到作家隐晦的意图?陈映真想传达的红色理想被审美化解读,这是他文学写作的一个尴尬之处。他宁可读者接收到他传达的信息,而抛弃其文本本身,进而投入现实的革命行动。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传播的中介,也就是他自谓的“文学工具论”。
王德威对陈映真文学书写与政治理念之间的错位曾有这样的评价,他认为陈映真“本身就是一则浪漫传奇”,“我们汲汲赞美陈映真的方式,其实抽离了他所执著的本质”[11]。在对陈映真进行阐释时,评论者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状态:或是被陈映真的文学形式所吸引,而沉溺于挖掘其形式中蕴含的人文悲情;或是为陈映真不为时下认同的政治理想所感动,而急于为其作出附和和解释。而能把陈映真的作品和他的思想理念结合,看透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咬合的,却是凤毛麟角。评论者不能作出两方平衡的解释,是否因为这是陈映真的个人经历与文学写作上的不对称所造成?
从处女作《面摊》(1959年)到《忠孝公园》(2001年),陈映真的整个小说创作生命中,除去系狱的七年,停笔的时间有两段:一是在出狱后的1976年到1978年之间,陈映真应苏庆黎之邀共同创办左翼杂志《夏潮》,并在1977年参与到乡土文学论战;二是《赵南栋》与《归乡》之间的十二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参与筹组“中国统一联盟”并于1990年访问北京,筹划“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系列,创作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和报告剧《春祭》,在世纪之交与陈芳明展开了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双陈大战”。
文学家的陈映真和社会活动家的他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而两者之间的交叉似乎对解释陈映真红色抒情的错位问题有所帮助。王德威认为陈映真的文学观是“自我否定、抹销的文学观,是达成目的的手段”[12],即是说当陈映真红色抒情的目的达到了,他便不再需要写作,反之而言,他的写作就证明了他的目的还未达成。而在此之上,现实中的陈映真还有比王德威认为的更积极的一面——文学不能做到的,他便通过社会活动去做。鲁迅说“正在革命中,哪有功夫做文学”[13],社会活动家的陈映真正印证了这句话。两者之间体现出的不同气质,其实为的是同一目的,只是表现了陈映真的不同面貌。
陈映真的作品在当下台湾社会中的特异性,在于其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却承载了不为主流所意会的抒情目的。因此陈映真在台湾受到一种他并不希望的“待遇”:他所受到的尊敬更多来自他自早期作品的艺术性所积累下来的地位,而人们对他的政治取向总持回避或保留态度。陈映真出狱后发表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在回归乡土文学的1970年代末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欢迎。而1980年代发端的“铃珰花”系列,以至世纪之交的《忠孝公园》等三篇,却是离台湾的主流意识越来越远。解严使陈映真的创作能够更多地表现他的追求,他能够不再隐晦他的马克思主义追求和共产主义理想,甚至是对大陆的向往。进入90年代他停笔转向社会运动后,陈映真的文学家面目逐渐被社会活动家所替代,这时出现的“统”“独”对立,使他的特异越发突出。
陈映真在台湾无异于成为了一个被隔离在玻璃罩中的观赏品,他被奉以极高的地位,却不能通过作品进入主流社会。他在作品中目的于理想传播的抒情,在读者却只能接受到其审美的外衣。因此陈映真用社会行动来弥补这种错位,可谓是一种无奈却切实的选择。
三 一个“异数”的作用——陈映真与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
陈映真被评论者贴上“孤独”的标签,他的“不合时宜”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是同样遭遇③。这个标签一方面显示了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他在文学上坚持自我、不与人为伍;另一方面似乎为陈映真挂上了“生人勿近”的牌子,把他作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异类,警告别人不要试图去理解他,换句话说就是“被孤独”。
黎湘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作家陈映真’受到欢迎,而‘思想家陈映真’却遭到冷遇?难道只是因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作品的充沛的感性经验,与读者更容易引起共鸣?而‘思想家陈映真’的那些理性思考,却是‘过时’的‘教条’?‘作家陈映真’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与‘思想家陈映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诸问题所思考、反省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是和谐一致的还是相互矛盾的?”[14]这也是存于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心中的共同疑问。黎湘萍认为,陈映真因其宗教信仰的关系而对人内在的道德律十分敏感,他早期小说最富思想力的地方,是他在感性世界之外对人内在“罪性”的反省和挖掘,到后期他加入了人与体制之间关系的思考,以此审视社会理想与实践间的悲剧。陈映真用小说去思考时代的精神困局,而小说不能满足的,他将之付诸现实世界的实践,甚至不惜因此身陷囹圄,因此“作家的陈映真”和“思想家的陈映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陈映真对自身革命理想的坚持已被重复述说,他在右翼政权下的左翼姿态已经深入人心。而在此我要就“孤独”的第二个方面提出一个问题:陈映真确实是孤独的吗?他是否脱离于当下的时代,而没有人能与他同行?为什么我们仍愿意阅读陈映真?
郑鸿生在回忆他所属的“战后世代”④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由保钓开始而至争取政治民主的过程时,多次提及他们阅读陈映真小说的的经历以及陈映真对他们的影响。1968年尚在读高二的郑鸿生参加了一个地下读书会,第一次讨论的就是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和张爱玲的《留情》,陈映真小说中描画的台湾当下氛围深深吸引了他们。
陈映真作品中极为浓厚的社会意识更让我们深受感动,他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文艺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内心充满进步理念却拙于行动的苍白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像罗亭那样的角色相互映照,一直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里隐隐作痛,难以摆脱。[15]
其实如同赵刚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这些青年学生选读陈映真和张爱玲,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16]。
陈映真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国民党政府投入监狱,1975年获释。我们习惯将陈映真的入狱作为他写作分期的界线,他的早期作品大多展现出“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17],到入狱前两三年发表的《唐倩的喜剧》、《六月的玫瑰花》等几篇才摆脱了感伤主义的色彩,增添了讽刺和批判。陈映真自谓他这几年的变化,是因为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18],而走出了原来的绝望和悲戚。左翼理想的渺茫,使陈映真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晦暗抑郁的色调,而他也不敢将他的理想直言于文字当中,只能化身为康雄、吴锦翔等等压抑不安的、被世俗厌弃的青年。而将陈映真和张爱玲、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阅读的郑鸿生们,与其说当时他们是为陈映真隐藏的左翼精神所冲击,毋宁说是因为在思想管制的高压下,这些尚在青春期的少年感受到小说那种忧郁的情调,对那些心有觉悟却无能于现实的人物产生共鸣。此外,在现代主义于文学中占有流行位置的1960年代,陈映真小说对内心的自省和挖掘,以及他所营造的个人的孤独世界,对这些象牙塔中的少年也是深具吸引力的。而且他们“当时并不清楚陈映真因何入狱,对他在1968年进行实践的内容也一无所悉”[19]。
郑鸿生们开始真正接近陈映真,是1970年代初他们进入大学,当保钓的风潮从大洋彼岸吹到台湾,在民族主义的带领下掀起校园民主抗争运动的时候。以台湾大学为主要阵地的校园保钓运动,其参与者多为承继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台大哲学系年轻师生,追崇《自由中国》、《文星》对威权的挑战;同时他们也多曾在阅读陈映真时被感动过,陈映真的小说和评论中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实践精神为他们启示了另一条道路。在保钓运动之后的台大校园民主抗争中,“走出校园,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入民间”这些理念都已成为学生的诉求基调,慈教会、“社会服务团”、“百万小时服务”活动,以至后来的“学生监票员”的争取,犹如大陆的“上山下乡”,学生们举起“拥抱斯土斯民”的旗帜介入社会[20]。曾将自己类比于陈映真笔下的无力青年的郑鸿生们,此时开始以走进现实的方式接近陈映真,并把陈映真作为他们反抗威权的“武器”。
陈映真在他入狱前发表的《最牢固的磐石》这篇文章,被我们这批在1971年春发起保钓并开始寻找另类出路的台大学生,奉为经典捧读再三。在接着的1972年底台大“民族主义论战”中,我还将这篇文章摘取精华,改头换面,以《理想主义的磐石》为题,以许南村谐音“喃春”为名登于学生报刊,用来辩驳对手。在1973年初春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爆发后,我又将他的另一篇评论《知识人的偏执》稍做剪裁后,以“秋木”为笔名登出来。如今想起,虽然陈映真入狱前的作品里头毫无半句左翼用语,但已是饱含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确实构成了保钓运动时期我们这批学生的重要思想资源。[21]
陈映真的《最牢固的磐石》就理想主义否定论,指出理想主义有其历史的阶段的性格,“真理的伦理条件”——即站在正确的正义的立场,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22]。《知识人的偏执》针对执著于派性和固有知识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知识分子要有自省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97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站在了一个包含了不同声音的思想氛围中——台湾岛内的现代主义,西方的左翼风潮,大陆的文革,这些声音使得指向的对国民党政府“反对”显得统一却复杂。陈映真虽然缺席了,却并没有因他的左倾的思想而被拒斥,他也构成了“反对”声音的一种。同属这一代的钱永祥回忆到,“岛外的事件(按:指文化大革命),会与陈映真的文学评论交互发生作用”[23]。与自由主义致力民主政治诉求的“反对”不同,陈映真的“反对”包含了阶级立场,因此他反对的对象超越了“反对国民党”的简单层面,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民间的、底层的观念从他这里传达到年轻一辈。在众多思想涌入的1970年代,这样一个“异数”的加入,使因白色恐怖而断裂的台湾左翼,有了重新接续的可能。
陈映真传达的信息,影响了这一代对日后台湾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人,此时大学校园里萌芽的社会意识和实践精神,后来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通过不同的形式获得实现。这些年轻时曾为陈映真的小说感动过的知识分子,如郑鸿生、林怀民、朱天心、季季、侯孝贤、陈怡蓁夫妇等,在当时甚至因此做出改变自身的重要决定⑤。他们在日后可能并没有跟随陈映真的旗帜,但是他们所呈现的多种面向的社会参与,是陈映真对台湾社会变化发挥作用的间接体现,也使陈映真在之后的时代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可能。
现在再回到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以及他是否“孤独”这个问题。
吕正惠曾言陈映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阅读鲁迅和马克思,是极为罕见的[24]。吕正惠自己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偷偷”阅读鲁迅和马克思的。这里一方面是他们的时代差距(吕正惠1940年代末生,陈映真是1930年代末生),其中关键的1950到1960年代,吕正惠尚在受教育期,而陈映真在1950年代初已初步具有成形的思想。陈映真带有的毋宁是上一辈的色彩,从父辈继承的对大陆的亲近和对大陆三十年代文学的接触,是与1950年代末才开始接受国民党政府下的中学教育的吕正惠一辈、以及更往后的郑鸿生们有很大差异的。1970年代,台湾岛内经由保钓运动带起了左翼风潮,政治松动伴随了文化松动,文化界开始对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挖掘,必然也引起了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左翼的靠近。其时,成长于战后国民教育下的1970年代的知识青年才开始透过重新认识杨逵,真正触摸到台湾过去的左翼传承,他们对陈映真的真正接近也是从此开始的。
陈映真的红色抒情意在传递他的左翼理想。在戒严时期严苛的话语环境下,陈映真通过艺术转化的手法隐晦地表达其左翼情感;在政治松动时及解严后,他便不再掩饰,直言不讳。陈映真把小说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然而不能避免读者在接受时与他的意图发生错位,更看重于其方式而非本质。但是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仍有一点达到了目的,那便是他对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产生的影响,这一代人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来回应陈映真在他们身上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陈映真并不孤独。
注释:
①按文中吴锦翔归来时“台湾光复已经近于一年”,而“第二年入春的时候,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触角,甚至伸到这样一个寂寞的山村里来”,可以推算出此处所指正是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
②“本土派”基于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本省人的不平等待遇,极力争取本省人的政治权力,进而将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统治等同于“再殖民”,由此强调台湾“自主性”,否定“中国意识”。如此将1970年代左翼乡土文学叙述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第三世界的立场强行扭转。
③在199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授予陈映真为客座教授的仪式上,有学生评价陈映真的演讲“比老干部还老干部”(见周良沛《在黄春明、陈映真作品研讨会上的随想随说》(《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1期)。八十年代接触到陈映真的王安忆、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等对陈映真的印象是犹疑或排斥,而九十年代中期的祝东力和刘继明则对陈映真抱有崇敬和共鸣。这与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变化有关,但是陈映真与大陆知识界的隔阂仍是普遍现象。详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祝东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个新左翼知识分子的三十年》(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2005年),刘继明《走近陈映真》(《天涯》,2009年第1期)。
④“战后世代”即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萧阿勤将如郑鸿生等在战后出生或成长、于1970年前后进入大学或步入社会的战后新生代知识青年,称为“回归现实世代”,这一世代通过推动政治改革和提倡回归乡土,深刻影响了台湾晚近民主政治的进程和“本土化”的发展。“世代”的概念主要来自Karl Mannheim的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1927)。萧阿勤《世代认同与历史叙事——台湾1970年代“回归现实”世代的形成》,《台湾社会学》,2005年6月。
⑤林怀民在年少住院时曾为陈映真的小说感动不已,多年后创作了舞台剧《陈映真·风景》;陈怡蓁夫妇在1970年代末因为读了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而毅然决定回台创业;侯孝贤年轻时也曾有将陈映真的小说拍成电影的冲动。
[1]陈映真.乡村的教师[M].陈映真小说集1.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36.
[2]陈映真.故乡[M].陈映真小说集1.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51页.
[3]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M].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4:56.
[4]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J].上海文学.2004,(1).
[5]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J].上海文学.2004,(1).
[6]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J].上海文学.2004,(1).
[7]陈映真.赵南栋[M].陈映真小说集5.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193页.
[8]吕正惠.我的接近中国之路——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J].读书,2007(8).
[9]陈映真.山路[M].陈映真小说集5.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88.
[10]陈映真.乡村的教师[M].陈映真小说集1.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38.
[11]王德威.王德威精选集[M].台北:九歌出版,2007:234.
[12]王德威.王德威精选集[M].台北:九歌出版,2007:237.
[13]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M].鲁迅全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9。
[14]黎湘萍。思想家的“孤独”?——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内在关联[J].励耘学刊,2010(1).
[15]郑鸿生.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重试论台湾战后新生代的自我实现[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6).
[16]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219.
[17]许南村.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M].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3页.
[18]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M].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4:59.
[19]郑鸿生.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重试论台湾战后新生代的自我实现[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6).
[20]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173-174.
[21]郑鸿生.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重试论台湾战后新生代的自我实现[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6).
[22]陈映真.最坚固的磐石[M].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123.
[23]钱永祥.青春歌声里的低调[M].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316.
[24]吕正惠.我的接近中国之路——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J].读书,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