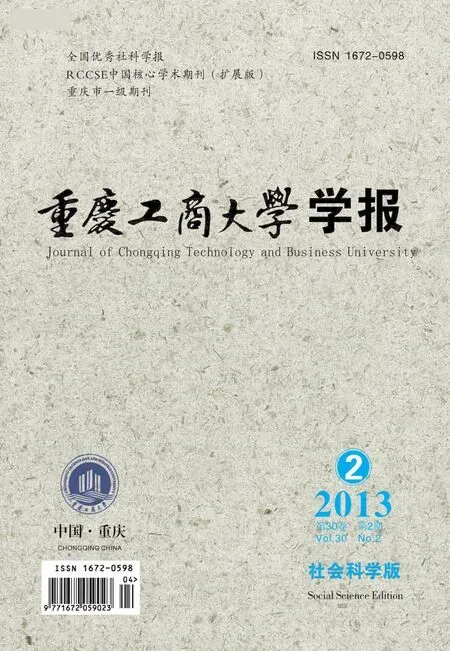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以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王恩科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400067)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近年来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研究中,钟玲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诗的英译文在美国的经典化问题,徐菊以女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为视角研究《简·爱》汉译本的接受历史,而宋学智则聚焦于一位译者的某个代表性译本,即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探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内外因素。三本著作虽然研究理路不尽相同,但都以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为对象,从不同角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翻译文学区别于本土原创文学,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异域特色,更在于不同译者对同一原作的不同把握与处理。因此译者的介入和作用是翻译文学经典研究中不可忽视,更不能缺少的因素。翻译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需要宏观上的把握,也需要从个案入手发幽探微。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张谷若的译本不仅是公认的佳译,而且1957年的版本也进入2000年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100种阅读书目(其中外国文学22种)。本文将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个案,以译者为重点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进行研究。
一、“道地的中文”:历史的呼唤
1936年,张谷若翻译的哈代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译者自序”中,张谷若指出:“我译这本书的理想,是要用道地的中文,译原来道地的英文。”“道地的中文”不仅是译者张谷若的追求,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声。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中“豪杰译”盛行,随意增删甚至改变故事情节或结构为数不少。为了还原作的本来面目,以保存原作风格为旨归的直译得到了不少学者和译者的推崇。然而矫枉过正,“直译”变成了“死译”。因此早在1922年,茅盾在论及“直译”与“死译”时就说:“近来颇多死译的东西,……唯因译者能力关系,原来要直译,不意竟变作了死译,也是常有的事。”(茅盾,1984:343-344)1929年薌叔在《文学周报》第8卷第9-13合刊上发表“哈代信托的翻译”,称“我很愉快,中国常有人嚷着哈代,然而没有谁认真译他的东西。现在哈代信托的翻译出现,而《金屋》同人极幸运地拿来发表,数重保证,其能使人满意可知。赶忙地找着来看,不幸我蹩脚的中文程度碰壁了。屏住气,运着脑,看不到二三页,禁不起涨痛昏花,莫名其妙!审慎迻录下数节,以见一斑。倘若有不怕如此硬涩的,不妨购读全文。”①此处指《金屋》月刊第1-3期上发表的郭有守翻译的哈代的《无名的裘特》。小说原文共53节,译文仅为小说最初的4节。《金屋》月刊第3期上《无名的裘特》译文后虽有“未完”字样,但其后几期直至停刊始终未见后续译文,至此郭有守的译文便无终而终了。在列举部分译文后,薌叔发出了这样恳切的呼吁:“救救仅仅知道ABC,不能直接看外国文字的人们!!”(薌叔,1929:269)1935年《读书顾问》第1卷第4期上刊登了志英的《一年来的中国翻译界》,作者指出:“最近几年来,翻译不很受人欢迎,虽然翻译的方法有人在辩论着,但是读者因为受了硬译的影响,大都不爱读翻译的文学作品了。……原来自从硬译吓退了读者以后,一般中等程度的读者对于翻译只感到失望,虽然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始终是被进步的作家和读者所感觉着。”(志英,1935:23-24)志英进而告诫日后的译者“不要像硬译者那样拿来作为骗取稿费的手段。”(同上:26)可见,无论是翻译批评界还是普通读者,许多人对张谷若在“译者自序”中所提及的“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四不相儿”的译文不仅失去了耐心,而且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期待流利译文的出现。《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四期上,萧乾在“评张译《还乡》”②即张谷若译哈代的另一部重要小说《还乡》。中指出:“在某一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担保这译文将为许多人所钟爱,为了年来国人厌倦囫囵吞枣的‘直译'了,冗长的名字,别扭的对话,复杂着需要推敲分析的复句。如今,握到一本这样艰深的舶来的杰作,读来却如吃面条那么顺嘴。仅仅这点‘流利’,便足给人以莫大喜悦了。”(萧乾,1937:44)因此,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长期忍受“死译”和“硬译”之后,无论是读书界还是翻译界,不少人发出了渴望流利通顺译文的呼声。正是响应时代的呼声,张谷若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时,“用合于中文文法习惯的中文,译原来合于英文文法习惯的英文”(《德伯家的苔丝》1936年版“译者自序”),不能不说是对“死译”和“硬译”的一种反驳,是“一个崭新的试验”。(萧乾,1937:44)
二、翻译兼研究:译者的追求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中,译者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译本中体现得十分突出。这部小说早在1891年就出版了,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汉译本。1932年,《文艺月刊》从第三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顾仲彝翻译的《苔丝姑娘》,至1933年6月第三卷第十二期译文结束,但可惜的是译文后来并未结集出版。1934年,吕天石翻译的《苔丝姑娘》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在1948年以前再版3次,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哈代这本小说影响最大的译本之一。1936年,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3年由上海文化工作社重印。其后,张谷若对原有译本一改再改,分别于1957年和1984年出版《德伯家的苔丝》的第二版和第三版③这里是就1936年版本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修订本时则使用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别指代1957年和1984年版本。。除上述译本之外,哈代的这部名著不仅过去有多个译本,而且至今仍有新译本推出。但在这众多的译本中,张谷若的译本多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尤其是1957年版的修订版,2000年入选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100中阅读书目(其中外国文学作品22部)。纵观哈代这部小说的汉译历史,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翻译文学经典是如何建构甚至重构的。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既涉及原作的文学地位和思想内容,也涉及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译者的个人因素。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截取了译入语社会文化因素中的语言使用予以探讨,本部分将主要从译者的个人因素入手,进一步研究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个别译者是如何凭借其独特的个人因素完成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
翻译原则是译者在动笔前就已经确定了,并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对有些译者而言,翻译原则可能只是模糊的潜意识,但对其他译者而言,则比较具体明晰。张谷若在《德伯家的苔丝》第一版出版后不久曾撰文指出:“翻译(文学的翻译)的原则要怎么样?要忠实。怎么才算真实?就是要reproduce the effect of the original。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要一个读中文译文的中国人,所得到的感觉,所引起的反应,跟读英文原文的英国人,所得到的感觉,所引起的反应,到最相似以至于完全一样的程度。”(张谷若,1937a:47)接着张谷若对读者“最相似以至于完全一样”的反应做了更为形象的解释:“总而言之,原文读起来难如天书,原[译]文也该难如天书,原文如吃面条,译文也该如吃面条,原文要硬着头皮读,译文也该硬着头皮读,原文让人落泪的地方,译文也得让人落泪……原文读人鼻酸的地方,译文也得让人鼻酸……这样才算是忠实,这样才算是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作者。”(同上)张谷若的这一翻译原则在其译文的“道地”与方言的使用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张谷若译文的地道流畅在翻译界是公认的,其实早在《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初期,就有学者指出:“译者张谷若先生能用中国式的通俗文章,加上流利而漂亮的修辞,把它介绍给中国的文学读者,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事。”(沈曙,1937:138)关于方言在译本中的使用,情况就复杂得多。哈代的原作中,作者的叙述语言是标准的书面语,但人物对话中却因人物身份和教育程度等原因夹杂了不少方言。面对这种情况,译者该如何处理呢?张谷若在《德伯家的苔丝》1936年版“译者自序”中指出:“原文分明是两种话,译文里变成了一种话,那怎么成呢?”“所以采用山东东部方言的原故,一部分因为译者除了北平方言,恰好懂得那种方言,二来因为那种方言在中国,和道塞郡方言在英国,仿佛有相似之点。”关于“译者自序”中提及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哈代研究专家的张谷若女儿张玲女士做了这样的阐释:“先父处理这些语言之前,比较过多塞特郡与英国首都伦敦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多塞特方言与标准英语发音的异同,发现其中和中国胶东(先父故乡)与中国首都北京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胶东方言与标准中国普通话发音的异同,大有相应的规律,因此翻译多塞特方言时,采用了大量胶东方言。”(张玲,2001:42)尽管张谷若在译文中使用山东方言曾在我国翻译界引起过一些争论(详见韩子满,2003,2008;孙致礼,2003),但从译者“reproduce the effect of the original”这一原则出发,山东方言的使用也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在30年代“死译”“硬译”成风的大背景下,张谷若在译文中使用极具地方特色的山东方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崭新的试验”,(萧乾,1937:44)一种有益的探索。
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基础,但是由于文化差异、一词多义现象等因素的影响,透彻准确的理解原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谷若在1937年“翻译者的态度”一文中就说,“就像我译《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started on her way up the dark and crooked lane of street…。这儿lane of street,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自然是‘小巷'或‘大街'了,而其实不然。要是译成‘小巷'或‘大街’,那就把原文的光景,完全译没了。原来哈代在他别的书里,也写过同样的情形,不过写得详细一点。他在他的The Distracted Preacher①哈代的一部短篇小说,通常译为“神魂颠倒的传道(教)士”。里有这样一句话,He thus followed her up the street of lane,as it might indifferently be called there being more hedge than houses on either side。这可以证明哈代这儿用的lane这个字,是指树篱夹路(hedge)的道路,并不是 narrow street的意思。(这我在《德伯家的苔丝》第三章注三十四里说得比较详细)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译,或者没有读到The Distracted Preacher里那一句话,恐怕很容易译错了,而且这个错还是很不容易发现,但是那样错下去,可就离原文太远了。像这一类的例,当然很多。”(张谷若,1937b:1117)张谷若对于像lane这样十分平常的小词都如此求证推敲,他在对原文的理解上所下的巨大功夫就可见一斑了。对原文的透彻理解不仅体现在词义的推敲和选择上,更体现在译者对作者和原作的研究上。在谈到研究原作对于翻译的必要性时,张谷若指出:“至于关于智识学问一方面,似乎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翻译家,同时也得是一个学者。……一个作翻译的人——应该从‘字典式'的懂进而为‘百科全书'式的懂。换句话说,也就是他得取一种研究的态度,把翻译当作一种研究工作。”(张谷若,1937b:1118)他对“‘百科全书'式的懂”的身体力行主要体现在译本的注释上。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先后有三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大量注释,尤其是1936年的版本以注释详尽丰富著称。该版本正文部分共有925条注释,原作“弁言”和各版“序言”译文部分也有28条注释,整个注释长达151页。在这将近1000条注释中,除少部分为译文中所用山东方言的解释外,绝大部分用以解释原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典故、人物、风土人情、建筑家具等等。这些注释,少则几个字,多则近千字。译本出版的第二年,萧乾就在《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37年)上“评张译《还乡》”中指出,“笔者在这里还想指出本书另一个特殊的美德,那是注解的详尽。这种傻功夫,是滥译粗译家所绝不肯卖的力气。为着学术工作的认真风气,这力气是应被推崇的。”(萧乾,1937:44)萧乾虽然评说的是《还乡》,其实将这样的评语用在张谷若同一年①张谷若在“谈我的翻译生涯”中说,“《还乡》译完后,又叫我接着译哈代另一本最重要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这两部书,一于1935年,一于1936年,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张谷若,1989:450)但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看到的商务印书馆民国版的《还乡》封三上有“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初版”字样。既为“初版”,说明1936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过张谷若译的《还乡》,而且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也只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还乡》,并无1935年版。因此笔者推测,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张谷若译的《还乡》可能在1936年,而非译者50多年后回忆时所说的1935年。翻译出版的另一部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上也同样适用。张谷若在《德伯家的苔丝》(1936年版)“译者自序”中指出:“至于本书的注解,全是译者加进去的,所以这样详细,一方面固然为的是便于读者,一方面还想对于研究的人有点帮助。”正如译者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东西虽然对于读小说的读者并不是顶需要,然而却足以表示译者对于原作的研究的功力和对于译文的负责。”(林辟,1940:117)至于注释对于研究者的作用,张玲女士曾说:“北京大学英语系文革中去世的俞大纲教授在父亲的译作出版后常主动索要赠书,并且直言:‘这些书我都早读过原文版了,可是我就是要你的注释。’”(孙迎春,2004:26)
尽管张谷若在《德伯家的苔丝》1936年版的译本上花费了巨大的工夫,但他并未满足,而是在其后近50年的时间里,两次重译哈代的同一部小说,那种热情执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作风,在我国翻译界是不多见的。与1936年的初版相比,1957年和1984年的两个修订版在两个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一是方言的使用,二是注释的数量。两个修订版中方言使用明显减少,尤其是一些仅仅在山东个别小区域使用的方言被使用范围更广的方言或标准语所替代。注释的数量在两个修订版中也大幅减少,1957年版的注释只有323条,仅占初版的三分之一;1984年版的注释增加到436条,仍不及初版的二分之一。1957年版本中注释数量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种。由于1936年版本中的部分方言词并未出现在1957年的修订版中,因此1936年版本中部分针对这些方言词的注释就不再需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在50年代特别响亮,为了使译本更好地满足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译者原来为研究者所设计的部分注释也就随之失去了市场和必要。也是为了满足当时普通读者的需要,1957年版本无论较1936年版本还是1984年版本,语言更加通俗、更加口语化。
张谷若将翻译工作建立在对作者和作品的深入研究之上,这不仅为他赢得了“哈代专家”(孙迎春,2004:4)的声誉,而且也为他的译本《德伯家的苔丝》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漫漫长路:经典的建构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也不例外。早在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出版第二年,即1937年3月,沈曙就在《华年》第六卷第七期上发表了“读了《德伯家的苔丝》”一文。在介绍了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后,沈曙总结道:“这本作品的价值,无疑地,还有许多材料给我们证明,它是伟大的。译者张谷若先生能用中国式的通俗文章,加上流利而漂亮的修辞,把它介绍给中国的文学读者,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事。”即便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张谷若翻译的哈代小说。林辟在《西书精华》廿九年夏季号(即1940年第2期)上撰文,向读者推荐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在这篇名为“两部汉译哈代小说”文章中,林辟指出:“我们的理想的翻译家,是应该在自己兴趣的范围以内,选择几部外国名著,一面力求自己对于这几部书的了解,一面再把它们译成中文。大家多方面这样的工作下去,中国的翻译界或者可以有些成绩。而这两部哈代的小说可以说是近乎我们的理想的。”作者用“近乎我们的理想的”来赞美张谷若的两个译本,其评价之高是显而易见的。时隔几年,同样是战火纷飞的岁月,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仍然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荐。1947年,徐蔚南在《青年界》第3卷第1期上撰文,称“我负责介绍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给青年们,保证青年们读此书时一定非一口气看完,不肯放手的,而且保证读了此书可以得到许多益处:第一可以知道英国的民情习惯,第二可以知道写作长篇小说的技巧;第三可以知道近代英国的文学名著,第四可以知道翻译应该如此翻法,才对得起原著。青年们要注意,此书中文译本已有多种,但我介绍的是张谷若的译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分印成二册的。”徐蔚南在这里不仅详细列举“读了此书可以得到许多益处”,而且还在几种不同的译本中力荐张谷若的译本。在笔者能够找到的民国时期有关张谷若译本《德伯家的苔丝》的评论中,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地赞赏,尚未发现负面的评价。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在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都受到读书界的高度赞扬。然而,张谷若的译本自1936年出版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再版,其中原委既无明确的史料记载,也没有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笔者推测,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不久,我国便陷入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或者由于《德伯家的苔丝》的铅板毁于战争,或者由于战争期间财物紧缺,才导致该译本未能再版。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的文化工作社便于1953年重印了张谷若的译本《苔丝》。①该版本为1936年商务印书馆《德伯家的苔丝》的重印本,但书名不同。1957年,张谷若重译了哈代的这部著名小说,但译本书名由初版时的《德伯家的苔丝》更改为《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1984年,张谷若在前两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德伯家的苔丝》出版,书名与1957年版本相同,仍为《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关于1957年和1984年的两个版本,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重复。
总之,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自1936年出版后,他的几种译本一直受到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2000年教育部为中文系推荐的100种阅读书名中,有22部外国文学作品,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1957年版)就名列其中。这既是对该译本的高度评价,也是该译本经典地位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结语
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译者是诸多因素中常常被忽视,但却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哈代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它在汉语语境中经典地位的确立却并非是任何一位译者都能完成的。这部小说在我国的经典化历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间许多译者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众多的译者中,张谷若以其深厚的中英语言和文学修养、对原作与作者的深入研究、顺应时代呼唤的翻译策略、反复修改的执着精神等,完成了哈代这部著名小说在我国的经典建构。张谷若在长达五十年里,三次翻译修改《德伯家的苔丝》,每个版本都受到当时读书界与翻译界的高度赞扬。然而在这三个十分相似却并非相同的译本中,入选教育部2000年为中文系推荐的100种阅读书目的是1957年版本。这就说明,翻译文学经典并非一个边界分明、结构单一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经典化过程曲折漫长、经典化程度高低不同、经典化地位变动不居的复杂现象。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既要关注社会文化等外在条件,也不能忽视译者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1]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04(2):86-102.
[2]哈代.德伯家的苔丝[Z].张谷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德伯家的苔丝(第一版)[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德伯家的苔丝(第二版)[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86-90.文学译文的语言杂合性——以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33-135.
[4]胡安江.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研究[J].外语学刊,2008(5):93-96.美国学者伯顿·华生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6):75-80.
[5]林辟.两部汉译哈代小说[J].西书精华,第2期,1940:115-118.
[6]茅盾.“直译”与“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43-344.
[7]区鉷,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J].中国翻译,2008(3):20-25.
[8]沈曙.读了《德伯家的苔丝》[J].华年,第6卷第7期,1937:136-18.
[9]宋学智.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孙迎春.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11]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1):48-51.
[12]王静艺,王伦.异化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成功应用[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13]萧乾.评张译《还乡》[J].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37:43-49.
[14]陈雯.翻译语言审美新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9).
[15]徐菊.经典的嬗变:《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16]张谷若.谈翻译——兼答萧乾君评拙译《还乡》[J].国闻周报,第14 卷第10 期,1937a,45-49.翻译者的态度[J].月报,第1卷第5期,1937b:1117-1119.巴金.谈我的翻译生涯[A].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50-458.
[17]张玲.传承的情谊——我与父亲张谷若[J].传媒,2001(5):41-43.
[18]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9]朱安博.翻译文学的重构与新生——《牛虻》的经典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08(2):264-266.
[20]谢柯.翻译认知研究范式论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