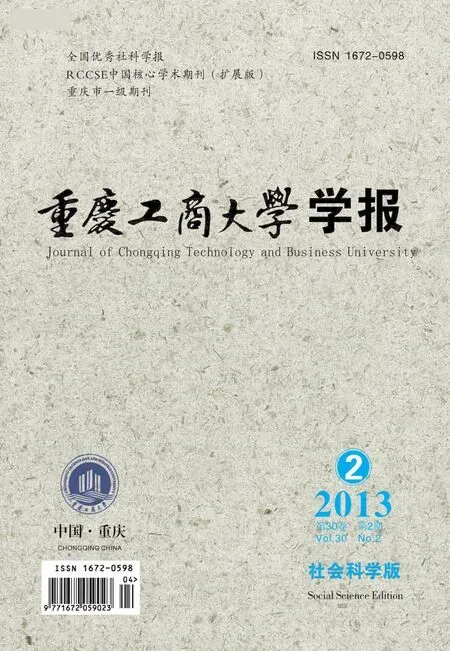流放与希望:澳洲的双重情结*
毕宙嫔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46)
一、引言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Judith Wright, 1915—2000)的《澳洲的双重情结》(Preoccupations in Australian Poetry, 1966)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论著。该著作分析了殖民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诗歌,全面表达了赖特独到的文学主张。得益于赖特的文学评价,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r)、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 Brennan)、约翰·肖·尼尔森(John Shaw Neilson)这些原本受到贬抑或不为人知的诗人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声名鹊起。
赖特在《澳洲的双重情结》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对于它的新住民来说,澳洲从它尚属短暂的历史开始直到今天,始终不只是被占领、被耕种和被征服的土地,它是内在现实的外在对应。首先,且一直是,流放现实。其次,新与自由的现实[1]。澳洲是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对欧裔白人的心理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像土著那样与原始、蛮荒的澳洲大陆和谐共处、息息相关,他们与脚下的土地也缺乏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结。殖民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诗歌等文化产品中。
二、对立形象的形成
澳洲,或者说曾经所谓的“新荷兰”(New Holland)、“无人之地”(Terra Australis)、“伟大的南方大陆”(Great South Land),究竟是片怎样的大陆?16世纪伊始,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登陆澳洲以前,就有不少欧洲的探险家或科学家以日记、报告等形式记载了他们对澳洲新大陆的感受和看法,关于澳洲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开始形成,即它要么是象征死亡和流放的不毛之地,要么是神奇美好的人间天堂。
一开始,澳洲主要以探险家笔下描述的负面形象出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最早来到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发现黄金和香料等值得贸易的物品。他们不喜欢澳洲,也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描述。如A.W.周思(A.W.Jose)所说,“他们没有被大陆的样子所吸引,贫瘠是他们的评价,同时,他们用‘原始、黑色、野蛮——残酷、贫穷、残暴’等形容词来描述原住民”[2]6。1642年,荷兰航海家亚伯·扬松·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登陆Van Diemen’s Land(现在的Tasmania岛屿)时,并不认为这个地方有贸易利益可图,并且因为受到土著惊吓而立即撤退。1688年,英国探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首次登陆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并作了较为翔实的记录。但是,他对这个他称之为New Holland的大陆的描述一点不比荷兰人的更具吸引力:
陆地是干燥的沙质土壤,如果不打井,就没有水源。有若干树种,但森林稀疏,树木不壮。……树下长着漂亮的长草,但也很稀疏。我们没看到结果实的树。
我们没看到任何动物或野兽的行迹,但有一次好像看到像大藏獒般的大野兽踩踏过的痕迹。这儿有些小鸟,但都比画眉小。海鸟极少,海里也没什么鱼,除非你把水牛或海龟看作鱼类。水牛或海龟倒是很多,但它们异常胆小。[2]7
丹皮尔感受到的澳洲是干燥、贫瘠与蛮荒之地。他还把土著描写成低级的半人半兽的怪物(Caliban),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2]8。
1770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为欧洲带去了关于澳洲的正面描述,从而使澳大利亚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片生活着高尚的野人,孕育着自由理想、科学希望的大陆。1768年,时任英国皇家海军中尉的库克受命探寻“伟大的南方大陆”。1770年4月,他抵达澳洲东南沿海岸,为之吸引,并将此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尽管库克认同丹皮尔提出的澳洲不适合殖民贸易这个观点,但他相信这个地方适合种植庄稼、蓄养牛羊。库克对澳洲的未来和前景充满希望和热情。他是这样描写新大陆的:“有着令人愉悦的秀美风光,海拔适中,小山、山谷、山脊和平原错落有致,一些草坪点缀其间,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山坡和山脊的起伏缓和,没有高耸的山峰”[3]9。此类正面描述为后来英国把悉尼的植物湾(Botany Bay)作为流放犯输入地打下了思想基础。库克对澳洲客观具体的描述在英国国内被进一步美化和夸张,以至于当英帝国决定将澳大利亚定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时,还有人强烈抗议,认为这样一个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地方不应该被用来安置犯人[3]10。
早期欧洲探险家对澳大利亚的正负双重印象在英国第一舰队1788年登陆悉尼植物湾后两百余年内仍然存在。1788年11月,罗伯特·罗斯少校(Major Robert Ross)[注]罗伯特·罗斯少校负责1788年首批登陆澳洲的第一舰队警备人员,随后辅助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任州长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建立殖民地。写信给英国朋友时是这样描述澳大利亚的:“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糟糕的地方了,贫瘠荒芜、令人生畏。或许这里的自然环境真的已经被颠倒,即使不是,这里也已经是千疮百孔”[3]10。还有不少英裔定居者在面对陌生的环境时“转向熟悉的英国乡村进行比较”[4]25,然而在比较时往往呈现出抑澳扬英的模式。1841年从英国移居到澳洲的路易莎·克利夫顿(Louisa Clifton,1814—1880)于1854年在澳洲Australind登陆西海岸时,承认“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个国家漂亮的风貌所吸引”,但她还是有自己的偏好:“我还没见到让我感觉特别漂亮的花朵;大自然当然也是可爱的;我也喜爱我去的每个地方,但是我不认为它比得上英国展现出来的魅力”[5]61。不管她的印象是好是坏,她都是以英国风光作为参照物衡量澳洲景色的。
C.L.因内斯(C.L.Innes)认为殖民者不认同当地环境这种现象很普遍,也很自然。他认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印度群岛等定居国,许多作家表达了面对不同于祖先国家的地形地貌和自然风物时的疏离感和矛盾感”[6]79。对同一地方的认识和感受中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心理因素。按照弗里茨·斯蒂尔(Fritz Steele)在《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一书提出的观点,地方感不仅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还与个人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书中指出,“地方”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地之灵(spirit of place)。地方感指的是人处于一个特定背景时的特定体验[7]11,如下图所示:
Sense of place—Setting (Physical Setting +Social setting)+Person(psychological factors)
直到1988年,布鲁斯·贝内特(Bruce Bennett)还指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精神上的流放状态比安定状态更为凸显”[8]1。按照《麦考利澳大利亚字典》所下定义,流放状态指的是“由于受情形所迫,与母国或家园长期分离。”印度著名批评家米娜克西·穆克尔吉(Meenkshi Mukherjee)的文章《流放心理》(“The Exile of the Mind”)对此作了更详尽的阐释。她把文学上的流放体验大体归为四类,其中一类就是身体并未流放,但作家在思考和写作时如同自己并未身在母国似的。她称这类流放为精神的流放,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8]2。穆克尔吉举了卡玛拉·马肯达雅(Kamala Markandaya)、雷杰·劳(Raja Rao)、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拉宾德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的例子说明流放意识导致他们的作品过度怀乡、寻根,并抵制与新环境的融合。比如雷杰·劳充其量是个印度的旅行者,但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印度的风景物候,而他真正生活的法国和美国的物理环境反而是缺场的。澳大利亚文学中也存在相同的现象: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诗歌除了合欢花,很少指名提到或具体描述澳大利亚的花树虫鸟。与夜莺和玫瑰相比,澳洲喜鹊和山龙眼这些字眼没有丝毫感情色彩[9]3
不少欧裔移民作家的怀乡情绪和流放心理导致他们沉湎于对英国的怀念,不能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他们表征澳洲大陆时流露出明显的反家园意识,对澳洲风景不是丑化就是绝口不提。
三、文学作品中的双重情结
赖特审视澳大利亚诗歌时发现存在澳大利亚风物缺场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英国风光。赖特在《浪漫主义和最后的处女地》(“Romanticism and the Last Frontier”)[10]中提到,第一部在本土出版的澳大利亚诗集《狂调》(Wild Notes,1826)[注]《狂调》是澳洲本土出生的诗人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ompson)的作品。而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的《澳大利西亚》(Australiasia, 1823)是本土出生诗人出版的第一卷诗歌,但出版地点在伦敦。中呈现的景色与英国的乡村风光大同小异、几无差别。除了有几处用桉树代替榆树和橡树的地方外,汤普森笔下的温莎(Windsor)、卡斯尔雷(Castlereagh)宛若英国18世纪的乡村。[注]温莎和卡斯尔雷是距离悉尼市中心以西60、70公里的小镇,也是“麦考利五小镇”(five Macquarie towns)中的两个。1810年,新南威尔士州第二任总督拉克兰·麦考利(Lachlan Macquarie)巡视霍克斯布里流域(Hawkesbury River)时命名了五个镇:里奇满(Richmond)、皮特镇(Pitt Town)、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温莎和卡斯尔雷。
在赖特看来,被追随者奉为澳大利亚第一位诗人的亨利·肯德尔(Henry Kendall,1839—1882)的诗歌存在与《狂调》同样的问题。赖特认为肯德尔描绘的澳大利亚景色不像澳大利亚,却更像欧洲:
尽管肯德尔应该很熟悉他家乡霍克斯布里鲜花盛开时的色彩斑斓和品种丰富,他的诗歌中除了丛林歌谣中已经开始吟颂的合欢花,没有出现本地的鲜花。除了哈珀的橡树,其他提到的树木都有欧洲名字,比如雪松,西卡莫; 但是肯德尔曾经在木材厂工作过,应该清楚许多其他的当地树种及其习性。诗中提及的鸟儿也仅有琴鸟和铃鸟。动物没有出现。[1]32
赖特指出,肯德尔的景物诗不是源于对周边环境的细致观察和喜爱,他称不上是澳大利亚的真正诠释者。这一观点针对的是1869年乔治·奥克利(George Oakley)对肯德尔的评价。奥克利提出,肯德尔是第一位表征澳大利亚的诗人[6]84。赖特则认为肯德尔笔下的地形地貌笼统模糊、没有差异、无法辨别。他以同样的措辞描写奥拉拉(Orara)、暮尼河(the Mooni)、纳拉拉溪流(Narara Creek),不借助地名的话,读者根本辨认不出哪是哪。赖特比较肯德尔的《九月》(“September”)、《暮尼河》(“ Mooni”)、《奥拉拉》(“ Orara”)、《铃鸟》(“The Bellbirds”)和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的《夏日意象》(“ Summer Images”)、《致沙锥鸟》(“ To the Snipe ”)时注意到,克莱尔细致入微地观察了英国的乡村风光,而肯德尔描写的澳洲景色却是主观想象而不是客观描述的。
至于为什么身处澳洲的肯德尔对澳大利亚的景物视而不见,看到的反而是欧洲的自然物候,赖特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白人]所看到的风景是局部的、不充分的、暂时的幻象,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利益”[11]32。对于各个阶层的英国定居者来说,这里气候和景物都陌生、险恶,唯有离开的母国才是他们的天堂[12]193。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极端,但至少证明将前往新世界视为被逐出伊甸园、遭到流放这种思想司空见惯。
将澳大利亚描写成与伊甸园形成鲜明对照的荒漠之城是赖特的第二大发现。赖特认为,肯德尔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次反映了整个澳大利亚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沙漠死亡主题”[1]40。他认为自己受到该隐的惩罚,才被放逐到澳大利亚这块大陆上,并渴望重回伊甸园。赖特发现肯德尔的《暮尼河》、《奥拉拉》、《纳拉拉溪流》等诗中反复出现代表伊甸园富饶的水的意象,而与此相对的是澳大利亚内陆的干旱炎热意象。伴随着他想象的干渴、炎热、流放,“该隐的惩罚”渲染了他所有描写内陆的诗歌[1]38,如他的《野橡树的声音》(“The Voice in the Wild Oak”)就流露出悲凉、忧伤的语调:
But he who hears this autumn day
然而,能聆听到秋日
The more than deep autumnal rhyme
聆听到那比秋韵更深沉的
Is one whose hair was shot with grey
是那被哀伤而不是时间
By Grief instead of Time.
夺去黑发的人。
He has no need, like many a bard,
他已经没有必要,像许多诗人那样,
To sing imaginary pain,
去吟诵那想象的痛苦,
Because he bears, and finds it hard,
因为他承担着,艰难地承担着,
The punishment of Cain.
该隐的惩罚。(吴起译)
(Preoccupations38)
肯德尔的《牛道上》(“On a Cattle Track”)、《探险家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Explorers”)等诗歌中呈现的景象都是无遮蔽、无水源的沙漠,就如该隐被驱逐到人烟罕至的地方;探险者在荒漠中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水,但很少成功。
赖特不仅探讨了诗歌中展示的流放之地,还评价了一些小说中描写的可怕景象。她选取了克里斯蒂娜·斯台德(Christina Stead)《悉尼七穷人》中的一段话:
布洛特动起身子,自问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除了气流、暴风雨和气候,没有任何其他事物会漂流到这片远方的南方大陆。……太阳炎热无比,为什么我们不能赤裸着奔跑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看透我们自己的命运?这片大陆最终被发现了。为什么?这个神出鬼没的地方,这片神秘的大陆;它的磁场扰乱了磁针,使得船只失去方向,冰雪、雾霭、暴风雨控制了海域,都保护了这片邪恶可怕的荒原。它的心脏由盐类组成,从它灼伤的伤口溢出东西,是可以毁灭贪婪之人的黄金,而不是解人饥渴的水。[1]xiv-xv
赖特认为,这段话是被流放的欧洲人在与新国度发生冲突时发出的呼声,充满了殖民者面对神秘、狂野的澳洲大陆时感到的那种巨大的无助感、失落感和孤寂感。赖特没有继续评论下去,但是斯台德笔下的新大陆也是缺少伊甸园水源的荒漠之城,邪恶、可怕、神秘。可以说,这也延续了肯德尔的沙漠死亡主题。
赖特还发现,澳大利亚自然风物的怪异性是很多作家极力渲染的方面。她以生于伦敦、移居到澳大利亚的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1846—1881)为亚当·林赛·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1833—1870)诗歌集所作的序为例:
澳大利亚景色的主旋律是什么?如同爱伦坡诗歌的主基调,是怪异、忧郁(weird melancholy)。……澳大利亚的森林有着葬礼般的阴郁气氛,隐秘、严酷。……在其他大陆,人们在哀悼逝去的一年,落叶轻轻地掉在棺材上。在澳洲森林,没有树叶凋落……这些山里的动物要么奇异,要么可怕。灰色的大袋鼠悄然无声地跳跃在粗野的草地上。一群飞过的白鹦鹉像恶魔一样尖叫着。太阳西下,枭突然发出半人类的恐怖笑声。土著坚称,夜幕降临时,从小水塘的深渊中升起恶魔(Bunyip),像妖怪一样的斑海豹。从沉寂的深林远处,传来忧郁的吟诵。土著围着火堆跳舞,身上画得像骷髅一般。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阴郁,都能激起恐惧。……[1]xiii
赖特认为,这段文字中,克拉克的语气好似一个澳洲异乡人的口吻,对他来说,澳洲是流放恐怖之地:平原毫无遮蔽、岑寂无声,花草树木奇形怪状。
本土作家尚且如此,旅居作家对澳洲丛林的感受或许更深。在这一点上,赖特考察的对象是D.H.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袋鼠》(Kangaroo)是劳伦斯一战后离开英国、自我流放到澳洲(1922年5月到8月)写成的充满自传成分的小说。主人公索默斯虽然向往原始神秘的自然风光,但是
这片广袤无垠、荒芜人烟的大地令他生畏。这片国土看似那么迷茫广漠,不可亲近。天空纯净无瑕,水晶般湛蓝,那是一种悦目的淡淡的蓝色。空气太清新了,还没有被人呼吸过。[……]可是那儿的灌木丛,烧焦的灌木丛令他胆战心惊。[……]那片幽灵鬼影憧憧的地方,树干苍白如幻影,不少是死树,如同死尸横陈,多半死于林火,树叶子黑乎乎的像青灰铁皮一般。那儿万籁俱寂,死一般沉静无息,仅有的几只鸟儿似乎也被那死寂窒息了。[13]9
像劳伦斯这样短期旅居澳洲的作家虽然对这片大陆望而生畏,但他毕竟领略到了澳洲的旷野之风。同样的,赖特也注意到,克拉克看到了澳洲大陆的另一面,只有爱着澳洲、反抗旧文明的那些人才能看到的一面。克拉克继续写道:
从没有树荫的树木、没有芬芳的鲜花、不会飞的鸟类和没有学会四足行走的兽类中,有些人是根本感受不到美的。但是荒野中的居住者,变得熟悉起这孤独的美丽……学会了粗犷的语言,能够读懂憔悴的桉树的象形文字。桉树被猛烈的热风吹得奇形怪状,或者在寒冷的夜晚开始痉挛,那时南十字星下万里无云的蓝天结冰……孤寂大陆上的诗人开始理解为什么比起埃及的富饶,自由的以扫(Esau)会更喜欢沙漠的遗产。[1]xiii
尽管赖特承认欧洲意识和新国度之间有着剧烈的冲突,但她也看到了两者实现和解的可能。她认为亨利·汉德尔·理查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的《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1930)和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沃斯》(Voss,1957)向世人说明死亡是实现欧洲意识与原始广袤的澳洲环境和解的一条途径,这种死亡是欧洲意识的死亡、流放心理的消解。通过不断地挣扎、受苦,新大陆将变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友好。
在赖特看来,抵制英国法律和等级制度的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r,1813—1868)是将澳大利亚视作象征自由与平等的乌托邦的典型一例:
Be then the bard of thy country! O rather
那么,成为你国家的诗人吧!
Should such be thy choice than a monarchy wide!
噢,你的选择比君主更为广泛!
Lo! 'tis the land of the grave of thy father;
看!这是埋葬你父亲的土地;
'Tis the cradle of liberty! I think, and decide.'
这是自由的摇篮!我认为,而且坚信!
(“The Dream by the Fountain”)
流放犯后裔出身的哈珀,虽出身微贱,在政治上却是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虽然知道澳大利亚是“埋葬你父亲的土地”(“the grave of thy father”),但他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自由的摇篮!”(“Tis the cradle of liberty!”)
赖特认为哈珀是第一个接受澳大利亚独特的环境并从中获得快乐的诗人[1]19。然而,赖特凭着独有的敏感和尖锐的洞察力,发现哈珀的景物诗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倾向,从早期的全景式、模糊性描写,逐渐发展到具体入微的描写。笼统的描写可以模糊澳洲景物与欧洲景物的差异性,也更易于被英国背景的读者接受,而具体的描写则更能凸显澳洲景物的特色。赖特将这种变化归之于哈珀所受的华兹华斯的影响以及他对澳大利亚的情感认同。[注]哈珀之后,亨利·劳森(Henry Lawson,1867—1922) 的《瓦纳塔与金合欢》(“Waratah and Wattle”, 1906)、多萝西·麦凯勒(Dorothea Mackellar,1885—1968) 的《我的国家》(“My Country”, 1908)等诗作也都大力讴歌了澳大利亚的物候之美。
四、结语
欧裔白人对待澳洲大陆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他们把澳洲看作流放之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澳大利亚视为希望之地。归属感的缺乏令他们往往将自己视为新大陆的客居者,对澳洲心存恐惧和疑虑,在文学作品中也往往不能客观真实地表现澳洲风景。如赖特所指出的,只有当他们对澳洲产生情感认同时,才能改变与环境的对峙关系;而只有对澳洲建立起亲切挚爱的感情,人们才能看到这片大陆的美丽,为它撰写绚丽的诗篇!
[参考文献]
[1]Wright, Judith.Preoccupations in Australian Poetry[M].Melbourne: OUP, 1966.
[2]Elliott, Brian.The Landscape of Australian Poetry [M].Melbourne: Cheshire, 1967.
[3]Falkiner, Suzanne.The Writers’Landscape: Wilderness [M].Sydney: Simon & Schuster, 1992.
[4]Bird, Delys.Gender and Landscape: Australian Colonial Women Writers[J].New Literatures Review, 1989, 18: 20-36.
[5]Frost, Lucy.No Place for a Nervous Lady[M].Ringwood: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1984.
[6]Innes, C.L.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English[M].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7.
[7]Steele, Fritz.The Sense of Place [M].Boston: CBI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1.
[8]Bennett, Bruce, ed.A Sense of Exile: Essay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M].Perth: The U of Western Australia, 1988.
[9]Cornwell, Tony.Australian Poet Judith Wright (1915-2000): an Appreciation[EB/OL].(31 Aug.2000) [ 18 July 2007].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0/aug2000/wrig-a31.shtml.
[10]Wright, Judith.Romanticism and the Last Frontier[M]// Judith Wright.Because I was Invited.Melbourne: OUP, 1975.59-80.
[11]Wright, Judith.Landscape and Dreaming[M]// Ed.Stephen R.Graubard.Australia: The Daedalus Symbolism.North Ryde: Angus & Robertson, 1985.29-56.
[12]Jones, Dorothy.Women, Place, and Myth-Making: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M]// Ed.Hena Maes-Jelinek, Gordon Collier and Geoffrey V.Davis.A Talent(ed) Digger: Creations, Cameos, and Essays in Honour of Anna Rutherford.Amsterdam: Rodopi, 1996.191-202.
[13]Lawrence, D.H..Kangaroo[M].1923.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