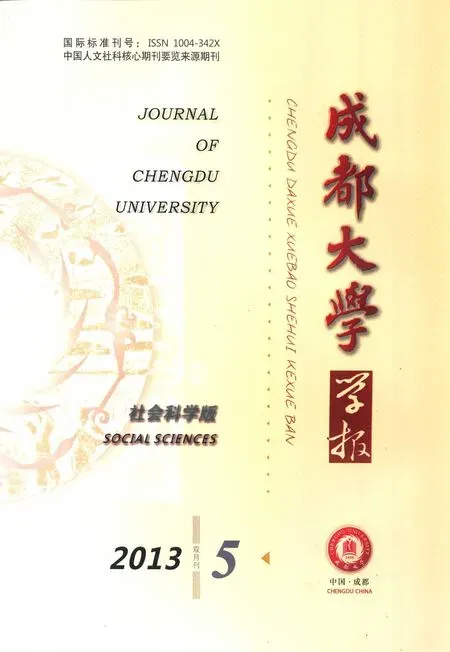天花藏主人小说“科举群像”之文化透视
刘雪莲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天花藏主人小说“科举群像”之文化透视
刘雪莲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玉娇梨》、《平山冷燕》为其代表作。实际上,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不仅弘扬了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也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士人群像。其中有穷困落魄的秀才,亦有混迹于科场的帮闲,还有靠夤缘而上的所谓名流。这些科举士人被遮蔽的生活状态以及人格上的裂变,说明了科举弊端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也侧面表明科举最终走向没落的一个内在原因。另外,天花藏主人赋予了这些人物以鲜活的语言特征和复杂的心理活动,亦使他们成为科举文化中的具有象征意味的人文符号。这些人物虽然包含了作者零碎诉求的整合,但却能够达到通俗小说所预期的读者效应与文化阐发。天花藏主人小说对科举士人的刻画,也表明了在《儒林外史》出现之前,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已经在古代小说中异彩纷呈。
天花藏主人;科举群像;文化;生态;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创作并编辑了十余部才子佳人小说[1],《玉娇梨》、《平山冷燕》为其代表作。天花藏主人的小说虽然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小说不仅塑造了金榜题名、娶得佳人的才子,也呈现了穷酸、变态士人的种种生活状貌。从文本来考察,秀才、举人以及假秀才、假举人、假名士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中数量较多,占有一定的篇幅,因此笔者简称其为“科举群像”。由于天花藏主人赋予了这些人物以鲜活的语言特色以及无意识的文化象征意味,而以往的学者对此关注很少,因此笔者针对“科举群像”的特点进行归类分析。
一 现实中的落魄秀才
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才子”在科举高中之前,多数是贫穷落魄的秀才,因此贫穷秀才在他的小说形象中占有一定比例。明清时期,秀才是进入士大夫阶层与官场的最低门槛,即是经过院试得到入学资格的“生员”。秀才本身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朝廷给予的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在明、清科举制度之下,士子一朝进学为生员,国家便复其身,免差徭,地方官以礼相待,非黜革,不受刑责。廪生并得食廪。贫寒者给学租养赡。”[2]如能考取生员,确实会受到社会普遍尊敬,考取廪膳生员,还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这对很多贫寒读书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毕竟名额有限,秀才又很少自食其力,所以难免陷入潦倒落魄的生活困境,甚至贫穷的读书人是否有经济能力参加科举考试也是一个问题。明清时期童生参加县试、府试、院试的费用问题很大,清代贫苦农民的弟子,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十分艰难[3]。而即便是考中秀才,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因此,明清小说中很多“未达”秀才给人的是“穷酸”的印象,例如明末清初小说《鼓掌绝尘》便直接把秀才看成是“酸丁”。
天花藏主人对落魄秀才有具体的描绘,如《玉娇梨》中的秀才苏友白因父母早亡,又在山东地界的旷野中被劫,因而身无分文,只好穷途卖赋。幸好得到了佳人卢梦梨的帮助,才摆脱了困境。而《平山冷燕》中的才子平如衡更是家境贫寒,后来又辞去了秀才,无法参加乡试,因好友燕白颔替平如衡纳了监,他才得以继续参加科考。实际上,平如衡的生活状况是很有代表性的,包括他率性耿介的个性,都显示了秀才身份的特点,也反映出大多数底层知识分子实际的生活情况。
天花藏主人小说中还有一部分秀才虽然生活潦倒,但却表现出了穷酸与自尊、自负相融合的鲜明个性特点。如在《平山冷燕》中冷绛雪的舅舅郑秀才,在冷绛雪被买入山黛府中时,倚着自己有前程,便打算帮冷绛雪讨回公道,理直气壮去找府尊进行理论。而府尊根本不把郑秀才放在眼里,听了郑秀才的一番理论,拍案大怒道:“甚么权门!甚么谗言!你一个青衿,在我公堂之上这等放肆……将郑生员逐出去!”[4]虽然郑生员有理,但一个青衿的理论如何抵得过宰相家买婢女的大事,结果他还是被驱逐了出去。明清时期秀才虽具有一定的特权,但是并没有做官,所以地位还是很有限。《赛红丝》中的袁通判也是同样,将来讨公道的一群生员驱逐了出去。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穷酸秀才的生活非常了解,也说明秀才的地位也只是在普通百姓的眼里较高,秀才也只有考中了举人才会有出路。
比较天花藏主人的其他作品,《赛红丝》中进一步呈现了穷酸秀才的落魄程度。如秀才宋古玉生活非常贫困,却经常同社友去丈人家吃酒论文。丈人死后,小舅子皮象十分吝啬,捐了民监,不喜宋古玉上门吃酒。宋古玉偏又和文友到了妻弟门前,皮象让家人谎称不在,结果宋古玉发现后挂不住面子,便大骂了皮象一番。宋古玉自认为:“我宋古玉胸藏贤圣,笔走龙蛇,自是科甲中人物。”[5]他虽然请不起文友喝酒,但从心底里瞧不上皮象这样的“白衣监生”,且自以为马上就会飞黄腾达。也正因宋古玉这一番谩骂,导致了皮象勾结他人一起来加害宋古玉。宋古玉不久就被诬陷入狱,使本来就穷困的家庭陷入了绝境。妻子先是当光了首饰衣服,然后卖了桌椅家伙,最后无物可卖,让儿子宋采去以书换馍。宋采到了点心铺中,看见许多人在那里吃馍馍,欲要开口,脸上早先红。没奈何只得与掌柜说话,没等说完又是满脸通红。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反映了穷困给宋采带来很多的难堪和辛酸,不过好心的卖馍人并没有要宋采的书,让人把二十个馍馍和一壶好茶送到宋采家里。因接下来还要过活,妻子又让儿子宋采找皮象借钱,不料宋采和舅舅发生语言冲突,被皮象打了一顿。其实宋古玉之所以被害入狱,与其过于自大而又生活困窘有关。他自身贫困潦倒,却要过读书人的诗酒生活,必然会与现实产生矛盾。不过宋古玉和儿子宋采后来都“高中”了,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天花藏主人自言“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6],可能也有贫穷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把贫穷秀才的生活写得很生动。
由天花藏主人对穷酸秀才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通常鄙视劳动生产。明清时期很多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包括已经成功做官的文人,不仅不参加生产劳动,而且也不关心生产。“耕读传家”是科举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参加科举应考的士人,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不过,明清之际海宁查氏是江南望族,历代科甲鼎盛,仅康熙朝便“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海宁查氏耕读传家,事儒不废,有学者认为:“如查氏一向强调以儒为业,耕读为务。这种导向,突出了读书与儒业,强调了自力与自养。”[7]但是大多数致力于科举又生活窘迫的读书人做不到这一点。王德昭先生认为:“士而不得志于科场,因他无所能,又无以为生,则上焉者为选家,为塾师,等而下之者则焉为巫卜星象。”[2]P158明清时期塾师是大多数秀才从事的职业,天花藏主人笔下的穷秀才主要以教书为出路,例如宋古玉出狱以后去做了塾师。天花藏主人的其他小说还写到了秀才们争先觅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遇到好馆很难,也便有了抢馆、争馆、抢学生的现象发生。如秀才常莪草、秀才强之良等以至于因坐馆不成,彼此嫉妒、陷害,基本都是秀才生活的写照。也有先在女方家里做西宾,然后再做女婿,如《玉支玑》中的长孙肖因生活穷困而到管灰家坐馆,然后与管小姐订婚。当然,也有用笔墨纸砚来赚取生活费的情况,而农耕生产在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中是没有的,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生活实际问题。
天花藏主人自身应该就是一个落第秀才,也可能当过私塾先生。科举时代的秀才们,除却少数是富足家庭,大多数未达的秀才往往生活困顿,年复一年的备考和科考,导致他们耗尽心血。他们又做不来庶民的工作,因此在无形的科举阴影之下,他们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但天花藏主人对秀才贫困的根源还缺少认识,远不及《儒林外史》反映得深刻。天花藏主人认为自身的贫困是由于怀才不遇、命运不济造成的,也是受当时历史文化与社会风尚影响的结果,这也表明了明末清初时期一批小说在对科举的反映与认识上还存在着缺陷。
二 混迹于科场的“假山人”、“假名士”、“假秀才”
天花藏主人对混迹科场的“假山人”、“假名士”、“假才子”描写较多,这些人物具有鲜明的语言特点,并以“群像”的方式大量出现,虽然有些人物并非小说主要描写的对象,但其个性化特色似乎超越了“才子形象”。很多故事情节富有喜剧性的色彩,明确表达了天花藏主人对这些人物的嘲笑和讽刺,也可以看出他对科举考试的疑惑、不满及无奈。
(一)“假山人”
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中,较为突出地刻画了宋信这个典型的“假山人”形象。宋信是《平山冷燕》中较为重要的人物,贯穿小说始终,他自称“山东宋山人”、“我晚生一山人布衣”等,经常以“山人”自居,又自夸是司马相如再生,并与很多社会名流是莫逆之交。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晚明时期“山人”的数量很多。方志远先生在《“山人”与晚明政局》一文中就谈到“山人”对晚明政局的影响,并对“山人”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山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山里人’,而是那些未入仕而想入仕、身在江湖却积极参与政治,以及虽入仕却处于在野地位的读书人。前者谋求的是入仕、是参与政治;后者谋求的是享受、是暂时逃避政治。”[8]就宋信而言,他并非逃避政治的类型,而是混迹于科场和官场的山人。实际上,宋信从未真正作过一首诗,他诬告才女山黛,自取其辱之后,便四处招摇。由于宋信不屑于科举,又不能被举荐,所以只能四处打秋风混饭吃。
宋信在打秋风的过程中遇见了才子燕白颔和平如衡,为了卖弄自己,一字不差地抄袭了山黛的《白燕诗》。燕白颔、平如衡对这首诗有些怀疑。但事有凑巧,在几人相见之时,宋信看见四五岁的小学生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落款是《新秋梧桐一叶落图》,触想起山黛做的“梧桐一叶落”的诗,于是当场作诗,一挥而就。燕白颔、平如衡信以为真。可是回去后,便从晏知府那里得知宋信所作的诗都是抄袭山黛的。燕白颔有意询问宋信时,宋信却吹嘘道:“……假他人之作而冒为己才,见人一味足恭,逢财不论非义,如此之辈,岂非不肖?若我小弟,在长安时,交游间无不识之公卿,从不曾假其片纸只字以为先容……所以遍游天下,皆蒙同人过誉。”[4]P143宋信言之凿凿,俨然一个正人君子。燕白颔便直接问起山黛的《白燕诗》,宋信听见问出“山小姐”三字,不觉一急满脸通红,一时答不来。燕白颔见宋信面色有异,知有情弊,一发大言惊吓他,而宋信无奈只是嘻嘻而笑。最终宋信“见事已泄漏,料瞒不得,只得借平如衡之言,便老着脸哈哈大笑……。”[4]P144
作者运用了大段的文字反复写了宋信语言、脸色和大笑,使人物形象极具个性化色彩。同时采用了“现世现报”、“自打嘴巴”的讽刺手法,与《儒林外史》有类似之处。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写严贡生在张静斋、范进的吹捧之下开始吹嘘卖弄,严贡生道:“实不相瞒,小弟为人率真,在镇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著实关切!”[9]接着又指手画脚地卖弄自己,正在这时,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9]P30这段当场“现世现报”的描写与上文极为相似,但却是更为冷静和客观的叙述,作者没有做任何主观的评判,也体现了吴敬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0]的特点。而天花藏主人的讽刺手法还显直露,总是在行文中对人物做出评价。不过从当时通俗小说适应市场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底层读者阅读,从小说艺术来看不及《儒林外史》。
《平山冷燕》刻画宋信这样的“假山人”,不仅是为了与才子对比,也嘲讽那些游走在科场与官场夹缝中的文人,不仅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厚颜无耻,最后成了权宦的帮闲。《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第十二回回评对宋信的点评是:“摹写无廉耻、不怕羞人,厚颜次第,一一如画”、“无耻中无耻之霸也”。[4]P140-141“山人”不过是这类人物遮挡自己的幌子,亦显示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对这类人物的负面影响。
(二)“假名士”
“假名士”在天花藏主人小说中较多。《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对张寅和宋信点评道:“张寅,假名士也,自应装腔作势,炫人耳目,乃一见宋信,便倾心吐胆,尽露真情,何也?盖假名士与假山人自意气相投,不谋而合也。”[4]P127点评中把张寅看成是“假名士”,其实“山人”中有很多名士和才子,宋信也可以说成是“假名士”、“假才子”,但是“名士”、“才子”并非都是“山人”,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中把“假名士”与“假山人”是区分开来的,因此笔者单独来论述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假名士”。
《平山冷燕》中的张寅、《玉娇梨》中的杨芳都属于“假名士”。由于父亲是朝廷重臣,他们便夤缘而上,直接得了秀才。这类人物不同于“山人”,他们没必要装作“山人”行藏,四处行骗。张寅倚仗父亲是礼部尚书,四处结交有才华的士人,目的是要扬名。不料被平如衡羞辱了一番,接着又在山黛家里考诗,被冷降雪用诗捉弄,最后涂了一个大花脸。而杨芳是杨御史之子,被白公约去考察是否有才,他在宴席之上还勉强过得去,席间与吴翰林在轩中散步,杨芳忽见上面横着一个扁额,题的是“弗告轩”三字。吴翰林见杨芳细看,便有意称赏这三个字。杨芳便卖弄道:“果是名笔。这‘轩’字也还平常,这‘弗告’二字,写得入神!”[11]却将“告”字读作常音,不知“弗告”二字取《诗经》上“弗谖”、“弗告”之义,“告”字当读与“谷”字同音。杨芳本自无才,这一卖弄反而露出了原形,结果与白公女儿的婚事告吹。
张寅、杨芳这样的“假名士”只是希望向“名士”靠拢,本身没有行骗的意思,也不是靠此来求生活。还有一类专靠“名士”之名来混饭吃的人物。《玉娇梨》十六回中,写白太玄游西湖之时,听说西湖上有赵千里、周圣王两位名士,每日间来拜两位名士的乡绅朋友络绎不绝,天下的名公贵卿都是相识,或是求他作文,或是邀他结社,终日湖船里吃酒,忙得不可开交。白太玄心中暗喜,但初次并未访到,不料二人突然来访,见到白太玄后一番客套,便问起籍贯,得知白太玄是金陵人。赵千里便问白公是否认识金陵的吴瑞庵翰林与白太玄工部。赵千里和周圣王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白太玄。于是接下来有了这样一番情景:
白公惊道:“闻是闻得,却不曾会过。敢问二兄,何以问及?”赵千里道:“此二公乃金陵之望,与弟辈相好,故此动问。”白公道:“曾会过否?”赵千里道:“弟辈到处遨游,怎么不曾会过!去秋吴公楚中典试,要请小弟与圣王兄去代他作程文并试录前序,弟辈因社中许多朋友不肯放,故不曾去得。”白公道:“原来吴瑞庵如此重兄。只是我闻得白太玄此老甚是寡交,二兄何以与他相好?”周圣王道:“白公为人虽然寡交,却好诗酒,弟辈与他诗酒往还,故此绸缪。”白公笑道:“这等看来,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矣!”……白公送了二人去,因叹息道:“名士如此,真足羞死!”(《玉娇梨》第十六回)[11]P181
赵千里、周圣王自吹天下的名公贵卿都相识、在西湖上几乎应酬不过来的情景简直令人不可想象。似乎是两位公众人物,也堪称骗子中的高手。至于二人诗文如何,作者只字未提,也没有说他们是否是科举中的人物。但是他们自吹去秋吴翰林楚中典试,要请他们去代作程文并试录前序,似乎才华高过翰林。由此可知他们对科举考试等情况了如指掌,又能与名士交流,笔者认为他们至少也应该是秀才。至于他们的科考与家庭背景并不清楚,他们只是混在才子、名流、公卿里打秋风,并未继续参加科举。但万万想不到“假名士”遇见了“真名士”,真假映衬,富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科举文化制度下富有张力的人文表情。
(三)“假秀才”
“假秀才”在天花藏主人的每部小说都有出现,他们有秀才之名,却多无秀才之实。至于怎么考中的秀才,小说大多没有交代。这些“假秀才”中有较为富裕家庭的子弟,也有穷困书生。首先来说富家子弟中的“假秀才”。《玉娇梨》中写白太玄在西湖冷泉亭上闲坐之时,忽见一班有六七个少年,都是阔巾华服,后面跟随许多家人,携了毡单,抬着酒榼,一拥都到冷泉亭上饮酒。从这些少年的打扮来看,都是富家子弟,白公便与少年们闲聊,得知有在庠、也有在监的,还有一个王姓的,被称为“簇簇新新一个贵人”,原来是新中的举人,白公便以为是斯文一派,而秀才、举人对自己身份却自有看法:
王举人就接说道:“甚么斯文,也是折骨头的生意!你当容易中这个举人哩,嘴唇皮都读易了。反是老兄不读书的快活——多买几亩田,做个财主,大鱼大肉,好不受用!”又一少年道:“王兄,你既得中,就是神仙了,莫要说这等风流话!象我们做秀才的才是苦哩:宗师到了,又要科考、岁考,学内又要月考、季考,朋友们还要做会、结社。不读书又难,读书又难。”又一少年道:“老哥只检难的说,府里县里去说人情、吃荤饭,容易的就不说了。”大家都笑起来。(《玉娇梨》第十六回)[11]P177
这段文字中,少年所说的考试,是指生员在学的考试,通常以学政按临的岁、科二试最为重要。岁考每三年一次,科考是录送乡试的考试,“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凡府、州、县之附生、增生、廪生,皆须考试。”[12]然后重分等第,“清初沿明旧制,顺治九年题准岁考生员有六等黜陟法,并有青衣、发社两名目,为考者降级之处分,由蓝衫改着青衫曰青衣,由县学降入乡社曰发社。”[12]P28可见科考、岁考对生员的重要性,当秀才也确实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考试是不能逃避的。“生员可因出贡或乡试中式出学,惟出学前,则按定制,不论在学久暂,教官按月有月课,四季有季考,除丁忧、患病、游学等有事故外,不到者有罚,重者黜革。”[2]P90而“清制于学校的月课、季考,规定甚严。其于各学校教官既频频督责如此,而于生员所定的处分,尤为严峻。”[2]P115因此不读书又难,读书又难,少年秀才的牢骚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他们在科举之下的真实困境。可是另一个秀才的话却揭穿了他们的老底,因为“说人情”、“混饭吃”也是秀才们的特权和本色,大家的“笑”完全是对这种“本色”的肯定。王举人似乎应该有些独到见解,可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王举人竟然张口就说自己的“斯文”是“折骨头的生意”,王举人似乎把科举看成了做生意,但真实想法还不好猜测。
清初话本小说《醉醒石》借助吕主事之口对科举考试进行了直接的讽刺:“读甚么书,读甚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读甚么书,做甚清官!”[13]比较来看,王举人的想法似乎昭然若揭。作者接着写了秀才和举人吃酒、作诗,大家作了半日,并无一个成篇,还是白太常为众少年作了限韵诗一首。这段文字让人哑然失笑,一群科举中人竟然是“混世假秀才”、“假举人”。“秀才”、“举人”不过都是欺世盗名。这段对秀才群像的描写,不似对宋信、张寅等的直接讽刺,显得笔无藏锋,而是对日常生活素材进行了加工和提炼,与《儒林外史》已经非常相似了。并且这些秀才、举人的语言极具个性化色彩,因此这些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文化象征的意味,从侧面呈现了科举时代的人文风貌。
第二类“假秀才”是借“秀才”之名骗钱、混饭吃的人。他们没有像《玉娇梨》中杨芳、《平山冷燕》中张寅、《两交婚》中暴文那样的家世背景,也不是家庭富有的纨绔子弟。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山人”、“名士”外在形象,同时也没有广泛的交往圈子,无法四处招摇,也只好假借“秀才”之名,坐馆来骗钱糊口,还有个别的是为了骗娶佳人。例如《玉娇梨》中的秀才张轨如、王文卿,《玉支玑》中的秀才强之良,以及《麟儿报》中后来才考中秀才的逄寅,都是毫无才学,假作名声,趋承势利,只想骗钱的“假秀才”,其中张轨如主要是骗取佳人。他们在坐馆不成后,均成为了纨绔子弟的帮闲,主要干些出谋划策、陷害他人的勾当。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愚蠢可笑、当场出丑都有很多生动刻画。
第三类是更为卑鄙无耻的市侩型秀才(也包括举人)。《赛红丝》中的“假秀才”常莪草,经常对不出学生出的对子,一次谎称家中有急事找穷秀才白孝立。白孝立却说想不出来,又说以前想得出是因为家计从容,故情兴所至,直觉思入风云,近因愁柴愁米,扰乱心肠,那些奇特才情,都不知往哪里去了。常莪草因请白孝立喝酒,又拿出二两银子,白孝立很快想出了对子,便将桌子上那锭银子取了,笼入袖中。不仅如此,还把喝酒和勒索银子称为“二味妙药”,一副厚颜无耻的市侩嘴脸,比常莪草有过之而无不及。常莪草的发财之道是“假才”加之欺骗,而白孝立发财之道是敲诈。还有与之类似的“假举人”,如《玉娇梨》中山东地界的钱举人,会做几句诗词,人家有事相求便敲诈勒索起来,又善于逢迎和见风使舵。作者认为这类人算不上有“真才”,作为秀才、举人在学识上或许是过关的,但其道德品质为人所不齿,因而笔者将其归为“假秀才”(“假举人”)之列。
第四类“假秀才”是“学霸”类型的秀才。常莪草、白孝立这类“假秀才”毕竟还是“按劳取酬”的,而这类秀才根本不是。例如《画图缘》介绍了“赖秀才”以及帮腔的“皮秀才”:
本县有一位赖相公,是个学霸,为人甚是凶恶,诈骗小民,是他的生意,不消说了;就是乡宦人家,也要借些事故,去瓜葛三分。……生员们来告状,必有冤屈,况谋死业师,人命大情,就是谎状,也须父母老爷审出甘罪……赖秀才道:“天下利弊,尚容诸人直言无隐,且公论出于学校。况谋师重情,又关学校。生员们为公检举,理之当然……。”[14]
赖秀才不似前文提到的郑秀才那么容易被欺负,他不仅胆大妄为、欺诈勒索,还包揽诉讼,振振有词,似乎张嘴闭嘴都是公理。他充分利用秀才受人尊敬的特点,连府县也拿他没办法。他连乡宦人家都去瓜葛,何况贫穷小户人家。他完全离开了知识分子的层面,与泼皮无赖等同,因此作者称其为“学霸”。“学霸”填补了我们对以往的“穷酸秀才”的单一认识,也让我们真正看到了“秀才”形形色色的类型,他们不仅奇特怪异,更包括变态心酸。
以上绝大部分“假名士”与“假秀才”都是未能从科举进入仕途,而暂时混迹于官场与科场之间的人物。他们或希望夤缘而上,或希望扬名天下,或希望不劳而获、谋取钱财,或兼而有之。他们都不是年复一年参加科考的穷酸秀才,而是不能参加生产,又不能经商或入仕,又不甘于穷困潦倒,本性又自尊、自负、自大的秀才,这种性格特征与生活状态导致了他们在夹缝中无法求得更好生存。虽然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很多文士四处交游、坐馆、入幕以及待选候缺等,以便曲线入仕,也是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与生活目的,但是部分四处打秋风的文人已经蜕变为敲诈勒索的骗子,个别乡里秀才竟成为了有学问的恶霸。这种生活状态与生存之道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科举的缺陷与弊端对他们产生的是另外一种负面影响,即非终身科举不第的痛苦,而是人格上的扭曲、摧残与裂变。由此也可知,科举制虽是为选任官员所设,但在实际运作的漫长过程中,一部分“未达秀才”形成一个独特而又稳定的社会群体,这与社会历史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困惑、痛苦与失败,表明了科举最终走向没落的一个内在原因,他们亦成为士人文化的一种象征。
虽然天花藏主人小说所呈现的“科举群像”仅是一种零碎诉求的整合,但并不妨碍这些文字具有批评的价值功能。实事求是地说,天花藏主人的小说没有《儒林外史》那样的艺术表现力,天花藏主人毕竟不是吴敬梓,他对科举看得不那么透彻,也没有那么通达。但是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知识分子被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生活状态,并使他们成为科举文化中的具有象征意味的人文符号,已经达到了通俗小说所预期的读者效应与文化阐发。在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政治理想的构建方面,天花藏主人的小说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蕴藏着儒家伦理化的精神内涵,足以揭示明末清初时期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的时代议题。由此也可以看到,早在吴敬梓之前,变态士人就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通俗小说中,《儒林外史》的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这对于我们研究科举题材作品的流变以及科举文化生态有着重要意义。
[1]刘雪莲.明末清初小说家天花藏主人及其作品研究述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5).
[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127.
[3]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9~77.
[4][清]佚名.平山冷燕·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9.
[5]古本小说集成·赛红丝(影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3.
[6]古本小说集成·平山冷燕(影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
[7]洪永铿.海宁查氏与查慎行世系考[J].浙江学刊,2007(1).
[8]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J].中国社会科学,2010 (1).
[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30.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5.
[11][明]荑秋散人编次.玉娇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3.
[1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8.
[13]古本小说集成·醉醒石(影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41.
[14]古本小说集成·画图缘(影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85.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Portraits of Scholar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Novels by Master Tianhuacang
Liu Xueli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81)
Master Tianhuaca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writers of fictions about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Gifted Romantic fiction,with Yujiao and Li,and Ping,Shan,Ling Yan a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In fact,his novels not only carried forward love stories between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but also present diverse images of scholars,including poor sorehead scholars,sit-forother-for living examinees,as well as so-called celebrities relying on connections.Their shaded liv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 of these scholar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not only indicat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rawbacks on them,but also reveal from one side underlying causes of an ultimate declining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In addition,he gives these characters vivid language features and complex mental activities,and thus enables them to become symbolic cultural symbol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Although these figures embody the integration of fragmented demands of the author,they can achieve the reader effect and cultural explication expected from popular fictions.The portraits of scholar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Master Tianhuacang's novels also show tha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Scholars,the images of various kinds of scholars had been in blossom and splendor in ancient novels.
Master Tianhuacang,portraits of scholar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culture,ecology
I206
A
1004-342(2013)05-63-07
2013-06-03
刘雪莲(1977-),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