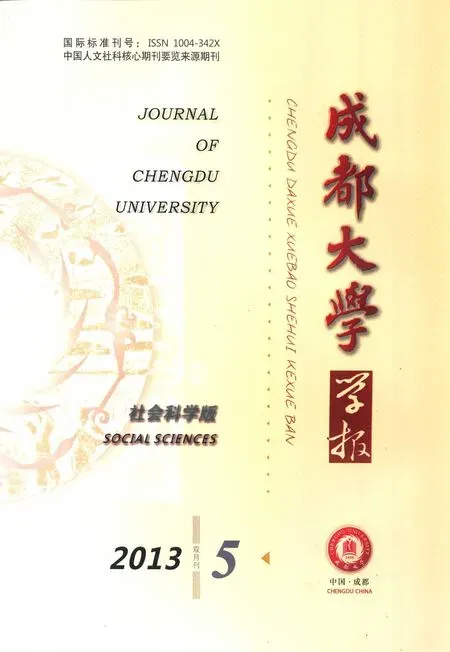新约新制下的邮件递送及制度回应*
吴 昱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32)
新约新制下的邮件递送及制度回应*
吴 昱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32)
在1858年及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了清廷须履行代递各国信件的职责,然而此项功能与传统的邮驿体制互有冲突,不仅引发固有体制内部的抵抗,亦促使清廷建立新的递信体制应付新职,由此逐步开启中国近代新式邮政的建设历程。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邮件传递;新式邮政
传统邮驿制度,乃为契合皇朝统治的体制而设,民间商业信局,则主要为商民信息流通服务,而这种官民两分的体制并非泾渭分明①。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当中,均列有清廷须为签约国代递信件的条款。此举不仅使清廷逐渐接触现代国家义务观念,亦促使其开始在体制内增设新的功能,甚至催生新的体制以应付困境。
一 条约权利与使馆文书传递
在1858年与各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前,清廷已利用驿站,为在北京俄罗斯馆的俄罗斯人提供邮递服务。但正如对此馆研究颇深的蔡鸿生教授指出:“建交伊始,清政府便用‘理藩’眼光看待俄国,给它‘特设邸舍,以优异之’的待遇。”②在其书第一章《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中,蔡先生从官制、给养、邮递和接送四项,分析理藩院对俄罗斯馆的管理,其中在“邮递”节中,蔡先生写道:“按理藩院则例,北京俄馆与恰克图之间往来匣只邮件,‘轻者由驿递送,重者彼时若无差便应俟每年四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前后,照例专差之便送往’(咸丰七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致署固毕尔纳托尔咨文)。”“在嘉庆年间,理藩院对俄馆实行过邮检制度。‘若寄信于其国者,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③由此可见,俄罗斯馆成员之所以可以利用驿站交递文书,乃因清廷以“藩属”相视,但其传递范围亦仅限于文书,而盘费银两,只容许“恰克图玛雨尔(边务委员)会同部院章京照数过秤装匣,给予恰克图商人运脚,代为运送。”④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后,列强对打开中国市场及公使驻京等问题,不断与清廷发生摩擦,最终酿成自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后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明确将外国公使及其随员眷属长期驻京写入条约之中,而随之而来的,即是各国公使与其国家书信往来的安排问题。不过各国与清廷签约时间有前后之分,在具体条文上亦有细微差别。以往研究多以中英《天津条约》为范本,而其画押时间尚在其后,新修之《中国邮票史》⑤注意俄国与其他各国权利之差别,但叙述时间上前后倒置,易生混淆。
咸丰八年五月初三(1858年6月13日),俄国最先与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十、第十一条与通信有关:
“第十条俄国人习学中国汉、满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份,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有驻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驻京之人及恰克图或各海口往来京城送递公文各项人等路费,亦由俄国付给。中国地方官于伊等往来之时,程途一切事务,要妥速办理。
第十一条为整理俄国与中国往来行文及京城驻居俄国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图二处遇有来往公文,均由台站迅速行走,以半月为限,不得迟延耽误,信函一并附寄。再运送应用物件,每届三个月一次,一年之内分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递,勿致舛错。所有驿站费用,由俄国同中国各出一半,以免偏枯。”⑥
在未签订《天津条约》之前,俄国即十分重视书信的安全问题。据蔡鸿生教授分析,俄人主要利用两种办法避开理藩院对书信的检查,一是寄送俄国外交部的报告,只盖私章而不盖北京布道团公章,避免理藩院视为官方文件;二是用隐显墨水书写情报⑦。1858年10月俄使入京换约,就曾发生俄方要求派员进京送信,而咸丰帝要求以“著照护送学生来京之使臣办理”,茅海建就此事指出:“按照新条约的规定,送信俄使一切费用自理。咸丰帝坚持清朝负责其费用,目的在于维护旧制,有所监管。”⑧而从此次签订的条文可以看出,俄国因原设俄罗斯馆之便利,所行路线与前基本无异,然有两点与之前不同,一是驻京人员及送递公文人员的费用,全由俄国承担,二是利用驿站之费用,亦由俄国承担一半。此种安排,无非为公文传递安全起见,避免清廷官吏拆阅信件,盗取信息。盖费用自付,必将自雇可信之人手,随带书信货物,沿途仅利用清廷台站休息换马,而不容清廷官吏过手书信。可见费用问题背后,涉及公使权力与清朝体制,条约行文字里行间,处处皆是别有文章。
继俄国之后,咸丰八年五月初八(1858年6月18日)美国亦与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四款即有关书信寄递:“因欲坚立友谊,嗣后大合众国驻扎中华之大臣任听以平行之礼、信义之道与大清内阁大学士文移交往,并得与两广、闽浙、两江督抚一体公文往来;至照会京师内阁文件,或叫以上各督抚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均无不可;其照会公文如有印者,必须谨慎赍递。遇有咨照等件,内阁暨各督抚当酌量迅速照覆。”⑨由于在列强之中,美国之势力相对比较弱,在文书寄递上并无特殊要求,这亦与当时美国在华之势力不强有关,在利益要求上亦比英、法等国相对较少。
而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与法国,则先后在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1858年6月26日)与五月十七日(6月27日)与清廷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第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英钦差大臣各式费用,皆由英国支理,与中国无涉;总之,泰西各国于此等大臣向为合宜例准应有优待之处,皆一律行办。”⑩而中法《天津条约》第二款规定:“兹两国幸然复旧太平,欲垂之永久,因此两国钦差大臣议定,凡有大法国特派钦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诏敕前来中国者,或有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按照泰西各国无异。又议定,将来假如凡与中国有立章程之国,或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住者,大法国亦能照办。凡进京之钦差大臣公使等,当其暂居京师之时,无不按照情理全获施恩,其施恩者乃所有身家、公所与各来往公文、书信等件皆不得擅动,如在本国无异;凡欲招致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毫无阻挡。所有费用,均由本国自备。大清国大皇帝欲派钦差大臣前往大法国京师侨居,无不各按品级延接,全获恩施,俱照泰西各国所派者无异。”(11)细读条文,则其比中俄《天津条约》之规定更进一步:俄国寄送文书之人员,尚须经台站行走,而英法二国信差则可于“沿海任何地方”带信走递,清廷则必须如对待驿站差使一样加以保护。也就是说,英法二国之信差或其他人员,可以不仅限于通商口岸之桎梏,借助此项权利,可以随时深入清朝内地,且清廷需要对其活动加以保护。这一条款,为日后内地民众与入境洋人之冲突,埋下了一个法理的伏笔。
额尔金在1858年7月12日向国内转报这一条约时,曾做出这样一番解释:“条约中从中国政府所取得的各种特许权,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为过分;除了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原则以外,并不超过各商业国家在习惯上相互自由让与的那些条件;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特权的让与等于一种革命,它涉及到在帝国传统政策上某些最宝贵的原则的放弃。”(12)而一个多世纪后,茅海建也在其研究中写道:“(中英《天津条约》)这与当时的西方今日的世界通行的国际准则相符,与清朝此时残存的‘天朝’体制格格不入。”(13)足见无论是当时的侵略者,抑或是后世的研究者,都指出在清廷所签订的条约中,不乏是时欧美各国通行的国际准则,而保护使馆人员的文书来往及通信安全,都是各国平等往来的准则之一。然而,欧美列强以武力强迫清朝签订条约,本身已构成不平等之行为,而清廷以“体制”为借口,以“夷务”为交往前提,亦是以一种无实力保证的不平等态度,来对待和处理条约问题。虽然与诸国最后签订一系列条约,而清廷最为关心的却始终是朝廷的体面,对现代国家应有之利权及应以何种手段保护自身之利权,一概不知。此种意识之启蒙,尚待出洋官吏之耳濡目染、媒体舆论之不懈鼓吹、及海关外籍税务司努力开办之后,方逐渐为清廷官民所认识和接受。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英法各国又因进京换约一事,与清廷再度燃起战火,最后落得文宗西狩、由恭亲王奕訢签订《北京条约》的结局。双方近四年的交涉与战争,以清廷继续开放口岸及出让更多权利而告终(14)。而为了方便办理涉外事务,清廷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在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并在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年2月3日)由奕诉、桂良、文祥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拟定章程以开府办公,其中第二条“司员分办公事,以专责成”,由各部抽调司员,根据其职能办理相关事务,其中“台站驿递事件,则由兵部司员经理。”(15)不难看出,总理衙门虽为清廷办理洋务之新机构,而其构成人员却仍以传统六部之司员为骨干,以旧管之职责而应付新生之事务。以兵部司员为例,其原本主管台驿事务,负责朝廷文报、官员招待及货物转运事宜,如今洋人传书递信亦纳入其职权范围,势必引起一番不适与争论,而这些反对意见,导致总理衙门将此带信职能转移至海关总税务司署,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海关对清廷邮政事务的掌控。
二 传统体制内的反对:以黄云鹄为例
同治初年(16),时任兵部郎中、充马馆监督的黄云鹄(17),就洋人以《天津条约》为凭、借用驿站车辆马匹传递文书一事上奏,力争不可:“驿站车马,查无应付洋人之例,所称递送各国文报及运解各国什物车辆,仿照中国定例一律办理之处,诸多窒碍。职既司此事,生死以之,不敢从同,以上误朝廷,下毒百姓。事若果行,中外衅端,必从此肇。”他认为“朝廷之驿站,如人身之血脉,血脉不通则身病,血脉杂则血脉亦病。与其为难于异日,莫若熟酌于目前。且驿站情形苦累已极,如此办理,苦累岂有穷期耶?所议决不可行。”(18)按黄云鹄所言,驿站关系朝政通畅,目前州县办理已苦累民甚,若洋人再用车马,无异再加重负,民何以堪。而且洋人使用驿站车马,拖累运转速度尚在其次,一旦影响文报安全,更为得不偿失,故其以“上误朝廷,下毒百姓”括之,力陈该事不可行。
由于外人借用驿站车马是获“朝议允之”之事,故“公时为兵部郎中,力持不可许,搘拄数十日,往复数万言,祸几不测。”但最后“幸终得公所议。”而其友人“贺良贞舍人谓公曰:‘我闻君近所为,固有劳师费饷万万计,能复不能复未可知者,而君以区区一郎官,折冲曹司,决胜万里,历危疑震撼而守职如故,国史不书,朝议不载,上下受其益而不之觉,事成而知勇,权谋泯然无可见,吾安得不大服。’”(19)不过黄云鹄“未几又以争外人在古北口市马事忤权要,遂出守雅州。”(20)揣其事端,以总理衙门涉其事之嫌为大。盖黄云鹄反对之理由几无可挑剔之处,然若照其意而行,极易为外人以违背条约而再肇事端。故黄云鹄于光绪十二年回想此事时,虽“上官格外优容”,但依旧只能奉命出守,后方明白当时“不置以夙谙曹事故也。”(21)虽有正理,而时势未足容其行。
不过,黄云鹄之所以始终反对洋人用驿,亦与其对当时驿铺状况之了解有关(22)。他认为是时铺递驿递之弊病,存在于几个方面:
一是寻常公文亦附驿驰递,以致官员“不知轻重缓急”,不仅虚耗马力,还延误紧急公文的递送。因此“本部议以一切公文全付驿递,恐一时未能周转,且非慎重邮政之道,请嗣后寻常文件仍由提塘递送,惟寻常事件之有关军务者,准其附驿递送,仍由各部填注‘附驿递送’字样,以凭传递。”除“例载凡有事关军务及紧要公文、刻难迟缓者,由马上飞递,其余概不准擅动驿递。”而“迟误公文,驿递夫役、铺司及该管官俱照例议处”,以期分清驿传与铺递的职责,避免滥用之弊继续蔓延,并且明确管职人员的责任,对以往违规官员要按例惩治。
二是提塘官必须尽忠职守。黄云鹄指出,“近来塘务实在情形,有不堪形诸奏牍者。向例驻京提塘年满者不准复充,今则不待年满辄思脱手。其已年满者,部中以无人接充,抑令留待后任。后任不来,则百计乞假而去,去则不复来矣。是以京塘只有直隶、河南、山东、广东、湖北、江西、四川等八省系正身充当,其余若湖南、山西、浙江、江南以及漕河,皆系代办。至云贵、陕甘,更不必言。若辈出充此差,岂尽出于忠爱。”提塘争相去职,乃因为已无实利可获,故过往“争缺涉讼”的职务,今日“不惟不争,乃至求脱不得,其故可想。”即使勉强承差,他们亦想尽办法逃避差事,“提塘既无经费给养铺夫,而各部文件又不能久阁,于是提塘将文件领下,俟有各省折差到京汇总寄省,此系例所本无。”托交折差乃“提塘央托私情,难保无大意之处。”而且“附弁私也,附驿公也。”若公私不分,又如何明晰权责,办理差事?故黄云鹄要求“重申旧制,定限严恭”,“拟令各督抚将每月收到部院各文缮列清单,按三月咨部一次,如有不符,将驻京驻省提塘分别议处。”
三是针对吏部所称,开缺文件多有迟误之情形而言。官员离任、到任,与地方民情息息相关,“假如有一知县缺出,实任文书未到,势不能不派员署理,而适当征收。在迩文书押扣不到,署事者自知为五日京兆,必尽力朘削,以偿夙逋而饱私囊,比实缺人员到任,则已无膏可润,非在京在省,本无宿累,而又能清苦自爱者,不能保其自立,使得早到,则自知蒞此必当有年,苟非大不肖,必不肯即行朘削,宦场中人较多甘苦一致者有几。”而这些缺分文书,“消息弗通,捷于邮置。”而“近来民生凋敝之由,未始不源于此。故缺分所关,似为国家最要之事。”由此则驿传铺递之明确职权、传递方式与工具使用,十分重要,若公器转为私用,或官吏疏怠松懈、不问政事,则必致衰败之政局。故黄云鹄坦陈“公事不厌求详,职分不可不尽”,以期所奏各法,可除现存之积弊而去已有之痼疾(23)。
除内地驿站传铺之积弊外,一直由理藩院主办的俄罗斯馆之恰克图寄京邮路,亦发生“开箱窃取银物至五百四十二元之多”的案件。由此事更加坚定了黄云鹄的观点,即“应请嗣后由京寄恰克图、及由恰克图寄京之件,均与内地一律办理,概不必附入银两,以昭慎重而免遗误可也。”(24)盖俄罗斯馆学生为清廷视为“外藩”学子,其利用驿站亦不能稍有特殊,更毋论被视为“外夷”的欧美列强,怎能轻易利用朝廷命脉的驿站来传书递物?故黄云鹄之坚持,并非简单的排外情绪,而是对传统体制有深刻理解、并在实际行事中体会到政情运转之难的官员,在既没有新的解决方式又无法借鉴外来制度的情况下,一种“坚持风骨”的无奈之举。每书至此,不由忆及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所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25)信矣。
总理衙门希望借用驿站传递外国书信的做法,始终受到黄云鹄的抵制。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四(1867年1月9日)兵部出示《申严驿禁谕》,声明“嗣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文,除官纸封套通行文件仍照常发递外,其布包、皮包、夹板、钉封及另纸包封紧要事件,均由该衙门自行填票拨递,本司概不准接递。”若总理衙门“不汇齐印总,擅自封发,本具官职守所在,舍命不渝,决不能为尔等宽宥也。言出惟行,决无后悔。”(26)态度之坚决与言词之强硬,为晚清官场所少见,亦可知总理衙门此举,虽迫于条约所囿而不能不于清朝体制内做出调整,但其受到之阻力,未必尽然来自反对洋务之官员,其体制本身的可容纳性,亦限制了司职者的见识与行事。
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理衙门不得不另觅良法,1865年8月自上海迁至北京的总税务司署,以其地位之特殊性,进入了总理衙门诸大臣的视野,并由他们开始了试办新式邮政的漫长路程。不过,新知新制与传统体制之间甚难前后接替、一蹴而就。虽然清廷负有代递各国使馆文书之责,但无论总理衙门抑或兵部官员,均对此事深以为患。总理衙门最后选择了由海关兼办使馆文书传递,既保证了由清廷职官体制对使馆文书传递的掌控,又避免了主管邮驿的兵部对此事的抗拒。惟此一时妥协之举,成为触发海关试办新式邮政的契机,不仅推动清代邮政体制的转型,亦导致海关及其外籍税务司对邮政利权的长期掌控,影响可谓深远。
注释:
①虽然清代明令禁止私信入驿,但并不能完全禁止清代官员附驿寄递私信的行为,官员利用民信局网络传递政报的情况并不罕见。故“官民两分”的邮递体制,只是从大体上进行概括,而并非意味二者截然两分。
②蔡鸿生著:《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初版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1版,第1页。
③同上,第21页。
④同上,第21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邮票史》第一卷(1878-1896),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第1版,第85页。
⑥《咸丰条约》第3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
⑦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第21页。
⑧茅海建:《公使驻京本末》,《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第200页。
⑨《咸丰条约》第4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
⑩《咸丰条约》第6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
(11)《咸丰条约》第6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
(12)[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29-630页。
(13) 茅海建著:《公使驻京本末》,《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86页。
(14)关于此事经过始末,可参阅茅海建:《公使驻京本末》一文。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第2716页。
(16)黄云鹄此奏折没有具体时间,按其在《兵部公牍》前言所推算,应为同治六年(1867年)。
(17)黄云鹄,“字祥人,蕲州人,咸丰癸丑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兵部郎中、充马馆监督。”(《湖北通志·黄云鹄传》,闵尓昌辑录:《碑传集补》卷十八,《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1988年4月第1版,第3294页)“一字祥云,又字翔云、缃芸、藏云,室名实其文斋。咸丰三年(1853年)二甲进士。宦蜀数十年,历任雅州知府、成都知府、永宁道、建昌兵备道、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晚年任江宁(今南京)尊经书院山长,继任湖北两湖、江汉、经心等书院山长。”(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版,第25页)其子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黄侃。
(18)黄云鹄:《兵部公牍》,第78页。
(19)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28页。
(20)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28页。
(21)黄云鹄:《兵部公牍》,第1页。
(22)黄云鹄在同治四年任职兵部时,已发现直隶等各省已多年不造册题报驿站报销事,“经臣部于咸丰七年八月暨同治元年十二月奏催,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行文各省督抚,遵照在案。嗣经臣部屡次咨催,仍未能一律按限造报。即如直隶近在畿辅,自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二年,驿站奏销均未补送,似此任意迟逾,实属不成政体。”而各省疏怠此事,“年限逾久,册籍逾繁,旷日稽延,此例将成废搁,于邮政钱粮均多流弊。”故黄云鹄奏请“饬下直隶各省督抚,将同治二年以前驿站奏销造具清册,悉数汇题,其同治三年驿站奏销未经题报者,仍按定例题报,随本送部,以肃邮政而除积弊。经此次奏催之后,如仍前玩忽,除查取各职名交部议处外,臣部应即随时严恭请旨惩办。”(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催各省驿站报销折子》,黄云鹄:《兵部公牍》,第25-26页)然而各省驿铺事宜,积弊甚久,且不说寻常公文传递,即使事涉官员开缺之文件,“近来铺递文件往往迟误过甚,虽开缺文件有行文坐日,程限可计,而各省接到部文竟有迟至一年半年,甚至遗失不能接到,于开缺截缺大有关系。”虽然此事由吏部奏请革弊,“然缺分驿站同为紧要公事,议祛之弊端亦公事,必不可不祛之弊。”(《马递铺递情形说》,时间未确,黄云鹄:《兵部公牍》,第81页)可见驿站于是时官员心中,是一不可忽视之公事,但其本身又存在相当的弊事,要趋利避害,必须将现有弊病革清,故黄云鹄提出诸项办法,以期肃清旧弊,而于公事有实际功效。
(23)以上三段所引,均见《马递铺递情形说》,时间未确,黄云鹄:《兵部公牍》,第81-94页。
(24)《咨理藩院文》,时间未确,黄云鹄:《兵部公牍》,第146-147页。
(25)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第219页。
(26)《申严驿禁谕》,黄云鹄:《兵部公牍》,第169页。
Mail Delivery under the New System and Its Response
Wu Y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The“Treaty of Tianjin”and“Treaty of Beijing”signed in 1858 and 1860 respectively clearly provided the Qing court be required to perform duties on behalf of the letter delivery from other countries.However,this function was conflict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postal system of China,not only triggering resistance within the established system,but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ystem by the Qing court so as to deal with its new role,which was considered a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 postal construction process.
Key words:“Treaty of Tianjin”,“Treaty of Beijing”,mail delivery,new postal service.
K251
A
1004-342(2013)05-01-05
2013-07-05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3YJC770056);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资助(wym11020)。
吴昱(1981-),男,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