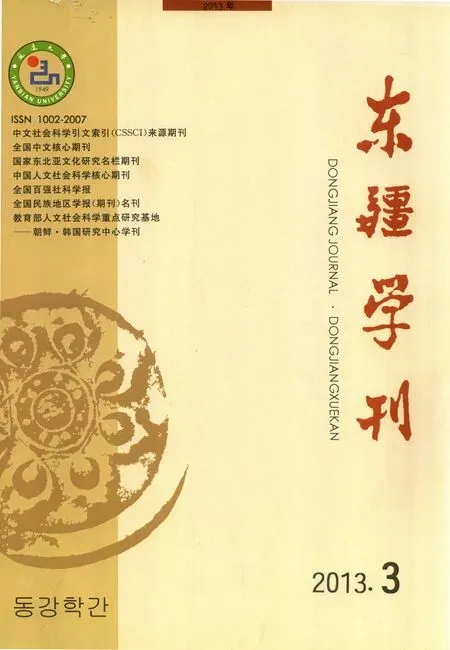《红王妃》中的文化霸权与东方主义
刘国清
[责任编辑 丛光]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 2004年创作的《红王妃》是作者在读完《王妃回忆录》(韩国称为《恨中录》,亦称《闲中录》)受到强烈震撼而创作的一部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力作。因《红王妃》在体裁上有别于作者原来的创作模式而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即“跨越了自传、传记和小说的文类界限”[1](79)而获得了文学界的很高赞誉。《红王妃》分为古代篇、现代篇和后现代篇。古代篇讲述了在朝鲜历史上家喻户晓并颇受尊崇的献敬王妃洪玉英,在朝鲜民间称为“洪夫人”的宫廷生活和悲剧人生,由王妃离世二百余年的阴魂以第一人称向世人倾诉。现代篇是王妃的亡灵以第三人称讲述她选中的替身、一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当代女学者的悲剧性婚姻及其在韩国的一段浪漫经历。后现代篇沿用现代篇使用的王妃亡灵以第三人称叙事,该篇采用开放性的结尾,讲述现代篇中的主人公芭芭拉·霍利威尔为完成在首尔邂逅的荷兰情人、人类学家占·范乔斯特的遗愿,与占的遗孀维维卡一起养育一个中国孤儿陈建依的故事。
从《红王妃》的结构设计上看,德拉布尔可谓是煞费苦心。古代篇主体上是离开人世的红王妃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与宫廷生活所做的回顾,而且不时地以一种穿透古今的鬼魂叙事对在世时发生的事件和当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点,从而将过去与现在、朝鲜与西方巧妙地连接起来。现代篇则实现了由伦敦到首尔在空间上的移转。虽然该篇主体上在展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也不时地加入全球化时代的韩国文化,甚至还有中国文化;既有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同质化的现代文化,也有东西方对彼此文化的不解与困惑,包括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红王妃对英国文化的不解和本篇中两位主人公对东方文化的困惑。后现代篇虽然很短,但无疑是对实现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交流融合所做的一次尝试。从中国孤儿院领养的中国小女孩陈建依在两位西方妈妈维维卡和芭芭拉的共同呵护下在异国他乡健康成长 ,她身上肩负着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重任。从表层上看,《红王妃》的古代篇和现代篇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恰恰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而后现代篇承载着作者沟通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美好愿望。在接受韩国学者李良玉采访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道出了《红王妃》的创作意图:“我想谈的是文化理解与误解的问题”,“我们生存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彼此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彼此理解,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彼此理解对方。这就要求我们跨越文化并且明白文化之间有接触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2](161~162)《红王妃》中既有东西方文化间的误解与困惑,也有彼此间的沟通与理解。显然,作者在小说中写文化上的误解与困惑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东西方文化间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于是,《红王妃》便被认为是具有全球视野、“代表东西方之间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的未来及希望”。[3](65)遗憾的是,评论界却对于小说中隐藏于表层之下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缺少认识。不管《红王妃》的鬼魂叙事多么别有创意,也不管作者想传达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并达到相互理解和文化融合)的理念多么诱人,对于读者,尤其是东方读者,不要轻易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对于隐藏于文本中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的内涵需要细心挖掘并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可忽视,更不该视而不见。
一
上世纪 60年代,英国历史小说开始复兴,至今繁盛不衰。笔者在《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一文中指出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六大特征,其中将历史素材作为展示作者理念的平台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4](48~49)虽然《红王妃》的古代篇以献敬王妃洪玉英所著的《王妃回忆录》中所述的宫廷生活为主要素材,但这些素材是作者用来展示自己理念的,作者有自己的取舍,而且还加入了很多《王妃回忆录》中不曾有的内容,甚至在某些方面颠覆了原有的记述。正如作者在《红王妃》的《序》中所言,红王妃的声音“已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它已成为一个混合体,其中包含了我的‘声音’,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当然,还有回忆录各位译者及评论者的‘声音’”。[5](序3)于是 ,《红王妃》中的王妃在思想上既有东方元素,也有西方元素,确切地说,红王妃已是一个高度西方化了的以东方阴魂的身份叙事的叙述者。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的红王妃声音已被嵌入了众多西方人的声音,还在于德拉布尔笔下的这位王妃在离世二百余年的时间里饱读了西方典籍,了解甚至洞悉了当今的西方社会。这位王妃不仅了解伏尔泰,熟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还善于使用当代学术术语,既能回顾前生,又能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对生前历经之事予以置评,甚至还不时地加入自己对当今的教育、女性地位、生命伦理、学术伦理等问题的思考,既能谈古论今,又能对东西文化加以比照并品头论足,绝非《王妃回忆录》中的王妃可比。虽然在小说的《序》中,德拉布尔本人曾说:“跟霍利威尔博士一样,我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5](序2)而且在《红王妃》中 ,连红王妃本人也数次否认死后灵魂的存在,但德拉布尔还是选用红王妃的亡灵作为叙述者。德拉布尔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了这种叙事的妙处,“通过让她在死后去评论,我便可以就此探讨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6]
评论界对《红王妃》采用的鬼魂叙事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叙述话语上超越了常规叙事的固定模式,打破了叙事主体的时空局限”,“拥有了宏阔的观察视野和充分的叙述自由”,“充分行使小说家独享的虚构特权,在今生与往世、现实与历史、西方与东方之间实施了多重时空跨越,进行跨越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历史对话和精神交流”,“独特的跨时空叙事在个体生命的叙说中演绎出人类共有的心理本原,增添了作品的历史底蕴,体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7](54)采用鬼魂叙事确实给《红王妃》带来了巨大的叙事空间,但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风险。作为亡灵的王妃被赋予了太多的声音,既有生前自己的声音,也有死后历经二百年所见所学而高度西化了的亡后的声音,加上红王妃的替身,英国的女学者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英国数位《王妃回忆录》译者的声音和西方评论者的声音,发出这么多的西方声音,《红王妃》很难彻底革除西方文化霸权意识,也难免有东方主义的色彩。
在《红王妃》中,作者借王妃之口数次提及文化相对主义,而且在小说的《序》中,以及在接受采访中,德拉布尔也数次谈到文化相对主义,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作者,也在昭示作品所持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或者说是文化平等主义的立场。但如果细心观察,读者还是可以发现,在《红王妃》亮丽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下,闪动着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鬼影。不仅如此,与西方文化霸权相伴而生的东方主义在小说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分布。
二
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互尊重与平等对话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旋律。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东西文化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存在着强弱之分。相较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支持者,但常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在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上习惯于用西方文化作为标尺来衡量东方文化,表现出文化霸权主义的一面。不仅如此,一些东方学者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面前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盲目认同西方文化,甚至矮化、丑化自己的民族文化 ,客观上成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帮凶。
虽然当今是崇尚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但西方的文化霸权却几乎无处不在,这种文化霸权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化的高扬、彰显和对东方文化的贬抑与消音 ,以及使东方文化的西方化上。《红王妃》中的叙述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人,而是离世二百余年对东西方有着深入了解并对西方文化有着高度认同的红王妃的亡灵,确切地说,叙述者已是高度西方化了的东方亡灵,红王妃亡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西方文化的代言者,这位代言者不仅以西方的视角俯视在韩国历史上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而且俯视当今的世界,作品中不时闪动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身影。
《红王妃》的古代篇大量借用献敬王妃洪玉英所著的《王妃回忆录》中的材料,但德拉布尔也加入了不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想像成分。她曾坦言,《红王妃》有很多与历史记载不符的地方:“不过我有所欺瞒,我是指某种程度上对素材的欺瞒,因为有些素材是找不到的。”“当然,我承认那完全是我的理解。”[2](158)在古代篇中,作者不仅特意设计了红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而且还频繁用喜鹊来昭示厄运。德拉布尔在《红王妃》序中承认了它们的虚构性:“我在小说里设计了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不知是否符合史实”,“我甚至也不清楚喜鹊(它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朝鲜到底是象征吉祥还是象征厄运。”[5](序3)
无论是在中国的宫廷,还是在朝鲜的宫廷,猫很少作为宠物来豢养,武则天却是例外,据说她在宫廷养了很多猫。很多西方人现在把猫作为宠物豢养,现在一些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韩国人也喜欢养宠物猫,但当时的红王妃是否养过猫却缺少证据。对猫和狗的宠爱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作为 18世纪东方人的红王妃如此爱猫,有了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如果说作者设计红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是为了讨好西方的读者,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那么,喜鹊作为厄运的象征则值得深思。
在西方文化中,喜鹊昭示厄运,而在中国和朝鲜文化中则预示喜事降临,德拉布尔对此十分清楚:“通常的说法是,在中国和朝鲜,人们认为喜鹊给人带来喜讯,而西方人则相信,见到喜鹊就会倒霉。”[5](序3)在《王妃回忆录》中 ,思悼世子被逼去自杀之前出现的是渡鸦,德拉布尔却故意在《红王妃》古代篇中将其置换为喜鹊,而且频繁使用它来预示接二连三的厄运。虽然德拉布尔宣称自己力避文化偏见,小心谨慎,以防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文化盗用主义者”,[2](162)但她的这一置换难免令人生疑。德拉布尔承认,在英国,人们对中国和日本有很多成见和偏见,而对韩国谈论不多,似乎没什么成见和偏见[2](155),但《红王妃》古代篇中的这种置换却无法叫人相信作者对韩国文化没有丝毫的成见和偏见。《红王妃》古代篇中用喜鹊来置换《王妃回忆录》中的渡鸦,客观上起到了对东方文化加以消音的作用,产生了使东方文化西方化的效果。
《红王妃》的古代篇不仅将在韩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喜鹊西方化为预示厄运的不祥鸟,而且颠覆了红色在韩国原有的文化寓意。在韩国,红色代表喜庆吉祥,但王妃的亡灵一再抱怨是因为自己喜欢红裙子才遭受生活的不幸与苦难,作者这种对异文化寓意的颠覆,其实是一种去异文化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文化霸权策略,只不过比较隐蔽而已。
西方文化霸权的身影不仅存在于《红王妃》古代篇中,而且还出现在现代篇和后现代篇中。在古代篇中,德拉布尔借红王妃之口批评韩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在现代篇则借红王妃的替身芭芭拉在首尔结交的新情人占·范乔斯特所谓的在中国的经历抨击中国的宴请文化和送礼文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清楚地表明了西方某些人士对异文化所采取的先入为主的傲慢与轻视态度,这同样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德拉布尔一再申明《红王妃》旨在实现跨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文化融合,其后现代篇无疑是作者为实现这一愿望所做的一次尝试,但遗憾的是,不仅这种尝试是否成功难以预测,而且作者在此篇的设计上明显存在着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痕迹。芭芭拉在首尔认识的情人占·范乔斯特的遗孀维维卡和芭芭拉共同抚养的中国女孩陈建依未来很可能难以摆脱身份的尴尬。陈建依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血统,但她在只有两岁时就被带到了欧洲,能有多少母国文化的成份尚存在她身上?显然不会负载多少中国文化。从文化角度讲,在纯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她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西方人。未来的她只能成为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一个有着东方面孔黄皮肤但骨子里却西方化了的夹心人。没有了东方文化,又何谈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难怪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作者的写作意图并没有实现。[8]不仅如此,这种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的操作。陈建依成了一个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最后只能彻底西方化的符号性人物,而湮灭东方文化、去东方文化并彻底西方化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终极目标之一。
三
西方文化霸权与东方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西方通过对自己文化的美化和普世化来压制东方文化,甚至贬损、丑化东方文化,从而吞噬、同化东方文化来达到传播西方文化并将东方西方化的文化霸权目的。为了实现西方文化霸权,东方主义不惜冒种族主义的风险对东方民族加以丑化,甚至妖魔化。于是,野蛮、凶残、邪恶、愚昧、落后、丑陋、奇异、怪诞、迷信、病态和非理性的东方就成了东方的标签。由于这样的标签是西方强加给东方的,不仅遭到了东方的强烈反对,而且与当今提倡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相悖而不得人心,传统的东方主义便进行了改头换面,一种新东方主义应运而生。但这种东方主义与传统的东方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是传统东方主义的变种,只不过因手段翻新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传统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的俯视,是西方的自说自话,而东方作为他者是完全失语的,是不在场的被言说对象。新东方主义则调整了策略,“不再是西方的自说自话,它以一种貌似宽容的姿态让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本土资料提供者的身份踊跃发言,并让他们在其话语中心占据一定的位置。”西方主流文化鼓励来自于东方的学者“以本土证人身份证明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而东方学者则通过对东方的矮化和丑化实现自我东方化来跻身西方的话语场,获得话语权。这样一来,“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军,在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9](32)
虽然《红王妃》的古代篇主要取材于《王妃回忆录》,但德拉布尔不仅加进了历史想像的成分,而且还对一些人物形象进行了颠覆,而这种颠覆的结果就是丑化与妖魔化了东方人,使得《红王妃》有着明显的东方主义的色彩。不过,尽管红王妃的亡灵作为叙述者是个混合体,她有着东方的躯壳,披着东方的外衣,但在骨子里却已是对西方高度认同而西化了的鬼魂。正因为这位叙述者混杂着众多西方人的声音,其东方主义的成分是传统的东方主义式的,而其东方的躯壳与外衣则使其表现出的东方主义色彩是新东方主义式的。也就是说,这位亡灵叙述者兼具传统东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的特质,或者确切地说,是在新东方主义外衣的遮盖下行传统东方主义之实的,正因为这种形式极为隐蔽而颇具欺骗性,人们才一直未对《红王妃》中的东方主义予以足够关注。
《王妃回忆录》由 1795年、1801年、1802年和 1805年分别完成的四部回忆录组成。前三部回忆录记述了王妃在宫中孤寂枯燥的生活,也对当时的政治有所针砭,并为屈死的家人伸冤。第四部最为重要,它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壬午祸变”的前因后果,极具可信性。在回忆录中,王妃立下血誓,是因为身患严重抑郁症的丈夫思悼世子屡闯大祸,威胁到了朝鲜王朝的存亡,无奈之下英祖国王才将其赐死。[10]在《王妃回忆录》中,王妃对自己的公公英祖国王并没有怨言与指责。在朝鲜历史上,英祖是一位以仁德治国、英明睿智的国王。但在《红王妃》中,英祖成了一位缺少理性的国王,他“性格暴躁,反复无常,时而自我克制,时而又放任自流”[5](45)。他的行为非常怪异,“但凡跟家里哪个他不喜欢的人讲过话,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洗耳朵、漱口”。[5](55)更令人奇怪的是,德拉布尔笔下的这位患了严重哮喘病而又神经质的国王总是试图把脏水泼到仅一墙之隔的女儿和协翁主院里 ,但因为院墙太高泼不进去而搞得自己满身溅上脏水。国王还有一种强迫症,他忍不住常常换衣服。国王还非常迷信,十分忌讳“死”和“回去”两个字,忘了带东西,不管多么重要,不仅自己不回去取,也不准随从回去取。国王不仅怪异迷信 ,而且还非常凶狠残忍。英祖一直为杀兄篡位的传闻所扰,为了平息传闻,他不惜大开杀戒,株连万千。德拉布尔笔下的英祖不仅为王不仁,而且为父不慈,甚至残忍无情。在朝鲜历史上英祖国王大义灭子这一迫不得已的行为,却成了《红王妃》中王妃亡灵对英祖国王不断声讨谴责的依据。对于思悼世子被幽米柜而死的缘由,作者或不愿对此加以考证,或可能虽有所了解却故意弃之不用,然而却妄自杜撰各种原因,津津乐道地以浓重的笔墨反复渲染这一惨剧,以此突显作为父亲的英祖国王的残忍与狠毒。将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包括国王或君主进行丑化是西方对东方人实施东方化的最有效手段,而挑选有东方背景的叙述者来承担此任,无疑使这种东方化获得了最大的合法性。
《红王妃》不仅丑化英祖国王,作者还无中生有地杜撰出宫廷中的乱伦丑闻。不仅有英祖国王最疼爱的女儿崇夫人与同胞哥哥思悼世子之间的兄妹乱伦,还有亲姑侄间的跨代乱伦。为了获得权力,曾与亲哥哥乱伦的崇夫人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勾引立为王储的亲侄子崇玉犯下乱伦的罪孽:“崇玉王储当时正进入青春期,他这个做姑妈的便毫无廉耻地挑逗他、勾引他。她的占有欲极强,我从崇玉口中得知,就连他读的书都会挑起她的妒火。”[5](105)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还跟小王妃争风吃醋,诽谤小王妃没有生育能力。在一个笃信儒教的国家,至亲间的乱伦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而且是绝少发生的,更何况在宫廷之中。德拉布尔如此丑化朝鲜的王子与公主,其实正是东方主义思想在作怪。
《红王妃》现在已是一部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品,无论其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广获好评。但正是因为它有太多美丽的光环,人们很容易忽视它在阳光下的阴影,这就需要我们不要被嘈杂的溢美之音所左右,而是深入挖掘、悉心倾听隐于文本深处的声音。因为作者在接受采访中一再举起文化相对主义的招牌,小说中数次申明奉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人们就更容易被蒙蔽,而且作者选用朝鲜王妃的亡灵进行自我东方化的手段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人们对于像《红王妃》这样的作品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更应该提高警惕,以防被表面的现象遮住双眼而无法深层透视,以致难以发出批判之声。
[1]Frankova,Milada.The Red Queen:Margret Drabble’s(Auto)B iographical Pastiche.Brno Studies in English,2011(37).
[2]李良玉:《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访谈录》,朱云译,《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 3期。
[3]王桃花:《论 〈红王妃〉中的异文化书写及其“理解”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 1期。
[4]刘国清:《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 6期。
[5]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杨荣鑫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
[6]Jays,David.Seoul Destroying.The Observer,August 22,2004.
[7]程倩:《历史还魂,时代回眸—— 析德拉布尔 〈红王妃〉的跨时空叙事》,《外国文学》,2010年第 6期。
[8]Eder,Richard.The Red Queen:Babs Channels Lady Hyegyong.New York Times.10 Oct 2004.〈http://w w w.nytimes.com/2004/10/10/books/review/10EDERL.htm l?-r=1 & oref=login〉。
[9]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 1期。
[10]《揭秘壬午祸变——思悼世子的死亡之谜》,http://w enku. baidu. com/view /a5d5fa 7002768 e9951 e738d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