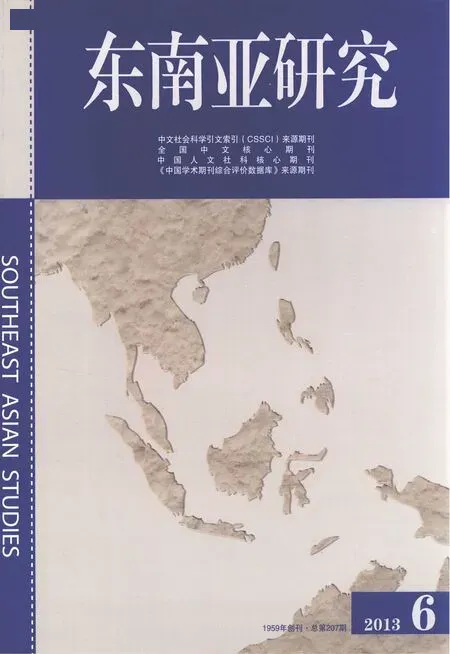革命路线与外交合作:20 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印(尼)关系发展
张小欣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1960年后中国发展对印(尼)政策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大跃进所带来的农业生产衰退严重困扰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对“三面红旗”如何认识在党内产生巨大分歧,而美蒋对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侵扰、中苏分歧加剧和中印边界争端所引发的“反华大合唱”,使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现实性和支持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而印尼总统苏加诺借争取民族独立和亚非世界的领袖地位,来进一步争取国内左右政治力量和强化民族凝聚力,并用反帝反殖运动所掀起的民族感来掩饰国民经济的不断衰退,收复西伊里安等就是其具体举措。在中国大力支持印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双方结成了亚洲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①相关研究见Ide Anak Agung Gde Agung,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1945 -1965,The Hague:Mouton & Co,1973;DavidPaul Mozingo,Chinese Policy in Indonesia,1949 -1967,A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olitical Scien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黄阿玲:《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聂会翔:《苏加诺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探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许振政:《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亲台湾群体:境遇与应对(1949—1960)》,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周陶沫:《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解析1959—1962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1 期;李一平、曾雨棱:《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 期等。已有研究对20 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的时代背景、政治理念以及印度因素对中印(尼)关系影响等问题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根据中方相关档案资料等对该问题展开具体探讨。
一 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
中国对印(尼)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受中国国内政治路线变化影响深刻,特别是进入20 世纪6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逐渐出现激进化现象,并在外交路线上通过党内批评“三和一少”和“三风”问题实现了思想意识统一,同时在中苏辩论中,中共中央将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当的理论高度,并由此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工作总路线的组成部分。
1960年以来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处于活跃阶段,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与蒙、朝、越签署含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加强了与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友好关系,而且在推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同时在解决边界划分和侨民问题基础上,继续拓展睦邻友好关系。而中国大规模对外援助成为巩固此类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的政策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坚定立场,灵活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坚决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和一切反帝和平力量。”[2]就对外援助问题而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互助,互相支持,增强团结;对民族独立国家,支持他们取得独立,扩大和平地区。”[3]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自20 世纪60年代初期起,中国对外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得到空前提高。例如,继1955年7月中国向北越提供8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及1959年2月提供3 亿元人民币贷款和1 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4],1960年10月和1965年7月中国又分别向北越提供6 亿元人民币贷款[5],以及10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6]。1960年3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1 亿印度卢比无偿援助,1961年9月中国再次提供350 万英镑无偿援助,支持尼方修筑从加德满都到科达里的公路。1960年12月中国向柬埔寨提供400 万英镑无偿援助。同年9月中国与几内亚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向几内亚援建火柴厂、卷烟厂、水电站、茶叶试验站等。1961年9月向马里提供700 万英镑无息贷款,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和农业技术援助。1963年10月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2.5 亿法郎无息贷款用于援建成套设备[7]。因阿尔巴尼亚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国,中阿关系获得快速发展,1961年2月中国向阿方提供相当于5 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1965年又向阿方提供相当于7.14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等等[8]。
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与大跃进后日渐衰退的国内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1960年后中国工农业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下降情况愈发严重。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承认:“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九六〇年麦收之后,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9]尽管《指示》采用“紧张”一词来委婉说明国内农业生产下降所造成的后果,但紧接着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直接明确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完毕时机,大规模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中央根据科学院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为代食品[10]。而1961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副总理阮维桢时坦承,中国建国11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3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粮食进口问题,说明截至2月22日的统计,中国在当年第二、三季度的粮食供给尚差74亿多斤,因此决定当年进口粮食100 亿斤(合500万吨),已经签好合同的有52.4 亿斤,正在谈判的还有50 亿斤[11]。
中国经济的困难与万分沉重的外援负担在党内引起深刻反思。1962年3月31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文中提出: “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12]而在此之前的2月7日,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其中认为世界战争并非不能避免;武装斗争并非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因而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与帝国主义谈判;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等等[13]。
王稼祥的报告反映了中国经济困难与大规模外援之间的客观矛盾,以及党内对大规模外援和中国多方面展开反帝反修外交路线的不同看法,这是继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同志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一次坦诚批评,不仅要求中央高层领导在中印1962年边界争端、中苏分裂和国内经济萧条等情况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求中央重新审视对世界大战在即的形势判断,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间是否可以较长时间和平共处等理论问题,其实质是要求中央慎重判断中央工作的重点是革命还是发展的重大问题。王稼祥作为主管外交一线工作的党内重要领导人,其言论和判断在当时无疑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是借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一度形成的民主风气,以及最高领导在前期工作自我批评基础上形成的较好政治氛围,来表达自身对外交工作的意见。但是王稼祥的报告遭到党内严厉批评,被称为“三和一少”修正路线。中国超越既有条件而实施面向亚非拉、不计成本式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国内革命思想在外交领域延伸的主要标志。
1962年7月2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14]8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提出阶级(即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形势(即对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个问题。此后毛泽东在多次谈到这三个问题时,进一步把部分中央同志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历史问题的诉求批评为“翻案风”。而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15]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为即将开始的中共八届十中会议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1962年9月14日在八届十中会议华东组开会期间,外交部主要领导人就“三和一少”问题做了重要发言,并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该发言谈到:
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16]
在上述会议基调影响下,9月29日正式公布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7]
八届十中全会的政治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将阶级斗争作为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提升为全党工作的中心问题,将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作为取得国际共运胜利的战略措施给予肯定,而且在党内统一了发展与革命何者重要的看法,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起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大反华”力量相抗衡的中国革命大旗。这一点表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认为:苏联修正主义无法正确诠释国际革命形势和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角色,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彻底结束,而在外交路线中坚持国际共运和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推进世界革命的两大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外交“不能一边倒”,刘少奇则认为,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革命这是最根本的,要有代表革命的方针,有代表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18]。
针对苏共中央的修正路线,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中提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问题[19]。
上述对20 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关于支持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思想变化的梳理,其用意在于:(1)中共中央有关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理论判断是导致革命化外交路线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在1962年9月29日《外事简报》第137 期的批语中指出,“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20],点明了在全党范围内重视阶级斗争的客观原因和阶级斗争的艰巨性;(2)八届十中全会是明确中央外交战略的关键会议,同时中央外交路线的确立是通过党内路线批判和人事改组获得的,王稼祥的报告被定性为“三和一少”,其本人被要求在中联部检讨,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书记处书记职务,以此获得党内思想意识的统一; (3)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共中央要全力支持的两大国际任务,而民族民主革命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占有优势,因此在本质上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4)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且能够影响全局的国际问题,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全力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是最终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根本保障; (5)在阶级斗争尚存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的阶段,革命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发展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因此,将中共中央外交主导思想的确立与下文中对印(尼)关系探讨结合起来就能进一步理解,当印尼因收复西伊里安等而掀起全国性的民族独立运动之时,中印(尼)关系在反帝反殖革命纽带下走向合作的原因。
二 印尼的反帝反殖外交路线
当印尼在苏加诺领导下实施“有领导的民主”后,西伊里安问题不可避免地作为考验苏加诺对国家领导力和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核心事件,而美国初期采取偏袒荷兰的所谓中立主义态度,以及联合国大会多次就西伊里安问题辩论未能通过的事实,一再表明印尼通过西方国家设定的解决途径根本无法迫使荷兰回到谈判桌前。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外岛叛乱、排华运动和马斯友美党、社会党政治对抗后,苏加诺已经确认印尼的革命道路远未完成,如何能将不同立场的个人、政党、派系糅合进统一的印尼民族意识,如何实现国家凝聚力,是苏加诺思考的大问题。为此,他在20 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不以阶级划分而以不同信仰融合为基础的“纳沙贡(NASAKOM)”思想(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体性)[21],而这种一体性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就是为实现收复西伊里安和清除殖民主义所做的群众动员。在此情况下,苏加诺试图采取军事对抗方式并在理论上提出新兴力量概念来解决印尼的国际困境,而此举先后得到印尼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尼共”)和印尼陆军的支持。
1960年8月17日苏加诺在印尼独立日演讲中强调:“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也仍然坚持着革命的主要精神,这就是团结国内和国际上的一切力量,反对以至最后消灭任何形式、任何地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特别地把重点放在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方面”,而在此方面“民族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力量是国家和民族中的一切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民事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总体,我们用这个总体来对付荷兰帝国主义力量!”[22]但是何者为印尼在国际社会能够团结的力量,显然成为苏加诺有关国际局势判断的主要问题。同年9月苏加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题为“重建世界”的演讲中提出,他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尽管接受世界三分的观点,但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23]。显然,苏加诺不认为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对立能够涵盖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形式。1961年9月苏加诺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明确提出:
当前的世界观点认为,国际紧张和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大国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我认为这并非真实。这是一种深入肉体的冲突,是一种在追求自由和公正的新兴力量,与一方面无情剥夺他国,而另一方面不顾一切地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历史进程的旧有势力之间的冲突。……不要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所迷惑。这个问题要留给各国。新兴力量与旧有势力之间的冲突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因为旧有势力在利用民族国家保持旧有平衡的同时,新兴力量却致力于发展这个世界。…… (因此)世界必须承认,新兴国家作为一种协调力量,致力于一种新型稳定平衡的建立,……在每一个个案中,国际紧张的根源和原因都是帝国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被迫分裂。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共存,但是独立公正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绝不能共存[24]。
贝尔格莱德会议所体现出的印尼外交政策特点和影响在于:
第一,用新兴力量和旧有势力概念来重新划分国际社会,不认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是主宰国际社会运行的根本因素,而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国际危机根源,视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为真正影响国际社会的因素。此种划分不仅有利于提升以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能动性,而且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尼反帝反殖运动的支持。苏加诺的外交概念和计划通过贝尔格莱德会议前的一系列双边互访,实际上已经获得很大范围的认同和支持。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杜尔访问印尼,双方表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国家获得独立的前提。1961年1月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访问印尼,苏加诺再次强调万隆会议的精神体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同年5月苏加诺先后出访安哥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6月访问罗马尼亚、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日本等国。贝尔格莱德会议后的9月21日,苏加诺在东京向印尼留学生发表讲话再次强调,“新兴的力量”同维护过去的旧制度的冲突才是国际社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印(尼)共和印尼陆军先后表示支持苏加诺的外交政策。印(尼)共总书记艾地从贝尔格莱德回国后即表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不结盟国家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精神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精神”[25]。印尼陆军对于苏加诺的支持更集中地表现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正如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提出的“中间道路”概念,军队在印尼事务中应该居于重要角色,但并不占据排他性的统治地位[26],因此对于总统的政策持支持态度。1961年1月纳苏蒂安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获得苏联4.5 亿美元军事贷款,用于购买苏制坦克、火箭、战斗机、中型轰炸机等,贷款期12年,年利率2.5%,且有数百名军事人员陆续被送至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接受军事训练[27]。尽管纳苏蒂安一直希望美国能提供重型武器援助,但是艾森豪威尔在执政末期,因为顾及荷兰在北约防务中的地位和警惕苏加诺领土扩张的野心,而始终没有提供[28]。1961年底,印尼成立“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部”;1962年1月由苏哈托少将任战区司令,通过空降伞兵和突击队渗透西伊里安而开始登陆作战[29]。
第三,与尼赫鲁的外交观点产生冲突。尼赫鲁认为不结盟会议的职责和功能就是告诉大国必须进行协商,而国际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美苏两个大国,会议应该促使它们尽快缔约以减少战争及维持和平,同时不结盟国家应该致力于减少柏林危机等可能引发新型战争的危险,而不是形成新的军事阵营,并且目前典型的殖民主义根本不存在。尼赫鲁与苏加诺截然不同的观点使得会议形成不同的支持派别,大多数激进的非洲国家、南斯拉夫、埃及等都支持印尼,而塞浦路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则支持印度,以至于在会议各专门委员会的讨论中都很难形成一致意见,甚至印尼认为收复西伊里安就必须采取对抗荷兰的政策,而印度则质疑对抗的含义。细究两国争论的背后原因可以看出,苏加诺为收复西伊里安而有意倡导第二次亚非会议,欲借助亚非国家集团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并进一步树立印尼的国际地位,但是尼赫鲁认为万隆会议已经充分体现亚非国家的团结,如果再开第二次会议可能将印中就西藏问题引起的争端公开化,有损印度的外交利益。因此,印尼与印度外交利益的差异使两国原本亲密的关系变得疏远,从而在寻求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道路上,印尼必须在新兴力量中寻找到新盟友[30]。
第四,中国对苏加诺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力量划分新提法给予了积极和正面呼应。1961年6月15日苏加诺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提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再一次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中国人民为收复自己领土台湾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一次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其一部分领土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斗争。”“双方重申,决心团结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不断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进行斗争;并且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完全独立和实现美好生活而进行的每个斗争。”[31]同时在此次访问中,苏加诺获得了中方此前已经答应的3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援建印尼的纺织工业[32]。而对于贝尔格莱德会议,8月17日陈毅外长在会见苏卡尼大使时就表示,中国政府完全赞同第二次亚非会议,并希望即将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能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警惕帝国主义企图转移会议斗争目标来破坏会议的阴谋[33]。周恩来于8月31日也致电不结盟会议表示:“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34]而在评价新兴力量时,周恩来还曾谈到:“新兴力量在开始出生的时候,看起来总是比老的力量弱一点,小一点,这是很自然的。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一个婴儿刚刚出世时总比老人又小又弱,但谁最有生命力呢?是婴儿,不是老人!谁最有前途呢?是婴儿,不是老人!”[35]中方不仅明确接受苏加诺的新兴力量概念,而且赞同印尼运用革命手段对抗新老殖民主义。
贝尔格莱德会议所反映出的印尼外交政策变化内涵极为丰富。苏联在提供军备销售方面奠定了印尼对抗荷兰的武力基础,此举一方面提升了军队在印尼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反殖民主义的支持,既反驳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又提升印(尼)共在国内的地位,使印(尼)共认识到不必通过国内的阶级斗争,而通过类似争取西伊里安的政治姿态所博得的广泛认同,仍然可以促使印尼和平过渡到人民民主阶段[36]。而事实上,沉重的还贷压力以及赫鲁晓夫对苏加诺拥护社会主义的质疑(如赫鲁晓夫私下里认为: “苏加诺所采取的立场相当灵活,虽然他嘴上说原则上拥护社会主义,但拥护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还很难说”[37])使得苏印(尼)关系在实用层面上的意义更为突出,而其引起的印尼内部矛盾也更为复杂。印尼与印度的矛盾是两国对东西方阵营和亚非集团国际职责不同看法的结果,且对亚非集团团结性的破坏以及改变印尼和平中立外交形象的影响极为深刻。印尼与中国在对外革命政策上极为接近,且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在亚非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加强两国关系能够弥补印尼与印度外交疏远的负面后果;同时在台湾与西伊里安问题上的相同命运,使得两国合作具有现实基础,而中方也通过安抚侨民以及提出稳定印尼国内经济的建议等,为印尼收复西伊里安创造条件。
三 中印(尼)外交关系的加强
1962年1月20日印尼华侨的选籍工作告一段落,其中除100 多万属于“不言而喻”的无须选籍者外,在152 万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中,有108万选择了印尼国籍,16 万选择了中国国籍,未按期选籍者有8 万,未达到选籍年龄者有20 万,他们要待成年后的一年中再行选籍[38]。而此前周恩来在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时曾表示:“如果经济上不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就不能算做真正的独立。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对于印尼籍华裔,应当由你们去劝导。对于华侨,我们愿意劝导他们帮助印尼发展工业。”[39]苏加诺对于华侨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1963年初新一波反华浪潮在西爪哇、中爪哇开始蔓延,此时苏加诺发表演说,不仅指斥社会党和马斯友美党两个非法政党是运动背后的煽动者,下令逮捕暴力活动的领导者,而且宣布排华是违背国家利益和受帝国主义挑唆的[40]。他警告“反种族行为将危害印尼根基,要求人民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呼吁印尼人民及华裔印尼人民团结起来。”[41]由此,排华活动得到制止。在中印(尼)双方合作解决华侨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在党的路线、双边关系和亚非国际论坛等三个层面大力推动有关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
196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将印尼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的胜利的斗争,作为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继续高涨的实例,在党的路线中要求对其加以支持[42]。
在双边关系上,除1962年初中方派出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医治肾病外,1962年9月苏加诺夫人哈蒂妮访华,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均予以热情接待,10月印尼驻华大使馆在华举办庆祝印尼共和国建军17 周年招待会,杨成武上将、罗瑞卿大将等到会并重申对西伊里安问题的支持,1963年1月印尼副首席部长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访华。中方对苏班德里约此次访华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外交部提出:“苏班德里约1959年以外交部长身份访问中国时,正值印尼掀起排华时期。苏返国后认为我接待安排简慢,表示不满。1961年陈毅副总理访印尼时,还有人企图以冷遇报复,后经苏加诺阻止,才给予陈毅副总理隆重接待。根据目前形势和中、印尼两国关系,此次苏班德里约访华,建议给予热情、隆重的接待,礼遇方面拟按照我对外国副总理访华的接待规格略为提高。”[43]此外,外交部在地方的接待宣传口径上要求:“指出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收复台湾和西伊里安的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赞扬印尼政府和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其成就;肯定印尼人民在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支持印尼方面提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主张”等[44]。苏班德里约此时也极为重视对华关系,其在印尼外交部会议上就曾提出: “现在的国际关系不再只是美苏两方的关系,而是美、苏、中三方的关系。”[45]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会见了代表团。1月8日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深为满意,作出一项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贸易安排”;“印度尼西亚政府重申支持中国人民收复台湾的斗争,感谢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解放西伊里安斗争的支持。双方声明,将继续同世界上一切其他进步力量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46]
在亚非国际论坛方面,1963年2月4 -11日在坦葛尼喀共和国的莫希举行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共54 国250 余位代表出席,在中印(尼)合力推动下,大会通过有关西伊里安问题的决议:
欢呼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迫使荷兰殖民主义者于1963年5月1日最后放弃对印度尼西亚的合法领土西伊里安的统治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并认为这是非洲和亚洲一切反对殖民主义和爱好独立的人民的胜利。
完全支持西伊里安人民所要求的迅速结束在西伊里安的联合国临时行政管理机构的过渡时期,立即把西伊里安归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西方殖民主义者关于举行“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而为一或成立自己的国家”这种公民投票的要求为无效。大会抗议1963年1月在当地联合国当局纵容下射击和平示威者的事件[47]。
在印尼的不懈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下,荷兰于1962年10月1日将西伊里安领土主权移交联合国临时管理机构,次年5月1日由联合国将西伊里安移交印尼,并决定在1969年12月31日前由该地居民自决归属。1963年5月1日在印尼实施接管当天,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苏加诺发出贺电:“我们深信,在阁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保持警惕、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解放西伊里安的彻底胜利,一定能够实现建立一个从沙璜到马老奇统一的共和国的正义事业。” “中国人民一向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共同奋斗。”[48]
小结
20 世纪60年代初期中印(尼)外交关系的强化,不仅是两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发展方向和目的的重要产物,也是东南亚冷战发展时期东西方对立的重要产物。其影响不仅在于进一步加大了美国面对的印支战争和印尼民族主义勃兴所带来的外交压力,还在于进一步疏远了印尼与印度的外交关系,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发生分化并形成愈加复杂的新形势。同时,这一影响还改变了东南亚冷战的格局,使得中国的外交影响延伸至中南半岛地区之外的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尼,东南亚半岛地区与海岛地区反西方主义的思潮以及亚洲共产主义影响显然逐步增大,东南亚冷战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注 释】
[1]《对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问题的批语》(1960年3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8 页。
[2][3][5][8][9][10][11][15][34][35][39]《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5 页、第387 页、第362 页、第387 -388 页、第338 页、第369 页、第388 -394 页、第492 页、第431 页、第574 页、第447 页。
[4][6][7]《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6 页、第281 -315 页、第289 -302页。方毅,1953年9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54年8月由中央委派担任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党委书记;1956年5月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1961—1976年期间主持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工作;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2][13]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9 页、第486-487 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35 页。
[16]《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62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8 -189 页。
[17][42]《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1962年9月2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共党史学习文件汇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1973年,第167 -174 页。
[18]《少奇同志接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1月14日下午),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工商联合会档案248 -1 -48,第1 页。
[1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1963年6月14日),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 页。
[20]《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 (1962年9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9 页。
[21]〈澳〉J·D·莱格,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6 -361 页。
[22]〈印尼〉苏加诺: 《我们的革命道路》 (1960),《苏加诺总统演说集(1959—1963)》,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1964年,第64 -68 页。
[23][28] Rex Mortimer,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1959 -1965,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79,p.187.
[24][27] [30] [32] [36] [40]Ide Anak Agung Gde Agung,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1945 -1965,The Hague:Mouton & Co,1973,pp.330 - 331,pp.294 -299,pp.328 -338,p.430,pp.296 -297,p.431.
[25]《艾地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会议宣言是独立外交政策的胜利和对修正主义的打击 某些人想使会议离开目标的立场遭到强烈反对而失败》,《人民日报》1961年9月23日第5 版。
[26]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39.
[29]〈印尼〉苏哈托自述,居三元译,黄书海校《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7 -93 页。
[31]《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新闻公报》, 《人民日报》1961年6月16日第1 版。
[33]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 (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6 页。
[37]〈苏〉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36 -2637 页。
[38]聂功成:《关山度若飞:我的领事生涯》(新中国外交亲历丛书),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4 页。聂功成,1958年毕业于外交学院,1960年赴中国驻印尼棉兰领事馆工作,1961年改任中国驻印尼巴厘省首府登巴萨市选籍办公室主任,后又在雅加达总领馆和马辰领事馆工作,1964年底返国。
[41]《印尼总统苏卡诺指责两个非法政党(社会党、右派回教党)是最近排华运动的煽动者》 (196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63年1 至6月份),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494 -495 页。
[43]《关于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 (1962年12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240 -1 -1341,第1 -2 页。
[44]《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首席部长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访华的宣传通知》(1962年12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240 -1 -1341,第5 页。
[45]《苏班德里约SUBANDRIO》 (1962年),广东省档案馆240 -1 -1341,第12 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63年1月8日第1 版。
[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21 页。
[4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3)》(第10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247 -24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