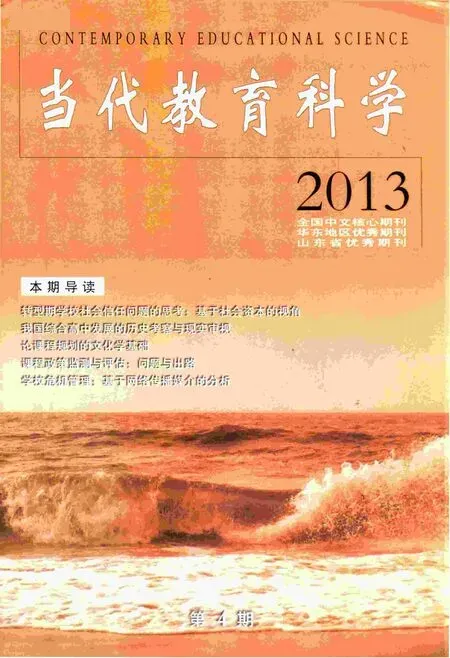论课程规划的文化学基础
● 丁念金
课程规划(curriculum planning动词)是对课程进行较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筹划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课程规划(名词,在我国称为“课程方案”、“课程计划”、“教学计划”等)。课程规划的研究需要从多个学科角度进行,其中一个极重要的角度就是文化学角度。本文就意在探讨课程规划的文化学基础。
一、课程规划需要文化学基础
课程规划是课程构建的宏观层次,课程具有文化性质因而需要有文化自觉,文化学角度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因此,课程规划需要文化学基础。
(一)课程规划是课程构建的宏观层次
什么是课程?对此,人们说法很不一致。我们认为,课程是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进程中对学习的系统化预设,是一种教育构建。这一定义可以做如下几点分析:其一,课程从本质上讲是用于学习的;其二,它是对学习的一种系统化预设,即具有鲜明的预设性质,这就区别于教学,因为教学是教育的实际展开[1]的基本途径;其三,课程与文化传承及发展直接关联;其四,课程是一种教育构建,教育构建的其他侧面有师资构建、教育制度构建、学习环境构建等,我们可以将课程这个侧面的教育构建称为“课程构建”。
课程构建有三个典型的层次:一是课程规划,这是宏观层次;二是课程标准,这是中观层次;三是教材(现在有人称为“学材”),这是微观层次。课程规划在整个课程构建中起着制高点的作用,它是课程标准构建和教材构建的重要依据,应该集中体现课程的基本理念,展现课程的总体思路。
(二)课程具有文化性质因而需要文化自觉
课程规划是课程构建的典型层次之一,而课程具有文化性质,需要文化自觉,这已得到广泛的认可。课程的文化性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课程属于文化范畴的一个领域。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涉及到人所创造的一切,或者说,“整个人类化的累积过程”[2],都可归入文化范畴之内。课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当然也是文化的一个领域。
其二,课程受大文化的深刻影响。综合国际上众多相关研究来看,课程具有四大要素,即学习目标(通常称为“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评价,无论在课程规划、课程标准还是在教材层次上,都需要对这四大要素做系统化的构建。这四大课程要素都受整个文化的深刻影响:学习目标直接体现一种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是文化精神的核心;学习内容的主体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精选和浓缩;学习方式是行为方式的一个领域,而行为方式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学习评价的灵魂是价值评判,而价值是文化精神的核心,而且价值评判活动也是在整个文化环境中进行的。
其三,课程本身是一个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文化具有连续性和可变性,在这种连续性和可变性的文化中,课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即参与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促进文化的传承,同时促进文化的发展[3]。课程作为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首先表现为人的培养,以人为载体整合各种文化,传递和创造文化;其次表现为各种课程文本的创制,这些创制出来的课程文本,不但体现了文化精神,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式。
(三)文化学角度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
整个课程构建,包括课程规划的构建,需要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4]。在此基础上,本人认为,文化自觉指人们明白一种文化的发展进程、特点和发展趋向,并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自觉探索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途径。应该说,课程文化自觉的途径是多样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合理而有效的课程规划实践正是需要借助于这种研究,因为,文化自觉需要人的理性能力的运用,而研究是理性能力之运用的最高层次的途径。只有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规划,才能准确而深刻地理解课程规划的文化性质、文化使命、文化学规律以及文化学的思路和方法策略。
对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自然需要较厚实的文化学基础。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为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提供了这样的基础。首先是整个文化学的研究。“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至为重要的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也较早引起人们的文化学研究。例如在西方,文化学的研究在17世纪已经开始,在18世纪得到发展,此后一直长盛不衰;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已有较多的文化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此后,文化学的研究繁荣起来。其次是课程文化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文化学研究和课程研究的深入,作为课程论与文化学之交叉学问的课程文化的研究得以兴起,首先是在西方,然后是在中国。文化学的研究和课程文化的研究,为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可供利用的重要基础。因此,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不仅成为需要,而且正成为可能。
二、课程规划视野中的文化学分析框架
要有效地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规划,就要在此方面有一个相对明晰的文化学分析框架,尤其是要明确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这个框架既要比较完整地反映文化学的框架,又要基于课程规划的视野。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这两个方面都还需要努力。
(一)文化的大致范围
对文化之范围的界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罗威勒(A.Lawrence)曾说:“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5]许多相关学者都努力去界定文化的范围,但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其中许多人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去界定文化的范围。笔者认为,需要用一种“集中弥散”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文化的范围,这种思维方式基于如下事实: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身的存在中心,同时又弥散性地与其他事物关联在一起,正因为这样,任何事物都既有其特殊性同时又与其他事物广泛地联系着。文化也不例外。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并基于文化的复杂现实和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类精神,同时这种人类精神又弥散到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之中。因此,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文化精神,即长期地积淀起来的人类精神,这是文化范畴中的集中的层面;二是文化形式,即积淀了人类精神的各种活动及其产物的形式,主要包括器物形式、行为形式、制度形式、语言形式、文本形式、思想形式、社会心理氛围形式等[6],这是文化范畴中的弥散的层面。
(二)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
由于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课程规划的范围也很大,即涉及到课程的各个方面,因此,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范围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
1.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
课程文化,简单地说即积淀了文化精神的课程现象。文化的首要层次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本质”[7],它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文化精神渗透于课程现象并在课程领域积淀时,就形成了课程文化。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包括以下几个具体方面:一是课程的文化性质;二是渗透于课程领域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渗透于课程领域中的价值观念;三是作为课程精神之一个重要层面的课程理念,即课程的深层的、基本的观念。这三个具体方面是整个课程研究需要注重的,也是课程规划研究所需要注重的。
2.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
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文化的历史变迁,因为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传承与延续、创造与发展的,课程文化也是如此。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相当复杂:从地域范围来看,既包括中国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也包括外国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西方课程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课程文化的内容来看,既包括课程精神与课程理念的历史变迁,也包括课程形式的历史变迁,所谓课程形式即课程规划、课程标准和教材(学材)等,这里尤指课程规划。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应该有历史的视野,应该体现历史性的延续与发展。
3.课程文化的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具有各不相同的课程文化,这些不同的课程文化一方面源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又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它们构成了全世界丰富多彩的课程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从课程文化的国际格局中来审视各国过去的课程规划,构建各国未来的课程规划,并达到关于课程规划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因此,课程文化的比较研究显得相当重要。
4.课程规划文本的文化学阐释
到目前为止,各国都已出现了大量的课程规划文本,而文本形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对这些文本做文化学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课程规划文本的文化学阐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之称谓的文化学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之内容结构的文化学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中体现的文化价值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中体现的课程精神、课程理念的分析;课程规划文本涉及到的各类文化形式的分析。
5.课程规划的文化使命研究
人总是在文化中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是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首要标志和一个根本性的条件,为了保障和改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需要在文化的生成、延续与更新上下大功夫。同时,人类是需要进化的,而人类进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文化的进化。那么,如何实现文化的生成、延续、更新和进化呢?在此,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而要使教育在此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在课程规划上对此有充分的体现。因此,课程规划的文化使命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
三、当前中国课程规划面临的文化学问题
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课程规划,一个重要的宗旨是发现和解决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应该说,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是复杂的,因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而异。在当前的中国,课程规划所面临的文化学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一)中华文化振兴问题
中华文化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到后来,中华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中华传统文化步入龚自珍所说的 “衰世”,即“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8]的状态。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中国一直处于全面的中西文化冲突之中,在这种冲突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劣势,到目前,中华传统文化只剩下一些碎片。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了无数中国人的伤感和忧虑,也引发和强化了无数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梦想。当前,人类又迎来了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既面临进一步消失的危险,又面临振兴的机遇,在此背景之下,振兴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理想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理想之一。从文化学角度来看,课程规划应该承载人类的文化理想,在当前的中国,即为中华文化振兴的理想。
(二)文化继承与创造的关系问题
文化的历史存在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是继承;二是创造。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阐明了这两种取向:“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9]中华文化振兴应该以文化继承为主,还是以文化创造为主呢?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造论”[10]的主张。
笔者的主张是:同等地重视文化的继承与创造,将继承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要特别注意:第一,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课程规划中,是重继承而轻创造的,现在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大力加强创造的取向,走向继承与创造之间的均衡;第二,继承为创造提供基础和源泉,而更高的目标是创造,而且在课程规划中,应该以创造有力地拉动继承,因为,文化创造能有效地激发人的创造本能,激发个人的强烈兴趣,又能促进民族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的高度丰富和高度繁荣。
(三)多元文化问题
当今的文化格局具有鲜明的多元性,而且这种多元性趋势还在加强并深刻地影响着学校教育,因此,多元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课程规划面临的一个重要文化学问题。就中国而言,这又包含如下几个具体问题:其一,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社会致力于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二,如何保持和优化国内多元文化的格局?其三,“去殖民化”是当前课程革新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重要理想[11],中国的课程规划如何真正体现这一趋势和理想?其四,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课程规划如何体现和增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跨文化理解?
(四)文化整合问题
在当今极端复杂的文化局面中,文化整合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12]。在课程规划中,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基于如下几点:其一,文化整合是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形成与发展所必需的;其二,文化整合是教育促进中华文化振兴所必需的;其三,文化整合是教育培养人格健全、尤其是价值观念健康的学生所必需的。在课程规划的视野中,文化整合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层面:其一是中西文化的整合;其二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整合;其三是各地域文化的整合;其四是各种组织文化的整合。就课程规划而言,这四个层面都包含着各种文化成分的整合,其核心是形成一个有序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形式结构,并将此简化,以适合于学生的高效学习。
四、课程规划视野中文化学研究的特别注意点
在课程规划视野中,文化学研究有许多要注意的问题,其中特别要注意的要点有:
(一)要整合多种文化理论
有些学者进行课程研究和课程开发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倾向:从某一种理论出发。这是一种不妥当的倾向,它往往会导致课程的偏狭。事实上,任何一种实践都应该以多种理论为基础,即整合多种理论。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也是如此。文化学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尤其是西方,已有约三百年的历史。在较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理论。每一种文化理论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在立场、思维框架、观念倾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其优点和局限性。而课程规划要真正达到科学、合理,就不能偏向于某一种文化理论,而应该对多种文化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这才能为课程规划提供可靠的文化理论基础。
(二)对文化现象要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对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当然要研究整个文化现象,因此需要对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其一,要全面地把握世界文化格局,尤其是中西文化格局,把握中西文化之异同,这样,才能在课程规划中适当地对待各种文化。其二,要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把握,这样,才能在课程规划中全面、简要、动态地体现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其三,要对当前中国境遇中的文化现实有全面的把握,如对当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多元文化、存在什么样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困境等有全面的把握。
(三)要有合适的文化立场
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价值体系,而价值强调文化主体的立场。在课程规划的文化学研究中要注重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合适的文化立场”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要以中华文化为主。中华文化既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又包括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自我。如果以西方文化为主,那就违背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就难以适应中国国情,会引起过多的文化冲突,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持有中华文化的立场,并非要在课程规划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但是应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合理的、优秀的因素。例如,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最高价值是“崇高”,“崇高”这一最高价值是值得传承的[13],而且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课程规划应该致力于传承这一价值。其二,要有国际视野,充分地关注和吸收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此为中国的发展服务。其三,还要有全人类文化的立场,即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致力于丰富、发展和繁荣全人类文化。
(四)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文化
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文化也是如此。从宏观层次来讲,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人类的进化;从微观层次来讲,文化的发展体现着每个个人的创造。当人类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之后,文化的发展将更快。既然文化现实是发展的而且是应该发展的,因此对文化现实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发展的眼光,我们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发展,而且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引领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固守文化中那些落后的、过时的内容,而应该及时更新文化,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因素。在晚近以来的西方,人们较普遍地以发展的眼光研究文化。例如,丹尼尔·贝尔指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已经走向衰竭[14],后现代主义就是文化从现代主义中“突围”式的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在迅速发展、在全面地转型,文化的迅速发展既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实,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和最重要的目标。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文化显得极为重要。
[1]J.G.Saylor et al..Curriculum Planning:For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1:258.
[2]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Z].第二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
[3]Craig Kridel(ed).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 Studies[Z].Los Angeles,London,New Delhi,Singapore and Washing ton DC:SAGE Publications,Inc.,2010:168-170.
[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5]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7.
[6]丁念金.人性的力量——中西教育文化变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8-10.
[7]高瑞泉.论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A].李灵,刘杰,王新春.中西文化精神与未来走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
[8]龚自珍.尊隐[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8.
[9][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83.
[10]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401.
[11]NinaAsher.Decolonizing Curriculum [A].Erik Malewski.Curriculum Studies Handbook-The Next Moment[C].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0:393-402.
[12]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Z].第二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8.
[13]丁念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J].全球教育展望,2011,(1):36.
[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