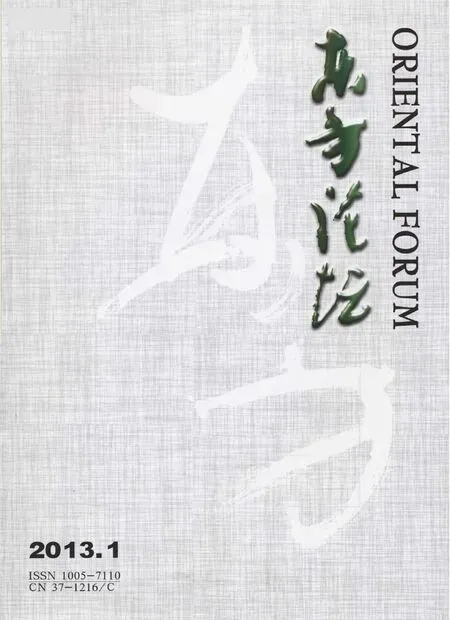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朱仰东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山东 250014)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朱仰东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山东 250014)
《儒林外史》与明代社会关系密切。吴敬梓何以厚洪武而薄永乐,是和洪武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而永乐篡位本身即是对周礼的违背,且自此之后,礼乐制度废弛。高启桀骜不驯,其性格与魏晋人物类似,吴敬梓推崇六朝,但由文中所及《高青丘文集》看,吴敬梓对高启极为熟悉,从其个人及文中王冕行迹看,吴敬梓及其创作受高启影响更大。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清代对于明人结社态度多为否定,吴敬梓当受特定时代思潮影响,对文人结社也比较反对。《儒林外史》涉及文人结社颇多,且多为反面,这一现象当与吴敬梓个人态度有关。
《儒林外史》;洪武朝;永乐朝;高启;魏晋风度;文人结社
《儒林外史》借径明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楔子题词即云“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其中“前朝”显然是立足于吴敬梓生活的时代而言的。虽然,《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是,“吴敬梓对明代历史兴亡的意识,贯穿于《儒林外史》中,成为小说主题的重要思想背景。”[1]吴敬梓何以借径明代,明代社会对吴敬梓及其创作有何影响,在作者春秋笔法下,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意,可以说,在对《儒林外史》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然而,学界虽然明知《儒林外史》与明史关系密切,但“绝少涉及作品写及明代历史的意义,以为那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应该说,“这是《儒林外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误区。因为从理论上讲说,《儒林外史》的假托明代不可能只是一种形式,而必然包含相应的内容,即它托明写清的地方正就是明清共有或可能共有的。读者若单认为它写了清朝,而作品之描写与明朝了无关系,就未免失之片面。”[2]基于此,故不揣浅陋,就这一话题续陈管见。①业师杜贵晨先生曾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发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一文,文中观点见解深刻,启人多矣。笔者阅读后也有同感,并沿此思路,写下此文,故以续论拟题,不当处望方家指正。又,杜先生之文后收入《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一书中,可参看。
一、“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
《儒林外史》第9回邹吉甫道:“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同回邹吉甫又言:“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 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的酒来。’像我这酒,是扣著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邹吉甫的话很有意思,在他看来,洪武时期像周朝一样好,永乐朝总之不如洪武朝,褒洪武而贬永乐的意味非常明显。
这就让人感到困惑了,因为楔子中写得明白,洪武即位,“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于是“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既然楔子意在“隐括全文”,由此出发,后世学者往往认为,《儒林外史》“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3];或进而由批判科举及至科举制度下文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如张锦池先生即指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问题,便成为作品……的同一主题思想的三个层面,而作者的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哲学反思,亦寓焉。是故,如果一定要从王冕的三段话中拈出一句话来概括吴敬梓的创作本旨,其最全面而义又最显豁者,当是‘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4]思考角度或有不同,但作为“隐括全文”的楔子,作者将一代文人之厄归咎于洪武,显然是颇含微词的,而文中邹吉甫又口口声声赞美洪武,将之比作上古时代的周朝,这岂不矛盾?
其实,如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明初历史有所了解。需要指出的是,以对科举制度的态度而言,吴敬梓并不赞成时文制艺、八股取士,楔子中对洪武朝的指责合乎逻辑。但是,对八股取士的否定并不等于对洪武一朝的完全否定,因为,朱元璋推翻元蒙,目的即在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所以,当明朝甫定,“他务未遑”,朱元璋便“首开礼乐二局,广徵耆儒,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曾言:
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齐家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明太祖宝训》卷二)
先王制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历世因之,不敢违越。诚以纪纲法度,维持世道之具。(《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七)
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礼官编成《存心录》,二年,诏儒臣修礼书,三年编纂完成《大明集礼》,此后,又多次以行政命令让精通儒学的大臣编修礼书。据统计,在洪武三十年间,所修礼书计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定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等。可以说,有明一代的礼乐制度基本上是在洪武年间制定完成的。所以,《明史·儒林传序》认为:“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
《儒林外史》的描写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吴敬梓对科举戕害人心,毒害士林痛心疾首,但对礼乐制度却肯定有加,并以之为理想追求。文中所塑造的迟衡山、杜少卿、庄绍光等“真名士”,其希望即在于恢复久已不存的礼乐传统,这一点也体现在回目设置上,如第33回回目“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横山朋友议礼”、第34回回目“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旌天子招贤”,第37回回目“祭先圣南京修礼,送孝子西蜀寻亲”,众所周知,其中第37回是文中高潮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作者理想的地方,对于真贤名士们恢复古礼古乐传统过程的描写,虽然作者写来不厌其烦、枯燥无味,但却极为认真,可见该部分之重要。而所祭泰伯,据《史记·泰伯世家》载,即周太王长子,由此可知,真贤名士们所恢复的古礼古乐即是周礼周乐,换言之,周礼周乐即是吴敬梓心目中理想的礼乐传统,而洪武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即是周朝礼乐制度的余绪,就此,清代《明史》修订者即已指出:“惟能修明讲贯,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孟森先生亦然:“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5](P15)所以,也就不难理解,邹吉甫何以推崇洪武,将其比作周朝了。不过,第33回里迟衡山却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有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如说洪武举业害人可以,但断然否定洪武朝“全然不曾制作礼乐”显然有违事实,如联系迟衡山说话的时间当在嘉靖三十五年,而此时,“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伪,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明史·儒林传序》)学风、世风江河日下,文运难系,迟衡山之言实属愤激之词,如以此为据,推断出菲薄洪武之结论,则未免武断。
与之相比,作者对永乐朝所持态度正好相反。其因在于:永乐即位乃以“靖难”之名行篡位之实。篡位,历代即为人不齿,《汉书》卷九十九下“赞”对王莽篡位评云:“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甚至连文人所不屑为的戏曲等俗文学也口诛笔伐,元尚仲贤《三夺槊》第四折:“那凶玩很劣,奸滑侥幸,则待篡位夺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圣贤泰伯,据《史记·泰伯世家》载即以谦让著称,“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佰﹑仲雍二人乃礶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儒林外史》抬高泰伯,“看来是这样的贤人更符合吴敬梓的理想”[6]而又贬责永乐,用意也就不言而明了。然而,学界多洞悉吴敬梓春秋之笔,但却少有人注意褒洪武、贬永乐所蕴含的春秋大义,实为可惜,看来正如鲁迅所言,伟大的确需要人懂。明乎此,那么第8回里,娄氏两公子的话也就不能等闲视之:“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联系邹吉甫所言,永乐之所以遭贬,在作者来看,实乃因为篡位本身即有违礼乐制度,而事实是,自永乐之后,“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第35回)作为肇始者,永乐朝自然难辞其咎,责之尚且不已,何谈为之美言。
二、“国初四大家,只有高青丘是被了祸的”
《儒林外史》第35回,庄征君应诏途中遇见卢信侯,二人相谈甚欢,言语之间有两处涉及高启与其文集:一处在卢信侯谈起自己等候庄征君之因时有言:
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藏在家里。二十年了,也寻的不差甚么的了。只是国初四大家,只有高青丘是被了祸的,文集人家是没有,只有京师一个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师,用重价买到手,正要回家去,却听得朝廷征辟了先生。
一处在谈到名人文集时,庄征君向卢信侯道:
像先生如此读书好古,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但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丘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
由上可知,因“太祖恶其为人”,高启文集当时尚在禁中,少有人收藏。卢信侯侥幸得之,后却因此遭到锦衣卫的通缉,差点送命;蘧公孙则为此吃尽官司,受人讹诈。文中大凡有《高青丘集》出现的地方,祸事都会如影相随,似乎,高启及其文集即是不祥之物。作者如此写来,用意何在?文中不明;态度如何?作者也未置可否。事实上,如细加推究,便会发现,作者如此闪烁其辞却另有深意,高启之于吴敬梓,影响可谓大矣!①杜贵晨先生认为,《儒林外史》写高启是别有深意的,“因为高启毕竟是历史人物,他被明太祖枉杀,著作在后世不禁而禁,是人所共知的的事实; 而且高启才华横溢,作为有明一代诗人之冠,他的死明清士人无不为之痛惜,说到明诗便不能不说到高启,而且因此不难想到明朝自朱元璋发难,文祸也曾是空前的严重。所以,写高启直接正面的意义首先还应当是这一冤狱的本身,是对高启之死的同情和对‘洪武爷’大搞文字狱的针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有关高启文祸的描写,用心似不仅在于揭露影射,还有教人防范自保的用心。”笔者以为甚是,但如从二者思想人格等方面看,高启对吴敬梓当也不无影响,或者说较魏晋名士风流影响更甚。
吴敬梓追慕魏晋,在某些学者看来,“吴敬梓大概要属于那些没有失去自我,企盼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个别文人,在人格意识方面,吴敬梓的心和魏晋人士相通的。”[7]程晋芳《寄怀严东有》一诗即云“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影响所及,《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理想人物也多具魏晋风度,比如王冕,学者指出:“凡是史传未及而吴敬梓所赋予王冕的性格因素,大抵不外魏晋风度遗留的痕迹。”书中所写季遐年不慕权势、怒骂他人,荆元‘诸事都由得我’的自主意识,杜少卿一手携夫人、一手持酒杯游清凉山等精彩之笔,“均可见到魏晋士人的身影。”[8]但殊不知,高启的人格意识也形同六代,崇尚自由,狂放不羁,比如被迫应征做官后,高启不但没有欣喜若狂,反倒认为是一种负担,《池上雁》诗云:“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为高,偶为弋者取。……虽蒙养育恩,饱饲贷疱煮。”而名作《青丘子歌》更体现了作者任性逍遥、人格独立的精神追求,“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庚。”如果说前者颇类竹林七贤,那么后者则明确以效仿陶渊明为旨归了。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之于文人品格而言,可谓难能可贵,但之于明初政治环境来说,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当此之际,百废待兴,朱元璋急需有用之才,曾多次颁布诏令广为搜求,“联为天下之广,故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今天下再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圣弃!”(《皇朝本纪》)对于不为君用者,朱元璋极为痛恨,于《大诰》中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高启的桀骜不驯违背了朱元璋的用材方略,这也是庄征君所谓“太祖恶其为人”的根由,其结局注定是一个悲剧。
既然,吴敬梓将其写进文中,说明吴敬梓对其人知之甚详;既然高启的人格精神与魏晋六朝亦相通焉,那么,对于高启,这位才华盖世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才子,吴敬梓当也不无敬仰。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乾隆十六年,皇帝首次南巡,幸临南京,吴敬梓不但没有迎銮献诗,反而“企脚高卧向栩床”(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三《寄吴文木先生》),这种勇气、胆量和气魄,与其说接近于魏晋人物的狂放,不如说更近于高青丘之孤傲,或者说二者兼之。允当来看,吴敬梓则似乎远绍魏晋,而近效高启。及于作品,楔子中的王冕最为典型,作为精心树立起来“隐括全文”的真贤楷模,王冕颇类高启,而又与作者经历相似,可以看出,由高启及至作者再到王冕这样一个相互影响的链条轨迹。比如,楔子中写时为吴王的朱元璋拜访王冕,曾云:
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
王冕告其“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朱元璋听后,“叹息,点头称善。”定鼎天下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如果与高启、吴敬梓事迹对照,不难发现,王冕的行迹几乎就是二人的翻版,只不过,高启因恬退而惨遭腰斩,吴敬梓因高卧而无缘仕途,后者则终老林下、得以善终罢了。如此来看,学者所言“凡是史传未及而吴敬梓所赋予王冕的性格因素,大抵不外魏晋风度遗留的痕迹”虽然不错,但却有失偏颇。
吴敬梓既然能够将高启文集择之入书,那么对于高启文集,想来吴敬梓当不陌生。联系其擅于将前人作品“化腐朽为神奇”的事实,那么,高启的作品是否也有为吴敬梓吸收改造的可能呢?高启文集中,《南宫生传》、《书博鸡者事》是两篇关于侠士的作品,虽为传记,但行文笔法更类传奇小说。无独有偶,《儒林外史》也写到了侠士,即凤四老爹。学界认为,凤四老爹原型乃当时大侠甘凤池。[9]甘凤池,南京人,性喜任侠,以武勇著名,《清史稿》有传。吴敬梓长期定居南京,对甘凤池应该耳熟能详,以甘凤池为原型极有可能,比如文中胡八乱子踢凤四老爹肾囊一事,即很有可能本事于徐珂《清稗类钞》卷十五《技勇类·甘凤池拳勇》所载。不过,这并不妨碍作者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学元素的可能。愚以为,吴敬梓所塑造的凤四老爹身上也有南宫生、“博鸡者”的影子。比如《南宫生传》所写南宫生,“少任侠,喜击剑走马,尤善弹”“家居以气节闻,衣冠慕之,争往迎侯,门止车日数十辆。生亦善交,无贵贱皆倾身与相接。”《书博鸡者事》中“博鸡者”“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里侠者皆下之。”与小说中凤四老爹出身市井江湖,交接黑白两道,大凡提起凤四老爹之名,无不敬让有加,颇似。尤其文中所写凤四老爹通过手段使身陷囹圄的万里不但得以释放,而且还弄假成真,帮助万里由“假中书”变为了“真中书”;即与《书博鸡者事》中“博鸡者”激于义气、帮助多有“惠政”而遭诬陷下狱的袁有守“官复原职”一事相似。只是前者事迹不太光彩,后者更显仗义罢了。吴敬梓反其意而用之,别具匠心。
三、“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
《儒林外史》第12回“名士大宴莺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写道,娄三、娄四“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在京师闲的无聊,返回故里,访求遗贤,欲以博个战国时期信陵君、春申君求贤养士的美名;于是召集蘧公孙等“名士”凑成了所谓的莺脰大会,“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和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的怪模怪样:真乃一时盛会。”第17回“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中,匡超人与景兰江相见,景兰江道:“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不瞒匡先生你说,小弟贱号叫做景兰江,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后匡超人与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等人相会,饮酒之间,景兰江提议:“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楼’字为韵,回去都做了诗,写在一个纸上,送在匡先生下处请教。”第34回“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中,杜慎卿与季苇萧、萧金铉、郭铁笔等“名士”突发奇想,“择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会”,文中写道:
到初三那日,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众客也渐渐的来了。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是单上画了‘知’字的,来叩见杜少爷。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众戏子应诺去了。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熏风,吹得波纹如觳。亭子外一条板桥,戏子装扮了进来,都从这桥上过。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让戏子走过桥来,一路从回廓内转去,进东边的格子,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
诸如此类的名士聚会,除上述,文中还涉及不少,《儒林外史》反映士林百态,文人结社自不可少。无他,盖因聚会结社历来即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时至明代,更是喧嚣尘上,甚为发达。据学者统计,“明代文人结社个案达到680多例,单隆庆、万历时期的社团或社集就有220多例,天启、崇祯时期短短二十几年间则有近200例。”[10]仅就吴敬梓家乡安徽而言,据郭绍虞先生考订,有明一代,其文社有12 家,“仅次于浙江和江苏,与上海并列,在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与江苏、上海共同组成的南直隶,结社总量居于首位,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安徽则位居第三,数量还是较为可观的。”[11]如此众多的文人结社,规模大小不限,小至二三人,如敬亭诗社、群社、晋社等;中至十数人,如白榆社、匡社等;大至几十人、上百人,如肇林社、南社等。类型也不一,依据结社的目的、活动内容和社事功能,明代的文人结社大致可分为诗酒之社、时文之社和宗教之社三类[11],其中以诗酒之社为多,酒酣耳热之际,拈题分韵,相互酬唱,素来被认为文人雅事,如《月泉吟社诗》、《西湖八社诗帖》等即是明代较为著名的诗社酬唱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二著录《西湖八社诗帖》云:
明嘉靖壬戌,闽人祝时泰游于杭州,与其友结诗社西湖上,……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诗集为此编,分春社、秋社二目。
时文之社次之,其结社目的在于揣摩时文,相互切磋,以便科举高中。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记甬上之会云:“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求一哄之平,盖齗齗如也。”为达中举之目的,甚至不乏有文社“仿场屋之例”者,如鉴湖诗社“仿场屋之例,糊名易书,以先生为主考,甲乙楼上,少长毕集楼下侯之。一联被赏,门士胪传,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黄宗羲 《南雷文约》卷一)“正因为专研时艺的文社甚多,所以有些与书铺有关的坊社,请了一班制艺名家,主持选政,揣摩风气,也会极盛一时。”[12](P153)宗教之社少见,兹不赘述。吴敬梓后迁居金陵,金陵文社同样兴盛,钱谦益《金陵社集诗序》云:
弘、正之间,顾华玉(璘)、王钦佩(韦)以文章立坛,陈大声(铎)、徐子仁(霖)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歙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日藩)、何之朗(良俊)为寓公,金在衡(銮)、盛仲交(时泰)为地主,皇甫子循(淓)、黄淳父(姬水)之流为旅人。
金陵本为繁华、风流渊薮之地,文人结社往往与青楼有染,一面“相予授简分题,征歌选胜”,一面“烟水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万历三十二年,张凤翼等人“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周亮工《书影》卷二记万历时茅元仪出入金陵发起午日秦淮大社,“尽两岸之露台亭榭,及河中之巨舰扁舟,无不倩也。分朋结伴,递相招邀,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茅元仪字)之社者”,真是盛况空前。
吴敬梓历经繁华与落寞,深谙前朝历史掌故,对于文人结社之习极为熟知。《儒林外史》所写大大小小社团及形式都于现实有证,比如莫愁湖之会即与张凤翼等人相仿,而莺脰湖之会则似乎可见茅元仪的影子。至于其他,更是于文人结社司空见惯。但问题是,吴敬梓对于文人结社似乎并不认同,这些与会的“名士”多半是胸无点墨、沽名钓誉之徒,莺脰湖大会尤其像是一场闹剧。换言之,文中大凡文人结社处,多是作者揭露士林丑态最为出色、有力的地方。
吴敬梓何以如此“丑化”文人结社?当然,作者如此建构情节,与其创作本旨有关,写文人结社更有助于创作本旨的表达。但如联系时人对文人结社的一般看法,作者如此“丑化”的确事出有因,不足为奇。有学者指出,明人结社,“自清代以来并未得到公允的评价,甚至被严重‘误读’亦不罕见。”[10]首先,就官方态度来说,在“集中代表了清代官方思想立场”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文人结社被四库馆臣“看作是一种极具危害的消极现象”,频繁地使用“明代诗社余习”、“明人诗社锢习”、“前明诗社之习”、“明季诗社之习”、“明季诗社之余习”、“明季诗社余风”、“诗社浮华之习”等贬义性表述,“这充分显示四库馆臣对明代文人结社现象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批判的”;且“长期以来因其权威性使人们对它取信者多,考疑者少,往往断章取义,奉为圭臬。”[10]比如《总目》卷一百八十二著录宋荦《绵津山人诗集》云:
(宋)荦所作诗有《古竹圃稿》,有《嘉禾堂稿》,有《柳湖草》,有《将母楼稿》,有《和松庵稿》,有《都官草》,有《双江倡和集》,有《回中集》,有《西山倡和诗》,有《续都官草》,有《海上杂诗》,有《漫堂草》,有《漫堂倡和诗》,又有《漫堂草》,凡十四集。大抵沿明季诗社之习,旋得旋刊。出之太早,故利钝不免互见。[13](P2537)
《总目》卷一百八十三著录的张竞光《宠寿堂诗集》则云:“竞光字觉庵,杭州人。其诗每首之后评语杂遝,殆于喧客夺主。盖犹明季诗社之余习也。”对于四库馆臣不遗余力地揭明代文人结社之短的原因,何宗美先生认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明代的文人结社在清代已经成为官方高度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对清王朝思想文化专制及其政权统治极为不利,所以才产生一种极度敏感、过分警觉的政治心态”;其次,由于官方的导向作用,“清代士人中思想观念受到官方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0]结果则是,清代文人对明代文人结社同样多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如黄宗羲即认为文人结社,“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彼此纷嚣,莫辩谁是”。(《南雷文定》卷六)清初朱一是《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中也云:“今日之事,尤多骇异,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横议朝政,要誉贵人,喧哗竞逐,逝波无砥,颠倒瀹乱,蹶张滋甚。”
彭荪贻《客舍偶闻》曾载:明季北京陷落,江浙士人犹踵武于复社之会,时时聚集作文饮酒,风流自许。一次嘉兴集会,一僧人从北方来,见此,作诗讥刺道:
各郡明贤试自思,就中孰个是男儿?燕京难挽龙髯日,鸳水争持牛角耳。滴尽冬青还有泪,歌残凝碧岂无词。长陵麦饭谁为奠?愿借尊前酒一卮。
一意结社而不顾国家危亡,实为可悲。至于研讨时文,不暇他务的文社,更是遭到清人极力排斥,“前明以制艺取士,立法最严。题解偶失,文法偶疏,辄置劣等,降为青衣社生。故为诸生者,无不沉溺于四书注解及先辈制艺,白首而不暇他务。”[14]可以说,文社走到清代,其地位也由昔日士人心目中的“黄钟”沦为了当代文人眼中的“瓦缶”。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体,吴敬梓同样不可免俗,彻底脱离属于他的那个特定时代。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将《儒林外史》文人结社与作者对科举制度批判联系在一起时,不要忘了,二者建立联系的基础还在于作者个人对文社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则是源自于清代特定历史环境及由此带来的“明人之学向清人之学”[10]的转变。
至此可见,明代社会与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之关系实质上已经逾越了“借径”的界限,水乳融合,化为情节筋脉。因此,这也即意味着,当我们解读文本时,尽管可以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加以观照,但如要将研究真正推向深入,文本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与时代,以历史视角予以解读或许能带来曲径通幽、别开洞天的效果。
[1] 周兴陆. 江风吹倒前朝树——试论《儒林外史》的“明史观”[J]. 明清小说研究, 2003, (4).
[2] 杜贵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1).
[3] 陈美琳.《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J]. 南京社会科学, 1994, (10).
[4] 张锦池. 论吴敬梓笔端的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现象——《儒林外史》的创作本旨及其深层意蕴[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 (4).
[5] 孟森. 明史讲义[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6] 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A]. 竺青选编.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C].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7] 宁稼雨. 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J]. 明清小说研究, 1997, (1).
[8] 宁稼雨.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J]. 南开学报, 1997, (3).
[9] 刘娴.《儒林外史》凤四老爹形象解读[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8, (1).
[10] 何宗美. 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批判之辨析[J]. 文艺研究, 2010, (5).
[11] 李玉栓. 安徽明代文人结社的特点、成因和作用[J]. 黄山学院学报, 2011, (6).
[12]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3]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4] 彭蕴章. 归朴龛丛稿[M]. 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Scholars and the Ming Dynasty
ZHU Yang-dong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The novel The Scholar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ety of the Ming Dynasty. Why did its author prefer Hongwu (1368-1398) to Yongle (1403-1424)? It was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in Hongwu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Moreover, Zhu Di usurped the throne, thus defying the rites of the Zhou Dynasty. Wu Jingzi, author of The Scholars, was against the practice of forming associations, which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Yong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what has in the novel was se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Hongwu Reign; Yongle Reign; Gao Qi; Wei and Jin demeanor; association formed by men of letters
I207
A
1005-7110(2013)01-0090-07
2012-09-
朱仰东(1979-),男,山东郓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