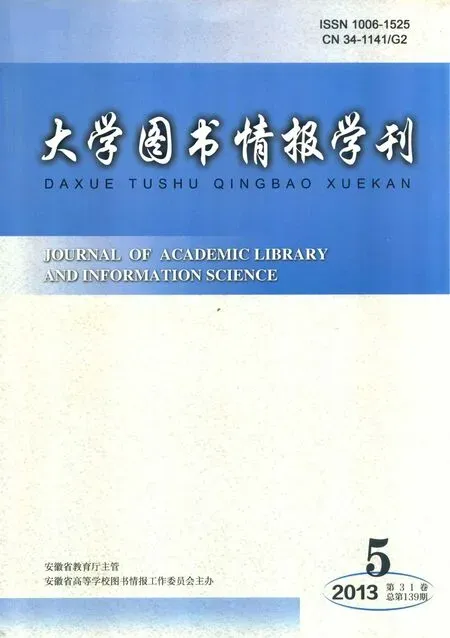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评介
王凤平
(安徽大学,合肥230039)
陈祖武先生(1943-)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尤以清代学术用力最多。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治清史的众多学者中,陈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开创性研究,使其成为这一领域的杰出学者。从早年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和《清儒学术拾零》,到近年的《中国学案史》和《清代学术源流》,中有《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旷世大儒顾炎武》、《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等等,都足以证明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耕耘与收获,自然也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公允评价和诸多赞誉。尤其这部以爬梳和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可谓集作者数十年研究之心血,结为此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上溯明代,下迄民国,于一代学术观澜索源,知人论世,不仅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源流嬗变,而且对学术演进与世运变迁、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向之间的密切联系,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扎实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进程,同时也深化和提升了学术史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该书的创造力和前沿示范作用,对当下推动学术发展、引导学风建设方面也有现实启示意义,故而能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既嘉惠士林,启益后学,也是众望所归。综览全书,并结合作者多年的治学经历和特点,笔者有以下三点体会,权当对于《清代学术源流》一书的介绍与评论。
1 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
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探讨和把握这一规律,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根本课题。所以,自清中叶至近代,就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徐世昌《清儒学案》、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以及钱穆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清代学术源流》一书在承续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运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清代学术演进分为清初学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三个阶段,既有宏观的把握与识断,也有微观的考辨与探析。作者从“明清更迭与清初学术”入手,由“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到“清廷文化政策的批判”,展开对清初文化政策的思想依据和历史作用的深入分析,指出:明清更迭是历史的前进,而学术的发展也进入到由乱而治的阶段。随着学术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继续推进,这将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启迪和提供更多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
清初的80年,学术界承先启后,开拓路径,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气魄之宏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该时期的学术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学术,又不同于尔后的乾嘉汉学,它以博大恢弘、经世致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之中,清初学术由经学考辨入手,翻开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陈先生以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的交涉和《理学宗传》与《明儒学案》的结撰为实例,重点阐释了江南刘宗周与河北孙奇逢及其稍后的李颙二曲关学的鼎足而立,以及同主顺治及康熙初年学术坛坫的是非和风雨。该书以刘宗周、孙奇逢、李颙为清初三大儒,此种做法乃取全祖望之说,与当下学界的一般说法略有不同。因为“近世考论清代学术史者,去夏峰、二曲而取亭林、船山,以顾、黄、王三大师并称三大儒。这样的看法固然自有道理,无可非议,但是由此以往,对夏峰、二曲之学的研究,相形之下则未为深入,所得也就不及其他三家”[1]。而“王夫之的晚年僻居穷乡,潜心编纂,其著述在他去世百年后才得大行于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对清初学术界的影响”。该书虽然注重对南方学者顾炎武及其《日知录》、黄宗羲及其《明儒学案》的探讨,但也注重对北方学者研究的平衡,譬如对孙奇逢、李颙、“颜李学派的历史命运”,以及范鄗鼎与《国朝理学备考》的研究,就显得内容丰厚、视野开阔,充分体现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开拓新途,富有新意。
2 考证求实的治学理念
陈祖武教授沉潜中国学术史研究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即为杨向奎先生的《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抄撮资料,其后沉潜多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多发前人所未发,也奠定了他在此领域的凸显地位。他强调:“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2]所以,《清代学术源流》一书就是从大到思想层面的总结,小到语言文字的校勘,言之凿凿,细致入微。譬如,对“学案”一词的解题,作者就爬梳于四部类丛,博洽于释道典籍,考证出“学案”即学术公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对《明儒学案》成书时间问题的考证,则从以下五个角度进行归纳求证:(1)如何理解黄宗羲所言“书成于丙辰之后”;(2)关于《明儒学案》的几篇序;(3)黄宗羲与汤斌;(4)“陈介眉传述”说纯属臆断;(5)《明儒学案》不可能在康熙十五年成书等,得出《明儒学案》初名《蕺山学案》,直到康熙二十年亦未竣稿,仅以前六卷流传。至于改题今名,已经是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的事情了。又譬如对于学案问题的整体探讨,作者首先追溯到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佛教史籍等对学案体史籍的影响,认为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作者虽然意在辨章学术,但字里行间无不事事剖析,处处考证,即使在页下注中,也不乏精到的考证文字。譬如,颜李学派的王源在康熙二十九年前后的经历,《清史稿·卷四八○·王源本传》称:“昆山徐乾学开书局于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与焉。”此说有误。据王源《居业堂文集》卷13《南游日记序》、卷18《先兄汲公处士行略》及方苞《四君子传》等文载记,康熙二十九、三十年间,王源一直在北京,未随徐乾学南归。《清史稿》当是将参加洞庭山修书的王原误作王源。作者目光如炬,又剖析毫厘,加之扎实的材料和校勘的功夫,其说确凿无疑,见解也独树一帜,裨益后学良多。
《清代学术源流》既能立足于文献考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又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统观一代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的关系,错综会通,兼容并蓄,突破以往相关著作的旧有格局。例如,作者考论乾嘉学风,从经筵讲论的角度把握朝廷的思想动向,认为:乾隆初叶以降,朱子学的传衍并未因清高宗之提倡而获推动。相反,朴实的考经证史之学,则已蔚成风气而不可逆转。以乾隆十四年之诏举经学特科为契机,不胫而走,风靡朝野,成为一时学术之主流。其说从史料而来,敦本务实,管中窥豹,堪称创获。同时,该书也能充分注意到地域学风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乾嘉时期的古学复兴潮流,是由江南中心城市发端,沿大运河由南而北,直入京城,在取得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之后,演为清廷的文化政策。于是朝野共鸣,四方流播,最终形成盛极一时的经史考证之学,因之拔宋帜而立汉帜,遂有汉学、朴学或乾嘉学派之目。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谓探赜索隐,鞭辟入里,考论结合,切理厌心。
3 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
清代学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整理和总结,无论在思想方法还是在成就和影响方面都是空前的。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对历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到《皇清经解》和《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清代前中期学术成果的汇集与探讨,都表明了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3]《清代学术源流》就是针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特殊现象和卓越成就而加以挖掘、爬梳和整理,探讨其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成就,及其各学派的师承源流和得失成败,以历史的眼光贯通三百年的学术思想脉络。譬如,该书对清代学术主流“乾嘉学派”的论定,就是在前期《乾嘉学派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高屋建瓴的总结,指出:“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惠栋、戴震、钱大昕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古学复兴蔚成风气。三家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为封疆大吏而奖掖学术,以道光初《皇清经解》及与之前后问世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为标志,乾嘉学术遂步入其总结时期”(参见该书前言)。嘉庆、道光以后,汉学颓势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等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作者以“晚清学术及一代学术之总结”为题,从汉宋学术之争的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入手,对方东树《汉学商兑》、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徐世昌《清儒学案》以及钱宾四和梁启超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加以深入剖析,借以揭示汉宋学术之争的由来及其发展,振叶寻根,洞悉幽微,认为晚清学术既不是汉学的粲然复彰,也不是宋学的振然中兴,它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随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而演进。而稍后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一批思想家的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序幕。这些文字的总结语句不多,而实为数十年潜心苦读、爬梳董理的心血结晶。作者取舍有法,不尚高奇,对该时期学术演进的历史做了高屋建瓴式的解析与会通,述往思来,鉴古训今,既深化了先前的专题研究,也为后学开启了继续前行的路径。
《清代学术源流》一书从明末清初学术的创辟规模,到乾嘉学派的经史考证,再到晚清社会的历史巨变,既有历史轨迹和学术思潮的剖析,也有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而人物思想的解读与理论的提升,又是建立在文献整理基础之上,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因此,考证求实和实事求是也一直是陈先生治学的理念和追求,正如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的历史学》中所强调的:“研究历史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必须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决不能急功近利、躁于求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本质上复原历史真相,我们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也唯其如此,中国历史学才能生机勃勃,永葆青春”[4]。今天看来,《清代学术源流》一书无论是对清代学术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个时期学术趋势的梳理,无不显示了基于深厚文献研究之上的卓越识断,体现出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路径,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追求。陈先生以陋室书斋为人生去处,“生存一日,即读书为学一日”的坚毅淡泊的学术精神,更令人钦佩。而其著述皆根本于文献,言尽于有征,平淡之处却有独到见解,其学风和文风也一如其人。我们相信陈先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也将随着学术发展的日渐深入,得到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而《清代学术源流》的出版,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还是对学术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6.
[2]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680.
[3]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M].合肥:黄山书社,2012.557.
[4]陈祖武.新时期与时俱进的中国历史学[N].人民日报,2008-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