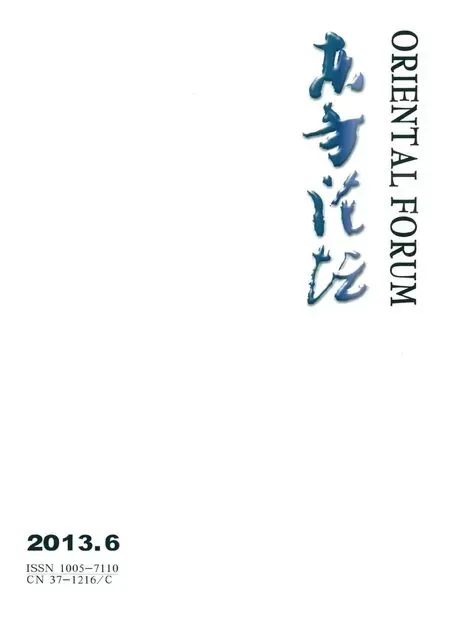孔子“五十以学《易》”辨正
程 旺
孔子“五十以学《易》”辨正
程 旺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历来对“五十以学《易》”的解释都不够圆满、周延,其原因是未能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经由义理、文势、事证等方面的论证可知,此章应是孔子暮年归鲁后的企求、哀叹之言,应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是五十岁时,与老而好《易》、晚而喜《易》并不同时;其五十岁开始学《易》的促因可从思想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可表述为从早年斥《易》到五十学《易》再到晚而喜《易》、老而好《易》的大致历程。
孔子;易;五十学《易》;老而好《易》
孔子是否学《易》 ?孔子何时学《易》 ?这是儒学史、易学史上的两桩著名公案。巧合的是,围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都与《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密切相关: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1]由此,正确理解“五十以学《易》”章内涵,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此章看似平实,实则内藏玄机,从字义到句意,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纷持异见,莫衷一是。其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鲁读”问题,即“易”是否当作“亦”,直接关乎孔子是否学《易》,不过,今人的许多“考辨”工作于此问题廓之已清①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金景芳《孔子对〈周易〉的伟大贡献》(《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7年)、吕绍纲《周易的作者问题》(见吕绍纲著《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李学勤《“五十以学易”考辨》(见李学勤著《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82-83页)、廖名春《〈论语〉“五十以学易”章新证》(《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黄沛容《易学乾坤》(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74页)等,近期成果如朱宏胜、钱宗武《“孔、〈易〉关系”公案考辨》(《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从考察《论语音义》条例出发,也对此问题作出了澄清。,本文不予再论;另一个是“五十”问题,即“五十”何解,此问题不仅指涉此章的言说时间,更关乎孔子何时学《易》,然已有的解答尚觉欠然,故针对“五十”问题做一点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就孔子的易学历程提一点新看法。
一、“五十以学《易》 ”之解的历史考察
欲解“五十以学《易》 ”,首先要对此章的言说时间作出认定,然后据言说时间推定“五十”之意义。历来之解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主“早年说”,则以“五十”为实指;主“晚年说”,则以“五十”为虚指。②历来对此章的言说时间的认定主要分两种:“五十岁以前”和“六十八岁以后”;称述方便起见,权以“早年”、“晚年”的提法代之。
“早年说”认为,此章应是孔子五十以前的言论,“五十”实指五十岁。以郑玄为代表:“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2](P78)也就是说孔子讲这段话的时间当在他四十余岁时。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说“当孔子尔时年四十五六”、宋代邢昺《论语》《论语注疏》说:“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云云,都是由此而发,其后崔适《论语足徵记》、宦懋庸《论语稽》皆主此说。“早年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若孔子时年才四十余岁,正值中壮年,怎会有“加我数年”这种衰年哀叹?而且若四十余岁就意识到《易》可寡过,为何非要等到“五十”才学?这两个问题,“早年说”都没有提供让人满意的解答。今人梁涛先生亦主此说,并试图完善解释,认为“五十以学易”是孔子五十岁以前的言论,孔子可能很早就已经接触《周易》,但他这时主要视之为占筮之书,快五十岁时认识到了《周易》之于人生的指导意义,于是立志重新学习《周易》,但由于四处奔波,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这一愿望,直到晚年自卫反鲁之后,才真正有时间来学《易》,孔子的易学见解主要在晚年提出,但他对《周易》的思考经历了从五十岁到七十余岁一个漫长的过程。[3]梁先生指出孔子的易学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五十岁到七十余岁一个漫长的过程”实属卓见,但仅以“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一语带过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深恐不妥。
“晚年说”则根据主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而喜《易》”语:
孔子晚而喜《易》……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史记》把“假我数年”一句系于孔子自卫归鲁(六十八岁)后,所以《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当为孔子晚年所言。按“晚年说”所论,加我数年方至“五十以学”就无从谈起,故他们认为“五十”不能是实指,只能是虚指。虚指何时呢?为了解决“晚年”所说与“五十”以学之间的矛盾,许多学者极尽想象之能事,如:
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朱熹《论语集注》)
加我数年,吾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俞樾《群经平议》)
加我数年,七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惠栋《论语古义》)
加我数年,九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何异孙《十一经问对》)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
对于经典我们也应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在原文可以承载的意义范围内,对原意进行合理的揣测,加以圆满、周延地解说,如若不能圆满解释,可以暂时存疑,而不应仅凭一己私见而妄断之,有如毛奇龄所言:“勿改经以误经”。(《西河合集·西河经解凡例》)前四说,改动经文,多任己意,不免穿凿,难予为训;第五说以一五一十为断,这样“五十”岁就成了五年、十年,但“五”尚合“数年”之说,“十”则有违,且此断句使语气极为不畅,就算“五”、“十”皆合于“数年”之说,则径言“加我五、十,以学《易》”岂不更显通畅。还有一说,以“五十”是指大衍之数五十,而不是“五十岁”,如明孙应鳌《四书近语》,此说固新奇,然与“加我数年”之义完全不相干矣。今人廖名春先生亦主“晚年说”,认为《史记》将此章定于孔子自卫反鲁后是正确的,他以“五十”为假设,将此章贞定为孔子晚年深入学《易》之后的追悔之言,其意思是:“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只要我从五十岁时就象现在这样学《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4]然如廖先生所论,若为追悔之言,悔恨自己如果五十岁时就已开始学《易》则该多好啊,那又为何须再希求“加我数年”;若希求“加我数年”,则何必又去追悔五十未学,犯了“大过”?
正是认识到希求“加我数年”与追悔“五十未学”之间不够恰切,一些学者就转变思路,开始在“加我数年”上动脑筋。如今人郭沂先生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他首先推定此语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他认为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以往未来的方向推,也可以往过去的方向推,此处正属于后一种情况,“加我数年的真正含义”是“如果我再年轻几岁”。①详见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按:廖、郭的观点当均对吕绍刚先生的说法有所采绎,吕先生曾言:“孔子垂老之年发这番学《易》 恨晚的感慨,意谓如果让我年轻几岁,五十岁开始学《易》,就可以不犯大过错了。既有自谦之意,也是赞扬《周易》之词。”参吕绍纲《周易的作者问题》(吕绍纲著《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然如郭先生所论,若“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5],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测若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所言,他会说“加我数年,六十以学《易》”,这和“五十学《易》”又有何相干?况且孔子若想表达“如果我再年轻几岁”的意思,为何不说“少我数年”而非曰“加我数年”,把“加我数年”“往过去的方向推”解为“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于情于理都难以让人信服。
现有的观点大都沿着“早年说——‘五十’实指”、“晚年说——‘五十’虚指”的思路进行思考,未能充分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解释力”似乎都不太理想。事实上,缺乏一个合法”的逻辑出发点,对经典“疑义”之处作出合情合理的诠解是很困难的。朱子曾言:“大凡疑义,所以决之,不过义理、文势、事证三者而已。”[6](P543)因此,重新反思以往的思路,立足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出发点,并考诸义理、文势、事证,庶几可得此章真义。
二、“五十以学《易》”章的新解
从逻辑组合的角度看,还有两条进路未受到前贤的充分重视,或可重新加以考虑,即“早年说——‘五十’虚指”、“晚年说——‘五十’实指”。经由论证,笔者认为此章的圆满解释应取径“晚年说——‘五十’实指”,请试言之。
首先,这句话当为孔子晚年所说。《论语·述而》“加我数年”本就可与《史记·孔子世家》“假我数年”所载相发明,而且现在也有了出土文献的新证: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帛书《易传·要》)①帛书《易传》均据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引,方便起见,错别字、古体字、异体字、假借字径以相应简体写出。
“老而好《易》”又可与《孔子世家》“晚而喜易》”相印证,孔子学《易》、好《易》、喜《易》,都应是不争的事实,“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7](P2-3)《论语》与帛书《易传》记载都可以使我们对《孔子世家》关于孔子学《易》的记载保持乐观的态度,所以,《孔子世家》将“加我数年”之语定在孔子自卫归鲁以后应是有据的。而且“加”者,通“假”,借也。②刘宝楠正义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参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8页。“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5]这就是说,“加我数年”的假设语气,预设了此章的话语逻辑前提,即孔子必须已意识到自己天年将终,所以此语当为孔子暮年所说,看来,《孔子世家》将“加我数年”之语定在孔子自卫归鲁以后是有理的。有理有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就是可信的。具体地说,此章应是孔子自卫归鲁(六十八岁,鲁哀公十一年)、老而好《易》之后说的。
其次,这句话中的“五十”应是实指。历来不把“五十”视为实指的主要是些“晚年说”论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五十以学”与晚年所说无法调和,加之前一句“加我数年”是一个假设语气,进而把“五十以学《易》”亦理解成了假设语气,误会此句为虚指,而附会种种穿凿之解释。大多学者未辨其中之异,导致对这句话的争论不休。其实“五十以学易”应是实指,孔子只是陈述了自己五十岁时就已开始学《易》的事实。曾有人批评以“五十”为五十岁之说“过凿无理”,“幼习六艺,便当学《易》,何况五十?”③不过,此说指明“好《易》、赞《易》非学《易》时也”则属洞见。[8]这个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五十岁决心“学”《易》之前,孔子接触过《周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彼时其对《周易》认识有所偏见,仅仅将《易》视为卜筮之书而不予重视(详及后文),故就算五十以前接触过《周易》,也不应将这种“接触”纳入“学”的范围内,④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学’,绝非初学,亦绝非一般性的学。因为一般性的学,看到的只是吉凶悔吝,绝不会看出《周易》是寡过之书。”如廖名春《〈论语〉“五十以学易”章新证》(《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五十以学《易》”之“学”不是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可参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2期)。如此来看,五十学《易》与幼习六艺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批评就更站不住脚了。若不然,孔子应该说“五十复学《易》”;其次,此说明显带有以今度古的色彩,撇开“学”的意义层次不论,当然,孔子是有可能幼时就已“学”《易》 (姑且称之为“学”),但孔子明确表述的是“五十以学《易》”,那么,我们就应当以孔子的自述为依据,而不应把我们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古人。
如上所言,若此章是孔子“晚年”所言,“五十”为实指,那么以此为逻辑出发点,能否在句意和文势上理顺“晚年说——‘五十’实指”的逻辑关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由前,“加”通“假”,假设语气;“五十”即五十岁,陈述语气。又,“以”通“已”,已经之意;①“以”“已”互释,早有先例,如《礼记·檀弓下》:“则岂不得以”,郑玄注:“以,已字。……以与已字本同”,又如《周易》损卦初九爻辞:“已事遄往”,《经典释文》:“本或作以”,故“以”“已”可通用。“以”字通“已”之例也并不鲜见,并有多种意涵:有太、甚之意,如《孟子·滕文公下》:“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有完结之意,如《墨子·号令》:“事以,各以其记取之”;有已经之意,如《榖梁传·文九年》:“襄公以葬”、《战国策·楚策一》:“五国以破齐楚,必南图楚”、《后汉书·荀彧传》:“今华夏以平,荆汉知亡乎”等等。“五十以学《易》”之“以”通“已”,表过去,当训为“已经”。前人诸说于此未辨,多认“以”字表未来意,造成此章句意逻辑隐晦不明,衍生诸不可能圆满之解释。“大过”即大的过错,兼指学《易》与人生。其句意可理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的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此语应理解为孔子暮年的企求、哀叹之言,哀叹的是“五十以学《易》”才略闻其“要”,企求的是“加我数年”继续学《易》,方可“无大过”。言外之意,孔子有感于天年将终,但自己从五十岁已经开始学《易》,直到现在,始对大《易》之“要”略有领悟,故哀叹时不我待,企求天命能多借给他几年时间继续研究《周易》,才能参透易理,对《易》理解不偏颇、人生不再有大过错。这并不是孔子的“追悔之言”,更不是“往前推,再年轻几岁”,而是一个垂垂老者在“安得益吾年”(《要》)的反思中涵咏出的企求之言,也是一个经历了长时期的学《易》历程后真正知晓了大《易》之美、深见《易》之无穷,老而好之、晚而喜之又不能尽之至之的哀叹之言。
刘宝楠看到了“五十”实指与“晚年说”之间的困难,曾“独辟蹊径”,认为《孔子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 之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9](P268)这个观点认识《论语》“五十”应实指五十岁、《世家》所言当在晚年是正确的,但由于他未能把两者贯通,只得将这两句同归殊出的话分别定位于两个时段;如果“五十岁”与“晚年说”实在无法调和,刘宝楠的说法不失为一个可能的精巧解释,但正如前文所论,《论语》“五十以学”不可能是“早年”(五十岁前)说的,而且“五十”实指与“晚年”所说也是可以圆满、周延地讲通的,所以即使刘氏复起,也“必从吾言”吧?《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是孔子学《易》自道的另一版本,其沿自《论语》“加我数年”章而来甚明,虽不涉及“五十”的争论,仍可与我们的理解互为印证,其意为“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能完全与易理相融”。“假”,借也,同“加”,表假设,与“五十以学《易》”的确定性陈述相对扬;“若是”,“竟事之辞”,“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10](P89),适与“无大过”相映衬;将两句话结合起来,则文义畅然明白矣:“加我数年,若是,五十以学《易》,我于《易》则彬彬矣,可以无大过矣”。为什么“五十以学”,到暮年还需“加我数年”?正因为《易》道精微,十几年如一日的学《易》仍未能“彬彬”,既使圣如夫子,也需加以年日方能尽之。为什么只需“假我数年”,就能“于《易》彬彬”?正因为孔子早就开始了学《易》的历程,五十岁就开始认真研究这部至命之书了。孔子表达“无大过”的愿景也说明孔子学《易》已久,学习的内在领悟与生活的外在坎坷相互印证,对“大过”的体认更深一层,才会发出如此哀求之言。
可见,未被前人重视的“晚年说——‘五十’实指”路向,反而可以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并且于字义考之则有据,于句意考之则有理,从字词句意上做出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解说。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是五十岁,与喜《易》、好《易》并不同时②廖名春《〈论语〉“五十以学易”章新证》(《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论语》此章之‘学’,实质就是《史记》、《汉书》、帛书《要》篇之‘喜’‘好’。只不过‘喜易’、‘好易’是他人对孔子的客观描述,而‘学易’则是孔子的谦称罢了。”此说是显是为了与作者前已论定的学《易》、喜《易》、好《易》同为孔子晚年之事相调和,附会“喜、好”解“学”字,看似有理,实则不免造作。将三者等同,未认识到孔子研《易》是一个由学到喜、好的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老而好《易》、晚而喜《易》是在六十八岁以后,“加我数年”章与帛书《易传》所载孔子论《易》亦应是此时而发。这也正是“吾好学而才闻要”(《要》)之语所由出也。
三、孔子五十学《易》之促因的可能阐释
孔子为何会在五十岁开始学《易》呢?这当然与春秋时代社会思潮的理性化转型、易学文化的人文化动向以及孔子思想的好学特质等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但具体的促因,史料则未载。据现有材料分析,可能有两方面的促因。一方面是思想促因,源自孔子自己所“逗漏”:五十岁时知晓天命,促使其开始研究《周易》。《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即是“五十以学《易》”的内证:
《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11](P91)
何晏此注引《说卦》赞“易”之语与《为政》晚年自述之语将“五十”、“知命”、“学《易》”有机联结,既阐明“五十学《易》”之“五十”即知命之年的五十岁,又提出“五十以学《易》”的原因应当是知命而为之,至为精妙。孔子在五十岁感悟到天命的於穆不已,于是会去研究生生不已的大《易》;也正是在大《易》的印证下,孔子对天命之纯完全吃透,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天道人道的冥合,逐渐达至“耳顺”乃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何注后曾受到许多学者批评,以其注为过凿、胶固,如崔适的《论语足徵记》批评说:“‘五十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12](P471)这个批评的立足点认为孔子“五十以学《易》”是其五十岁之前所说,由此认为何注不成立;而正如前文已交代明白的,“五十以学《易》”应是孔子暮年归鲁(六十八岁)之后所说,这样,崔氏的批评不仅站不住脚,反而为何注提供了一个反证,孔子七十岁后追述“五十知天命”之辞适与其六十八岁后追叹“五十以学《易》”之言相吻合,两者都是孔子对自己人生学思历程的回顾,何注之解正可明其中三昧,若径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恐怕才是一种武断呢。有观点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应理解为五十岁,而是概指“五十至六十这一个阶段”(同理,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①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如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2期)。,与“五十以学易”所指不同。这种观点至为荒谬,实不足一驳,若如此论所言,那么“十又五而志于学”的“十五”应概指十五岁到三十岁的一段时间都在立志,这合情理吗?“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七十”应概指七十到八十的一段时间,这合事实吗?“五十”确指五十岁无疑矣,而不应是五十至六十之间的一段时间,其他几句话皆当如是观之:孔子十五岁已立志为学,承担斯文以学礼(“不学礼,无以立”);三十岁已立于世,向知者进取(“知者不惑”);四十已然不惑,开始下学上达,体认天命;五十已上达天命,并契悟于大《易》;六十耳顺,达致自在自如之境;“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勉而中,在规矩中自由,这也就是《易》之天人圆融无碍之道的体现。
另一方面,孔子五十岁时可能在鲁国见到了《易象》一书。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这将是孔子五十学《易》的现实促因。《左传》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昭公二年)
由韩宣子所言可以看出,《易象》当为周公阐释《周易》的书,主要是发扬了他的敬德理念,这就很容易与仰慕周公、重德务德的孔子产生共鸣。《易象》之所以名为“易象”,很可能也与“易象”的两种属性分不开,“一方面,代表易象的符号是抽象的”,“另一方面,易象具有伸展特点”[13](P28),这样,周公以“易象”解《易》,既能与《周易》的卦爻辞发生联系,同时又能与德性理论发生联系,可以根据需要说明各种德性条目;《易象》成为沟通《周易》与德性的桥梁②有学者推测文王《易象》与今《周易·大象传》相近,如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亦见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第370页)认为:“文王周公之《易象》,今《易象》(《周易》大象)可略当之。此乃易学之正鹄。”刘大钧《“卦气”溯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也曾指出:“《易象》的内容,与今本《大象》之内容相去不远。”,这又与孔子学《易》主张观其德义、上达天道、阐扬哲理而依重《易》之卦爻符号系统的理论原则是一致的。可见,孔子见《易象》而学《易》,在思想性上是顺理成章的。从现实性来看,孔子五十岁时尚在鲁,此时(定公八年)距韩宣子见《易象》(昭公二年)已有近四十载,《易象》可能已经流传出来或早已流传出来,孔子学无常师,五十岁时在鲁见到《易象》并认真学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定公八年时的鲁国内忧不断,既有三桓之旧患,又添阳虎之新乱(阳虎欲去三桓,谋杀季氏未遂),故面对如此世道衰微、王纲失纽的国家秩序,孔子虽还未出仕(五十一岁时始任中都宰),但对天道变化之则、阴阳变易之理肯定深有领会,因此受《易象》影响并对《周易》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
廖名春先生论述孔子易学观的转变时[14],也曾推测可能与孔子见《易象》有关;不过廖说一贯主张孔子学《易》、好《易》、喜《易》是同一时期的事,同在孔子暮年归鲁之后,故廖先生认定孔子见《易象》的时间亦是孔子暮年自卫归鲁(哀公十一年,六十八岁)之后。前面已得证明,孔子学《易》在五十岁,与晚年归鲁后好《易》、喜《易》并不同时,撇开这点不谈,只就见《易象》时间而论,自卫归鲁后始见的看法,也颇有不妥。若如廖先生猜测:“孔子自卫反鲁时,《易象》可能早已流传出来”,那更有可能早在去卫之前就已流传出来;况且直到自卫反鲁的垂暮之年才见到《易象》,时不我与,故只能立即转变易学态度,开始研《易》,那孔子这个转变过程也太快了,难怪廖名春先生会用“突然改变”来形容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若言这是王室藏书,平常人见不到①如有观点认为《易象》是鲁国秘府所藏,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那为什么自卫反鲁后就能见到,而自孔子仕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直到官至鲁国大司寇(定公十二年,五十四岁)的三四年时间里,却没机会见到?再者,从孔子晚年对子贡等弟子的传授来看,孔子的易学思想已相当成熟,这么短的时间就研《易》如此,怎还会有“加我数年”、“无大过”之叹?孔子自卫反鲁后见《易象》说法,无乃而太晚乎?
总而言之,孔子由五十岁(知天命、见《易象》)开始对《易》产生兴趣,易学态度慢慢发生转变,从此走上了学《易》之路。其间,在孔子出仕治鲁、周游列国的人生历程中,饱经磨难、历尽坎坷,无不伴随着《周易》的人生指南,以及对《周易》的不断契悟;②《说苑·敬慎》即载有一例: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说,授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句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霸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据《史记》载,陈蔡之困,事在鲁哀公四年,孔子时年六十一岁。孔子现身说法,以“困之道”解说自己遭厄的人生际遇,借自己的处境阐发《困》卦的哲理,说明他在周游列国时已经研究《周易》了。虽然《说苑》并非正史,多为故事叙事,但与《孔子家语》、《韩诗外传》一样,其事并非空穴来风,不可全盘抹杀,而且此处所引最后一句“子曰”在帛书《易传·昭力》篇有相近记载。自卫归鲁之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与弟子论《易》、传《易》,益发觉悟易道之精深,直至发出“加我数年”之哀叹与企求。
四、从“早年斥《易》到“老而好《易》”
对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的认识,是受到帛书《易传·要》篇启发。从《要》篇来看,孔子晚年不仅喜《易》、好《易》,还与他的弟子讨论过《周易》,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孔子晚年的易学态度,与其早年对待《周易》的“它日之教”迥异,不得不谓之一大转变。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什么样态呢?晚年孔子易学态度转变,学《易》几近痴迷,其弟子也颇感疑惑,在对这些疑惑的解答中,孔子易学态度转变的样态初露端倪。面对夫子的老而好《易》,子贡(即子赣,贡、赣古通用)大为不解:“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不仅认为孔子好《易》有违“它日之教”,而且将好《易》与信“筮”挂钩;这说明早年的孔子直接认定《周易》为卜筮之书,而求神问卜之类活动与其仁义礼乐的人文教化思想难以相容,甚至是“德行”、“智谋”的对立面,真正的仁者、智者,不忧亦不惑③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论语·宪问》),不需要卜筮与神灵,所以对《周易》是不重视的、有意回避的,难免颇有微词。在弟子以它日之矛攻今日之盾的“质问”下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评论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辞”、“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这在《要》篇此处表现的最明显,此论很可能就是据《要》篇而发,作为“良史”,司马迁确实看到过许多后人不曾见到的材料,其记载基本都应是有根据的。这一点最早由廖名春先生指出。,孔子如此解惑:“察其要者,不诡其福”,“予非安其用也”,“《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解释称自己的好《易》并不是安于卜筮之用,祝巫卜筮只是次要的东西,因为他更为关注《周易》之“要”——“德义”;摆脱占筮的形式,从德义的角度对《周易》卦爻辞进行创造性的诠释,这一转向时革命性的。晚年的孔子已不再单纯地把《周易》视为卜筮之书,而是重新衡定了《周易》的性质;从早年斥《易》到“老而好《易》”,孔子实现了对《易》之态度的根本转变。当然,这一转变之可能,不能忽略这中间还经历了一个“五十学《易》”的阶段。孔子五十岁开始学《易》,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领悟过程,十余年上下求索的学易》、研《易》,六十八岁自卫归鲁后更是“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才逐渐晚而喜之、老而好之。由此,孔子易学态度转变的历程大致可示之为:
早年斥《易》→五十学《易》→晚而喜《易》、老而好《易》
由早年知其名、未得其实(知之)到五十以学《易》、好学之(好之)再到闻要得道的喜《易》、好《易》(乐之),这个转变历程与孔子厘定的学问三层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如出一辙,此语虽不必是对自己易学心路的完全摹写,但肯定对此一波三折的易学态度转变之精神有所体现。
综而言之,孔子早年认定《易》为卜筮之书,未予重视,所以一直没有去研究;五十岁开始沉潜于大《易》,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研究与探索过程从五十学《易》到暮年自卫归鲁),孔子逐渐发现易》之德义、《周易》未失的教化功能、“古之遗言”的文王之教、以及依重《易》之卦爻符号话语系统而得以获取的超越天道与内在哲理,晚而喜之、老而好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重新衡定了《易》的性质,奉之为崇德广业、显幽阐微、彰往察来、求道明理之书,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求其德以观其人道教训,上达天道以贯通天人。伴随着易学态度的转变,孔子晚年的思想由此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境地。
[1] 李学勤. 出土文献与《周易》研究[J]. 齐鲁学刊, 2005, (2).
[2] 王素.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3] 梁涛. 孔子学《易》考[J]. 中华文化论坛, 2000, (4).
[4] 廖名春.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新证[J]. 中国文化研究, 1996, (1).
[5] 郭沂. 孔子学易考论[J]. 孔子研究, 1997, (2).
[6] 朱熹. 朱子全书: 第六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7] 王国维. 古史新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8] 毛奇龄. 论语稽求篇[M]. 《皇清经解》本.
[9]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 何晏注, 邢昺疏. 论语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3] 林忠军. 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一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4.
[14] 廖名春. 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J]. 孔子研究, 1995, (4).
责任编辑:潘文竹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us’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at 50”
CHENG Wang
(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of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at 50" said by Confucius are not perfect due to the failure o sort ou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 it was uttered and the fgure "50". Actually it means "Given several years, I will be 50 years old. If I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now on, I can avoid making grave mistakes." Why he thought the age of 50 a proper time can be analyzed form ideological and realistic dimensions. It also shows his shift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study of his book.
Confucius; The book of Changes;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at 50; love The book of Changes in old age.
B222
A
1005-7110(2013)06-0008-07
2013-09-22
程旺(1987- ),男,山东曲阜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