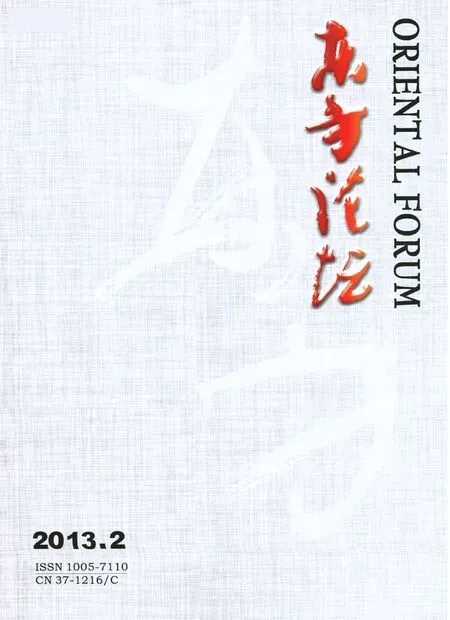超越与入世——中国佛教舞蹈的审美精神
李鸿宇
(中国艺术研究院 设计艺术学系,北京 100029)
佛教是以拯救和慈悲为宗旨,以解脱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在后世的宗教构拟的知觉里,外在的神的世界的形象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人的主观性臆想被降到了次要位置。在这种宗教场合下,艺术形象表象为对神性或者偶像的一种提示,或者表现为一种被宗教理解的现实和神性的某种实物。佛教是睿智的宗教,它在诞生之时,便用种种方式来传播自己,特别是艺术方式,而佛教舞蹈就是其中的一种。佛教舞蹈在统治者在宣传佛法的过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既张扬了佛教的神性,也显示了舞蹈艺术在宗教领域中的超越性和世俗性。而佛教舞蹈在其由神性向世俗性转变过程中,也彰显了不同时代或不同时期人们对佛教舞蹈的审美精神和审美理想。
一、 中国佛教舞蹈的超越性
(一)佛教舞蹈的精华:中国古代石窟乐舞形象中的佛教舞蹈
中国古代的石窟艺术是在南北朝是随佛教东传而兴起的。首先在丝绸之路西端出现,由西而东,从西域发展到中原,沿路留下了众多的石窟寺。这些石窟的壁画和雕刻中,乐舞形象几乎触处可见。佛经规定对佛的十种供养中应包括“伎乐供养”,雕塑佛像要“如帝身”,天国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神佛。
中国的佛教舞蹈比起中国的其他佛教艺术门类的研究比较滞后,佛教作为心灵的安慰剂,不同的人对他的需求不同。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宗教教义的传播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就宗教艺术而言,人们给予更多关注的是雕塑、塔寺、绘画、音乐,而宗教舞蹈始终是宗教雕塑旁边的小侍女,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了雕塑的伟岸和神圣,却没有注意到围绕在它们周围的飞升的陪衬物,它们或活泼、或优雅、或妩媚、或瞋怒、或英姿,都体现舞蹈这一造型艺术在宗教领域中的特殊作用,以及自身所独具的审美精神和宗教意蕴。作为佛舞一体的佛教舞蹈,它一面借“以舞传佛”拓展其影响,宣传其佛法;另一面则以“佛在舞中”给舞蹈——特别是东方或中国佛教舞蹈灌注灵魂,使其在佛光中奕奕生辉。
无论是在史前文明中还是在现代科技世界中,人类都保持着神性文化的眷恋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人类没有真正放弃神——无论这种神是人格化的还是象征性的,没有真正放弃对于神的皈依。宗教是具有超越性的,人类只有在超越过程中才能体会到彼岸的神性,也惟有这种超越性才能够摆脱世俗性而真正直面上苍。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也是一种升华,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与近在咫尺的功利迥然不同的境界。当我们将要由宗教转向艺术、转向舞蹈的时候,首先就要对超越有所准备。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终极指向就是宗教的对象。而文化产生的内在动因就是人的超越精神。宗教也可以算是一种艺术,是舞蹈的一种内在精神。
中国佛教舞蹈的精髓在于中国石窟和寺院中的舞蹈形象,它们记载了中国古代佛教舞蹈的最高水平和标准。而正是这些石窟中飞升的精灵具象化的体现了宗教的超越性,无论是上层的士人阶层还是下层的民众,与那些伟岸的佛像雕塑相比,这些供养佛、敬佛、娱佛的伎乐天、飞天更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佛国世界的神性。
佛教初传,佛教经典在文人士大夫中间传播的主要是大乘般若派的基本景点《般若经》、《维摩经》中所论述的“一切皆空”的思想,这与当时在上层文人中流行的“玄学”思想是很契合。所以,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是玄学化的佛教;在普通大众中,则是一种浓重的依赖佛像的信仰倾向。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人重直觉,同样也重视抽象的玄思冥想。一种玄虚的精神体物的方法把握宇宙和人生。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内在的精神活动达到一种超越语言和思想的境界,获得身心的彻底解脱,从而达到超脱,进入彼岸的极乐世界。佛陀在涅盘后已经永远摆脱了轮回,到达了了一个超验的彼岸,这样,佛教徒们是不敢在此岸用肉眼可见的雕像去直接表现它们所敬仰的佛。作为宗教信仰,采用借代的方式来照一种寄托物,这就是早期佛教中对佛的塔寺、宝座等物的崇拜,通过这些引发信徒对无限美好的彼岸的向往。总之,是从观念中把握佛而不敢让佛现出人的形象。但在希腊雕塑传统影响下,印度的佛教造像得以产生。这种具象式造像因符合中国人善感性和知觉的性格而使佛造像在中国得以繁衍与盛行。当佛教进入中国后,那些因果业报、三世轮回的思想以及追求实际功德的方法为普通民众接受,成为它们的宗教信仰实践。
这种具像式的佛教思想得到当时南北朝统治者的重视,于是,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时,沿西域大漠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一路留下了它的遗迹——石窟。它作为佛教徒求道修行的场所,不仅留下了无数修行者精勤历炼的痕迹,还给后人留下许多赞叹不已的雕塑与壁画。而正是这些石窟中舞动者的东方精灵,形象地再现了佛教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那些主佛像的庄严和伟大使膜拜它的人们感受到了天国世界佛性的力量无边,佛的庇护和眷顾使人们心灵有了归属感,却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和无力。而能够拉近人与佛、人与神的距离的正是那些飞升在佛像周围的舞动的精灵们。那些动感的舞姿、四散的鲜花、飞升的飘带、迷离的手势、弹拨的仙乐,使人们更实在感到佛国世界的“超胜独妙”的超越境界,也更能够感染和叩击人们的心灵。
石窟中的乐舞形象,主要是指飞天、天宫伎乐、伎乐菩萨、金刚、力士等形象;他们被雕刻在窟壁、窟顶、龛楣、明窗和佛座下,或绘制在壁画中。它们作为佛教艺术形象,首先是以宗教性、神性、超越性展示给世人的。这种超越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诠释:
1.石窟中乐舞形象是用于供佛、礼佛、赞佛的,它是超脱于世俗性的乐舞,并与世俗性的乐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乐舞与其他的贡品一样,皆是对诸佛菩萨的赞颂和供养。在佛经记载妙树种,乐舞之用,非世俗感官声色“五欲”响了,多是断惑见道的“法喜充满”,正如“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比如,敦煌272 窟的“听法菩萨”,人物盘坐于地,回手击掌,欠身回顾的动作形象,实是表现佛经中菩萨们聆听佛陀教诲时“欢喜踊跃”的场面情景。[1](P46)佛教中的乾达婆是佛教的乐神,紧达罗是佛教中的歌神,它们是石窟乐舞形象中的主要角色。他们手执乐器和鲜花,在佛说法时出现于空中,演奏乐舞,散诸香花,赞叹诸佛。佛教的乐神伴乐演奏,与世俗的乐舞不同之处,他们的演奏能使人升起持法修行的清净心,而不是“昏迷放逸”。佛教思想认为,贪恋“五欲”(色声香味触)是众生堕落受苦的根源。所以佛国乐舞多用“清净”、“微妙”、“妙胜”等词语,这种强调佛国的乐舞呈现和受用,有别于现实中乐舞的“五欲”之乐。
2.石窟乐舞形象营造了超越世俗的佛国境界。以敦煌石窟为例,乐舞形象和乐舞场面,都与经变的内容和境界融为一体,主体佛像为中心,围绕着诸菩萨,上有楼台殿阁,碧空祥云,飘散各种乐器,佛像前面是乐舞表演。乐舞前面由宝池莲花等。这已构成在各种不同的经变中几乎不变,只是中间的佛不同。敦煌莫高窟220 窟“东方药师经变”乐舞中,有四个相当大的伎乐天,在璀璨的灯楼灯树下,四个舞伎两两对称,均在舞动旋转之中,锦带服饰飘然而起,着重渲染“左铤右铤生旋风”的动态美感。乐舞表演与佛像和背景形成豪华壮丽的佛过景象,使人感受到,佛国的天宫伎乐正在以音声舞姿传递着理想彼岸的超凡。[2](P273)
3.石窟乐舞形象的超越性突出表现在舞姿造型的不可模拟性。舞蹈文物专家刘恩伯曾在《敦煌舞姿》一书中指出,敦煌石窟乐舞形象中的舞蹈动作,许多花样是现实中舞不出来的。石窟乐舞形象尤其是飞天形象,其一来源于我国传统,特别是汉代画像砖石中的羽人、飞仙等造型艺术;其二来源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香音神、音乐神等的形象描述中。而且特别是由于佛教造像绘画因素的参与,以及雕刻家和绘画家的艺术想象力和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介入,使得中国石窟舞蹈形象成为中国宗教艺术和造型艺术中的精品。
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十分丰富,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一方面是因唐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对各种艺术都比较广博采纳,另一方面,各种宗教在在唐代都进入了黄金时期,形成了儒、佛、道三位一体而以儒家为主的思想统治形势。佛教在这个时期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佛教舞蹈也由于当时统治者对这种造型艺术的推崇,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光大。唐代石窟和壁画中舞蹈形象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后面的宋元时期的舞蹈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唐代石窟舞蹈形象更具有超越性、宗教性、神性这种特征。唐代的飞天形象中优美的舞蹈动作,是现实中的舞者无法模拟的,多为艺术家想象中的舞姿,是被神化而变形的造型动作。她们的下半身,尤其腿部,都是卷裹在长裙中,曲折飘浮,无重心,无体重感,像随风飘佛的云朵。这种描绘,强化了伎乐飞天凌空飞舞的特点,给人带来无穷的遐想和动态美感。[2](P271)
莫高窟里的飞天早期为西域式的,上身半裸,半乳袒裎,宝冠裙帔,双脚与腿平直,舞姿圆转流畅;后来出现了中原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还有全裸的飞天,有女亦有男。飞天袒露的肌肤,白如凝脂,衣裙和飘带则表现了丝绸的质感,无处不显出飘逸的美。她们的舞姿千姿百态:有的展臂上升,有的俯首下降,有的前呼后应、扬手散花,有的双脚反垂,手捧鲜花。飞天的美妙身影和舞姿,常常使那些正襟危坐的佛菩萨相形失色了。
从审美造型上看,唐代壁画上的飞天由两种形态,婀娜苗条型和流畅丰颐型。初唐时的飞天多为苗条柔美型,盛唐时期崇尚“丰厚为体”的审美时尚,这使得飞天就以丰颐典丽,雍容飞动为美。唐代飞天上身多为半袒,姿态灵动多变,帔巾飘带随飞天动势而凌空飞腾,多呈“S”型翻卷,得体有致,飘逸流畅,给人以温馨而安恬的美感。敦煌莫高窟320 窟中的两个飞翔在“极乐世界”的供养飞天,是敦煌飞天造型中的典型。前者作侧面横向飞翔状,散发出朵朵鲜花;后者扬起双臂,腾跃追赶,那婀娜多姿的体态和翩若惊鸿的舞姿,以及缭绕于项际的飘逸绸带,不仅惟妙惟肖地显示出肌肤的丰满和柔润,还把她们心灵深处所蕴藏的欢愉情愫委婉地表达出来,极好地体现了“先人共天乐俱行,花雨与香云相逐”的意境。
敦煌壁画伎乐天的舞姿是人们或者具体地说是当时的画工们臆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乐舞。伎乐天的服饰与舞姿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佛教发源地——印度、尼泊尔的风格。伎乐天的舞蹈形象与真实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墓室俑、画不同,与敦煌壁画中供养人出行图的舞队不同,审视和描绘佛经故事生动场景中舞人形象也不相同。画工们臆想的天国伎乐多半裸上身,仅配项圈、臂环轻纱,而当时墓室舞俑、画和敦煌壁画供养人出行途中的舞人,和佛经故事画所展示的现实生活舞蹈场景的舞人,都与伎乐天有很大不同。这与唐代绘画造像的审美精神和审美风格相一致的。石窟中的人体描绘、服饰描绘伴随着舞蹈动作、表情都显示了佛教的超越性和神性,也只有佛教舞蹈形象才能具有这种超脱人世的飘逸感,它们是向着佛国世界飞升的使者,注定是与世俗的舞者不同,而人体是美的本体,更是圣洁的象征,半裸着上身佩着飞扬的舞裙和飘带,更能够唤起普通大众对佛国极乐世界的向往。
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舞蹈是虚幻的力的意象”。[4](P200)萨克斯也认为“舞蹈就是征服地心引力,摆脱各种重量的压制,使人体进入虚化境界,是被创造者上升为创造者;使人能和‘无限’也就是和神灵融为一体,愿为上帝和理解舞蹈的力量的人同在。”[5](P426)这是西方舞蹈学者对舞蹈这种造型艺术的宗教性概括,这也是对中国佛教舞蹈尤其是中国佛教舞蹈形象做的很好的总结。
中国的石窟舞蹈中最具有神性和超越性的就是飞天和伎乐天身上的那些飘带,也正是这些艺术符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和审美风格,虚幻的力和真实的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造型艺术写意和写实最完美的构图,同时更显示了唐代画工们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夸张和创造想象才能。唐代飞天的飘带以汰除了南北朝是飞天飘带的牙饰和尖角,显得更为轻柔,其造型更有飘逸感,长度有时可达身长的好几倍。这些飘带拖在飞天飞过的轨道上,显出迅疾的力量动势之美。209 窟(初唐)的双飞天,飘带飘扬于飞天身后,飞天之前则围着密密的云气。320 窟对称所画的几身飞天,在敦煌飞天造型中堪称婀娜、丰润。39 窟(盛唐)西壁龛内南侧飞天俯冲之势,形成逼人的感觉,这种冲势的造成,其从繁的飘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58 窟(中唐)西壁飞天五身,身后的飘带和云流宽、长、呈弧形,形成一条条道路似的轨迹。飘带是敦煌飞天的灵魂,是飞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是飞天的灵魂,也是飞天的特殊的肢体。佛教的飘带是飞天衣饰中常见的部分,由夸张飘带所带来的飞动美,是膜拜在她们脚下的普通大众们既感到神的亲切召唤,又感到天使圣洁的沐浴。飘带的舞动,不但是对人衣饰的升华,而且是对于空间的扩展。正是由于这些飘带千变万化,绚丽斑斓,形成内在的力,向任何方向去呈现,把飞天本体的力感扩展到周围和空间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飘忽的人体向无限动见探寻的非美学所蕴含的巨大命题——世界的本质是虚幻与空无。那么佛教作为普渡众生的心灵归属,是教导人们超脱此岸的束缚和烦恼,去追求彼岸的自由和快乐。
(二)石窟乐舞形象的审美特征
在这里,我认为中国佛教舞蹈中飞天的飘带与西方基督教中天使的翅膀是殊途同归,但中国佛教舞蹈中飘带与基督教中的天使有着俨然不同的审美精神和审美风格。
1.石窟乐舞形象突显了中国古典艺术“飞”的审美精神。“飞动之美”是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尤其重要的审美精神。在中国古典绘画、书法和建筑中,无不体现这种“飞动之美”。
中国绘画主要是从线条中露出形象姿态,着重于线条的流动,使得中国的绘画中带有了舞蹈得意味。正是通过这种飞升的线条来表现中国传统绘画的气韵生动之意境。常书鸿先生认为:“敦煌飞天所代表的佛教艺术创造性的成就,是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顾恺之的‘曲铁盘丝’之线描、吴道子的‘春蚕吐丝’之线描的绘画造诣分不开的。”[6]确实如此,特别是唐朝时绘画造像的繁荣,“吴带当风”成为当时绘画的审美标准,更是把这种通过线条之美来表现“飞升之美”的精神凸显无疑。中国古典建筑也具有这种“飞”的特点,中国建筑特有的“飞檐”,就是一种典型的动态之美。而这种“飞”的审美精神,正是中国古典哲学生生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而西方传统艺术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崇尚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2.石窟乐舞形象凸显了中国古典艺术中“虚实结合”的审美理想。石窟乐舞首先是体现佛法,佛陀教导人们超越此在的世界,去追求只有歌舞升平的彼岸世界,用有形的艺术体去表现一种佛经中的幻像。这是一种典型以实显虚的创作观念。埃及、希腊的造型艺术讲究一种团块的造型,讲究实的艺术。[3](P335)就中西的表现手段而言,中国的飞天用飘带,完全是一种虚幻的舞动,但正是用这种现实中难以模拟的舞动形象,再现了人物超越现实的景象;而西方的天使则给人物加上了动物的翅膀,我们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实在的振动,却不能有中国飞天那种幻化色彩。中国石窟乐舞形象正是这种虚实结合的典范,都带有超现实类型化的特征。而飞动的线条的运用,更是画家在构思中为了使得整个形象更美,同时更能够表现深层内容内部节奏而运用的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二、中国佛教舞蹈的世俗性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宣传了它的佛理,更是一个被接纳和吸收的过程;它在表现自己的神性的同时,更体现了它在不断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民间化和世俗化。特别是北魏在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推行汉化政策,这使得佛教艺术在沿着自己轨道发展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改造。
云冈石窟早期的伎乐飞天,大都半裸上半身,形态健壮,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这是由于北魏最高统治者是鲜卑族有关,显示了鲜卑族的审美情趣。这说明佛教在一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带有民族化的色彩,与纯粹的印度佛教舞蹈开始不同。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石窟的佛像改袒右肩或通肩大衣,为褒衣博带式的汉装,而飞天也变半裸上身,赤脚位短襦长裙的汉族女子传统服装,脸形和体态也都逐渐中国民族化了。在云冈石窟第十二窟外小龛飞天,那含蓄、目光下视的表情,活像一个美丽温柔的中原少女。[1](P21)云冈石窟的飞天,与唐代敦煌壁画大幅经变画中,在佛前“表演”舞蹈的伎乐天不同,她们不是正在“舞蹈着”的天女。但她们的优美姿态,却具有强烈的舞蹈感。云冈石窟的飞天,与敦煌壁画隋唐时期那些飞舞天际,身姿飘逸,富有仙气的飞天也不相同,云冈的飞天,动作更真实合理,有一定的模拟性和可舞性。那些雕刻得十分细腻的面部表情妩媚深情,俏丽的身形婀娜多姿,再现了当时活跃在皇宫、贵族之家以及寺院、民间的歌舞伎人的身影。能够表现佛教舞蹈世俗性一面的更在于雕刻在石窟中的那些民俗舞、杂技与力士的舞蹈形象。第十窟前室北壁,有两个雕刻在似门框内的舞人,一人扬首,盘右腿如坐姿,举手挥臂而舞;另一人平视,双膝并拢,如坐姿,亦举手挥臂而舞,他们那“压腕”、指尖抚头的姿势,是今天新疆民间舞的常见动作。[1](P22)第五十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实际是人间缘幢(爬竿)杂技表演的写照。云冈石窟的力士像,几乎每窟都有,力士是石窟的“守卫者”,是佛神的卫士或侍从,他托起巨石支撑石窟,具有粗壮健美的体魄,凸起的肌肉,充满着力量。[1](P26)云冈石窟风格各异的舞蹈形象,正是北魏荟萃西域乐舞、北方民族乐舞及中原汉族传统乐舞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撩开那一层宗教神秘的幔纱,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时的人间世俗生活。端坐演乐的天宫伎乐,轻盈飘舞的飞天,似曾相识的民俗舞姿,引舞入场的侏儒,杂技表演的情景和形体健美的力士等,无不来源于生活,是民间世俗生活的真实反映。
北魏孝文帝仰慕中原文化,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又开凿了龙门石窟,继续依重佛教来巩固统治。这个时期的舞蹈形象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更加具有“民族性和世俗性”色彩。随着北魏政治中心南迁及佛教传入时间的推移,中原风格就更为浓厚。只有极少数窟龛,如露天交脚弥勒像龛背光上的伎乐飞天是肥壮的裸身儿童外,其他洞窟的伎乐飞天大多是眉清目秀,婀娜多姿,具有中原汉族美女的特点。她们飞舞翱翔于窟顶、佛的背光、龛楣等处,他们富于舞蹈感的姿态虽然很美,但还是没有可模拟性。但是龙门唐代石窟的伎乐天,形象就更为真实,除了空际飞舞的伎乐飞天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雕刻在佛座下或窟壁底部那些正在奏乐、舞蹈的娱佛天女。她们的下身,不是卷裹在长裙重,淹没在云海里,而是聚精会神地在演奏着,脚踏实地在舞蹈着。她们的体态姣美,脸型丰腴,是典型的唐代美女,她们的舞姿具有可模拟性。在雕刻精美的万佛洞,在层层佛像的壁基下,又两组伎乐浮雕。南壁,大佛下面又一个舞伎,身穿长裤,双手托掌腴头顶,左腿直立,右膝曲掖,飘带飞扬两侧,似乎是在激烈舞动中,双臂上下挥动一瞬间的停顿造型,颇具唐代“健舞”风貌;北壁紧挨大佛下面的另一舞伎,身穿细腰长裙,出胯侧腰,伸右腿,足尖点地,上身向右倾斜,双臂抚头,感觉向下,富于“软舞”神韵。[1](P32)
在保存了大量丰富、珍贵的舞蹈形象的敦煌壁画中,能够体现民族性、民间性的舞蹈形象也是很多。南北朝时的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的基调、造型、风格及精神气质,由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不同而体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北朝各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建立的政权,他们能歌善舞,其舞蹈形象的基调就是豪放、雄健的神韵风采,造型和精神气质也以奔放、雄健的气质为主。而南朝各代,由于政治的失利,精神状态的伤感,以及南方的传统乐舞,其舞蹈形象的基调和风格就以婉转缠绵、优美深情为主。唐代的敦煌壁画供养人行列中的乐舞场面和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佛经故事画中的民俗舞蹈,是与墓室俑、画具有同等历史价值的艺术珍品。它们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地舞蹈活动情况。晚唐修建的敦煌156 窟,著名的张仪潮出行图,就真实地描绘了当时贵族出行仪仗地乐舞队伍。敦煌第445 窟的《嫁娶图》,一向为学者所重视,图上所绘舞人,与五代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舞人的服饰与舞姿风格十分相似,由此可以证实《嫁娶图》中的舞人形象是当时习俗舞蹈的真实反映。[1](P53)第360《维摩诘变》舞人在酒店起舞的场面,使我们看到衣着质朴无华的唐代民间艺人,在酒肆献艺的生动舞姿。[1](P54)晚期的敦煌壁画主要是宋、西夏、元各代的作品,舞蹈形象主要使经变画中的伎乐天和佛经故事中的舞蹈画面。但这个时期的舞蹈造型远不如唐代那样生动灵气,而是显得呆板僵硬,缺乏舞蹈的美感和动感。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发展到唐代以及宋代,已形成了中国化的宗教了,世俗化民间化倾向日益严重。在敦煌“五欲图”中的几个舞蹈场面,其中有一幅女舞者抛撒长袖,拧身回头,撅臀出胯,显示欲以舞蹈诱惑释迦牟尼,使其依恋人间声色享乐,放弃出家的念头。而释迦牟尼则双手合十,仰望长空,根本不观看舞人表演。[1](P56)莫高窟现存的元代洞窟中,舞蹈形象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第465 窟中双身佛像即欢喜佛。佛立作等弓步姿,女一腿与佛主力腿叠立,另腿绕跨在佛身腰后,作交合状。这类佛教艺术中的双身像,可以溯源到古老的生殖崇拜。[1](P59)但是能够在神的光环中,在宗教神秘外衣的笼罩下,以另一种面貌被人类供奉在神坛之上,说明佛像已没有了早期的神性特征,越来越世俗化了。
[1] 刘建,孙龙奎.宗教与舞蹈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2] 张育英.中国佛道艺术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3] 宗白华.意境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 [德]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 [M].郭明达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
[6] 常书鸿,李承仙.敦煌飞天 [J].舞蹈论丛,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