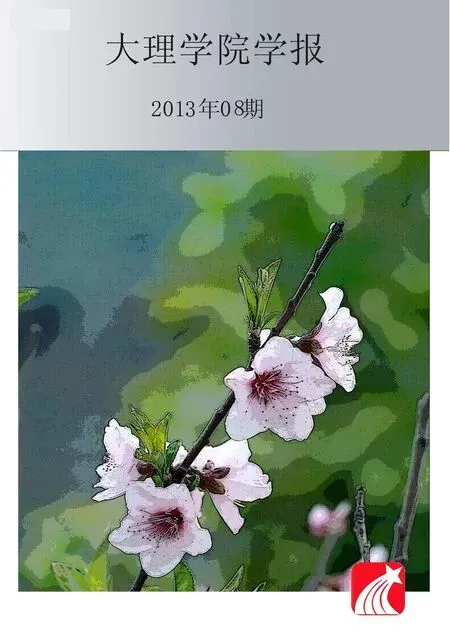自由是文化创新的基石
赵映香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一、谁是文化创新的真正主体
毋庸置疑,人是文化创新的主体或主词。比如在“人是具有创新性的动物”这一判断中,内涵着两个结构:一个是横向的主谓结构,在此结构中,“人”是相对主词(说它相对是因为它还可以做谓词,比如“张三是人”,而主词“张三”是绝对主词,因为它不可以再做谓词,即我们不能说“这是张三”“那是张三”等,除非“张三”是在同名异义上使用),“创新性的”“动物”是谓词,系词“是”把二者连接了起来。一个是纵向的意指结构,在此结构中,主词“人”意指着人这个主体或属,以及泛指着诸如“张三”等众多的个别对象。但由于“人”是一个普遍实体词,对任何普遍实体词都可以通过引入不同的属性作为标准,然后把它们划分为抽象性程度不同的普遍实体词。显然,划完或划出“人”这个种所包含的各层级的属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任务或目的是紧跟本文主旨对其作一个示范性的划分。
比如若引入属性词“生活领域”,则“人”可以分为“经济人”“政治人”和“文化人”。因为我们可以说“经济人是人”“政治人是人”和“文化人是人”。以上是对“人”这个普遍实体种词所作的划分,我们还可以对人所包含的属,即对“文化人”“经济人”和“政治人”再作划分,通过划分得到更低的属。当然,划分标准要始终如一,比如若再引入属性词“高校领域”,则“文化人”可以分为“办学者”“治学者”“大学生”。因为我们可以说“办学者是文化人”“治学者是文化人”“大学生是文化人”。
以上划分所得的“文化人”“办学者”“治学者”“大学生”相对于“人”这个种词来说,是普遍性和抽象性相对更低的实体属词,但终究不是绝对主词或个别词。它们的意义或价值在于最终用来述谓个别词或绝对主词,如“张三”“李四”等,即做个别实体词的谓词,所以,个别实体词所意指的个别对象是所有普遍实在意义的归宿。比如我们可以说“张三是大学生”“大学生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李四是办学者”“办学者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王五是治学者”“治学者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它们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同质性关系。当然,不同属种系列之间是异质性的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人、文化人、办学者、治学者、大学生、张三等都可以充当文化创新的主体,但人、文化人、办学者、治学者、大学生都是相对主词,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其普遍性和抽象性程度的不同。所以,文化创新的真正主体是高校领域中的一个个具体的只做主词不做谓词的诸如“张三”“李四”“王五”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体(substance),就其最真正的(truest)、第一性的(primary)、最确切的意义而言(most definite of the word),乃是那既不可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individual man or horse)。但是在第二性的意义(secondary sense)之下作为属(species)而包含着第一性实体(primary substances)的那些东西也称为实体(substances);还有那些作为种(genera)而包含着属(species)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例如个别的人是被包含在‘人’这个属里面的,而‘动物’又是这个属所隶属的种;因此这些东西——就是说‘人’这个属和‘动物’这个种——就被称为第二实体(secondary substances)”〔1〕(括号中的英文摘自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edited by Richard McKeon,The modern library,2001:9)。
二、文化创新的主体应该是自由的
确立了一个个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等是文化创新的真正主体后,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张三、李四、王五等作为文化创新的真正主体应该是怎样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主体应该是怎样的?本文的答案是:主体应该是自由的。很显然,答案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如果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张三、李四、王五等是不自由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是受束缚的、被强迫的、被越俎代庖的,即他们在文化领域不能自由地思和做(“自由:自己能做主。”参见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辞海》(缩印本),舒新城、陈望道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284。“自由”对应的英文是“freedom”和“liberty”。前者来自德语,后者则来自拉丁语。在英语世界,大都是不加区分地替换着使用这两个词。参见(美)汉娜·皮特金:“‘Freedom’与‘Liberty’是孪生子吗”,陈伟、刘训练译,《第三种自由》,兴奇、刘训练编,东方出版社,2006:312-345)。这样一来,每一个能以“我”自称的一个个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等文化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就被否定、搁置。也就是说,这样一来自由就只是某一特权或某一个人的自由,有名有姓的众多的个别的人却没有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2〕167。显然,没有了自由的真正的主体,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性的文化大师以及真正创造性的成果。本文的答案除了具有逻辑上的依据以外,还具有充分的哲学史依据。下面就拣选一二来加以佐证。
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的“自由”词条中,谈到了自由与思想文化之间的相关性,自由是“涉及思想和行动的概念,它有两个相关联的方面:一是消极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或‘解脱’(freedom from),即没有外部的约束、强制或强迫而行动的力量,另一个是积极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或‘自主’(freedom to),即主体在各种选择方案中选择他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力量。在上述的一般规定之下,自由具有各种形式,诸如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思想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结社自由(freedomofassociation)和各种经济自由(various economic freedom),它们在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自由形式”〔3〕。
这些自由确实很重要,不同的哲学家或政论家分别对其中一种或几种进行了讨论。比如17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John Milton)就集中讨论了“出版自由”〔4〕。160多年后,即公元1811年,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也就是《论自由》的作者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父亲,继续讨论了“出版自由”〔5〕。而其儿子约翰·密尔在《论自由》(1859年)中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他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Civil,or Social Liberty),“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individual)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6〕。密尔在书中具体讨论了社会自由或公民自由中的思想自由(liberty of thought)、讨论自由(liberty of discussion)和个性自由(liberty of individuality)(括号中的英文摘自随书赠送的英文本On Liberty)。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则在1819年讨论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即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7〕。而马克思则讨论了新闻出版自由。其论述特别体现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2〕136-202。比如他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2〕167-168。“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the absenc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makes all other freedom illusory)”〔2〕201(括号中的英文摘自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第43卷,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1975:180)。总之,“西方人历来有把真作为独立价值来追求的智识趣味,在近代经过无数像马克思那样的斗士的奋力抗争,又逐步争取到了自由地追求真知的政治权利及其制度保障。这样一种智识传统和法权制度使得西方的智识生产发展成了一个新知识、新思想层出不穷的庞大产业”〔8〕。由此,“我们可以醒悟的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禁锢其成员的头脑,否则就会丧失把握命运的能力;一个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会思想失职而有负天下”〔8〕。
自由和思想文化创新的关系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主要体现在开始提出时振聋发聩,而后变得耳熟能详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或“我想,所以我是”中。实际上,笛卡尔这一思想的理论用意或需求并不复杂,他只不过想寻找一个思想的起点或直接性前提即“我在,我思”。这里的我是个别词“我”即“实践主词”所指的实践主体。而且这个我不是别人就是笛卡尔自己。因为笛卡尔自己就坦言,他认为书本上的学问、众人同意或赞成的说法等都觉得不可靠,所以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过去接受的意见统统自主地怀疑一遍,以便把错误的意见统统从心里连根拔除。“我的打算只不过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地上从事建筑”〔9〕13。笛卡尔起初把自己关在暖房里自主地想,想来想去给自己定了3条准则。为了顺利完成自己的清扫工作,他从暖房里走出来跟人们交往,到处游历。整整9年,在世界各地转来转去,看热闹,仔细思考每一问题,特别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怀疑、可以弄错的地方。这样就把过去马马虎虎接受的错误一个个连根拔掉。他说他这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架势〔9〕12-23。“因为事实正好相反,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9〕23。这样看来,笛卡尔无非是想强调每一个人的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必要性,是想唤醒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体即“自由本体”去积极地思和做,不轻易放弃自己作为“实践主体”的资格。“自由本体”是指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而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都能以“我”自称,就像逻辑专名“这”作为所有个别词的代表可以指任何一个个别事物一样,所不同的是,“这”用来指认知的对象,“我”用来指实践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称作“实践主体”〔10〕。而这种思和做是我独立自主地思和做,不是别人强迫或代表我去思和做。众所周知,正是笛卡尔那自由的头脑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哲学思想,发明了那令人惊叹的解析几何。
三、自由是怎样的
“张三是自由的”,在这个实然判断中,“张三”是绝对主词,“自由”是相对谓词。说自由是相对谓词,是因为它也可以充当主词。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充当主词,自由也不例外。当自由充当主词时,自由和别的任何词一样都有两种谓词,一种是表示自由的“怎么样”的“属差”词,即自由的属性词,一种是表示自由的“是什么”的“种词”。比如在“自由是一种自因的状态”中,“自因的”是它的属差或属性,“状态”是它的种。这样一来,就把“自由”与“必然”区分开来了,因为“必然是一种他因的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例示,不断地为自由找出表示它的怎么样的属性词,比如我们可以说“自由是自主的”“自由是有选择的”“自由是有决定的”等等。“自由”除了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多的直接的属性谓词外,还具有无限多的间接的属性谓词,这些属性谓词通过述谓自由的直接的属性谓词来间接地述谓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属性谓词做主词时,也有用来述谓它的无限多的属性谓词,属性谓词又有属性谓词,等等,以至无穷。比如“自主是独立的”“自主是无干涉的”“选择是主动的”“选择是情愿的”“决定是由己的”“决定是无胁迫的”等等。在这里,属性谓词“独立的”“无干涉的”“主动的”“情愿的”“由己的”“无胁迫的”归给主词“自主”“选择”“决定”的意义同样是“怎么样”,表明自主具有独立性、无干涉性,选择具有主动性、情愿性,决定具有由己性、无胁迫性。它们做主词时又可以被在理论上无限多的属性谓词所述谓,这些属性谓词又可以被另一些在理论上无限多的属性谓词所述谓等等,以此类推,不一而足。显然,我的任务不是找全自由的各层级的属性谓词,而是为如何层层打开自由的属性谓词或为自由如何非空洞化或具体化做一个示范,刻画一个层层展开的自由的述谓结构。
通过分析自由的内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自由的内涵达到具体化。当我们说“张三是自由的”时,虽然自由的主词的外延达到了具体性,即主词是个别词或绝对主词。但谓词“自由”的内涵却是空洞的。所以,如果“张三是自由的”属实,那么“张三是自主的”“张三是可以选择的”“张三是可以决定的”等等也同样应该是属实的。如果“张三是自主的”属实,那么“张三是独立的”“张三是不被干涉的”等等也同样应该是属实的。如果“张三是可以选择的”属实,那么“张三是主动的”“张三是情愿的”等等也同样应该是属实的。如果“张三是可以决定的”属实,那么“张三是由己的”“张三是不被胁迫的”等等也同样应该是属实的。只有这样,自由的外延和内涵才达到了双重的具体性。
综上所述,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化创新的重阵——大学,就应该提倡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以及清华大学的前教师陈寅恪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精神〔11〕。中山大学的徐长福教授认为:“这两种精神是一颗种子的两瓣,相合于‘思想自由’或‘自由之思想’。依此,其联读的正确顺序应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把这四句话称为中国大学精神的‘四句教’”〔12〕。两位先生播下的大学精神的种子要开花结果,还需国人辛勤的耕耘和认真的守护。
四、自由与规范的关系
当然,本文所说的自由不是任意的、放纵的自由,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13〕的自由。下面简要地谈谈自由与规范的关系。一方面,自由是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法规的基石。关于这一点,康德有明确的说法,他认为自由是“道德的基石(foundationstones of morality)”〔14〕(括号中的英文摘自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by J.M.D.Meiklejohn,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York Street,Covent Garden,1947:292-293)。以赛亚·伯林对此有深刻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都是被决定的话,那么,某些居于人类思想核心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概念与词语的意义与用法,将不得不受到修改,甚或被根本改变。但事实上,现如今,人们还是在不厌其烦地使用着这些概念和词语。更有甚者,许多公开宣称这一学说的人却很少实践他们所鼓吹的学说;“实践常常欺骗信条,不管它表白得多么真诚”〔15〕11。而且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言行不一致的情况。“给予道德褒贬、对人的行为进行赞扬或谴责的习惯,就意味着在道德上他们对这些行为负责”〔15〕6。“如果我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是被决定的,他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行动(感受、思考、欲求与选择),那么我必须说,这样一种褒贬用在他身上是不适当的。如果决定论是对的,那么功绩与应得的概念,就像我们平常理解的那样,就没有用途”〔15〕9。另一方面,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作为“自由本体”就必须文责自负,即必须受到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和规制。总之,只有在先验的意义上承认自由是人的本性,经验世界的规范才有效。而经验规范则不断地佐证着先验自由的存在。
另外,本文这里讲的自由是学术探索方面的自由,它是独立自主之学术人格得以正常发育的基因或基石,这里所谈的学术自由或思想自由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教育有纪律”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社会时代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间并不矛盾,只要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那么就会呈现出自由实现学术的百花齐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达致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局面。
〔1〕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5.
〔4〕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1-60.
〔5〕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M〕.吴小坤,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35.
〔6〕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7〕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6-47.
〔8〕Xu Chang-fu.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 and Kang Youwei’s Predictions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J〕.Studies in Marxism,2011(12):118-119.
〔9〕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徐长福.实践主词、实践主体和自由本体:从“我”说起〔J〕.现代哲学,2010(4):24-32.
〔11〕陈俊伟.自由面面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9-104.
〔12〕徐长福.治学精神和办学精神不可分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4-08(3).
〔13〕孔子.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31.
〔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9.
〔15〕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M〕.胡传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