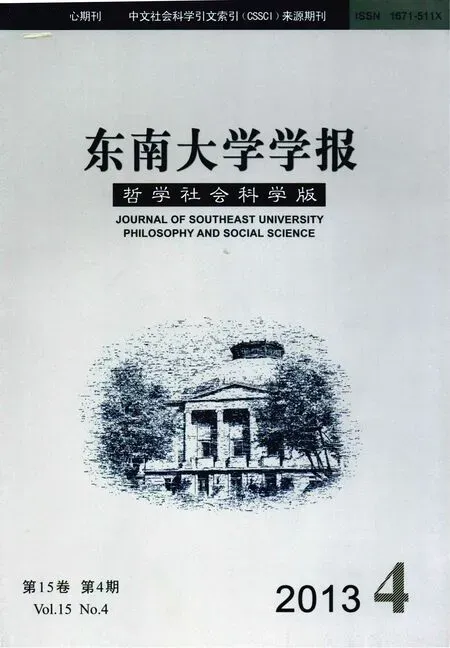《牡丹亭》在当代戏曲舞台
赵天为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但是任何一个剧本在搬上舞台的时候,都会因为时间、场地、时代、审美等等原因而面临二度创作,即便著名如《牡丹亭》也无法例外。作为案头文学来阅读,《牡丹亭》当然是无可挑剔的杰作,但作为舞台演出的“场上之曲”,《牡丹亭》却不免有其不足。许多人评说:此“案头之书”,非场上之曲。于是《牡丹亭》“欲付当场敷演,即欲不稍加窜改而不可得也”[1]2028。由是,《牡丹亭》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问世后不久,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改窜,自明而清而近现代,绵延未绝。在当代舞台上,原封不动地搬演《牡丹亭》,同样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个篇幅太长,许多文辞过雅,某些场次中科诨的俗恶,古代题材和现代生活的距离……然而剧作家们的改编热情并没有消退,雅部、花部、国内、海外,《牡丹亭》的身影在舞台上层现叠出,像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姹紫嫣红开遍。
国内当代戏曲舞台上的《牡丹亭》改编本迄今已有三十余部。其中昆剧改编本有:上海市戏曲学校苏雪安改编本(1957年),北京昆曲研习社华粹深改编本(1959年),郴州专区湘昆剧团余懋盛改编本(1962年),北方昆曲剧院时弢、傅雪漪改编本(1980年),上海昆剧团陆兼之、刘明今改编本(1982年),江苏省昆剧院胡忌改编本(1982年),江苏省昆剧院丁修询改编本(1986年),浙江昆剧团周世瑞、王奉梅整理本(1993年),上海昆剧团唐葆祥改编本(1994年),上海昆剧团方家骥改编本(1997年),上海昆剧团王仁杰改编本(1999年)、浙江京昆剧院谷兆申改编本(2000年),上海昆剧团王仁杰缩编本(2003年),苏州昆剧团白先勇青春版改编本(2004年),江苏省昆剧院张弘改编本(2004年)等。其他地方戏改编本有:粤剧《牡丹亭》,谭青霜改编本(1953-1957年间);粤剧《牡丹亭惊梦》,唐涤生改编本(1956年);赣剧弋阳腔《还魂记》,石凌鹤改编本(1957年);豫剧《牡丹亭》,张景恒改编本(1957年);北路梆子《牡丹亭》,项在瑜改编本(1961年);青海平弦戏《游园惊梦》,袁静波改编本(1962年);采茶戏(抚州采茶调)《还魂记》,张齐改编本(1982年);传奇清唱《还魂曲》,黄文锡改编本(1986年);华剧《风流梦》,朱学改编本(1993年);越剧《牡丹亭》,吕建华改编本(1995年);赣剧弋阳腔《还魂后记》,黄文锡改编本(1997年、2000年);黄梅戏《牡丹亭》,林青改编本(2002年);赣剧《牡丹亭》,曹路生改编本(2003年);小剧场越剧《牡丹亭》,刘平改编本(2004年)等。另有串演性质的北京皇家粮仓版《牡丹亭》(2007年)、南京多媒体版《牡丹亭》(2009年)、上海实景园林版《牡丹亭》(2010年),京昆合演版《牡丹亭》(2005年),坂东玉三郎版《牡丹亭》(2009年)等。海外上演的《牡丹亭》也非常丰富,最著名的莫如美籍华人陈士争执导的五十五出全本《牡丹亭》。一时间,整个世界都掀起了《牡丹亭》热,这与以前中国传统戏曲只在华人社区演出已不可同日而语。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当代舞台上的戏曲改编本加以考量,串演本和全本暂不涉及。
正如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改编者心中也都有自己的一本《牡丹亭》。改编者不同的理解与斧斫决定了《牡丹亭》不同的舞台面貌。本文试从主旨、情节、人物、语言、表演等方面探讨当代改编者对《牡丹亭》的不同解读,以期对当代戏曲舞台上的戏曲名著改编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主旨——突出对“情”的讴歌
《牡丹亭》的主旨是什么?上海昆剧团1999年本导演郭小男说:“汤氏只写了一个字:情。”[2]6改编者们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以歌颂“至情”作为改编的出发点和基石。近年风靡海内的青春版《牡丹亭》编剧之一白先勇认为:“改编是必要的,但改编要与汤显祖时代以‘情’颂为美的原则相一致,充分体现情深、情真、情致的主题。”因之,他所改编的上中下三本《牡丹亭》分别标作了“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
更多的改编者为了突出“情”的主题不约而同地删去了原作中反映宋金矛盾的李全一条线,以期浓缩精华、凸现主线。如北方昆曲剧院1980年本的编剧之一傅雪漪说:“整理时我们经过缜密思考,决定抓住‘情’与‘理’(封建礼法)斗争这个核心,……减去了不必要的头绪和‘姻缘之分’、‘功名之念’等封建迷信色彩,删去了可剪裁的毋关紧要以及迹近猥亵的词语。”[3]11新版赣剧本《牡丹亭》的编剧曹路生更把新版《牡丹亭》比作是赣剧的《人鬼情未了》,因此主要围绕“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这一脉络设计剧情,尽行删去了汤显祖原著中有关宋金战争、社会、民俗等其他内容。目前就笔者所知的国内三十余个改编本中,除了上海昆剧团1999年本和苏州昆剧团白先勇本这两个力图反映《牡丹亭》全貌的改编本外,其他改编本莫不如是。
上海昆剧团1999年本《牡丹亭》的编剧王仁杰却认为:“汤显祖是伟大的作家,百科全书式的,《牡丹亭》绝对不只是表现一对痴男女死去活来的爱情。”因此“全演才好,字字珠玑。”[4]10演全本《牡丹亭》,当然是最理想的,然而却不现实。美籍华人陈士争执导的五十五出全本《牡丹亭》,分为六集,剧长二十小时,用三个下午和三个晚上才能演完。这是五十五出《牡丹亭》首次在舞台上得到全本演出,其意义是重大的。然而,尽管该剧组还分别于1999年11月、2000年2月参加了巴黎艺术节和澳大利亚帕斯艺术节的演出,但终究属昙花一现。就近年国内上海昆剧团王仁杰改编本的演出情况来说,先是排演了连演三个下午和晚上的55出全本《牡丹亭》(未公演),后缩编为演出三个晚上共九个小时的35出上中下本《牡丹亭》(1999年公演),后又缩编为演出两个晚上六个小时的27出上下本《牡丹亭》(2003年公演)。这不能不说是出于现实的演出时间、观众需求等考虑而做出的修改了。
当然,除了“至情”,“《牡丹亭》里还写了另外的一些人和事,表现了汤氏对政治、社会、历史、宗教、世俗、战争等诸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这些内容构成了表达汤氏传奇理念的主客观环境,组合成戏剧开展的多条线索,对应出主要人物的终极目标。”[2]7那么,怎样选择才能准确而全面地传达原著的思想意蕴?总之,既要尊重原著,反映原著的意趣神色;又要面对观众,考虑观众的现实需求。《牡丹亭》无疑向改编者提出了高难度的课题。然从大部分改编者的选择来看,删去枝蔓,突出对“情”的讴歌还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因为只有删去了庞杂的事件与人物,突出主旨,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加鲜明有力地表达原作的基本精神,才能更清晰地凸显汤氏的思想精髓。
二、情节——切入与收煞的选择
汤显祖《牡丹亭》的情节,起于《言怀》,终于《圆驾》,然而纵观当代舞台上的《牡丹亭》改编本,除了上海昆剧团王仁杰缩编的上中下三本《牡丹亭》外,几乎没有遵循此例的。
大部分改编者选择了“训女”(包括“学堂”)或“游园”(包括“肃苑”)作为全剧的切入点。从“训女”切入者,无疑是在强调环境(“理”)对杜丽娘的束缚、压抑;从“游园”切入者当然是要突出自然(“情”)的美好,表现人物对自然的热爱。前者的色调是阴暗的;后者的色调是明丽的。学堂也好、花园也好,切入的目地都是要凸现人与环境的矛盾,凸现“情”与“理”的冲突,为下文杜丽娘对“情”的不懈追寻设下铺垫。事实证明,其效果都是好的。
全剧的收煞就不这么简单了。绝大多数当代的改编者们不约而同的舍弃了《圆驾》,选择了《回生》作为故事的结束,但回生及其后的情形又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顺利还魂
如上海昆剧团唐葆祥改编本《掘坟回生》:由花神幻化成尼姑和园子,试探柳梦梅的真情,帮助其开棺,与还魂复生的杜丽娘重圆。又如浙江京昆剧院谷兆申改编本《圆梦》:陈最良约柳生扫丽娘墓,促使丽娘还魂后一对有情人即晚拜堂成婚,最后由石姑姑陪着,驾一叶轻舟离开杜家故宅。而且让人物在水上行舟的动作中下场,以显出意境幽远、意在言外。
2.还魂受阻
有陈最良阻拦的,如石凌鹤改编的赣剧弋阳腔本《还魂记》第九场《花发还魂》:赖大奉观主命为柳梦梅挖坟,陈最良前来阻拦。但真正举起锄头时,陈最良却无了下文,不了了之。也有杜宝前来阻拦的,如黄文锡改编的传奇清唱本《还魂曲》第四乐章《还魂》:柳梦梅要开坟,杜宝阻拦,最终花神唤来了狂风怒啸,将杜宝卷下,丽娘得以还魂。更有强调柳梦梅的至情,加进了柳梦梅欲撞坟殉情的情节的,如上海昆剧团陆兼之、刘明今的改编本《回生梦圆》。还魂受阻说明了现实阻力的强大,虽然结尾有些草草,但还是引人思考,有一定的意义。
3.还魂迫认
杜丽娘回生了,但怎样解决与父亲的矛盾呢?苏雪安改编的昆剧本《硬拷迫认》是:杜母威胁杜宝,如不相认便要与女儿、女婿一道出走。杜宝只得同意。张齐改编的采茶戏本《硬拷闹喜》是:最后由花神逼杜宝允婚,杜、柳团圆。项在瑜改编的北路梆子本《牡丹亭》则是丽娘还魂后与柳梦梅结为夫妻,同拜杜宝,杜宝因丽娘自婚而贱之,不肯相认。丽娘气恼之下,随梦梅毅然而去。这里的杜丽娘更增加了果敢和坚强,原著中《回生》至《圆驾》所展示的杜丽娘重新为人后与现实的矛盾也提了出来。
4.还魂见柳
在林青改编的黄梅戏本《牡丹亭》中,杜丽娘是因“与柳梦梅犯有私情”,被阎王罚了三年女监,期满还魂后才来寻找柳梦梅的,二人相见时,她已是人而不是鬼了。因而删去了幽媾情节,二人携手牡丹亭,共忆梦境,被石道姑撞见,恰逢杜母、春香赶来祭奠,一家团圆。这种处理很少见,有独特处,但也有不足。杜丽娘的还魂靠的不是情的力量,而是阎王的恩赐,带有了宿命论色彩,反而削弱了杜丽娘对“情”不懈追求的精神。
关于《牡丹亭》之《圆驾》的结局,前人多有论及,或者斥为大团圆的俗套,或者认为这个矛盾依旧尖锐、团而不圆的结局安排正是汤显祖的过人之处。选择在《回生》收煞,改编者或认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惊梦》是个梦,《回生》也仍是梦,是人生大梦的结局,是爱情想望的完成。”[5]387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如夏写时先生认为《牡丹亭》当然歌颂了生死不渝的爱情,但更歌颂了执着追求的精神,而杜、柳“得到朝廷和父母的认可则是追求精神的胜利”,所以“《回生》后二十折之不可废”[6]41。平心而论,《回生》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圆驾》同样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但全本而外改编者们还是选择了前者,出于篇幅的考虑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相比而言,把《圆驾》的矛盾移到《回生》来展现,走“还魂受阻”或“还魂迫认”的路子,倒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人物——提升与典型化
作为第一主人公的杜丽娘,汤显祖强调了她对“情”生生死死的执着追求,历来的改编本也都抓住了这一点。但是,更多受到改编者关注并改动的人物是柳梦梅。
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是杜丽娘的梦中情人,但在杜丽娘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比较被动,比起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执着,他要逊色许多。因此许多人认为《牡丹亭》中的柳梦梅这一形象留有遗憾。明代冯梦龙就认为:“真容叫唤,一片血诚,一遇魂交,置之不问,生无解于薄情矣。”[1]2034所以改编者们不约而同地为其“补过”。不仅如此,当代的改编者们还由此深入,将柳梦梅的形象进行人格提升与典型化——削减他世俗的一面,强化他的浪漫、痴情、坚定与专一。具体的做法是:
其一,突出追求的执着。
汤显祖原本中,美妙迷离的“惊梦”,在杜丽娘是青春的渴望、生死的追寻,在柳梦梅则不过“梦短梦长俱是梦”(《言怀》)——虽然值得记忆,但也只是一“梦”而已。因而此后,柳梦梅仍然延续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到赵佗王台访友、去香山奥多宝寺干谒、赴京城应试,直至旅寄南安才有幸拾得春容、遇到杜丽娘鬼魂。这样的柳梦梅未免太俗气,当代改编者就此着手,将柳梦梅到南安的原因由求功名路过改为专去寻梦。如上海昆剧团陆兼之、刘明今改编本,增添了“访园”一节,写柳梦梅“访园不惮途程杳”,专门为寻找梦中所见的女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以致身染沉疴,最后才找到梅花观。吕建华改编的越剧本第三场,柳梦梅“读尽十年寒窗月,如今始觉梦中有真情,……今日是,大梦初醒离家去,游学四方觅知音”。于是他卖掉果园,携跎孙而去。又上海昆剧团方家骥改编本,柳梦梅离家的初衷是游学,而途中一梦使他“常挂在心”,因而改变了主意,转而去寻“梦中去处”了。
其二,强调感情的专一。
汤显祖原本中的柳梦梅,旅寄南安与丽娘相见,“并未认出是画中人,便欣然接受这位午夜來访的陌生女子,一度春风之后还盼她每晚都来。这种表现,有损题旨,也破坏了柳生的形象。”[5]384较之杜丽娘的至情至性,柳梦梅未免显得轻浮和寡情。当代的改编者几乎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通过情节的衔接,将梦中人、画中人、眼前人统一起来提升柳梦梅的形象。江苏昆剧院张弘先生的改编本最为突出,充分利用了柳梦梅与杜丽娘相对应的几个情节,以“柳梦梅三会梦中人”为线索,通过梦会(对应“惊梦”)、画会(对应“写真”)、幽会(即“幽媾”)的层层渲染,将梦中人、画中人、眼前人勾连起来,针线细密。特别在《幽媾》中,柳梦梅见到丽娘之魂,惊呼:“画中人、梦中人、眼前人,岂不就是我柳梦梅心中之人呵!”这样处理,突出了柳梦梅对情的专一。
至此,经由梦会、画会、幽会,一个浪漫多情的书生、一个至诚可爱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原来那个并不怎么可爱的柳梦梅,在当代舞台上已是一个被赞作“义深情奇”的形象了。
《牡丹亭》中另一个改动较多的人物是杜宝。原著中的杜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有他的正统和顽固,也有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人之常情。章诒和先生认为:“当观众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有疼爱之心的父亲,阻碍着女儿走向幸福的道路,也就更加理解了这个悲剧产生的社会思想根由:不是肤浅地痛恨一个美满婚姻的破坏者,而是能够认识批判杜丽娘所处的环境,即那个令人窒息的可怕社会。”[7]18然而,许多的改编本中,杜宝是作为阻止丽娘还魂、反对柳、杜婚姻的反动势力出现的,如吕建华改编的越剧本《牡丹亭》、项在瑜改编的北路梆子本《牡丹亭》等。有的改编本甚至将杜宝进一步极端化,改造成了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典型,如黄文锡改编的传奇清唱本《还魂曲》。朱学改编的华剧本《风流梦》则不但强化了杜、柳和封建卫道士杜宝的冲突,而且增加了杜宝把丽娘许与“两淮节度王大人的公子”并严厉逼嫁的情节。其实,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8]387,而非哪个具体人物的阻挠破坏。杜丽娘是那个压抑人性的时代的对立者,她所要反抗的“理”不是某一简单行动就可以代表得了的。改编本的这些改动,不仅将杜宝的形象简单化了,而且缩小了杜丽娘和《牡丹亭》的丰富意蕴,落入了一般言情剧的俗套,不如原著感动人心。正如夏写时先生所说:“双方的‘立场’鲜明了,冲突尖锐了,但无视人物间的规定关系,背离生活逻辑,以人所共知的斗争公式,代替原著中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是否为种种据名著改编之作无法如原著般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呢?”[6]47——值得思考。
四、语言——通俗化与现代化
《牡丹亭》的语言是典雅的,这是它的特点,但对普通观众来说,理解起来又有一定难度,这又是它的不足。清代李渔曾指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9]48所以如果不愿意把这样经典的戏曲锁进历史博物馆,就必须将曲词、宾白改深从浅,使之通俗化,让现代普通观众们接受。
对语言的处理上,昆剧改编本更尊重原著,大部分改编者对词句只缩不改,保持了剧作的原有风貌。地方戏的改编,则更为通俗一些,但也注意了保持原著的意趣。赣剧弋阳腔本《还魂记》的改编者石凌鹤是这样把握的:“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尽可能改译得比较通俗一些。”有的地方“虽然换了曲牌,并因乐曲规定而改动了不易理解的若干词句,但没有改变原词句的本色,藉以存真。”[10]8以《惊梦》中的【步步娇】“袅晴丝”为例,石凌鹤改作【桂枝香】:“妩媚春光、吹进深闺庭院,袅娜柔如线。理秀发、整花钿,才对着菱化偷窥半面,斜梳发髻恰似彩云偏;小步出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只是将原词稍作布局和浅释,通俗而不失原作意趣,被认为“达到雅俗共赏”,较为成功。
当然,通俗化也有个“度”,王季思先生认为这个界限即“尽可能的少用现代汉语,避免把古人现代化,而要适当采用宋元话本、元人杂剧中的白话,改写那些骈四俪六的宾白,灵活的运用传统诗词散曲的句法,改写唱词中有些过于艰深的句子。即既要改深从浅,又要保持古代那些有文化修养的人物的优雅风格”[11]。
而新版赣剧《牡丹亭》的舞台呈现中(非文本),台词也融进了许多时髦的现代语汇。如《拾画》一场,石道姑见到英俊的柳梦梅时,惊呼:他真是“帅呆了,酷毙了”。当被陈最良拖着下场时,石道姑还冲着柳梦梅“Good-bye”,并不断地抛出飞吻。这样的安排,轻松搞笑的效果是有的,但石道姑也变成了“跨时代”的小丑,失去了原作的意趣,显得不伦不类。倒是《幽媾》中,地府里的黑白无常与牛头马面一起来捉拿杜丽娘时所说“得饶鬼处且饶鬼”,还有“让天下有情鬼终成眷属”等词句,相比之下更幽默、恰切些。
五、表演——花神歌舞的运用
《牡丹亭》的表演是日益丰富起来的,最突出的是花神。
在汤显祖原本中,花神是作为杜丽娘“情”的见证而出现的。一次是“惊梦”时,花神上场,“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一次是“冥判”时,为丽娘证明“慕色而亡”的因由。但剧中的花神只有一个,且是男性的“末扮”,“束发冠,红衣插花上”。他上场后,念引子,唱一段【鲍老催】,然后抛下花片惊醒杜、柳,就离开了。至乾隆年间,台本演出已增至十二月花神,另有“末”扮大花神和闰月花神。众花神“依次一对徐徐并上”,合唱【出队子】、【画眉序】、【滴溜子】诸曲,大花神唱【鲍老催】、【五般宜】两曲。花神歌舞的增加,渲染了故事情节的浪漫主义色彩,凭添了舞台表演的变化形式,在一出生、旦的对戏中,加入了群舞、合唱的热闹场面,冷热相剂,感官效果上较原本增色许多。
当代的许多《牡丹亭》改编本中都充分发挥了花神在剧中的作用,收到了不同的效果。
如上海昆剧院唐葆祥改编本,在《游园惊梦》前加写了《花神巡游》一场,叙生前相爱的花公花婆,受天帝敕封为护花之神,催开南安府后花园凋零的百花。在最后一场《掘坟回生》中,花公花婆又幻化成尼姑和园子,试探柳梦梅的真情,帮助他开棺,与还魂复生的杜丽娘团圆。这里的花神不但是杜丽娘“情”的见证者,而且是其维护者、帮助者。另如黄文锡改编的传奇清唱本《还魂曲》中,花神唤来了狂风怒啸,将杜宝卷下,使丽娘得以还魂。张齐改编的采茶戏本《还魂记》中,花神逼杜宝允婚,使杜、柳团圆,都属此类。
在吕建华改编的越剧本和林青改编的黄梅戏本中,花神还以歌舞的形式担起了诠释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如黄梅戏改编本:杜丽娘游园入梦时,众花神翩翩起舞,引柳梦梅上场;杜丽娘“写真”时,花神在一旁伴唱;杜丽娘伤情而亡时,哀乐声阵阵传来,花神托举着身着白色衣裙的杜丽娘缓缓走来,其余花神悲伤伴舞、伴唱。这一改编本中花神歌舞贯穿始终,不仅诠释主题、渲染气氛,而且帮助叙事和抒情,最大可能地运用了黄梅的载歌载舞,视觉效果很好。与原作相比,花神歌舞的成分、作用显然已大大增加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牡丹亭》原本中的花神在当代已发生了性别的转化——由“末”扮的男性花神变成了女性的花神花仙。在唐葆祥的上昆本中,还有一个男性的“花公”,而到了石凌鹤改译的赣剧本中,便已在出场人物中特意注出:“大花神(女性,年可二十左右)、众花神(均为妙龄女郎)”。表演的氛围当然也与原本大有差异了。张庚先生曾回忆说:“《牡丹亭》过去的演出,大花神是由男角担任,副末扮,当杜丽娘和柳梦梅两情欢好时,花神在严肃的歌唱。场面处理得庄严。记得我从前看《牡丹亭》,看到这里便感到气氛肃然,感受到汤显祖那‘人情即天理’的精神力量。”[12]45当代的改编本用女性花神,则更侧重于对“情”的美好的歌颂和渲染。如越剧改编本中于开场、游园、惊梦、回生等几处反复出现的花神花仙的载歌载舞。更如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花神由三位男神和十二位女神组成,并特意请著名编舞家吴素君为《牡丹亭》编排了三段花神的舞蹈。在三段舞蹈中,还别出心裁的设计了大花神手中飘扬的长幡:“惊梦”中的幡为绿色,表现纯洁的男女之爱;“离魂”中的幡为白色,表现伊人逝去的伤痛;“回生”中的幡为红色,表现还魂团圆的喜悦。三种颜色的幡配合舞蹈,形象地传达出剧中的情景和气氛。
对于戏曲中的歌舞形式,是有不同看法的。或认为:“大量的新编舞蹈取代了传统的戏曲程式,使戏曲看起来更像是歌舞剧。”“中国戏曲独特的美学精神被‘解构’了。”或认为:“戏曲艺术在观念上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演剧方式。”[13]41这无疑要牵扯到戏曲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其实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段话说得非常好:“至于传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9]136。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在《生活与美学》中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为那一代而存在……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戏曲当然要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更何况戏曲所属的俗文学其特质就是:大众的、新鲜的、想象力奔放的、勇于引进新的东西的。[14]3
当然,“新”也要有度,李渔将之界定为“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具体说来,“曲文与大段关目不可改”,“科诨与细微说白不可不变”[9]142。所谓“改编”,当然会包括两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思想内容的创新,二是艺术形式的变革。将古典戏曲搬上舞台,当代的改编者们都力争做到“好看好听”,既要留住老观众,又要争取年轻的新观众,添加进一些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青春版《牡丹亭》策划者白先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台湾万象”采访时这样诠释他们对与古典与现代的把握:“我们是按照正宗、正派、正统的演做方法。可以这么说,我们尊敬、遵从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对此,香港的王堂纯先生提出了“新旧并行”的改革思想,并推崇一位专家陈守仁的观点:“我们自不能希望所有年轻人具有耐性欣赏戏曲,但青年人也总会有成熟及有耐性的一天,革新性的尝试当然值得鼓励,但应以传统戏曲音乐并进,而非以前者取代后者。”[15]13——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冯梦龙.风流梦小引[M]//冯梦龙全集·墨憨斋定本传奇: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郭小男.挚情与梦幻[J].上海戏剧,1999(10).
[3]傅雪漪.意、趣、神、色——整理《牡丹亭》浅识,兼谈臧晋叔改编本[J].戏剧学习,1982(2).
[4]感受《牡丹亭》[J].上海戏剧,1999(10).
[5]谷兆申.情系生死说牡丹——昆剧《牡丹亭》上下本改编说明[M]//古苍梧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夏写时.谈《牡丹亭》的改编问题[J].戏剧艺术,1983(1).
[7]赏心乐事《牡丹亭》[J].中国戏剧,2000(1).
[8]徐朔方.论《牡丹亭》[M]//徐朔方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9]李渔.闲情偶寄[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0]石凌鹤.关于《临川四梦》的改译[M].汤显祖剧作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1]王季思.从《牡丹亭》的改编演出看昆剧的前途[J].光明日报,1982-6-28.
[12]张庚.和上昆同志谈《牡丹亭》[J].戏剧报,1983(1).
[13]陈世雄.当代戏曲舞台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J].中国戏剧,2004(3).
[1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5]王堂纯.从新版《牡丹亭》谈昆剧改革[J].上海戏剧,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