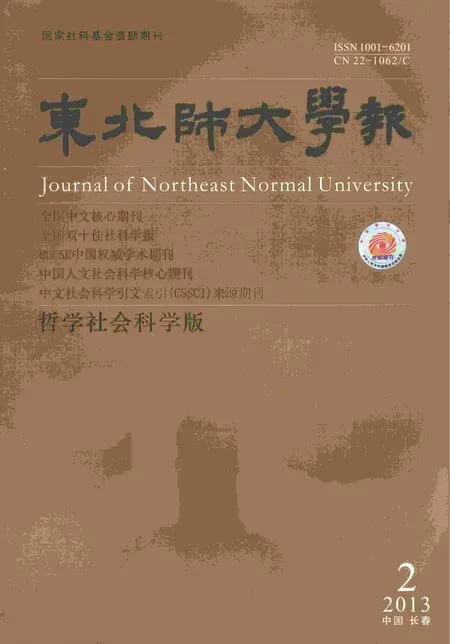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
罗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24)
康熙朝争储及雍正帝得位相关史事,雍乾时敕纂的《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大清会典》等史籍,都做了精心删改,甚至连原始档案都做了选择性销毁①如胤祯任抚远大将军期间的奏折。。因此,现存清朝文献,很难揭示康雍时期争储和皇权授受的真相,雍正继位问题成为疑案。但翻检朝鲜汉文史料,会发现许多被清朝文献缺省、掩盖甚至有意回避的记载。
李氏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确立后,每年有派往清朝的三节年贡使及因事派遣的庆贺使、陈慰使、陈奏使、赍咨使、谢恩使等等。这些使节留下了《燕行录》、《别单》、《闻见录》、《手本》等主要以汉字记录的丰富文献,本文拟就其有关康熙晚期争储及其雍正初年政治影响的记述为核心,考察和评价这些文献的价值和可信度。
一、朝鲜使臣记述的文献类型和来源
明清时期,李氏朝鲜使臣出使北京(或南京)的见闻录,由书状官记录并上呈朝鲜国王,由此形成了《朝天录》和《燕行录》[1]。林基中教授编辑的100卷的《燕行录全集》[2]将高丽、李朝使臣出使元明清三朝的使行纪录,统称为“燕行录”,为目前搜集最全的朝鲜使臣使行纪录汇编。本文所引诸《燕行录》,皆以此版本为依据。
朝鲜使臣回国后所提交文书,除《燕行录》外,还有使臣别单、闻见录及译官手本等三种。此三种文书,不见于《燕行录》,而见于《同文汇考》。《同文汇考》的编纂始于朝鲜正祖八年(1784),由礼曹判书郑昌顺等主纂,于十一年完成(1787)。其后续有增补,收录文件至高宗十八年(1881)。该书初纂分为原编、别编、补编三类,续纂仍按此分类补入,名为“原续编”、“补续编”、“附续编”、“原编续”、“附编续”。收录于该书补编卷一至卷六的《使臣别单》(包括《闻见录》、《译官手本》),尤为珍贵。该书原线装96册,台北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80年按原大影印,精装30册,是目前便于使用的较好版本。
综上所述,作为清代朝鲜使臣往来的副产品,形成了一个由《燕行录》和《使臣别单》构成的文献体系。另外,《承政院日记》[3]的相关记载构成此文献体系的补充。朝鲜使者回国后,要接受国王的召见,在书面报告外,还要口头汇报出使见闻。口头汇报及相关的君臣对话,反映了朝鲜方面对相关事件的认识、立场,有助于判断相关记载形成的动机。
这个文献系统所记述的史事来源,大致有闻见、访谈、邸报(塘报)、清廷文书等。除存在某些传闻讹误、译舌致误、传抄误写外,所记史事可信度颇高。
二、二废太子中的得麟案
得麟,为《清圣祖实录》官定汉字译名,《钦定八旗通志》称“德麟”,朝鲜文献称“德琳”,《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则译为“德林”。
该案,《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九月甲戌记载云:
先是随从二阿哥允礽之得麟,为人狂妄,奉旨锁禁在家。因伊父阿哈占补授福陵关防时,奏请将得麟带往奉天。既而得麟之叔佛保奏得麟怙恶不悛,请交奉天将军正法,上命交伊父阿哈占将得麟处死。伊父阿哈占及伊子白通诡称得麟自缢身死,潜踪逃匿。上察知其诈,遣刑部员外郎纳齐喀等至山东胶州,拿获得麟,付法司会勘。至是,刑部等衙门覆奏:“得麟系屡犯重罪,奉旨处死之人,乃擅行悖旨,假死逃匿,情罪可恶,应照大逆律,将得麟凌迟处死。其父阿哈占虽已身故,应开棺戮尸。得麟之子白通,拟绞监候。其逃匿地方文武官,失于觉察,应行令该抚查参议处。”从之。
得麟获罪的具体缘由,《实录》并无交代,只是笼称之为“狂妄”、“怙恶不悛”。
康熙朝的满文奏折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得麟案。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025折附康熙帝给步军统领隆科多密谕,内云:
盛京佛保之兄阿哈占之子德林行止不端,狂妄恶劣,曾谕交其父兄正法。兹据风闻,虽谓自缢死,但空棺殡烧。德林(得麟)自海上来至天津、登州等地,现不知其往南省或在何处。对此消息,舆论哗然,皇太子亦闻其大概,告知于朕。此事著尔尽力密访,若系在京,即执之奏来。似此两面欺罔之人,惟恐漏网。[4]1616
该密谕不具日期,杨珍认为“写于康熙五十年秋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不久,五十一年十月第二次废太子之前。”[5]进一步证以其他文献,可以确定该密谕下于五十一年六月。
该密谕里称“风闻”,未交代“风闻”于何处。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5186、5187折系盛京将军唐保住奏报缉拿得麟的奏折,无具奏日期,折内称“奴才于四月二十日到”[6]下255。其前任嵩祝于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二日调礼部尚书[7]卷248,则唐保住接任之命当下于此日期前后①《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甲寅载:“赐盛京将军唐保住、宁古塔将军觉罗孟俄洛、黑龙江将军宗室杨福,银各一千两。”,则该折所称到任日期当属康熙五十一年。唐保住到任后,即探明阿哈占诡称处死得麟实情,并称得麟去向不明,有说乘船渡海者,有说已去苏州者[6]下2557。查《钦定八旗通志》,该书卷169《赛喀纳传附子纳齐喀》云:“(康熙)五十二年,(纳齐喀)迁本(刑部)部员外郎。时皇太子允礽护卫德麟获罪,其父阿哈占任福陵总管,上命其自行拘禁,德麟诈自缢死,潜逃窜,奉天将军瑭保住以奏。上命选才干司员访缉,纳齐喀同主事舒琳往胶州捕获之。德麟伏诛,纳齐喀议叙即升。”据此可以确证,康熙帝给隆科多的密谕下于唐保住密奏之后。换言之,康熙帝密谕下于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至九月热河避暑、秋狝期间。而据上引4025号隆科多奏折,则此密谕约下于六月间。得麟原是允礽护卫。而其得以脱逃,正出自允礽授意[7]卷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丑。杨珍认为调查得麟事件是康熙帝“下决心彻底解决太子问题的一个先行步骤”[5]。
总结以上清朝文献记载可知,得麟系皇太子允礽护卫,因“狂妄”交其父阿哈占锁禁于家,后阿哈占出任福陵总管,奏请带往盛京。复因“怙恶不悛”,康熙帝令阿哈占将其正法。而阿哈占与得麟子白通遵允礽授意,纵得麟出逃,而诈称自缢身死。康熙帝侦得实情,于山东胶州捕获得麟,五十二年九月将其凌迟处死。
但是清朝文献没有交代得麟获罪的具体原因。得麟案发后,正值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团赴北京。回到汉城后,正使临昌君李焜、副使左参赞权尚游于别单中记述得麟案始末[8]补编卷3使臣别单三,V11P618-619,不仅与清朝官方记载一致,而且指出得麟得罪的直接原因乃是依仗皇太子威势为其私贸人参,不仅获罪前如此,而且至沈阳后仍依然如故。因此处死得麟、惩其家人,就等于断了允礽的关键财路,成为康熙帝二废太子的重要措施。
三、雍正帝继位的矛盾记述
朝鲜《景宗大王实录》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记载是中国国内史学界熟知的。该《实录》卷10景宗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卯)记载了清朝敕使额真那、吴尔泰至汉城传宣康熙帝遗诏的过程及遗诏全文。经国内学者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遗诏原件比对,除个别字词差异外,内容完全一致[9]91。该《实录》次日又记远接使金演以闻于“译舌”者言于户曹判书李台佐,涉及雍正继位的诸多细节[10]V41P271。
细节之一是康熙帝病重时遗言必封胤禛第二子为太子的说法,与乾隆时所修《清世宗实录》里因爱皇孙弘历而传位四子胤禛的说法一致。而对皇长子、废太子的处置,与雍正年间的情形也基本相同①。胤禛于御榻前亲承末命的细节,在雍正十年(1732)成书的《大清会典》里也有记载[11]6402-6403。但马齐受遗命、康熙帝授念珠和嘱托胤禛遗言的细节,俱未见于清朝文献记载。饶有兴味的是,远接使转述“译舌”的话中提到“新皇累次让位”,而僻居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的童生范世杰竟杜撰三兄遵父命让位于弟、弟三揖三让始即位的说法,做阅读《大义觉迷录》的心得,以为“颂圣”之词投呈学政,企图侥幸上进[12]。
那么,与雍正《大清会典》同年(1732)成书的《景宗大王实录》所记载的康雍大位授受的细节,该如何理解呢?
冯尔康认为马齐受诏是译员的私人看法,不代表官方,又是孤证,且不排除编造卖钱的可能,难以据信;即位时谦让绝无可能,“汀州传说”“有着民俗的社会色彩”,无根据;授念珠一事也不可信,大约是雍正帝手下人欲取媚于他的说法,但喜爱弘历一事可信,对于雍正继位的影响而言,可以解释为“因喜欢孙子而坚定选择儿子为继嗣的决心”[9]131-132,97-101。
译员(译舌)的话,假定没有转述的错误与曲解,那么至少可以理解为译员个人的看法,也可将译员如此说法的意图理解为取媚他的主子。既然是取媚,其中又涉及当时活着的大臣马齐,那么译员也就不能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下文将要引用的李混、李万选《别单》,曾提到马齐与隆科多、十二王(贝子允裪,雍正帝即位后封为履郡王)相与谋议拥立雍正帝的事情。当时臣庶无法得知雍正帝受诏继位的实际情形,马齐既然参与了拥立,那么称他“奉诏”就是合情合理的说法。当然也不排除雍正帝嘱意如此放话。另外,谦让之说不尽是无根据的“民俗”。众所周知,雍正帝曾屡屡宣称从无冀望皇位之心,只是因为自己的大德大能获得了皇父的默认才在猝然之间被推上了无上的宝座,正应了传统圣君的理想。所以“谦让”之说,不仅是“民俗”,更是传统政治文化“圣君”的应有之义。清代民间有种传说,认为乾隆帝的位子也是抢来的,所谓因喜欢孙子而选择儿子为继嗣的说法也就被怀疑为乾隆帝的杜撰。但现在有了朝鲜人的记载,可以知道乾隆帝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爱孙而立子之说。既然这个说法在雍正继位之初就存在,且为敕使所传宣,而雍正帝为自己得位合法性辩护的上谕中又从未提到,那么做如此的推测或许更加顺理成章:雍正继位之初即已默定弘历为继承人且为近侍所知晓。总的来看,把译员之言看作雍正帝拥护者的言论大致是不错的。
在清朝派遣敕使到朝鲜告讣之前的十月二十七日,朝鲜派出了以全成君李混为正使、左参赞李万选为副使的“谢恩陈奏兼三节年贡行”使团[8]V12P974,补编卷7使行录。该使团约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左右到达北京②,雍正元年(朝鲜景宗 三年)四月初二日回到汉城复命[10]V41P287,《景宗大王实录》卷12,三年四月辛亥初二。在回国后提交的《别单》里,李混、李万选记录了关于康雍之际皇位转移的所见所闻[8]V12P640-642,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
该《别单》所记康雍授受之际事情与清朝文献多合,但有三事不见于现存清朝文献。
第一,七旬庆诏颁发之事,到目前为止,笔者于清朝文献中未找到记载。但以康熙六旬庆典例之,即使没有所谓书面的“庆诏”,而七旬庆典
① 雍正帝即位后,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封废皇太子允礽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允礽卒,追封为和硕理亲王。
② 此日期据康熙五十二年三节年贡行使团出发抵达日期估算。该使团发于十一月初三日,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达北京,见金昌业(清代汉文文献作“金昌集”)《燕行日记·往来总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1卷第297页。于此时当已进入筹备程序①查《清圣祖实录》,礼部首请庆六旬在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庚午(十九日),康熙帝未允。十一月己亥(二十日),王大臣公奏合请,仍不允。不允者,显康熙帝之“谦德”,而庆典的实际准备工作已经展开,不然无法解释五十二年的盛大的万寿庆典了。又“庆诏”系朝鲜汉语词汇,指吉庆诏书,如捷报、皇子出生、圣寿等,如明天启五年十月皇第三子生,颁诏朝鲜,该诏书被称为“庆诏”,见《仁祖大王实录》卷13,四年(天启六年)六月甲申(十三日)、己丑(十八日),《朝鲜王朝实录》第34卷第106、109页。据此,则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所颁通免地丁钱粮的诏书(见《万寿盛典初集》卷1),亦属于“庆诏”的范畴。。
第二,康熙帝逝世当日早朝及早朝间昏迷、大学士王掞问病请旨事,清朝文献中亦未见记载。王掞在朝鲜正祖八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成了同承顾命的阁老。朴趾源还记录说:王掞“误认禛字为祯字,第四为十四。惔(掞)被罪,而允祯为逆魁,改祯为禵。”[2]V55P260,《热河日记》卷23《铜兰涉笔》朴趾源此说,也不见于清朝文献的记载,当来源于乾隆四十五年他在热河所听到的传说。这一传说与58年前李混、李万选使团的所见所闻又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殆朴趾源揉合李混、李万选《别单》的记载与清朝传说之所致②从雍正七年九月颁行的《大义觉迷录》可知,当时流传一种雍正帝篡改康熙帝遗诏的传说,称添改“十四”为“于四”。。而考诸王掞在康熙末年屡言立储之事,则其跪问国事何如的说法,盖即当时舆论对其言立储的一种附会。
第三,十五日,马齐、隆科多与十二王等谋议,称有遗诏,拥立新君后始为举哀的情节,清朝文献未见记载。
考《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十四日)条记载,该日任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但是,再查《上谕内阁》,则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任命是在十五日,而非十四日[13]V6P7下。虽然《上谕内阁》并非第一手的原始档案,内中亦免不了改窜,但其成书早于《世宗实录》③《上谕内阁》初刻于雍正九年,收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至雍正七年末的上谕。剩余部分在乾隆初续纂刊刻,于乾隆六年成书。《世宗实录》于同年十二月告成。,对照两书的相关记录,则仍可以看出改窜的痕迹。可以肯定,将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任命事由十五日提前到十四日,乃是《世宗实录》纂修大臣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有意改窜,而改窜的目的则不外乎掩盖康雍之际帝位授受的真相。也就是说,在十四日,胤禛继位之事尚有待于诸王大臣的确认。再者,隆科多在康雍之际帝位授受中的地位已经明确,那么从马齐、允裪在此前后地位的变化也可以证明他们在雍正帝即位一事中必有“功绩”。根据这条《别单》提供的线索,再细检清朝留下的文献资料,可以对雍正帝继位疑案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雍正元年正月,因康熙帝逝世,朝鲜派出“陈慰兼进香行”使团。该使团正使李枋、副使金始焕回国后所提交别单[8]V12P643,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对康雍之际事情记载的日期比李混、李万选别单的记载都早一日。为何会出现早一日的现象,或是使臣听闻的错误,或是出于当时清廷有意的宣传,不能确知。但有一点两份别单是一致的,那就是“诸王各大人俟议定储君后举哀”,或者说,在康熙帝逝世后不久直到雍正改元后,两个朝鲜使团所听闻的雍正继位情形都是经王大臣议定储君后始为举哀。
再次,李枋、金始焕别单所记康熙帝传位遗诏内容与清朝传讣敕使所宣遗诏一致,也与清朝其他文献记载一致,有核对后者的意味。
另外,李混、李万选别单提到,鉴于继位的情形,当时人即有“秘不发丧”、“矫诏袭位”的议论。这一记载,比雍正七年《大义觉迷录》提到的矫诏传言要早近七年。这一点值得注意。《大义觉迷录》所载上谕,提出了康熙帝召见七位皇子宣布传位遗命的事,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出此说呢?冯尔康先生认为,这并不是出于弥补篡夺皇位的谎言,而是出于针对曾静(张熙)投书案供词中谋父篡位言论所做的说明[9]90。但是,据李混、李万选别单的记载,“矫诏篡位”的传言在雍正帝即位不久就已出现,那么雍正帝当时为何不加以说明呢?是因为没有合适机缘?还是因为以不同的方式做过说明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混、李万选别单还记载了使臣认为可以构成“矫诏袭位”证据的康熙帝第十四子胤祯(允禵)的事迹。这些事迹的记述,与清朝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但有数点仍值得注意:
第一,“赐玉玺”之说未见于清朝文献,可能属于对“抚远大将军印信”的误听误解。
第二,康熙帝染病之初密召胤祯,不见于清朝文献。从当时机密文书传递速度及允禵闻讣后的反应看,当属不可能。但是,仔细分析清朝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别单中“矫诏”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雍正帝曾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令允禵等回京。上文已指出,指定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是十五日的事情,则将召回允禵的谕旨系在十四日并下于“总理事务王大臣”,要么是改窜了日期,要么是改窜了内容。又据满文奏折、传教士书信及《永宪录》等文献记载的印证,可以肯定,雍正帝召回允禵之旨利用“廷寄密旨”的形式假借了康熙帝的名义,属于“矫诏”无疑[14]。
四、雍正帝位的合法性危机
李枋、金始焕别单详细记载了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大渐”到雍正元年三月间与雍正帝继位、康熙帝葬礼、雍正帝即位后所面临政治局势的各项事宜。大部分的资料,当来源于当时的邸抄,而且大部分内容与《清世宗实录》、《上谕内阁》所载相符。其中监察御史柴谦所上谏雍正帝“六失”疏[8]V12P656-658,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到目前为止,未在清朝文献找到原文。该疏所透露的雍正继位之初所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信息,饶有兴味。据疏中“历观两月”之语,则此疏上于雍正元年正月中或二月初。柴谦,字南屏,杭州人,为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疏合请举行东宫典礼八御史之一[15]。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坐“不端”同当年公疏署名的吴镐、邵璿两御史被罚充军[13]V1P48第133谕。后于雍正帝四年七月获赦,放归原籍[16]卷46,雍正四年七月癸巳。此疏是否确为柴谦所撰,笔者未找到直接证据。但柴谦“不端”罪名的确切内容既然需要隐去,那么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不利于尊者颜面的情节。
雍正元年八月,为吊慰仁寿皇太后崩逝,朝鲜派出礼曹判书吴命峻为主使、户曹参判洪重禹为副使的“陈慰兼进香行”使团。使臣在北京“又得见皇帝传谕诸王大臣等说话誊本”[2]V37P282,黄晸:《癸卯燕行录》。这份“说话誊本”记录在吴命峻、洪重禹的别单里:
九月二十八日,皇帝御午门,传诸王满汉大臣并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面谕:“朕自登极以来,览阅各部奏本,都写得好。只有工部廉亲王八阿哥总理,其奏本抄写甚是不好。贴补涂注甚多,轻忽不敬如此。当初圣祖仁皇帝未殡天之日,诸王大臣都保举八阿哥可承大统。大学士马齐亦保举八阿哥君临天下。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仁皇帝龙驭上宾,将大统托付朕躬,你们俱不心服,道我暗窃大宝。我若将你们诸王议处,又恐伤手足,必定坏我名声。我想诸王阿哥们原系妃嫔所出,朕亦是妃嫔所生之子。朕自登极以来,有说不尽苦楚。每日无一刻安时,都不如我在旧王府时,娇妻美妾,并为(未)拘束。朕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并无一日快活,吃的未有好东西,穿的并无好衣服。我想起来,做皇帝有甚好处!如八阿哥要做皇帝,我情愿让做他,何如?”诸王大臣俱叩头谢罪。又谕马齐等云:“你们若能劝与诸王敦伦和睦,使我兄弟各无猜嫌,共理大事,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必欣悦矣。”诸王大臣又谢罪而出。[8]V12P663-664,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
除宣布律典、受俘外,明清无皇帝“御午门”颁布诏谕之礼。但该别单所记谕旨内容却并非杜撰。相似的内容在后来公布的雍正帝上谕中赫然醒目。如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切责允禩的上谕里说:“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有足取重之处,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为君非易事,若只图一身逸乐,亦复何难。”[13]V1册P70这段文字与别单所记谕旨后段意思基本一致。查《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学士等“复请宗人府议处廉亲王等一疏,上曰:‘允禩着从宽免其永停亲王俸米,余依议。’”十月十一日,又复议“吏部所议奏本字画草率,应将廉亲王等罚俸一疏”,雍 正帝做相同指示[17]V1P106、115。可见别 单 里记载雍正帝责备允禩“奏本抄写甚是不好”并非无据。
可以说,以上“别单”中不完全见于清朝文献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从中可以看到雍正初年雍正帝皇位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斗争。
五、雍正帝的迷信与内心紧张
雍正六年五月,朝鲜以“缉扑逆党”移咨清廷,遣“赍咨行”使团赴北京[8]V12P979,补编卷7使行录[16]卷74,雍正六年十月庚子。此 行 宪书赍咨官卞昌和手本记载了一份得自序班金超的“圆明宫说话”,内有一段雍正君臣对话和一首谶语:
[A]皇上云:“荒熟乃天道循环,非朕之福。实由圣祖余荫,所以朕耿耿留心,唯恐不如圣祖政令,常自日夜思维,兢兢不忘。想先帝欲图久远,见《推背图》云‘胡人二八秋’,即行批仙,求大仙明示何谓‘胡人二八秋’,朕当重修庙宇?仙批云:‘不用修来不用修,谁识胡人二八秋。红花落尽黄花发,五月干戈八月休。’先帝欲明此语,终不能明,一惟从宽省刑薄税,从天听命。所以刑部每停秋决,广膳(善)库设法借俸。有官弁家贫不力者,预借俸银,三五年扣除清完。即如康熙六十一年间借俸三年,扣至康熙六十四年扣完。谁知六十一年一朝驾崩,何能至于六十四年!朕每见扣除俸银册内有扣至六十四年者,未尝不涕泣三四也。今朕效先帝所谓(为),将各省每年钱粮解送户部者,除动用外,尚有余剩八百万两,欲放给八旗官弁兵丁,未得总管之人,所以八旗各设收卖米局,以便兵民。宗人府借俸,并无苛刻。至于刑罚,皆人自惹,不得已而行诛戮,亦必着诸王大臣详议真情。即如年羹尧、隆科多辈,朕贷(待)他殊恩,尔等之所共知。孰意他欺君罔上,最(罪)大莫逭,即朕不诛,天亦不赦。就如查弼纳,你为两江总督时,犯罪来京,在朕面前自改前非,朕即宥罪擢用。皆由你自知前愆,自勉自励,小心供职,朕亦优待。若诸臣中能如此者,岂肯舍之而不用乎?”
查大人叩头回奏:“臣蒙主子洪恩,赦罪擢用,虽粉身碎骨,莫报隆恩。愿求皇上寿登千百,臣子子孙孙生生世世,永报不尽而已。”
[B]皇上大笑云:“人岂有千百岁在生之理。今年仓(昌)平州掘碑一座,碑上诗语,朕甚不解,未知是何应兆。欲将明年七月起,不必写出年号,只写己酉、庚戌、辛亥。尔等详议,传示各衙门知之。”钦此。
十三王等回奏:“皇上以孝治天下,仁德化民心,虽古圣贤君,无以复加。况我朝定鼎以来,四民咸服,五谷丰登,皆天赋久祚于大清。碑文解语,何足凭信。若据碑上之诗,不写年号,一若外扬,反为惶惑。若有借俸一二年者,可只写年分,不写年号。其现年历日文书稿案,仍照旧例。至于各衙门启奏事内有字眼不好者,请为改正。即如‘年终尽数’四字,以臣愚见,改为‘岁底全数’,未知可否,伏乞圣裁。”
奉旨:“甚是。‘年终’改为‘岁底’,‘尽数’改为‘全数’,传示各衙门知道。”钦此。……
更问其仓(昌)平州碑上诗语,则金超又誊示一张,曰:皇上筑万年吉地,差官到仓(昌)平州取土,掘至丈余,见碑一座,长一丈六尺,宽七尺,厚四尺,明刘伯温所立。有句八联,曰:红花落尽放黄花,遍地胡儿乱似麻。东来西去归藏土,南上北下返牛家。七九之年虎哺兔,一人骑马踢双猢。八六家鸡夜宿粮,十个孩儿九哭娘[8]V12P700-704,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
手本A 段所说查弼纳改过擢用事、官弁广善库“借俸”事及雍正帝动用官帑设立八旗“米局”事,俱与清官方文献记载合。
手本B段记载雍正帝欲改雍正七、八、九的三年为干支纪年的说法,乍看很玄,是否可信呢?翻检《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并无相同记载。难道是序班金超杜撰以图贿赂?再细查,发现该书六年六月初九日戊子有这么一条记载:
内阁奉谕旨:“朕从前曾降谕旨,不必写雍正七、八、九年,缮写己酉、庚戌、辛亥年。此旨下于何人之处,着查明。”[17]V3P2046
清朝文献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就找到这么一条。但是,这条简单记载却足以证明朝鲜使臣手本的记载并非凭空捏造或者出于序班金超贪图贿赂的杜撰。与清朝文献过于简单的记载相比较,朝鲜使臣的手本提供了雍正帝改变纪年方法的详细背景、动机及实际执行情况。
去雍正年号改用干支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避免童谣预言的应验。该童谣的寓意,据手本的记载,雍正帝以为“甚不解”。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做了解释。从回避“雍正”年号、改“年终”为‘岁底’、“尽数”为“全数”来看,雍正帝将昌平碑上所刻童谣与“国祚长久”做了联系,这反映了他内心对于“国祚长久”所怀的紧张和疑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解读雍正帝大搞祥瑞、宣扬“天人感应”的内视视角。
其实,这种紧张心态并非雍正帝的虚幻感觉,而是有着现实的依据。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在康熙年间变得严重,从北、西、西南三面对清政权构成压力。早在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朝鲜使臣在北京就听到过类似的童谣:“白塔一身孝,四塔都修到。西犭達子若要来,东犭達子就跪倒。”[8]V11P531,补编卷2使臣别单二这首童谣寓意清朝将亡于准噶尔蒙古,虽不能排除其中含有某种内地人民的反清情绪,但所传递的准噶尔威胁信号却是毫无疑义的。经过康熙年间三征噶尔丹、驱准安藏、雍正二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在与准部的博弈中变得主动,然而准部一日不亡,青藏与喀尔喀甚至内地就难以长久安宁。因此,雍正五年二月始,雍正帝接受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做直捣准部的秘密备战。这一备战,到六年七月已是一年有半,西征大计已定。从后来公布的计划看,七年是北西两路出征之期,八年直捣伊犁,那么九年就是善后之期[18]V14P220-222,岳钟琪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折。因此,将七、八、九三年改用干支纪年,目的就不外是祈求西征奏凯。
当然,限于信息来源的局限,朝鲜使臣有时候也会得到假情报。例如康熙五十五年,朝鲜使臣从辽东驿丞处获得一份“西犭達讲和表文”,录入别单中。回国后,他们听说此“表文”实为明末琉球国讲和表文,于是查核文献,发现“表文”出自刻本《燕居笔记》,有字句增删,但全篇大体相同[10]V40P648上,《肃宗实录》肃宗四十三年〈康熙五十六年〉五月戊午。此事益发可见朝鲜使臣记录“别单”的谨慎。另外,官名、人名等,或因译音,讹误多有。由于是闻见,所记述的有些事件发生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有出入。但是,这些闻见记述并非凭空捏造,并且朝鲜使臣在记述时力图做到真实可信,与《承政院日记》中朝鲜君臣的评论有着不同的性质。如上引雍正六年卞昌和手本所记载康熙时官弁的广善库借俸一事,手本原文记叙非常清楚,但是到朝鲜君臣议论此事时,却被理解为雍正帝“借百官之俸禄以为祈祷之需”[3]V37P161下,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把时间和内容都搞错了。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因为《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里面所记载的朝鲜君臣评论有误解、误断而否定“别单”等朝鲜使臣闻见记录的可信性及其史料价值。
总之,尽管朝鲜使臣的见闻记述,与清朝的官方文献一样,也存在局限,但如果能参证以清朝官方文献的相关记载,就如本文就有限史事记述事例考述所见,朝鲜使臣以清朝历史见证者身份所提供的相关记述具有颇高的可信度,是一种可以拓展清史认识的珍贵历史文献,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宝藏,值得清史纂修者予以更多的注意。
[1]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1).
[2][韩]林基中编辑.燕行录全集[M].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3]承政院日记[M].汉城(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1961.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杨珍.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A].清史论丛[C].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合肥:黄山书社,1998.
[7]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
[8][朝]郑昌顺.同文汇考[M].台北: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9]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M].汉城(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11][雍正]大清会典事例[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77辑·第776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12]雍正朝文字狱·范世杰呈词案[A].文献丛编:第7辑[C].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
[13]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罗冬阳.雍正帝矫诏召回抚远大将军王允禵考[J].明清论丛,2012(12).
[15]康熙建储案[A].文献丛编:第4辑[C].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
[16]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
[17]雍正朝起居注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3.
[1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