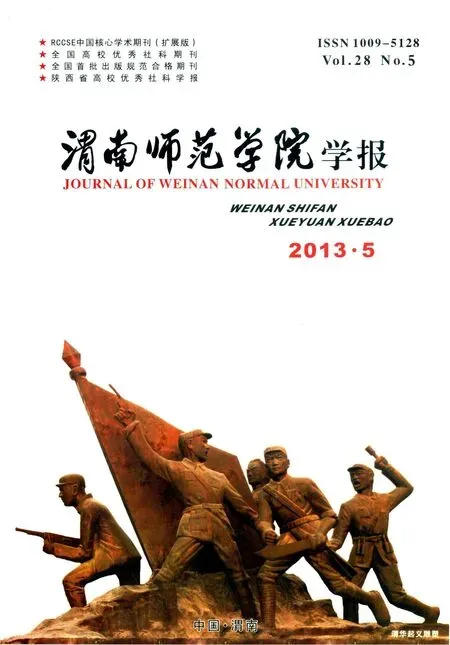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指瑕
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056005)
一、别集与总集均兼收文学与非文学作品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别集,是四部分类法中‘集部’的主干部分,集部与经部、史部、子部在内容上有着明确的区别,《隋书·经籍志》别集类序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由此可见,别集是‘属文之士’作品的各自汇集,开始是后人为前人编集,后来是‘辞人’自己为自己编集。别集收的是文学作品,这是与经、史、子三部的区别。”[1]379-380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同[2]302,该说是对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典型误读。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而至东汉,虽属文之士众多,然其所谓文与后世之所谓文学性作品绝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种与后世之所谓文学性作品绝不可同日而语之文所构成之集,也自然绝非文学作品之汇集,即别集收的是文学作品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云:“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3]1056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二十九·经籍三》云:“《孙卿子》十二卷楚兰陵令荀况撰。梁有王孙子一卷,亡。”[3]997《孙卿子》十二卷三十二篇,再加上刘向叙录,平均一卷三篇。荀子之文学作品只有《成相》《赋》两篇,编为一卷而成《荀况集》明显单薄,而梁二卷,则可证楚兰陵令《荀况集》所收荀子作品必多于《成相》《赋》两篇之数,楚兰陵令《荀况集》必为荀子作品之选集,另外,楚兰陵令《荀况集》所收荀子作品必不仅包括荀子全部之文学作品《成相》《赋》两篇,而且选录了部分荀子之非文学作品。总而言之,《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所载之楚兰陵令《荀况集》之集含有选集之意,且楚兰陵令《荀况集》所收之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
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云:“汉胶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3]1056《隋书·志第二十七·经籍一》云:“《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3]930董仲舒之文学作品只有《士不遇赋》一篇,不能形成一卷或二卷之规模。另外,既然题名为《董仲舒集》,一篇《士不遇赋》不可能曰集,一篇以上方可曰集。由此可见,首先,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所载之《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所收之董仲舒作品必不止《士不遇赋》一篇文学作品,必还收有董仲舒之部分非文学作品。其次,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所载之《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绝不能收录董仲舒之全部作品,由此可见,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所载之《董仲舒集》必为选集,而绝非全集。总而言之,长孙无忌等《隋书·志第三十·经籍四》所载之《董仲舒集》之集含有选集之意,且《董仲舒集》之集所集之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
根据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之实际情况,上文已证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所著录之楚兰陵令《荀况集》《董仲舒集》所集之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即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之实际情况也证明别集仅收文学作品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事实上,早在王粲的别集中就有经说的内容。《颜氏家训·勉学篇》:‘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可见,当时文集虽以诗赋铭诔为主体,但也不排斥说经之文。宋元明清以来,别集中有关经说、史论及诸子方面的内容普遍存在,而且视作者情况,比重不同。清代学者如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顾千里《思适斋集》等,基本上以学术性书跋为主体。可见,别集所收的作品,实际上只是形式上单篇文章和诗、词、曲的汇集,内容上则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越往后这种特征越明显,绝不限于文学作品。”[1]380-38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仅仅将《颜氏家训·勉学篇》修改为《颜氏家训·勉学》而其余与此引文全同[2]302-303,杜泽逊此处之论又与上文所引之论矛盾,既然此处明言别集所收绝不限于文学作品,则上文所引其所谓别集收的是文学作品及这是与经、史、子三部的区别之论就不恰当了。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总集,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之汇集。其单收一人之作者为别集。”[1]36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同[2]288,该说以总集为多人文学性作品之汇集,该说为误,根据《隋书·经籍志》之实际情况,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之四部分类法中经、史、子、集四部只是对当时图书大致之分类,《隋书·经籍志》集部之情况尤其复杂,集部总集类之诏书本可收录于史部,而《隋书·经籍志》收录于集部,诏书有何文学性则不言自明,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集部收录杂文,杂文多为无法归属于经、史、子三部者,由此可见,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集部之一部分内容为不归于经、史、子三部者集于集部。由此可见,所谓总集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之汇集不符合《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实际情况,此说自然是片面的,也自然是不正确的。《隋书·经籍志》收录于集部者有文学之集,也有非文学之集,多数则是其中既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之集。根据《隋书·经籍志》集部这一实际情况,总集应当定义为总集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其中之作品既可是文学作品也可是非文学作品。同理,别集应当定义为别集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其中之作品既可是文学作品也可是非文学作品。
另外,由于对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集部之误读,不知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集部之总集也收录非文学作品,仅仅承认总集收录文学作品,而萧统《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4]3之《昭明文选》又被称为总集之祖,《昭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为文学性之诗文,遂以诗文定义总集或以诗文为总集定义之要件。潘树广《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汇录多人的诗文成一书的,叫诗文总集。总集可依其收录面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选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等,全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等。一般说来,选集的编辑,旨在推荐佳作(当然是编者所认为的佳作);全集的编辑,旨在保存文献。”[5]27潘树广以上之论存在多处明显错误。汇录多人的诗文成一书的,叫诗文总集。如此,则诗文总集是否等同于总集?抑或总集是诗文总集之简称?若诗文总集等同于总集或总集是诗文总集之简称,则《昭明文选》可称为总集,因《昭明文选》是汇录多人的诗文成一书的,自然是诗文总集。《全唐诗》收录的是诗而未涉及文,自然不是诗文总集,那么,《全唐诗》是否是总集?由此可见,汇录多人的诗文成一书的叫诗文总集之定义存在明显缺陷,诗文并提以限定总集实际上缩小了总集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诗文总集是否等同于总集抑或总集是诗文总集之简称也不明确。既然如此,为避免上述问题计,只能重新定义总集,总集的正确定义应该是也只能是:总集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
二、全集和选集不属于总集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云:“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有专集乐府歌辞者,有专集连珠碑文者,甚至有单篇之赋焉,有专门之作焉(如《文心雕龙》),有漠不相关之《女诫》焉,有绝非文学之诏集焉,有表奏,有露布,复有启示,《隋志》所载,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至。此岂‘总集’?乃杂书耳。其实只须稍一分析,则文学史学,各有攸归。而撰《隋志》者惮爬梳之烦劳,蹈《七录》之覆辙,又复并‘杂文’于‘总集’,乖分类之义远矣。”[6]75-76
姚名达误读《隋志》而以总集为文学之集,屏非文学之作品或曰杂文于总集之外,其说似有据,然姚名达以己意强古人之所难,诬撰《隋志》者惮爬梳之烦劳,撰《隋志》者非惮爬梳之烦劳也,实劳而无功,绝不可为也。何以言之?目录学研究之对象定之也。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至。反映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之书籍也必然五花八门而极凌乱渗杂之至。所谓渗杂者,即各个学科相互渗透杂糅交错。姚名达所谓其实只须稍一分析则文学史学各有攸归,不啻于痴人说梦,姚名达所追求的那种纯而又纯、如数学一般精确之目录分类根本不存在,自然也就永远无法实现。故撰《隋志》者非惮爬梳之烦劳也,实劳而无功,绝不可为也。撰《隋志》者也绝非蹈《七录》之覆辙,并杂文于总集实乃势所必然,实乃顺应自然、符合实际之举,非为乖分类之义远矣,实乃深得目录分类之大义,即一切分类包括目录分类只能是也永远是大致之分类。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云:“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6]7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成于1937年,为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该书影响甚大,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再版重印,王重民为之作《后记》,评价之高,已至无出其右者。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实际上已成研究目录学与文献学之必读书,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云:“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6]76姚名达此处所谓之“选集”,实为动词,乃选择收录之意,即相当于选录。姚名达论述总集时仅仅上述引文中两处使用“选集”一词,且仅仅用作动词,姚名达论述总集时从未将“选集”一词用作名词。文言文中名词动用至为平常,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以文言文写成,姚名达此处两次用作动词之“选集”,当是由名词“选集”而来。但是,这也仅仅是推测,姚名达论述总集时仅仅上述引文中两处使用“选集”一词,且仅仅用作动词,姚名达以今人写文言,不可以其动词皆由名词动用而来,即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论述总集时两处使用动词“选集”是否暗含论述总集时可以使用名词“选集”还在两说之间。但是,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以其巨大之学术影响使其在论述总集时两处使用动词“选集”之举产生了重大的学术误导作用。
潘树广《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汇录多人的诗文成一书的,叫诗文总集。总集可依其收录面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选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等,全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等。一般说来,选集的编辑,旨在推荐佳作(当然是编者所认为的佳作);全集的编辑,旨在保存文献。”[5]27潘树广一方面误读《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内容,另一方面附会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论述总集时两处使用动词“选集”之说,以为既然总集中有选集,与选集相对者为全集,则总集之中也当有全集。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认为总集“自编辑方法而论,则可分选集、全集两大类。”[1]36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同[2]288,此说也是一方面误读《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内容,另一方面沿袭潘树广《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将总集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之错误并附会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论述总集时两处使用动词“选集”之说。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总集中之全集,旨在网罗一代诗文之全,零句残篇,搜剔不遗余力,其可贵在于全。”[1]37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同[2]29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与《文献学概要(修订本)》明言总集旨在网罗一代诗文之全,接着列举总集之例,第1例即为严可均校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绝非一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网罗者为文而非诗文;所举第13例为王季思所辑之《全元戏曲》,但该书所收为元代杂剧及南戏,杂剧及南戏与诗文又有何干?即杂剧及南戏非诗非文,杜泽逊以总集中之全集为旨在网罗一代诗文之全,元代确属一代,而至于杂剧及南戏,则其非诗非文甚为明显,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前后矛盾,真是令人遗憾!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别集的编集是有诸多讲究的。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属于选集,就是说基本上要删汰一些作品。而后人所编,则大都属于全集,片语只字也不遗漏,这是因为编者往往是作者的子孙或学生,或者是乡后辈,或者是作者的研究者、爱好者。”[1]38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同[2]303,别集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既然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在一人全部作品中删汰一些作品所编定之集为选集,则选集即是收录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既然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云在一人全部作品中片语只字也不遗漏所编定之集为全集,则全集即是收录一人全部作品的集子。即别集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而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又认为总集“自编辑方法而论,则可分选集、全集两大类”[1]36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与此引文全[2]288,如此则别集等于总集,但事实上别集并不等于总集,因为别集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而总集则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如此则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将别集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与其将总集分为选集和全集两大类相互矛盾,必有一误。总之,选集是收录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而全集是收录一人全部作品的集子,选集和全集属于别集,选集和全集与总集无关。
三、结语
别集与总集均兼收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以为别集与总集均只收文学作品是错误的。
别集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别集又分为全集和选集两大类。全集是收录一人全部作品的集子。选集是收录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总集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总集又可分为断代全本式总集、断代选本式总集、通代全本式总集、通代选本式总集四大类。截取一代或一朝而收录其全部之作品或某种作品之集子为断代全本式总集,或曰断代全录式总集。截取一代或一朝而收录其部分之作品或某种作品之集子为断代选本式总集,或曰断代选录式总集。截取一代以上或一朝以上而收录其全部之作品或某种作品之集子为通代全本式总集,或曰通代全录式总集。截取一代以上或一朝以上而收录其部分之作品或某种作品之集子为通代选本式总集,或曰通代选录式总集。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南朝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潘树广.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