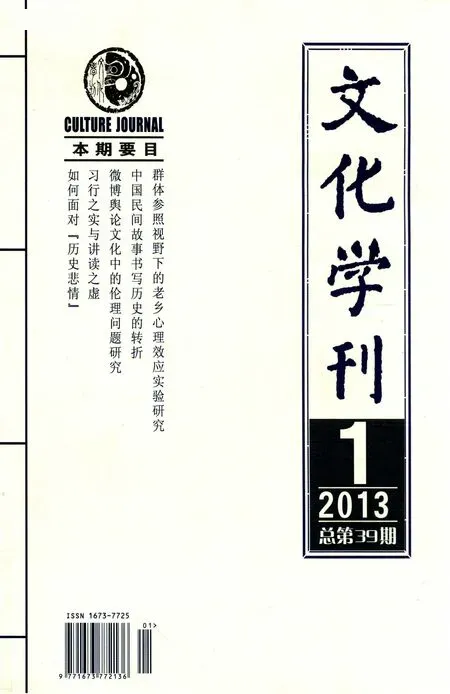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下之嬗变
郑艳艳 程文佳 文成伟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在现代社会中,网络社群的出现带来了网络生存,使得其中的隐私权产生了不同于传统隐私权的一系列变化。它一方面使隐私权内涵增加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使隐私权的属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权,并理性面对各种隐私信息的运用和商业化过程?这些问题涉及到保证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问题,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隐私权内涵以躯体为标识转变为以个人数字信息为主
传统隐私权侧重于与人的身体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私人信息、行为和生活空间,其内容无关公共利益、群体利益,具有纯粹的个体相关性,且不愿为他人所知。在网络技术时代,科技人员建构出虚拟现实的世界,嵌入社会系统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尤为凸显的是网络技术构建了具有权利特征的社会生存环境,它处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创造着具有全球连通性和分权化特点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1],为隐私权带来了全新的存在空间。
“网络隐私权”是指公民在网上私人生活安宁权与私人信息权,它具有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复制、公开和利用的属性,属于人格权;它要求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与个人有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毁损的意见等[2],还包括“网络使用者不愿被他人知悉的个人网络数据、不愿被他人干涉的个人网络行为和不愿被他人侵入的个人网络领域”。[3]具体包括:第一,网络个人信息,即基于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而产生的各种资料,包括网络用户名、账号、密码、邮箱地址等;网上电子消费卡、上网卡、上网帐号和密码、交易帐号和密码等。第二,网络个人行为踪迹,即个人在进行网络行为(包括注册、网上消费、交友、医疗、发帖等)时的相关记录等以及在网上的活动踪迹,如个人浏览网站的习惯,收藏的页面、浏览的网页、浏览时间和频率等。第三,网络个人空间。网络上的个人空间不仅是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展示自我的平台,而且是与他人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如电子邮箱、博客、空间等,更是很多网络用户的个人情感倾诉寄托之处,这样的空间,同样需要保持独立,属于隐私范畴。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需要身体的直接参与,而网络行为隐藏于屏幕之后,主体不在场,其网络空间行为痕迹亦可成为隐私的内容,它较之于肉眼捕捉的现实行为,更为隐秘。这些私人的网络行为往往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被记录并存储于计算机系统中,且具有连续性。通过以上网络个人隐私内容进行搜索、概括,可以基本准确地对一个自然人进行相对完整的描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把他对应地搜索到,这也是“人肉搜索”之所以可能的技术根据。
这种隐私权内涵的转变,表明个人真实而明确的存在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在此基础上还衍生了个人的精神存在空间,这样使个人拥有增大了的隐私空间范围与展示自我的平台。隐私权表征形式的这种变化是以数字化的信息形式为基础。它表明隐私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领地,在现代技术社会已经和我们的日常行为所涉及到的数字信息息息相关,只要关涉个人的能够数字化的东西,都可以展示一个人的行为踪迹,都可以成为被记录的对象,隐私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身体和私密空间。
网络隐私权建立在权利客体数字化的基础上。它将客体复杂多变、形式各异的个人隐私内容通过网络的信息转变为统一的数字、数据信息。人不仅是“物理存在”,还是一种“信息存在”,是各种信息组成的集合。这种信息累计到一定程度,就能构成与实际人格相似的“信息人格”或“数据人格”。[4]个人数据的重要性,在于依据数据组合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定位数据的依附主体。这为搜集、加工、传播、利用具有隐私性质的数据提供了方便,使个人隐私在网络环境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5]
这种变化使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的存在方式、精神境界都有了新的认知途径和把握方式,这彰显了社会对隐私的权益意识,明确了个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隐私权的内涵的基本性质属于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相关性,尊重这些东西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威胁,这是隐私权的界定范围,其宗旨仍然与传统隐私权一样,是保持人的心情舒畅、维护人格尊严。
二、隐私权由简单、消极型转变为积极控制、复合财产型
传统的隐私权是一种简单的消极隐蔽权,即指其依附主体人肉体、作为被保护的对象而存在,强调权利人以一种象征性或实质性的行为对自己的生活划定一个范围,在范围内,任何未经允许的刺探、收集、公开和使用等都是不允许的,否则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而作为绝对权的隐私权的相对人,只要不积极侵犯他人隐私权就是尊重了隐私权,从这个角度讲,隐私权就是一种权益主体的简单、消极的隐蔽权,它是自然人生活的权利和不受干扰的权利,通常情况下权益主体不会主动运用隐私催生利益,因此,它不具有财产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个人的信息以数据形式存在且和主体身体相脱离,一切个人的数据信息都成为隐私权的客体,这为隐私权由消极的隐蔽权转变为网络积极的控制权提供了条件和环境。在现代社会,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向社会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以明示或者彰显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权利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自愿地掌握、处理个人信息,甚至从中获取某种利益,换个说法,就是他可以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开放或缩小并处理自己的信息,并允许他人运用自己信息获取某种利益。隐私权就从原来消极地被他人尊重转变为自己积极主动地掌控权。这种主动的权利作为人格权不仅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个体生存普遍的最低限度的人格要求;尊重这种权利既是自然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属性,也是对人最低的道德标准要求。
传统的隐私权被排斥在财产权范围外,它“没有财产内容,不直接表现为一定财产利益的权利”[6],包括隐私权和身份权两种。网络隐私权与传统的隐私权相比,更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了财产属性和商业价值,即是指隐私的某些内容已进入市场而商业化,对隐私信息的利用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其兼具财产权的性质[7]已相当明显。随着网络环境的普及和渗透,隐私信息的财产价值日益凸显,成为商家可供交易的商品。商家了解客户的个人兴趣、文化素养、学历等等隐私信息,由此可以定位不同的客户群制作商品,提供有特色的专业服务,它在满足了客户需要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些信息包括传统的隐私权内容,也包括个人可以以信息方式存在的所有数据,网络隐私权开始具备财产权的属性。
网络隐私权相对于传统的隐私权尽管发生了如此之变化,但是它仍然属于民法当中的人格权。其人格权的基本特征不变而同时兼具有了财产性。网络“隐私权在内容上不再是单纯的隐蔽权,也开始逐渐添加了新的内容——利用权,而利用权已经开始具有财产权的属性”[8],这是网络时代的必然。[9]其财产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个人信息等隐私的让渡,取得经济利益或获得网络运营商的相应服务。我们国家有关网络运营商隐私保护政策的规定,网站经营者不得拍卖其所拥有的无形财产从中非法获利,就是指大量的顾客资料信息被用来获利。很多情况下,网络用户为得到更多的权限,不得不以更为详细的个人信息作为交换,获得更多的资讯或服务。因此,网络隐私权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网络隐私权虽然具有了财产属性,但是它和传统的以“物”为标的财产权却不同。作为财产,隐私权关涉到的信息作为商品总是和权利主体的个人意愿相关,不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的物成为买卖的对象,且具有不可逆性。隐私权所涉及的信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其特殊性是其商业意义取决于权利主体的个人意愿,随附着主体的认知和决断,权利人有权控制和自己有关的隐私信息的使用和传播。因此,隐私权信息不能够随意买卖,否则就是对隐私权的侵犯。这与物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明显不同,物作为交换的对象可以随意通过商品交换行为而得到转移,而隐私权信息作为交换的对象由于其具有不可逆行的特点其决定权应掌握在权益主体。因此,隐私权的财产属性是以人格权为主,且兼具财产权的复合权利。
随着隐私权属性从“消极隐蔽权”逐渐发展为“积极控制复合型权”,其内容增加了知情权、选择权、支配权作为控制权。它有两项权能:一是权利主体有权按个人意愿自由控制权利客体,如个人信息、行动自由、住所;二是权利主体有权使用自己的隐私从事各种活动,以满足自身的需要。[10]网络隐私权上述两项权能更多地体现了权利主体对个人事务的自主决定权,只要无关乎公共利益、集体利益,隐私权主体应有权决定是否提供相关的资料,有权限定所提供隐私资料的使用目的。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个人隐私信息进行支配,获得经济利益,包括以一定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自己的部分隐私,允许他人知晓自己的个人活动和进入自己的个人领域,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隐私。[11]当然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支配利用,须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并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
三、网络隐私权更易于遭受侵犯
网络隐私权较传统的隐私权更易于遭受侵犯。作为第四媒介的网络技术,已逐步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人们把技术视为人的肉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尤其当人们熟练使用网络工具后,工具往往被忽视并消失在使用者的视野中,而把技术装置被观察系统所内化,由此技术内化为人的一种生成信息的功能[12],由此形成敞开式交流、交往的平台,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展开了自己的个人私人空间。麦克卢汉说“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13],“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14]人的隐私在这样的网络空间环境中有了新的场所,其特点是它可以和人的物理形态相分离而独立存在,从而使衍生出来的隐私权呈现独立性、空间的开放性、内容的多样性。由于网络空间造成的“身体缺场”,为人们的羞耻感提供了一层保护膜,极大地冲淡人们的害羞和尴尬心理。[15]网络技术一方面开拓了人类生存的无限广阔空间,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与困境。[16]这使人们抛开现实因素的束缚,以一种更为开放大胆的姿态介入到网络存在中,增加了隐私遭受侵犯的机会。
隐私“符号”信息遭受侵犯成为网络侵权中的常有现象。网络技术环境塑造了人类隐私对象的符号化,每个肉体的人都以符号的形式生活在网络上,数据符号成为身体的延伸,“符号在场”成为人类存在的新形式。这就使隐私内容不再局限于身体部位及住所等实体范围,作为人体延伸的符号也被纳入隐私的范围。在网络平台上,任意的相同之处都可成为人们建立交往关系的纽带,对他人私人领域的介入也越来越多。技术一方面成为完善自我、展示自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为窥探他人隐私的工具。Cookies对网络行为的记录使人们的网络行为透明化,其广泛收集信息的能力结合计算机的高效处理技术,使得个人信息被迅速汇集,瞬间描绘出一个人的“数字人格”,个人成为没有隐私的“透明人”。[17]因此,人们进行网络行为时,更多地关注起个人信息的被收集及其使用和被使用情况,也提醒人们应该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网络环境对于可能操纵和运用隐私内涵的潜在主体 (责任人)有了明确的指向。保护隐私除了原有内容以外,还要控制企业、政府和整个社会对个人信息的掌握,控制对个体符号的延伸保护。这在历史上有惨痛的教训,二战期间,希特勒正是利用政府收集的个人信息指认犹太人残忍迫害犹太人。
四、网络隐私权的运用与保护
隐私权涉及个人的自由、尊严与发展。在网络环境下,针对人的隐私权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亟待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规范,一方面确保人的自由不受他人侵害,另一方面也防止有人滥用隐私权谋取私利。在现代社会,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不仅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适当暴露自己的行踪,而且根据自己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需要掌握并控制着自己的个人信息使用的权限和范围,甚至有人还有意宣扬自己的部分行为及信息,以满足内心的需要。因此,“隐私权在内容上不再是单纯的隐蔽权,也开始逐渐添加了新的内容——利用权,而利用权已经开始具有财产权的属性”。[18]隐私权部分地走向市场,实现了隐私权以人格权特征为主兼具财产性特征的复合性权利的转变,这激发人们对隐私权的保护。
从法理上讲,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只要无关乎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隐私权主体有权限定所提供隐私资料的使用目的。因此,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个人隐私信息进行支配,获得经济利益。为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建构健康有序的社会发展,理性的进行人际交往行为,需要慎重对待变化了的网络隐私权。
人类创造并选择发展互联网,对个人隐私而言就必然是一个挑战。借助于网络增强自己的主体性,还是受制于网络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并不取决于网络而取决于自己。[19]网络技术一方面以其强大的功能特性带来了信息资源即时共享,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对网络行为全面记载,使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时时发生,这又压迫着人类的心理空间。因此,面对安全与效率的两难选择,平衡网络的运用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
鉴于各国对互联网行业利益和网络用户个人利益的权衡取舍不同,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模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规制模式。前者强调为了保障网络产业的快速发展,应当尽量减少对互联网的法律限制,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上实行较为宽松的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模式;后者则认为单靠技术控制和行业道德自律无法满足网络隐私权保护的要求,必须由立法、司法及行政系统占据互联网络控制的优势地位。结合国外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的选择和立法经验来看,我国的立法模式也应主要在二者之间选择。总体来说,两种立法模式在规制效果上各有利弊。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无国界媒体,倘若对其进行单纯的立法规制会阻碍网络产业的自由发展;而单纯的行业自律则过于偏重技术手段和行业内部纪律约束,不具有强制力,很难有效地保障网络隐私权。
我国互联网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网络参与主体日益增多、网络活动和网络行为日新月异,网络隐私权保护更是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要求,此时更应当把握好促进互联网行业发展和保护网络隐私权利主体利益之间的“度”。鉴于我国的国情,我们应首先借鉴欧盟的立法规制模式,因为该模式与我国具有“法律思维的相容性和法律实践的契合性”[20],一方面容易为理论和实务界所采纳和接受,另一方面也符合国际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发展趋势。其次,兼采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协调网络发展与私权利益的平衡,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同时,积极关注国际立法趋势和立法动态,鼓励网络行业技术创新对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支持,并从中汲取先进的经验措施,进而形成我国独特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模式,使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意义在于保障人格尊严。《维也纳宣言》序言第2段指出,“一切人权都源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作为重要的人格权之一,隐私权的确立不是人类的最终追求,蕴含于其背后的人格尊严才是最终的保护目标。世界著名的计算机伦理学家Moor就认为,虽然隐私本身不是一种“核心价值”,但它却是“核心价值的表达”。[21]网络隐私权的确立所表达的核心价值,其目标也是人的尊严与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维护着个人内心的平静,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这在人们网络社会的今天,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1]鞠姗姗.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8.
[2]李德成.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初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3]胡晓红,梁琳,王赫.网络侵权与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4][9][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权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5][8]刘德良.互联网对隐私保护制度的影响与对策[J].新视野,2003,(4):72-74.
[6]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0]Jiang Zhao.Human Flesh 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Privacy——Defi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ght to privacy under the new form of society[J].Human Rights.2010(5):12-16.
[11]张秀兰.网络隐私权保护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2]肖峰.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 -6.
[13][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刘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4][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曾国屏,李正风,段伟文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6]刘同舫.技术的边界与人的底线—技术化生存的人学反思[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1-3.
[17]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8]刘德良.论隐私权[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50 -55.
[19]李雪梅.信息网络时代人的主体性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
[20]崔华强.网络隐私权利保护之国际司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1]Moor J H.Towards a Theory of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J].Computers and Society.1997,27(3):27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