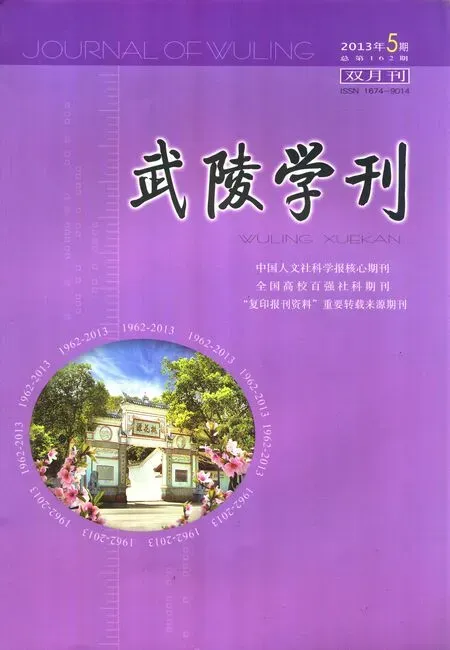具身认知与读心
[美]香农·斯鲍丁著,陈 巍,庄文旭译,李恒威校
(1.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哲学系,麦迪逊 WI 53706;2.浙江大学“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28;3.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引 言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EC)是认知科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它挑战了认知心理学中的传统观点:认知主义(cognitivism),简而言之,认知主义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应从对于符号、内部心理活动的计算加工过程来解释,因此认知科学也就理所当然当关注这些内部状态及加工过程。具身认知对心智的解释则与之不同,它认为认知科学应关注身体与环境是怎样塑造了心智[1]①,而不是认知主义的那种脱离身体和环境来研究心智的错误观点。具身认知对于读心(Mindreading)②的反驳实则是更为一般的具身认知论对认知主义反驳的一种应用。
具身认知主要是驳斥了之前关于读心文献中的两个基本假设:(1)读心关于发展的根本性质的观点;(2)读心普遍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具身认知论的反驳成功的话,那它将表示整个读心领域的研究都被严重误导了。我将在此文中考查具身认知对于读心的各种反驳。考虑到这一研究的新兴性,能找到大量在强度和范围上相异的,但都是举着具身认知之旗的论证。不过,取其精华,找到最有力的论证还是可能的(Bermúdez,2004;Gallagher,2005;and Hutto,2004)。可最终,即使最好的论证也失败了,这使得具身认知对于读心的反驳是极为不成功的。
一 争论的术语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解释一下读心和具身认知各自的具体内容、两者的分歧以及谁能在这场争辩中更胜一筹的理由。两方究竟为何而争呢?读心与具身认知都对社会认知进行了解释。大体上,社会认知就是我们理解他人、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中进行观察、理解与互动。支持某方的政治观点、传播流言蜚语、进行体育运动、参与到一场哲学争辩之中、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都是社会认知的一些例子。
举个例子的话将会更有帮助。假设Jill正在一个咖啡馆忙于她的论文。此时一个年轻男子Jack走了过来并坐在了Jill的旁桌。Jill礼貌地表示了一下微笑,Jack也回笑一下,之后Jill又投入到了她的论文之中。Jack问她是不是个学生,Jill说是的。Jack又问她的专业是什么,Jill回答说是哲学。Jack说:“哲学?那你肯定很渊博。”Jill回应道:“当然。”Jack又问她是不是本科生,Jill说不是。Jack不断地问些小问题搭讪,而Jill却每次只用一两个字敷衍。很清楚,在这一场景之中,Jill认为Jack对她有意思,而且Jack也错误地认为她对他也有好感。为了打消Jack的这一念头,Jill才用只字敷衍他。Jill想让Jack明白她并不想和他搭讪,以此对Jack的行为施加影响。如果Jack明白了这一点,那他就会识相地走开。
社会认知的上述例子正是读心和具身认知想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认知构成能让我们理解并参与到像上述例子中那样的社会互动呢?读心是一种解释。具身认知又给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回答。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首先解释什么是读心以及它如何解释社会认知。然后再介绍什么是具身认知,以及它的拥护者所提出的与读心相对的论证。
标准的读心解释是我们通过领会别人的心理状态并且用此解释和预测他们的行为来理解他人、与他人互动。发展读心这一能力,首先必须能理解到别人也具有心理状态。关于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细节为先天论者和经验论者所争论。先天论者这边,Alan Leslie认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理论机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TOMM),这一特别的注意机制能让人调动诸如信念、愿望、假装的固有概念,并且让正常发展的儿童能够选择性注意心理状态。这些天生的特定概念和对心理状态的选择性注意解释了儿童如何获得别人的心理状态并且怎样对其归因[2]。而在经验论者那边,Alison Gopnik则假定正常发展中的儿童就好像是个小科学家。他们将有关别人在社会环境之中行为的理论进行更新、验证来不断使其更精准,以此获得有关心理状态的知识。最终,由于大量的与原先理论对立的证据,儿童舍弃原有关于愿望和信念的不合适理论,而逐渐采用与成人相同的方式来对心理状态作出解释[3]。在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心理状态这一问题上,先天论者与经验论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一个像Leslie这样的先天论者会认为我们至少与生俱有一些有关心理状态的概念,并且会更加易于关注别人的心理状态。一个像Gopnik这样的经验论者则认为我们逐渐发展出并检验一系列有关行为的假设来获得对心理状态的学习。但是,双方都承认这一共同的假设:儿童基于理解心理状态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社会理解与互动的能力。我把这称之为发展观(the developmental claim)。
在读心的描述之中,一旦儿童对心理状态有了认识,他就学着去进行归因,并逐步采用这种能力来解释和预测基于心理状态的行为。这一过程是如何作用的,又是理论论(Theory Theory)与模仿论(Simulation Theory)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理论论主张我们用有关心理活动如何形成行为的常识心理学理论(folk psychological theories)来对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和推理,我们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来推测他可能的心理状态,并运用这一推测的心理状态加上理论中的心理学规律来联系心理状态和行为,从而我们预测了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模仿论则认为我们是以自己的心理状态为模板来做到这一点。也就说,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假想自己处于那样的情境之中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更具体地说,我们构想对象的心理状态可能怎样引发可观察的行为,然后把其心理状态作为假装形式的信念与欲望当作输入,以自己的决策机制加工它们,得出结果,并将之归属给对象。这种模仿,就同理论论所推测的一样,可能是发生在意识层面或者是亚个人层面(sub-personal)的。尽管理论论与模仿论对于读心的过程持不同观点,但就我们在社会环境中是如何彼此理解、互动这一点却是一致的:通过对心理状态的归因来解释和预测别人的行为。文献中经常指出读心是一种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理解他人的方式。读心在社会环境中的导航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热切的读心者,那么与他人彼此理解、互动就会困难重重。这一论点成为读心观的普遍观(the broad scope of mindreading claim)[4]。
有了读心的解释,让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社会认知的例子上去。对于这一情境,读心将会这么解释:根据Jack的行为判断,Jill逐渐认识到他以为自己有和他交谈的意愿,而且,Jill还认识到Jack所持有的是错误的信念。然后,Jill试着表现出能让Jack不认为自己也对他有意思的做法来改变Jack原本错误的信念。如果Jill的确是在随意应付,那么Jack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停止搭话走人。用大致的术语来说就是,Jill将一种心理状态归因于Jack,并据此解释和判断了他的行为。
与之相反,来自具身认知阵营的学者对于发展观和读心的普遍观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认知能力并不是基于心理上的理解,而是来自于更加基本的、非心理(non-mentalistic)的具身实践活动。这一具身实践又是由“原初交互主体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和“次级交互主体性”(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构成。根据具身认知的说法,原初交互主体性是对他人前理论(pre-theoretical)、非概念(non-conceptual)和具身的理解,而且是高级认知技能的基础。用Shaun Gallagher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天生的或者很早就发展出来的能力,这一能力使我们能在知觉经验水平上和他人互动——我们看到,或者更为一般性的是,我们知觉到别人的身体动作、脸部表情、眼动方向等等,还包括他们的意图和感受。”[5]与其说是读心,原初交互主体性不如说成是身体阅读(bodyreading)。对于脸部动作和躯体本体感受(proprioceptive sense)的模仿能力、觉察跟踪眼动的能力、觉察意向性动作并能够从动作和别人表达性的运动(expressive movements)中读取情绪的能力都是原初交互主体性的表现。尽管读心和具身认知的术语使用不一样,但两方都赞同原初交互主体性对于读心的发展是必须的。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次级交互主体性在1岁左右发展起来,以开始于一对一、即时的交互主体性转变为联合注意的情境为特征。随着次级交互主体性的发展,儿童除了能够追踪眼动、觉察意向性行为和解读情绪之外,还具有了加入到联合的注意(shared attention)行为之中。用发展心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次级交互主体性的特征是一个客体或事件可成为人们共同的聚焦对象。客体和事件是可以被交流的……婴儿和他人的互动开始以周围的事物作为参照。”[5]在这一阶段,儿童学会了去追随别人的关注,并向别人指出、同别人交流一个联合注意的客体[6]。因次级交互主体性的发展,儿童的社会理解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重要的是,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这一理解仍然是不涉及内在心理活动的。
具身认知论认为个体若要发展他人具有心理状态的这一信念,必须先有更为基本的具身实践,也就是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认识到具身认知论并不是在行为主义上旧瓶装新酒。具身认知区分了坚固心理状态(robust mental states)和亚信念(sub-doxastic)的心理状态。信念(belief)和愿望属于前者,而意图和情绪则归于后者。虽然坚固心理状态和亚信念的心理状态都是心理活动(mentalistic),但理解和对信念进行归因却比理解和对意图进行归因需要更多的认知复杂性。正是基于这点,我把信念称之为坚固心理状态,而把意图称之为亚信念的心理状态。这一分法并非特设性区别(ad hoc distinction)。黑猩猩或许能表现出理解和归因意图的能力,但却不能理解和归因信念这一点可以证明上述的分类[7]。因此,黑猩猩③或许能理解一些亚信念的心理状态,却不能理解诸如信念之类的坚固心理状态。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促成了个体对于意向性行为和情绪的觉察,但这只能被理解为是亚信念层面的心智活动。从而,当具身认知论者表示我们对于他者的理解是非心理(non-mentalistic)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这里指的是非坚固(not robustly)的心理活动。
具身认知论认为日常人类生活中的主体间活动要获得意义的话就需要通过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因此,具身实践活动是发展性的基本原则(developmentally fundamental)。而且,即使作为成年人,我们的一般日常互动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变得更为复杂的一个例子。我们的主体间活动很少涉及对于心理状态的归因并且基于此来解释和预测他者的行为,即进行读心。与之相反,在读心中作为高级的、更加特殊化的、罕用的认知技能之基础的非心理的具身活动才是我们用于理解他者的基本方式。
现在,让我们继续用上面提到的那个社会认知的例子来解释具身认知的描述。从Jack的眼神交流、脸部表情、身体姿势、语调及其他的具身线索,Jill就能知道他的意图,而无需对信念进行归因并用此来解释判断他的行为。Jill不需要对心理状态进行归因,然后再对Jack的心理状态理论化或模仿来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些具身线索通常足以理解他人的意图及其意图所产生的行为。正如Gallagher所说:“在大多数普通、日常的主体间活动情境之中,我们具有一种直接的、基于知觉的对于他者意图的理解能力,因为他者的意图很明显地显露于他们的具身动作之中。”[5]
在阐述了读心和具身认知的内容之后,我们也就认知到了两者的分歧在于发展观和读心的普遍观。具身认知认为非心理的具身实践是在个体发展水平上居于根基地位,并且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他者的基石。因此,具身认知也就认为认知科学的重点应该在基本的具身活动之上,而非专门化的,或者很少使用的读心技巧。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决定哪方能够赢得这场争论。在发展观这点上,标准相对简易。如果具身认知的理论能够证明发展观是错误的,那么具身认知论就赢了。
而评估有关读心的普遍观这一点上就要略施诡计了。具身认知并没有声称读心从未发生过。当我们遇到非常诡异的行为时,则会求助于读心,此外,在读心的文献中也没有说读心是我们理解他者的唯一方式。并不是所有社会互动事件都是以理论化和模仿为基础的。有时我们运用启发式(heuristics),也可以说是依靠自动导航装置(autopilot)。具身认知论所持有的观点是,大多数情况下,读心并不是我们用来进行社会活动的方法。读心的理论则与之相反:大多数情况下,读心是我们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我的建议是,如果具身认知能够证明我们仅仅在极少数遇见非常古怪行为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读心的话,那么在关于读心普遍观的争论中,具身认知就赢了。这一标准看上去还是相对公平的。对于两方的支持者来说,他们都会认同读心在上述相应的情况下发生。但分歧在于,具身认知者认为读心在且仅在上述情况下发生,而读心论者则认为读心也会在别的场合发生。因此,如果具身认知能够证明读心至多仅仅在这种罕见情境下而非在我们日常的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话,具身认知的论证就是成功的。如果具身认知能证明上面的发展观和读心的普遍观是错误的话,那么这也将表明整个对于读心的研究被过分地关注和强调了。
二 读心的发展
如上所述,读心的发展观认为逐步发展而来的理解和社会互动的能力使儿童能够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而具身认知则否认这一观点:儿童必须具有理解心理状态的能力才能进行社会互动。Shaun Gallagher尤其反对这一发展观④。他认为发展论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在读心文献中普遍的假设:某一特定能力要求一个发展充分的心理理论,而对此,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比方说,Simon Baron-Cohen就列举了八种需要发展充分的读心能力的行为⑤:带有目的地和他人交流、弥补与他人失败的交流、教导他人、目的性地说服他人、目的性欺骗他人、建构共同计划和目标、目的性地联合注意一个观点或话题、假装[8]。在4至5岁期间,正常发展的儿童逐渐认识到他人可以持有与己不同的信念并且这一信念可以是错误的⑥。能够认识到某人会持错误信念这一点要求能够认识到某人持有的信念可以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这样的理解就建构起了理解信念的表征,而诸如成年人和读心者理解信念的方式。因此,对于错误信念的掌握通常标志了心理理论的诞生[9]。
Gallagher指出儿童从4~5岁开始能通过错误信念的任务,这也标志着他们对于信念的掌握。然而,在这一年龄段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不足为奇的。不能认为仿佛儿童在4岁之前一点儿也不能参与社会行为,但在掌握了信念的概念之后就立即成为了社会个体。与之相反,Gallagher在论辩中指出,在掌握信念的概念之前,儿童对于人类互动行为的一个基本理解就已经存在了。Gallagher认为这一更为基本的社会理解由原初交互主体性和次级交互主体性构成[5],这一点将会在下文阐述。
如上具身认知论所阐述的,随着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发展,儿童能够在社会情境中进行主体间的理解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Gallagher认为这一能力无疑是在儿童掌握心理状态概念之前发生的。事实上,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在发展读心上都是必须的。Gallagher指出,一个人在知晓他者的心理状态之前,必须对其自身和环境有所了解。一个人必须理解身为一个经验着的主体(experiencing subject)意味着什么?周遭环境中的事物都是这样的主体,且是与己相似而又有所区别的主体,也必须有特定的关于人们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行为的前理论知识[10]224。缺乏这一理解,一个人甚至不可能试着去学习掌握他人的心理状态。Gallagher所说的其实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儿童在领会心理状态之前就能够进行主体间的理解和互动;第二,这一进行主体间理解和互动的能力对于读心技能的发展又是必须的。
虽然我认为这样一个过度基于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社会理解模型有严重不足,但我却不打算深究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问题⑦。现在是时候看看具身认知的解释是怎样来挑战被Gallagher认为是在读心文献中的标准发展观了。儿童能够进行社会认知之前,要首先能理解心理状态和掌握其概念,然而,非常有必要指出这一发展观能被从一个更为强硬或是更为温和角度来阐释。强硬的观点是:在儿童领会心理状态之前,是不能够理解社会性互动的。在掌握心理状态概念之前,他们的社会理解能力非常有限或也许根本是不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儿童们是处于自闭状态的。但当他们掌握了这些概念之后,就能够进行社会性的理解和互动了。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在获取心理状态的概念之前,社会理解能力仅仅是有限的而非不存在的。动物在不具有心理状态概念之前就能以有限的方式理解人类并和人类进行互动。同样地,儿童也可以认为是如此的。对心理状态的领会给予儿童更为精准和完整的对于社会情境的理解。
Gallagher的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看法只能是反驳强硬的发展观(strong developmental claim):完全掌握心理状态的概念对于社会理解和互动来说是必须的。正如Gallagher所示,儿童远在掌握心理状态概念之前就有社会认知的能力。但是,Gallagher并没有反对温和的发展观(weak developmental claim),即认为儿童社会理解和互动的能力受限于心理状态概念的缺乏。领会到心理状态是如何促使行为发生将给儿童们一个更好或许远好得多的对于社会环境的理解,并且使他们能进行更为成功的社会互动。
事实上,温和的发展观正是先天论者所主张的。先天论者认为我们生来就拥有一些心理状态的概念,而且有对心理状态给予选择性注意的先天倾向。这一固有的心理状态可能并不是健全的,但是当伴随有对于心理状态的选择性注意后,儿童对于心理状态的学习与掌握就会加快,也就获得了更好的对于社会互动的理解。较之先天论者,那些反对人们拥有先天性特定概念和对心理状态选择性注意能力的经验论者可能更难去解释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特征。但是我并不认为有理由去认为经验论者坚守强硬的发展观。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持Gallagher所反对的那种强硬的发展观。即使是在Baron-Cohen所列举的八种需要读心能力的行为之中,虽然这看上去像是支持了强硬的发展观,但也仅仅是表象而已。他的观点承认了这八种行为的充分发展需要发展完善的读心能力。要充分理解这些行为,个体必须在发展了读心能力后才可能够读懂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但这并不是指在掌握心理状态概念之前儿童是完全不能参与到这些行为之中的。Baron-Cohen也并没有比Gallagher站在更强硬的发展观立场上。所以,Gallagher对发展观的反驳犹如攻击稻草人(a straw man argument)。Gallagher并没有认为读心中温和的发展观是错误的。
事实上,Gallagher关于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描述就取自于Baron-Cohen对于读心的先天论(nativist)、 模 块 论 (modularist)、 理 论 论 等[11]。Baron-Cohen提出了“意向探测器”(Intentionality Detector)、“眼动方向探测器”(Eye Direction Detector)等说法,顾名思义,Baron-Cohen认为这些都是先天的机制(innate mechanisms)使得儿童具有了觉察意图和跟踪眼动的行为倾向。这和Gallagher的原初交互主体性说很相似。Baron-Cohen还提出了“联合注意机制”(Shared Attention Mechanism),这一能力稍晚得了到发展并使孩童进行联合注意的行为。Gallagher的次级交互主体性描述部分来自于此理论。在读心理论中,这些能力都属于心理理论的雏形[12],但在具身认知理论中,正是它们构建了我们理解他人的基本方式,而且不仅是在儿童时期,成年人也用这种方式。这就是两个理论的核心不同之处。Gallagher和其他具身认知论支持者认为这一理解他人的基本方式是非心理的、具身化的交互主体性。他们争辩道,读心的范围远比读心文献中假设的要狭隘得多。要想证实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的机制并不是心理理论的雏形,那么就必须证明读心并不是我们最为基本的且普遍使用的用来理解他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具身认知能够证明我们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少见的场合(比如遇到些非常古怪和难以解释的行为时)使用读心的话,那么具身认知的反驳也就成功了。这一关于读心使用范围的争论将在下文讨论。
三 读心的范围
读心的支持者们通常认为读心是我们用于理解他人的基本和普遍的方式。这就是读心的普遍观。许多关于读心的文献也以其重要性和使用的普遍性作为开头。比如上文我提到的Baron-Cohen所列举的八种需要读心的行为[8]4-12。虽然有些读心论者(或许是很多)将会不赞同Baron-Cohen关于读心的结构和细节的描述,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普遍性这一观点和其在日常交往中的重要性。而这对于具身认知论来说,却是其要击破的观点。即使解释和预测别人的行为需要理论化或模仿来得知他们的心理状态,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认知是否用预测(predicting)和解释(explaining)就能得到最好的描述?Gallagher提出了基于现象学的论点,这也意味着是对读心的普遍观持否定态度的(4.1部分)。Gallagher同样也批评欲证明读心是社会理解基石的实证研究(4.2部分)。心智哲学家和具身认知的支持者José Bermúdez给出了一个基于计算考虑的理论来反驳读心。Bermúdez认为人类社会互动之流畅恰是驳斥读心的普遍性一说的证据,因为读心反而是复杂、相对冗长的一个过程,以此作为我们理解他人的最基本方式恐怕太不明智了(4.3部分)。如果这些具身认知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这将对现有的社会认知描述很有威胁。
(一)现象学的论证
Gallagher提出了来自现象学的例子来反驳读心的普遍观。在理论论和模仿论中,我们都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去理解通常的社会互动⑧。在理论论中,我们观察别人的行为,并采用常识心理学的理论来揣测其心理活动并对行为进行归因和预测。而在模仿论中,我们则将自己比为他人,通过感同身受来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当然,这只是对这两个理论的概括性总结。Gallagher却认为我们日常的互动交往不需要解释和预测(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的介入。现象学告诉我们社会互动并不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理论化解释,抑或需要模仿⑨来复现诸如信念之类不可见的、抽象的实体[4][5][10]208-216。
当然,这一观点也不完善。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下采用现象学的解释是不必要的。大多数读心都被认为是无意识、亚个人层面的,而现象学在亚个人层面上无用武之地。Gallagher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对此他也进行了回应。的确,现象学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亚个人层面的运作过程,但可以间接地告诉我们,即:“现象学不能告诉我们,比方说,在对别人怒言的反应中是否存在内隐的(潜意识的)(sub-conscious)理论或者假装的信念。但一个仔细而具有条理的现象学解释应当能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怒言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否包括解释和预测这个人接下来将怎么做这个过程。如果其中的无意识过程可以经由现象学来表述是基于假想的心理状态的解释和预测活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和他人的交往就不适合用理论化或模仿来描述。”[4]如果无意识的读心过程的确正在进行的话,那么现象学的解释也应当是基于第三人称的解释和预测。现象学告诉我们用第三人称的解释和预测来描述常规的交互主体性的经验不是最合适的,因此,无意识的读心就不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的交互主体性经验之中。
Gallagher举了三个例子来证明我们日常理解他人的模式并不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第一,即使当我们理解他者的过程是有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通过推测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其行为。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普通的社会互动的例子:和一位同事的谈话。在谈话中,你真的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了吗?对其心理状态进行归因,然后据此解释和预测他/她的行为吗?现象学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在这个例子中,互动行为最宜被描述为是种快速的、实效的、评估性的理解⑩。我们的互动行为是快速的、流畅的而且显然不涉及对心理状态的归因,也不涉及根据这种归因再进行解释和预测行为的过程。Gallagher认为,倘若读心的确是处于亚个人层面的,那么现象学的描述就应当是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读心就不可能是这个例子所讲的那样。
第二,即使我们需要去揣测言外之意,并且得到了诸如这样的结论:A相信B有点儿不对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没有去假定一个被称之为信念的实体,然后将其归因于A。在文章第二部分所举的那个社会认知的例子恰是这样的情况。Jill并没有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来解释和预测Jack的行为,从而理解到Jack以为她有兴趣和他交谈。从现象学角度来说,Jill非常快地领会到了这一误会。更一般地,也就是说当我们必须去体会这样的言外之意时,现象学的解释是:我们采用了一种基本的、迅速的理解方式,而并不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
第三,当我们处于旁观者的时候,假设你正在偷听别人的谈话:
女:我要离开你了。
男:他是谁?
当听到这段对话时,Gallagher问我们是否是被驱动而去根据心理状态来解释谈话中的行为,或者是从评估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Gallagher认为即使当我们是处于第三人称视角来观察行为时,现象学也告诉我们,我们进行的是非常快速的、评估性的理解,而非因果性的、费力的心理解释和预测。
鉴于上述三个社会认知的例子,Gallagher认为读心并非是我们理解他人的模式,而且要有的话也很罕见。仅仅当实效性的、评估性的理解方式失败时,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才会发生。仅仅当我们处于不熟悉的状况或是碰见非常怪异的行为时,解释和预测的方式才会被使用。从而,Gallagher总结出读心的普遍观是错误的[10]208-215。
更为简洁明了地说,Gallagher的现象学论证包含两个主张:(1)欲证明我们通常的理解方式并非基于第三人称视角;(2)即便当我们处于第三人称的旁观者时,理解模式很少是解释和预测。
对于现象学论证的一个回应是,即使Gallagher是正确的:现象学能告诉我们正常的社会互动并非是基于第三人称的解释和预测,也不能排除现象学在这个问题上犯下错误的可能性。有大量关于错觉和内省性虚构(introspective confabulation)的实证研究数据(Gopnik,1993;Carruthers,2007,2009)表明,没有理由认为现象学对社会认知的解释比其他领域更准确。因此,这些实证数据至少让我们不能仅仅只依靠现象学来描述在亚个人层面运作的过程。
现象学的不可靠性是质疑Gallagher的现象学论证的理由之一。而现象学的完全无关性(total irrelevance)则又是另一个理由。一个人应该很容易拒绝Gallagher关于无意识的读心会导致意识的、外显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的主张。为什么亚个人层面的理论化和模仿应该兑换为普遍存在的、意识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Gallagher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读心中理论论和模仿论的争论事关社会认知中的结构和亚个人过程。但两个理论都没有涉及在日常互动中现象学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在读心中,包含一个过程:理论化和模仿,并且有其结果:解释和预测。总的来说,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无需是意识的,更别说是可用现象学来陈述的。只要读心的结果(对行为的解释和预测)是意识层面的,那么才有可能是现象学的,就好象我们的互动行为是快速、非心理的理解的产物。或许,这是解释Gallagher对于我们一般互动行为的现象学描述的一种方法。
我们日常互动行为的现象上的流畅性并不能确认理解他人的方式并非是读心的。现象学能告诉我们的是:互动行为看似(seem)是基于快速的、实效的、评估的理解。但是,由于在读心文献中所存在的疑问并非是关于这看似的理解,而是关于真正(actually)普遍互动行为的结构和亚个人层面的过程。因此,Gallagher对读心的普遍观的反驳并未成功(11)。
(二)科学的证据
在读心的文献中,有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持读心的发展观和普遍观,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便是错误信念的任务。在任务中,被试会看到一个名叫Sally的洋娃娃把一个玩具放到篮子中后便离开了房间,此时,另一个洋娃娃Ann来到房间把玩具藏到了碗柜里。被试则会被问及当Sally回来后,她会去哪里找那个玩具[9]。Gallagher却认为诸如这样的实验并不能证明读心就是我们最为基础和普遍的理解他者的方式。对此,Gallagher有三点看法。
首先,这些实验很明显是设计用来测试特定的或者相对而言少见的理解他人方式,也就是说是需要解释和预测的,因而并不能作为读心普遍观的证据。虽然,实验的确显示大约4岁的儿童能够对错误信念进行归因,并且正确地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Gallagher仍然认为就算儿童能够展现出这样的认知技能也不能证明他们在日常的互动中也是这么做的。解释和预测只是特殊的认知活动,并非我们通常的用于理解他人的方式。通常的方式是快速的、实效的、评估式的理解,是由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构成的。以上是Gallagher的现象学论证,Gallagher对读心普遍观的实验证据给予了否定。
其次,读心的实验是要求被试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理解行为的。回忆一下,在错误信念任务中,被试是要求以旁观者视角来观察洋娃娃的行为的。但是,第三人称的角度却不是我们通常的方式。Gallagher对此的反驳同样是现象学的。正因为我们平时并不是处于第三人称视角来理解的,故而以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实验来说明我们日常理解他者的方式也是不妥的。
最后,Gallagher认为这些实验测试的是被试意识层面的元表征过程。被试是有意识地、反应性地根据推测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客体行为的,但这种意识的、外显的思维模式并没有表明在亚个人层面发生了什么。如果关于读心的争论是聚焦在亚个人水平的话,那么这些涉及意识过程的人为实验并不会有助于解释亚个人层面的过程[4][5]。
在上述Gallagher对于实验的三个反驳观点中,第三个似乎是最为有力的。前两个观点有赖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他人的方式这一说法。对此,Gallagher的反驳仅来自于现象学。因此,Gallagher的前两个关于读心普遍观的反驳若真要起作用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证明第三人称视角——更不用说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解释和预测了——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他人的方式。Gallagher所需的不仅仅是声称这些实验是极度人为的,更需要的是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测的理解与我们日常的方式是有区别的。至今,Gallagher也未能证明这一点,而且在我看来,近期也没有对这一观点的很好的论证。因此,Gallagher的前两个对于读心实验的批评是不成功的。
然而,Gallagher的第三个用以支持亚个人层面加工的反驳却是对读心实验的一个强有力挑战。回想一下我对现象学论证的批评:读心中的争论焦点是关于支持读心的结构和亚个人层面过程,而意识层面的、现象学水平的事件并不能说明在亚个人水平上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并不能用现象学来作为主体间活动中亚个人过程的标志。在现象学的论证与用实验测试社会理解意识的、外显的过程来支持我们的亚个人过程之间显然存在冲突。如果我对Gallagher的现象学论证的反驳合理的话,那么可以初步认定,上述实验并不能支持亚个人层面的加工过程(12)。
如上,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现象学和读心的实验之间存在两个显著区别。第一,在现象学的论证中,Gallagher依靠的是从现象学角度来思忖亚个人层面加工过程的本质。而读心的实验并不依靠现象学。而且,他们以实验情景中特定行为作为某一亚个人层面的加工过程。其逻辑是如果存在一特定亚个人加工过程的运作,那么在一给定的实验中,被试就能表现出相应行为。比方说,如果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被试报告说Sally将会在篮子(而并非Ann将玩具挪到的碗柜)中寻找玩具,那么就能说明被试已经具有了信念的概念。因此,表现出的行为能够代表亚个人层面的过程。第二,这些实验并没有要求被试真正参与到意识、外显的元表征加工。回想一下我对读心的过程和结果所作的区分,错误信念任务只是要求被试报告对洋娃娃会看向哪里的预测,即实验要求的是读心的结果,而并没有要求被试去卷入意识、外显的加工。这一加工过程已经在被试观看实验场景时于亚个人水平完成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实验都要求的是读心的结果。
以上两点区别所要说明的是对实验的解读并没有犯与Gallagher的现象学解释相同的错误,也没有从意识的、外显的加工过程到亚个人、无意识加工不当的推断。
(三)计算角度的论证
José Bermúdez给出了反对普遍观的计算论证。Bermúdez界定了读心的狭隘性和普遍性两个概念,并且指出出于计算的考虑,我们更倾向于狭隘性的读心。其基本的思想是无论在理论论还是模仿论之下,解释和预测都是复杂、冗长的认知活动。拿理论论来说,解释要求对观察到的行为进行分类,并应用一些基本原则将行为与心理状态、心理状态与其他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和行为联系匹配起来。一个人必须考虑众多情况来选择适宜的原则:该情境的背景是否恰当?有没有补偿性的因素?有没有指示该使用何种原则的线索提示?考虑到我们的社会互动包括了许多行为与心理状态都相依赖的个体,其要求相当量的计算,以及对接踵而至的使我们都能够成功进行社会交往的信念(belief)的扩展性处理[13]8-9。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的理解和社会互动却都是流畅的、简便的、迅捷的。在多数状况下,社会互动和包含大量计算的处理要求并不相符。
对模仿论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计算问题。在模仿论中,个体需要识别出导致客体行为的可能心理状态,然后通过自己的(离线)(offline)决策来执行这一心理状态,一旦这一可能的心理状态得到识别,便将输出的决策归因于客体,以作为解释和运用于预测。对于涉及众多人物和行为的社会互动而言,一个人必须首先识别出所有人的可能相关的心理状态,并同时进行模仿,到达与客体行为相符的解释,再用这一解释去模仿客体的决策。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通过自己的决策机制执行同时性的多重模仿是否可行?而且,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客体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是彼此依赖的。即使模仿论中的模仿和相互依赖性的模仿是可能实现的,它也会遭遇理论论中应用一般原则时相似的计算困难。无论是理论论还是模仿论,对于计算复杂性的担忧都无疑让我们质疑读心是否是理解他者的基本、普遍的方式[13]8-12。
Bermúdez并没有把计算论证视为对读心普遍观的确凿否定,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社会认知的快速和便捷让计算复杂性成了一个负面特征。Bermúdez指出:“我们大多数的社会互动都涉及对他人行为快速的调整适应,然而常识心理学的解释却是一项复杂和冗长的工作。”[13]8理论上得出的读心是一复杂、时间上拓展的过程,而实际的日常互动并不见得如此,因此,认为我们的日常互动行为是读心的一个例子是说不通的。
然而,我却认为这一计算的论证也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亚个人水平的过程当然在计算上要比个人水平复杂,但这并不表示是对亚个人加工过程理论的反对。比方说,视觉和语言的加工在计算上就极为复杂。以视觉计算为例,其包括了在视网膜细胞上的光传导过程,以及从视网膜输入到对远距离刺激可用的三维表征的算法转换过程[14]。这一过程涉及了对光亮的觉察、光的强度、物体表面的反射系数、物体的形状和朝向以及它们在视野中的连续变化。根据Bermúdez的推理,既然“看”这一动作是非常迅速和方便的,与上述的计算要求毫不相干,那么我们就应该质疑关于视觉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即使你不赞成像Marr这样的视觉理论,那么你也必须承认视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加工过程,但在意识层面上,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快速、便捷、没有痕迹的。这同样能被用于读心过程。计算的复杂性和现象上的便捷性以及社会互动的瞬时性之间的反差,就其本身并不是否认读心是我们通常用来理解他人的方式的证据。因此,计算论证并不能证明读心的普遍观是错误的,即并没有证明读心极少被使用。
对Bermúdez的计算论证还有一个更深切的担忧。对于一些认知过程而言,其加工的信息范围实质上是没有限制的。Jerry Fodor将其称之为等效加工(isotropic processes)[15],原则上可以对任何领域的相关信息进行读取。鉴于相关的信息原则上是无限的且可以来自任何领域,对理论论而言,它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在特定情况下可应用的一般原则;对模仿论来说,问题是怎样才能识别出导致行为的可能的心理状态,因为与之相关的信息原则上也是无限多的且可以来自任何领域。Bermúdez也讨论过这一担忧,但他认为这与他的计算观点是毫不相干的[13]8-11。这种担忧并不是关于计算复杂性的问题,而是关于判别哪些因素是与读心的等效加工相关的问题。如果读心的确在社会认知中占很大部分,那么问题就当是我们如何才能决定哪些因素能成功地加入到读心中。以上就是框架问题(the frame problem)的一个版本。
此外,具身认知的支持者还可能坚持认为框架问题只是认知主义解释的一个副产物,认知主义原则上把社会认知大致等同为读心。一个具身认知的理论家还会认为对于具身认知来说,框架问题是不会存在的。具身认知对社会认知的解释背景就(差不多)是Gallagher的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这些理解他者的具身方式并不会产生等效加工的问题,因而这也是接受具身认知的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好理由[16]。如果找到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具身认知将能回避框架问题,那么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然而,也不能肯定框架问题对于具身认知的影响就小于读心。具身认知必须要解释我们怎样才能决定哪些因素与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是相关联的。具身认知必须要解释究竟是哪些脸部表情、眼动、表达性动作等与理解他人有关,很显然的,并非每一个表情、眼动都是有关的。对于哪些具身线索与理解他人有关并不存在推理上的先验(a priori)限制[17]。而且,无论具身认知用什么策略化解框架问题,在原则上,读心都可用它化解框架问题。因此,框架问题也不能给出让我们偏向具身认知的确凿缘由。
框架问题是个难题,在此我无法给出解决办法。然而,对此我还是有几点要评论。首先,如果框架问题真是个问题,那么其对读心反驳已超越了读心的普遍观的范围。普遍观加重了对框架问题的担忧,但即使考虑到相关因素是无限的,而且可能是来自任何领域,根本的问题依旧:我们是否真的能成功地实现读心。其次,我也不确定这个问题的层次究竟有多深?据我所知,没有人否认读心的存在。具身认知只是认为读心并不像其假设的那样广泛、普遍,但框架问题关心的是既然读心是等效加工的,那么在真实情况下读心的过程还是否可能发生?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存在,我们就该质疑读心到底存在与否。但是,正如Bermúdez表示的∶“这点可以说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确从事了常识心理学的解释……问题是这是否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社会认知模型。”[13]3我们大多都同意至少在某些时候读心确实发生了,这点让框架问题不能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最好将框架问题理解为要去解释我们是怎样确定与读心加工相关的因素,而非挑战读心的存在。我们用某种方式限制了相关的信息,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有限理性的、资源约束(resource-bound)的生物。我们无法预见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即使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无法将它们全部记住并且仍然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互动。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某种方式将信息缩减至能够注意的范围,在限定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决定哪些信息是有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上文提到过的Leslie的心理理论机制。心理理论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注意机制,它能够调用先天性的概念,使个体更易于注意心理状态,而非其他事物。如果Leslie的解释合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先天性地关注与读心相关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心理理论机制是一种内置的启发性装置,它能够将信息范围限定至读心相关的范围。心理理论机制并没有直接决定心理状态的内容,但它的作用在于限制等效加工从而决定与读心相关联的因素,从而有助于限制决定特定心理状态内容的过程。这种启发式的装置并不总是带来成功的结果,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只使用启发式来决定相关因素,但上述这些事实是与读心的解释一致的。这一解释同样能够缓和Bermúdez对于读心计算复杂性的担忧。据此,我们就不必侦测、追踪在复杂社会情境中的所有信息了,只需对其中一些信息给予关注。因此,Leslie的理论虽然也不是最完美的,但却合理地对付了来自框架问题的挑战。
结 论
我已经论证了现象学的观点并没有对读心的普遍观构成威胁。而且,对于读心实验解释的反驳也没能对普遍观的支持造成破坏。同样,我也论证了计算的观点也不能对普遍观构成威胁。对于框架问题所提出的等效加工,它对我们是如何将信息限制到与读心相关的部分提出了疑问,但因为这一解释性的挑战并不是只针对读心的,它也不能算是对普遍观的反驳。
具身认知对普遍观的反驳最终还是失败了,它并没能证明读心仅在少数情况下发生。事实是,对读心的发展观的反驳同样是不成功的。回想一下,读心的发展观有强与弱两个版本。我已指出具身认知对于发展观的反对犹如攻击稻草人。Gallagher并没有反对温和的发展观,而这种发展观实际上存在于文献中。读心的发展图景与具身认知的发展图景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儿童在社会理解过程中使用的机制是心理理论的原初形式,后者则认为这些机制构成我们理解他人的基本方式,其不仅存在于儿童早期,也存在于成人之中。欲证明这些机制不是心理理论的原初形式,就要证明读心并不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完全发展的社会理解能力之中。对读心普遍观的反驳就要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种反驳却失败了,这也导致对发展观的反驳也是不成功的。因此,具身认知对读心的反驳最终是失败的,同样它也无法表明整个对读心的研究领域正被严重误导。
注 释:
①具身认知存在强硬的和温和的两个版本:一些人认为身体和环境构筑了认知,因此认知科学当仅关注身体及其环境,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身体和环境在认知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认知科学的重点应该是身体及其环境。关于具身认知的不同主张可参见:Shapiro,2007和Wilson,2002。
②我将会在下文详细说明什么是读心。读心的基本意思就是我们通过领会他人的心理状态来理解他人、和他人互动,同时在此心理状态的基础上运用这一理解去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
③但请参考Povinelli和Vonk,2003,对于Tomasello观点的批评。Povinelli和Vonk认为Tomasello过多地将心理理论归到了黑猩猩上。
④Hutto(2004)在Gallagher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发展观点。我对Gallagher的批评同样适用于Hutto。可参考Hutto和Ratcliffe,2007。
⑤参见Goldman,2006;Gopnik和Wellman,1994;Leslie,2000;以及Nichols和Stich,2003所提出的类似观点。
⑥在读心文献中,通常的论述是4岁左右儿童可以通过标准的错误信念测试。然而,却有很好的证据显示更为年幼的儿童能够通过改良版的错误信念测试。通过减少标准错误信念测试的要求,更年幼的儿童能够成功地对错误信念进行归因。15个月左右的儿童就能够通过非语言的、观察违背的错误信念任务(参考Onishi和Baillargeon,2005)。对于真实的社会性技巧超出了实验测试的理解范围的担忧,可参考Davies和Stone,2003。Hutto(2004)在Gallagher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发展观点。我对Gallagher的批评同样适用于Hutto。可参考Hutto和Ratcliffe,2007。
⑦比方说儿童在2岁左右表现出的假装行为,我认为纯粹依靠原初和次级交互主体性来解释就不可行。具身认知还有待于去解释一个儿童假装时发生了什么,比方说,他的宠物蜥蜴晒伤了。对于假装行为的系列探讨,可参考Funkhouser和Spaulding,2009。
⑧Gallagher使用了基于“第三人称”的互动(‘Third-person’based interaction)这一术语。他用此来作为“第二人称”互动的对照。比如说,“在一个第二人称的对话场景中,我们虽然的确可以默认性地遵守对话的特定的规则,但我们对此的加工似乎不包括一个分离的或抽象的第三人称的因果解释。”(Gallagher,2001,p.89)。我觉得很难找出非隐喻性质的第二与第三人称的互动。对于这一术语最合理的解释,我能想到的就是从陈述方式上来说明。以阅读为例,基于第三人称的互动就好比一个第三者(有限知晓的)的旁白叙述,讲述者是故事的外在观察者。第二人称的互动则像一个第二人称的叙述,叙述者直接对主人公对话。这一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有些晦涩的。然而,因为这一术语在Gallagher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没有更好的替代词的状况下,我将依然采用这一术语。
⑨模仿论者Jane Heal非常支持对于第三人称互动的批评。她以相类似的方式批评了理论论,并且提出了一种和Gallagher的观点相似(在某些方面上)的模仿论。可参考Heal,2004。因此,也不是所有的读心描述都坚持具身认知所要批评的那个第三人称的解释。
⑩快速、实效、评估性的理解是一种在原初与次级交互主体性解释下所描绘的理解。
(11)可参考Davies,2000以及Stone和Davies,1993,有关现象学解释和亚个人加工过程关系的一个有趣讨论。
(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Gallagher对读心实验的批评。假定现象学可告诉我们亚个人过程,奇怪的是他认为测试意识、外显过程的实验却不能证实在亚个人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1]Lakoff,G.and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
[2]Leslie,A.‘Theory of mind’as a mechanism of selective attention[M]//M.Gazzaniga(ed.).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2nd edn.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3]Gopnik,A.and Wellman,H.M.The theory theory[M]//L.Hirschfeld and S.Gelman(eds).Mapping the Mind:Domain Specificity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4]Gallagher,S.The practice of mind:Theory,simulation,or interaction?[J].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001(8):83–107.
[5]Gallagher,S.Understanding problems in autism:Interaction theory as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of mind[J].Philosophy,Psychiatry,and Psychology,2004(11):199–217.
[6]Nichols,S.and Stich,S.Mindreading:An Integrated Account of Pretence,Self-Awareness,and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7]Tomasello,M.,Call,J.,and Hare,B.Chimpanzees understand mental states—the question is which ones and to what extent[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3(7):153–156.
[8]Baron-Cohen,S.Evolution of a theory of mind?[M]//M.Corballis and S.Lea,(eds).The Descent of Mind: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ominid 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12.
[9]Baron-Cohen,S.Theory of mind and mutism:A fifteen year review[M]//Baron-Cohen,H.Tager-Flusberg and D.J.Cohen(eds).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2nd ed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0]Gallagher,S.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1]Baron-Cohen,S.Mindblindness:An Essay on Autism and Theory ofMind[M].Cambridge,MA∶MIT Press,1995.
[12]Goldman,A.I.Simulating Minds:The Philosophy,Psychology,and Neuroscience of Mindread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Bermúdez,J.L.The domain of folk psychology[M]//A.O’Hear(ed.).Mind and Pers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4]Marr,D.Vision: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M].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83.
[15]Fodor,J.The Modularity of Mind[M].Cambridge,MA∶MIT Press,1983.
[16]Dreyfus,H.L.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M].Cambridge,MA∶MIT Press,1992.
[17]Haselager,W.F.G.and van Rappard,J.F.H.Connectionism,systematicity,and the frame problem[J].Minds and Machines,1998(8):16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