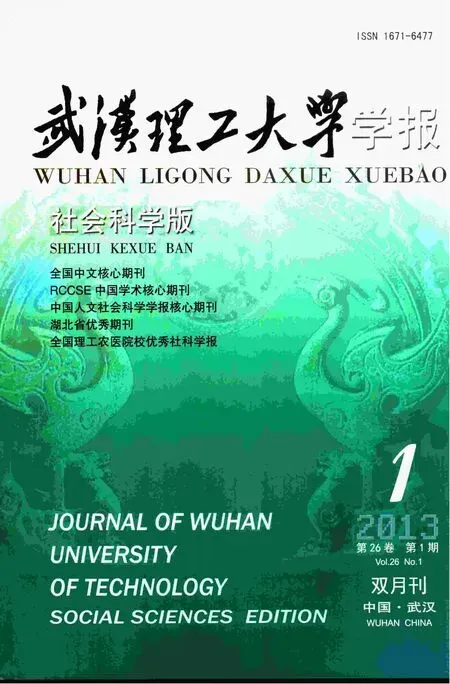农村土葬之“弊”:事实抑或话语
崔家田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洛阳471022)
我国推行殡葬改革已经行之有年了,但是对其效果的评价官方与民间却各有不同,甚至大为迥异。近年来殡葬改革的方向、方式更是引起了诸多讨论与质疑,双方辩驳,非难,多有争论①。长期以来,土葬之“弊”既是火葬论者和有关部门进行殡葬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火葬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官方政策批评者乃至反对者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概略来看,现实中火葬论者(更多时候他们只是火化论者)对于土葬弊端的指责主要集中在文化上的“迷(信)”(也常被指为精神污染),经济上的“费”(包括对公民的经济压力与国家的资源压力:土地、木材、财力、时间)以及秩序上的“乱”三个方面②。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究这些指责就会发现,其实它并非如火葬论者所宣称的那样严谨周全。虽然,各种报章杂志、网络论坛对这些火葬论者的部分指责也偶有或多有涉及,但是学术界却几无人对之进行撰文探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学术性质的研究与回应,从理论层面上作一系统阐发。这种针对火葬论者的指责无“理”可讲,有“理”不讲与有“理”讲不出的研究状况,致使现今充斥于媒体与网络的官方政策批评者乃至反对者的论说多是一些基于粗浅观感甚或泄愤性质的感性肤浅言说。这些非学术性质的回应不仅不能推进人们和相关机构对于殡葬活动的深入认识,影响或者改变现实的殡葬改革进程,而且使得土葬论者在与火葬论者论战的开始就成了“弱势”群体(无“理”可讲与讲得无“理”)。这就使得火葬论者对土葬的上述指责成为一个双方都要接受(尽管土葬论者不愿意)的几乎不言自明的论题,引领着讨论的方向和进程——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便是官方政策批评者乃至反对者的论说也常常跳不出发展主义的窠臼,而那些跳出发展主义窠臼的反驳或者批判常常又被官方或者学术界认为是“无法理喻”的奇谈怪论或者成为根本无法“出声”(不敢或不能出声)的“地下私语”③。
对发展主义的承受有意无意地成为双方讨论和言说的前提与潜题,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论战进程与结果,甚至会更加固化火葬论者群体中形成的对土葬和土葬论者的刻板印象④。为了更好地推进殡葬改革理论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基于多元话语立场与农村殡葬改革的调研实际,仅就农村土葬相关问题略陈管见,抛砖引玉,以期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农村土葬问题。
一、打破概念迷思与禁锢,正确认识丧葬活动的仪式与信仰性质
长期以来,火葬论者对土葬在文化上的一个指责就是“迷信”,或者“封建迷信”,或者将之直接归结为“陋俗”、“落后”之类,所指责的大体上为烧纸、烧香、看风水、做道场等“迷信”,乃至磕头、跪拜等“不文明”行为⑤。“迷信”这一指责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土葬的丧仪部分,但这一指称却似是而非。因为对于村民的这一活动,可以作出不同方面与意义的多维度解读,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迷信”。对于“迷信”的界定,长期以来几乎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共识:信了“不该信”的东西。这是一种从对象角度来进行界定的方法,但是对于其中何种对象“不该信”的筛选和排除有时候却不尽然都是出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权力”和“利益”更是掺杂期间,甚至某种所谓的“客观知识”本身就是某种权力的后果或效应。这就导致所有从对象角度界定“迷信”的定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它只有放在一定的时空和具体的环境中才可能被理解。
杜赞奇在其关于近代中国反宗教运动的研究中就曾发现,在这种“话语”的变化中(由“宗教”到“迷信”)其实更蕴藏着另外的“深意”,即“主张现代化的改革者很快就看出,民间宗教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财政来源,而且取得这些资源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1]。我们从殡葬改革推行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无论如何它都为相关部门开了一条“财路”——无论村民是违反(罚款)还是遵行(火化费用)。至于“封建迷信”的指责更是严重误读,虽然作为约定俗成的日常惯用语使用无可厚非,但是就学术角度而言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且不说其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仅就其组合(封建+迷信)即不能不仔细推敲。这一指称背后隐藏的“封建=前近代=落后”语用范式更非严谨之论,实为政治话语[2]。“封建迷信”这一独断式的界定背后是对自身的过度自信和全知全能角色的设定。
众所周知,全知全能的角色似乎只可能在宗教信仰领域中存在。笔者认为,从程度上来界定“迷信”比从对象上来界定似更为合适,尤其是在民间生活领域。如果从程度来界定的话,“迷信”就是因信而“迷”,再因“迷”而“唯(唯独、唯一)信”。简单来说就是信仰某种事物到了“迷狂”的程度——以为任何事情只要做了其所信奉的某种行为之后,就不用再去作其他的努力便可以成功或者实现。若我们以此视角来看待“迷信”,便会得出与火葬论者大为迥异的结果。再者,按照人类学者对于人类行为的划分,人的行为可以分为实用(非仪式行为)、沟通(仪式行为)、崇奉(仪式行为)的两类三层次结构[3]。在土葬中,以火葬论者指责最为集中的所谓“迷信”行为(烧纸钱、纸扎与看风水)而言,这些行为只是一种典型的仪式行为乃至祈福行为,而多不是或根本就不是“迷信”行为,更多的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一种人们安顿身心的程序与心灵的内在沟通和寄托,或者说对自己及家族的人生与生活进行文化疗治的一种特殊方式,甚或可以说是中国人追求和谐与均衡的宇宙观的一种具体体现[4]。
此外,“迷信”这一指称里边还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承不承认诸多民间生活行为与民间仪式的信仰性质或者说宗教性质的问题。现在国家倡导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一般指的多是那些制度化宗教,而作为汉人围绕生活而形成的那些信仰(如祖宗崇拜、多神信仰、生死信奉)却不被承认。这种以外在形式而不是内在内容作为判定标准的方法与政策是民众信仰与“迷信”指责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这些包括土葬信奉在内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信仰呢?只不过这些信仰与那些改革者所熟知的信仰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它具有变化、多元、信(仰)与生(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特点,而不是像其他宗教那样从生活之中单独抽离或者分立出特殊的时空环境要素或要求。
简而言之,如果从多元话语分析立场来看[5],改革者对于土葬“迷信”的指责是立基于对“迷信”特定含义界定上的,只有在他们所界定的“迷信”范围内,它才可能成为“迷信”。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迷信”的指责多是一种“话语性”的存在,而不是“客观事实”。另外,对“迷信”行为进行批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无神论”的倡导——虽然它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言说或者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是它却不符合民众生活的客观实际。在现实中,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人们在意这些所谓“迷信”仪式的恐怕比不在意的要多(虽然仪式的规模、程序会因人因地因时而有所变化)。同样,丧葬活动中“迷信”所可能带来的“精神污染”也似是而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火葬论者所言说的“迷信”恰恰可能是汉民族的自性。就此而言,任何人都不应该用一个要求特殊人群的要求(如信奉无神论的要求)去强行要求普罗大众,进而强制要求他们破除自身所拥有的所谓“陋习”。或许真正理性的做法应该是移情入境,作同情之理解,承认其正当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再徐图改进其内容,控制其规模。
二、转变狭隘和单一视野,以人为本,全面看待农村土葬之“费”
土葬“浪费”(非“理性”消费)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显而易见、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具体而言就是土葬占地、用木、浪费钱财、耗费精力与时日等⑥,但是这种对于农村土葬的指责,实际上却是火葬论者言说中内生的逻辑和约束条件下的一种话语陈述,而并不一定就是“客观事实”,或者说这一“客观事实”的产生有赖于它内藏玄机的论述方式以及特殊的视野。
首先,火葬论者对土地及相关环节经济利益高度集中的关注限定了他们只寻求对农村殡葬问题的特定回答(强制推行火葬)。在火葬论者的视野中,土地的多种用途与价值被压缩为单一的经济价值,经济以外的价值都被剥夺或者视而不见——土地成为“单一的商品生产机器”,而实施殡葬改革,特别是火葬的各种外部化成本却避而不论,如农村社会文化生态的破坏,能源浪费,大气污染,对村民身心的戕害,基层矛盾的增加,腐败的滋生,违宪乃至国家形象的败坏等等。同样,土地所具有的任何生存或生态的价值及其由此而生的情感价值也都被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村民的伦理与情感用地也被自近代以来的各种批判视为“落后”与“封建”而失去了存在的资格。正因如此,“一席之地”的数字意义顶替了“一席之地”的伦理与情感价值,而具有了让“国家”管控的价值。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是土地对于村民而言不是像火葬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只具有经济价值与数字意义,而是具有多种或多元化的价值。人们对土葬的选择来源于人对土地的依赖和特定环境中人生观的文化约定,它植根于现实的生存体验和活生生的情感积淀。土地对于村民而言不仅仅具有生存(或商业)价值,更具有情感价值。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会不热爱土地,依恋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土地是生活的来源,更是一生操劳的所在,埋在土里,心里踏实自然。村民所言说的“吃土还土”与坚持“入土为安”以及不少人持有的“落叶归根”的逻辑或者就在于此。
其次,在火葬论者的论述中看似“科学”、“客观”的具体量化的陈述,同样存在诸多隐秘。在有关殡葬改革的相应论辩中,数量陈述是火葬论者论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也是他们最为看重的论述推行火葬必要性的杀手锏⑦。如经常有论者论述“死人与活人争地”或者公布与展示杞人忧天式的科学占卜——“多少年以后将无地可耕”的恐怖前景[6]。这种貌似“科学”、“客观”的数量陈述虽让不少人深信不疑,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火葬论者根本没有深入生活进行相应的调查,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这一情况的发生与无视村民所拥有的“本土知识”和村民的能动性有深刻关联。民间自有一套新陈代谢的知识体系,并不像火葬论者想象的那样“愚昧”和“顽固”:那种遍地坟墓的境况并没有出现便是一个明证。
第二,火葬论者的量化测算与节省成效也可能同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一个明显的反证就是测算中“节省”的土地都归到可耕地之内。这种量化测算不仅忽略了具体地貌的限制,还忽视了其他的各种外在因素的限制。这种只遵照了数字逻辑规则的测算,没有认识到农民在具体环境中所拥有的与他们生活更为紧密的有关土地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7]。据有关学者根据火葬论者测算口径进行的计算,所谓的土、木消耗实在是不值得大惊小怪[8]。另外,若考虑到土葬多可利用非可耕地(荒山野地)及可对旧式土葬加以优化改进⑧,则火葬论者所谓的“浪费”几可以大部甚或完全规避,姑且不论人死后是否有权占用部分土地以及实践中土地绝非仅具经济价值这一事实。从实际来看,土地资源浪费最大的地方恰恰不是土葬的继续,而是各种规划导致的浪费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导致的可耕地减少。
总之,评判者所持有的特定视角及判定规则是“事实”生成与命名(如“浪费”)以及由之而来的价值判断的前提。就此而言,即使是所谓“客观事实”的呈现同样是在评判者自己所秉持的一套话语系统之内的“自言自语”而已。事实的判定以及意义的宣称并不一定就是那样的“客观”。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丧葬具有多重社会意义,而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评判。对于土葬之“费”,在殡葬改革中我们要做或能做的应是适当节制土葬活动的经济表达,使之能够“发而皆中节”,而不是完全取缔这种表达与选择性计算火葬成本以编织强制推行火葬的理由。同样,节约土地等自然性维度的声称也不应该是殡葬改革唯一或主要的目标与目的,尽管火葬论者那些不仅有意夸大而且还内藏玄机的量化核算是多么符合非现实的数理逻辑。因为对于任何被规划被建立和合法的社会生活形式,人们应该考虑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其参与者的能力、知识和责任”[9]488,而不应是火葬论者所言说的单纯数字成效的取得。
三、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辩证认识农村土葬的可控后果
对农村土葬后果的再一个指责就是在秩序上的“乱埋乱葬”及由此滋生事端所导致的“无序”[10]。这种指责主要集中于社会与自然两个方面。社会方面的指责主要集中在由于土葬选址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祭奠可能引发的消防安全问题,土葬可能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以及丧葬活动中官员借机敛财,丧仪规模超标等与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社会乱相,也即“社会景观秩序”的破坏;自然方面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乱埋乱葬”中的“无序”,因为它一方面破坏了火葬论者信奉的“规划美学”与自然景观,一方面牵涉到了火葬论者对于“效率农业”的独特信仰。
就土葬对社会景观秩序所可能造成的破坏而言,多可以通过相应的举措来进行调整。如由于土葬选址引起纠纷造成的社会失序,可以通过建立公益性的集体墓地并按照死亡顺序进行安葬来解决。再者,墓地选址纠纷虽多同风水等“落后”观念有关,但纠纷发生多是因当地或者事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压迫性或对抗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土葬本身。土葬选址只是一个由头与借口,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况且这类纠纷也并不是其他葬法无法产生的。祭奠引起的火灾或祭奠时“引火烧身,致人死亡”的新闻则是一个忽视了民众祭奠过程中自有约束机制的选择性报道。就丧葬活动中出现各种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不正之风而言,乱象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操持丧葬活动之人,而不是取决于丧仪与土葬。况且土葬之仪也是可以改进加以删减的。在实践中,村民也自发地进行着革新,并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故而,此类问题的发生即使涉及到土葬中的丧仪部分,也可以通过丧仪的革新而解决。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不能成为必然推行火葬的理由。一方面这不是土葬所特有的问题,火葬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卫生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对遗体进行消毒处理来解决(特殊情况可另外处理)。就土葬自然方面的“无序”而言,实际上主要是由于火葬论者用单一的“自然地理”观而非“文化地理”观审视土葬所致。若就“文化地理”而言,所谓的“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地方的坟墓是“乱”埋“乱”葬的(最多也就是“散”而已),都有其内在秩序。只不过这种秩序与火葬论者的“规划美学”或“政治美学”要求的秩序不同而已。火葬论者注重的是土地的景观意义,而村民注重的则是土地多重价值的使用以及文化地理环境的营建。在火葬论者看来的“乱”并不妨碍土地功能的发挥和乡村社会制度的运行,村民在这其中反而与自然与土地形成一种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此处火葬论者所谓的“乱”也是既定原则下(“规划美学”)的选择性论述,并不见得是多么“客观”。在村民看来它也可能是“美”的,而且这种所谓的“乱”也可以通过制定相应举措进行控制(如建立集体墓地)。对于土葬影响机械化作业或者可能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运作的指责则涉及到火葬论者对集体化“效率”的迷恋与独特生产力形式的“信仰”。就现实而言,对土葬影响机械化作业可以有诸多办法进行调整(如深埋等),农业集体化设想则更是不仅与现实不符,同时其也有自身局限性。因为就现今情况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长期政策,土地的分割使用也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事实。土地的分割使用实际上对于土地地力恢复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都有重要的作用。从理论层面来讲,火葬论者的“信仰”多植根于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及其可能的商业价值与特有生产方式的崇拜——只有规模化集体化的经济形式才能提高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现实中或者潜意识中,工业化发展程度虽被视为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而被加以使用与解说,或被视为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与创建新生产关系的改革而备受青睐、拥护和“政治正确”的眷顾,但是这种大规模改革与改制的社会后果,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其成本,或者说社会生态代价却极少被纳入思考的范围。这种现代科技控制的规模化、集体化,并着眼于生产效率和农作物商业价值的“高效农业”,不仅使得作物自身的机能变得更为脆弱,缺乏对多样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得不靠使用农药及各种无机肥料来维持生存,更重要的是它对生态循环及物种可持续性的直接与间接的毁坏。这些后果将会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正如斯科特所言:“工业模式可以应用于农业的某些方面,但不是全部。然而实际上它们被不加区别地作为教条而不是作为需要持怀疑态度加以考察的科学假设,到处应用。那些现代主义者对巨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标准化的大众化产品以及机械化的信念在工业的主要领域已经形成了霸权,从而使他们相信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完全被应用于农业。”[9]261而实际上,工业化农场超越一般生产者的优点在其他方面,而不一定在或者不在“效率”方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政治影响和销售渠道。它们失去了灵活性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补偿的是它们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9]263
总之,自命正确、先进和“污名化”他者是火葬论者和有关部门建构论述自身相关实践的合法性及自身拯救者形象的主要自我赋权手段。火葬论者或有关部门在殡葬改革过程中对现实生活的误读和片面认知根源于他们所拥有的“现代知识”、“科学知识”的排外性与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就知识体系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现代知识”不能理解或综合其模式之外的知识——他们系统和概括的知识是在以静止和短视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为代价的前提下取得的[9]56。消灭土葬推行火葬的规划理想,“并不是对社会全面观察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有局限性的观察的结果,并且常常是大大夸张了他们所最重视的目标的结果”[11]。它虽令人赏心悦目,但这种以“国家”的名义与形式呈现的对村民个人生活的“爱”实质上却是一种十足的“哀(粗暴干涉)”。就现实利益而言,火葬论者和有关部门对民间本土知识的拒绝或有意忽视——不屑或不敢于理解多元的文化现实,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上的傲慢与“致命的自负”,更源于他们特殊的部门利益追求。因而,农村土葬“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实为火葬论者基于现实利益的“话语建构”或者说“污名化”策略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事实”。因为对农村土葬指责中的“迷”、“费”、“乱”不仅不实或不确——或误指,或夸大,而且“迷”可导、可纠,“费”可缩、可避,“乱”可改、可控,并非像火葬论者想象的那样固化而不变。因而,这些似是而非的指责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有关部门在全国推广乃至对村民强制进行火化的理由。正如已有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火葬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出现“既不是某种预先发生的社会变迁或者社会需求的结果,也没有以一般的方式‘反映出’某种新的现实——诸如土地匮乏、公共卫生的需求或‘世俗化’”,它只是“通过主张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安置死者,而使得一种政治性的和广义上文化的规划在竞争中获得了文化权威”[12]。在这里,我们无意为土葬或者火葬的优劣进行申说、辩护,只想将火葬论者论述中存在的隐秘揭示出来,以供各方参考。事实上,那种土葬之“美”的言说或者火葬之“坏”的论述都有相应的局限,火葬更不是像火葬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先进”、“科学”与“完美”。因而,相关部门应有该有的自知之明与足够的谦虚与自制,这样才不致导致“特定知识或者世界观衍生的权力滥用,转而制造人民的另一种受苦与创伤而不自知”[13]。在人文世界中,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恐怕都没有单一的方式,更不用说那种借助于权力强制推行的“以王法易风俗”的方式。在人文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方式似乎从来就是而且也应该是多元的。故此,有关部门在推行殡葬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真正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在地化”地切实比较各种可行的改革方案,全面辩证地看待农村土葬,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
注释:
① 可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全国殡葬改革论坛”的书面发言:《坚持殡葬改革方向,完善殡葬管理 制度》(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wzx/fzxw/200908/20090800138747.shtml,2009-08-26)。
② 此类言词不胜枚举。可参见《人民日报》与民政部门主办的《中国社会报》、《中国殡葬报》、《中国民政》、《社会福利》等媒介上刊发的相关报道,以及民政等相关部门出台的有关殡葬改革文件中对土葬的定性。近期的可参看《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0)》(朱勇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中相关部分对土葬的定性与火葬的肯定。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可参见《推进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纪念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40周年》(多吉才让撰,载《人民日报》1996年4月29日第3版)或《李学举部长在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李学举撰,http://preview.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flhshsw/200711/20071100003365.shtml,2007-11-09)。
③ 如张存义为代表的火葬政策批评群体就长期很难“发声”,相关文章很难甚至无法在刊物上发表,只能通过发公开信,给国家相关部门与领导写信的方式,表达己意或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相关文章或意见即使能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也多是打擦边球或者以关爱国家政策的“纠偏、补漏”赞同改革的样貌出现,而不是也不能是以“颠覆”国家相关政策为前提。《关于当前农村殡葬改革的调查与反思:以河南为例》(崔家田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与《农村殡葬改革的法社会学思考》(汪俊英撰,《学习论坛》2009年第3期)两篇学术论文即是如此。其他社会各界反对火化的声音同样很难“发声”,只能厕身于网络上的各种论坛、贴吧与博客等处。
④ 在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举办的为殡葬立法征求意见的“全国殡葬改革论坛”上,不少民政部门及其外围组织的参会代表即视反对火葬政策取向的参会代表为异类,并对这些代表“螳臂当车”式的举动多有讥笑、讽刺之表态。
⑤ 因“迷信”本身在一些人的眼里就包含“落后”之意,故下文仅就“迷信”这一指责而谈。
⑥ 后文仅就占地、用木进行论述。因为后两者实际上都极具弹性,没有前两者那么“客观”,而且前两者也是火葬论者论述中最核心的论据。
⑦ 近来甚至有论者采用经济学的“科学知识”来为殡葬市场上的政府垄断地位张目。参见朱勇主编的《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282页。
⑧ 如可推广使用环保棺木或类似如回族人民白布裹尸的方式进行平原林地入葬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改进措施或者其他少占耕地及不永久性占地的丧葬方式。
[1]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7.
[2]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李亦园.田野图像[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375-377.
[4]李亦园.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J].汉学研究,1994,12(1):1-26.
[5]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2-298.
[6]舒 瑜.死者对生者的挑战[N].人民日报,1989-03-08(4).
[7]拉巴·拉马尔,让-皮埃尔·里博.多元文化事业中的土壤与社会[M].张 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陈华文.殡葬改革与农民利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6):48-51.
[9]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多吉才让.推进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纪念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四十周年[N].人民日报,1996-04-29(3).
[1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7.
[12]托马斯·拉奎尔.现代火葬的出现与亡者的作业[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6-65.
[13]蔡友月.在跨界中寻求知识的可能性与定位[J].台湾社会学,2007,13: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