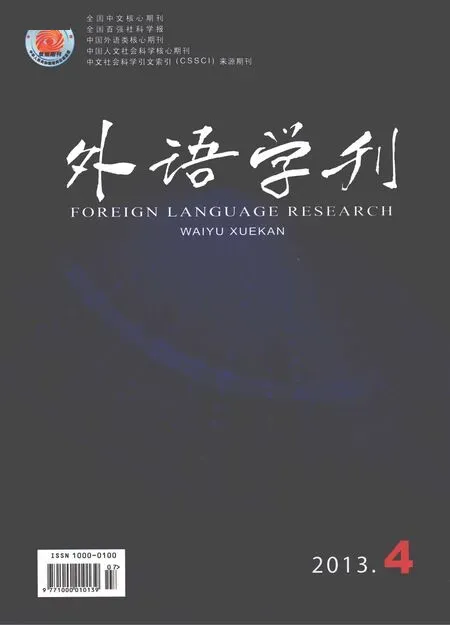基于相关术语意义的19世纪初期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研究*
刘 超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1 引言
同其他民族的自我意识相比,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问题突出、特点鲜明。Кознова(2007)指出,“俄罗斯问题”是为数很少的对俄罗斯思想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之一,俄罗斯文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中一直进行着身份求证。其中,哲学和文学占有特殊地位。作为俄罗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恰达耶夫命题(俄罗斯与欧洲)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首次表达,包含着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民族认同全部的张力和矛盾。
2 “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界定
在考察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之前,有必要考察相关术语。首先要考察术语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和 рус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以及 этнос与 нация。
этнос来自希腊语 ethnos。郝时远(2002)曾引用大量资料,全面分析ethnos:该词最初的意思是“一群”、“一窝”等;此外,可以指属于同宗、同血缘并且能够为切身利益施加政治压力的群体,尽管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实体,但是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物,该词是与“人民”(people)或城市(city)对应的族体(nationality)的称谓。在古代,该词还有“部落”(tribe)或“种族”(race)的含义。随着历史发展,特别是在拉丁化过程中,这个词的语义不断扩展。在纪元后的几个世纪里,该词用以指称“非希腊部落”。随着“希腊化”的影响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以及基督教的兴起和内部分裂、东方”蛮族”的迁徙、伊斯兰帝国的扩张及“十字军东征”,这一词语在传入英语后增加“异教徒”和“民族”含义。须要指出,ethnos在拉丁化并引入其他欧洲语言后产生词义的扩大或者转义,但是不论哪种欧洲语言,该词都是指那些在血统、族体、宗教等方面的”异己”群体。
到18世纪末,ethnos概念的使用在俄国还很有限。Бромлей(1983:8)认为,术语 этнография(民族志学)出现于 18 世纪末,этнология(民族学)出现于19世纪初。但是,当时只是限于“种族”和“部落”研究,该术语直到19世纪才接近现代意义。этнос的派生词 этничность 经常用来表示民族群体的识别特点及其认同的存在,不过首先强调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多民族特性。
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民族或者国家的认同,但是national identity经常译为“民族认同”。这种状况是源于西北欧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既有的领土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层面进行分析。俄语нация译成汉语也是“民族”之意,与英语词nation对应。从nation可以看出,нация指人类共同体依托于民族国家而形成的现代形式,将 нация理解为“国族”很贴切。在斯大林的“民族”(нация)定义中,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由人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也不是部落。例如“法兰西民族”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组成全体法国居民。列宁充分肯定斯大林对“民族”(нация)的定义(郝时远 2003)。这样,在谈到“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时,使用 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而不使用 русское этниче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我们就不再奇怪。русский этнос只能在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民族区别于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少数民族时使用。
在术 语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中,российский 一词由 Россия 派生,更具有国家政权的特征。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19世纪初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自觉的年代,俄国已经从昔日地处欧洲僻静一隅的小国发展成为疆域横贯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因此从主权独立性和疆域完整性来看,国家认同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与 рус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都指向国族层面的民族文化认同。
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可以看出,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中的 нация 一词也指向国家层面的“民族”意识。因此,在杂乱的俄语表述中,“俄罗斯自我意识”均指向国家或者国族层面的民族文化认同。这样,不难理解类似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俄罗斯的命运);Россия:в поиске себя(寻找自我的俄罗斯);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俄罗斯向何处去)等表述。
3 恰达耶夫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认同
作为一种心理机制,民族认同是对民族共同体自我同一性的确证,是个体对自己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认知以及由此表征出来的归属感和身份意识。它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建构过程。“民族心理认同是民族成员在与外界交往中形成和产生的,是对外界的一种心理反应,是一种心理上寻求自我保护和归属感的动力源泉。”(任新民周文2011)19世纪头10年的俄国受到反拿破仑战争胜利的外在刺激,民族意识空间高涨。俄国以强国姿态雄踞欧洲,其国人纷纷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能够见证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以及俄国伟大的事物。在此社会情境中,恰达耶夫抛出《第一封哲学通信》,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对俄国历史和文化提出超常规的质疑和挑战,要求实现俄罗斯民族认同转换,解决俄国文明的世界意义、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等问题。俄国旧有的因政治角色和军事强大而树立起来的传统民族“自我观”在恰达耶夫那里遭到解构。
按照马丁的“叙事理论”,“认同”实际上就是一种“叙事”,是一种“情节”,是可以按照需要重新组织、重新建构和重新阐释的叙事。同时,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叙事,民族认同对情节的遴选通常围绕着与“过去”的关系展开,即通过对本民族历史事件和文化特质进行叙事性的重构来实现民族认同的转换(Martin 1995)。恰达耶夫命题是俄罗斯“民族认同”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其认同模式围绕着历史叙事的重构展开。
3.1 俄国文明的孤立状态
首先,恰达耶夫站在基督教天命论立场上,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思想为指导,指出俄国被排除在天意之外,孤立于统一的人类历史,处于人类东西方文明的边缘和夹缝。以普遍形式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永恒的神的力量主导民族发展,相对于实现地上天国这一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来说,天意为既定的民族提出确定的个别目标。在恰达耶夫看来,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之一,但是这一规律不适用于俄国(Чаадаев 1991:16)。
民族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是一种互动过程:既有它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又有它受益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问题。这种互动的介质是“思想”。这种情形的互动在俄国没有形成。一方面,“这一绵延了数世纪的人类思想的神奇线索,这一人类精神的历史,它们使人类达到了如今的这个高度,可却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在其他国家早已构成交往之基础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仅仅是理论和思辨”(恰达耶夫1999:6)。另一方面,“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他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恰达耶夫1999:13)。
恰达耶夫之所以从“思想”、“精神”角度出发看待俄国参与世界历史的程度,是因为他受自己“存在观”的影响。恰达耶夫十分重视精神存在,最高理性只有在精神存在中才能展现全能。不但如此,精神存在只有在历史存在中才能与最高理性融合。历史发展是传统的运动,是人类思想代代相传的结果。所以,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俄国社会中思想缺乏的一个表现就是思想家的缺位。在此,他受到谢林精英论观点影响。民族发展主要是民族思想家的工作,民族大众并不思考,他们从天意拣选者那里获得思想:“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智慧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进。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除了某些仅仅具有人的外貌的不开化的部落外,这一现象存在于地球上所有民族之中”(恰达耶夫1999:12-13)。但是,俄国游离于规律之外,没有思想和思想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就无从谈起。
3.2 俄国传统的缺失和文化的模仿性
在俄国,思想和思想家的缺乏与另一规律联系在一起,即有关传统的规律。基于传统和真理不间断的直接传承,人们才得以发展、统一到某个民族中。传统保证人们的统一、对人的精神教育和对民族的培育,俄国传统尚未形成。“我们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没有遗产,与在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没有联系,我们心中没有保存在我们之前出现过的任何教训。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己去系上那被截断的种族之线。在其他民族那儿已变为习惯和本能的东西,我们还不得不用锤头将其砸进脑袋。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我们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世界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行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恰达耶夫1999:9)
恰达耶夫认为,民族的发展需要一定原则,这些原则经过传统的传承,构成一个民族的生活氛围和基本框架,正如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观念之于西方社会。民族的发展不仅与这样的原则相联系,还与这些原则的缺失相联系,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族类面貌的无根基性:“请看一看您的周围。难道您感觉不到,我们大家都没有坐在原地?我们都有着一幅旅行者的模样。任何人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生活范围,任何事都没有良好的习惯,任何事都没有规则;甚至连家园也没有;没有任何能留住我们、能使我们产生同情或爱的东西,没有任何坚固的、常在的东西;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离去,没有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留下任何痕迹”(恰达耶夫1999:7)。俄罗斯民族内部没有思想发展,那么思想的产生只能通过外在借用方式,由此导致俄罗斯文化的模仿性。
恰达耶夫认为,彼得大帝西化改革既是俄国历史传统缺失的明证,又是俄国文化模仿性的肇始。最为复杂的是从彼得时代起,俄国不得不面对西方,彼得“在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掘出一道鸿沟”。但是恰达耶夫看到彼得改革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彼得大帝之所以能够“将西方的历史”教给俄国,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俄国自身历史基础薄弱,没有丰富教益,其发展只能是外源性的;其二,俄国历史中没有能够抗衡彼得西化改革的东西,也就是说,俄国历史中没有能够与欧洲历史相抗衡的东西:“他看到了,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历史素材,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未来……难道你们认为,如果他在自己的民族处找到了丰富有益的历史、生动的传说和根深蒂固的机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民族投入新的形式?难道你们认为,如果他面临的是一个轮廓清晰、表达明确的民族,组织者的本能就会迫使他转而朝向这一民族本身,去寻求他的国家之复兴所必需的手段?另一方面,他的国家是否能允许人们抽取它的历史、并将欧洲的历史系在它的身上呢?然而,这一切均不曾有过。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仅仅是一张白纸,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了”(恰达耶夫1999:138-139)。由此出发,恰达耶夫追溯俄国孱弱的历史基础。
3.3 俄国青春期的积弱
民族的发展如同个人的发展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民族的青春期将构成各民族日后发展的基础,民族青春期的“疯狂骚动”、“伟大激情”和“丰富思想”将构成民族成年时期的教益。以浪漫主义视角为支撑,恰达耶夫判断俄国恰恰是缺少有效的青春期,这种状况导致俄国到了成年的时候仍然找不到自我。“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青春可悲的历史。这样一个疯狂行动、民众的精神力量翻滚游戏的时期,我们完全不曾有过。我们在这个年龄段上的社会生活,充满着浑浊、阴暗的现实,它失去了力量和能量,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恰达耶夫1999:8)
在此,恰达耶夫显然提到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鞑靼统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而且他认为,鞑靼统治给俄国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使俄国在政治制度上获得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其二,使俄国脱离欧洲。国内外学界普遍承认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社会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张建华(2004:17)指出:“13-15世纪,蒙古鞑靼人的大规模入侵和长期统治也为俄国专制制度注入了新的基因”。关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使俄国脱离欧洲的说法也有一定历史根据。在金帐汗国入侵之前,罗斯文化主要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随着东正教从拜占庭的引入,与教堂艺术相关的建筑、雕塑、绘画等都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同时罗斯文字的统一也与接受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在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它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也在扩大。但是,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罗斯与欧洲各国的联系中断了。当罗斯处在蒙古奴役中时,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了,自然科学、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等许多领域都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没有抵达罗斯。当罗斯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后,罗斯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欧洲文明了。
3.4 俄国的样板——欧洲
恰达耶夫依据欧洲标准完成其对俄国的彻底批判。在恰达耶夫看来,欧洲最根本的特点是“统一原则”的盛行,这是受到他万物统一的哲学本体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尽管从种族上,欧洲民族可以划分为不同人种,但是欧洲民族有着“共同的面孔”,有着“某种家庭般的相似性”,这一特点将欧洲所有的民族联结为一个整体。欧洲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特征之外,还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都完全是由历史和传统造就,它们构成这些民族代代相袭的思想遗产,这就是欧洲的精神统一。这种统一原则是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的成就。“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一直操着同一种与上帝交流的语言,一直有着同一种宗教权力和同一种信仰。请您想一想,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一年都和每一天一样,都和每一时刻一样,欧洲各民族都将同样的话语递向最高的主,颂扬他最伟大的善举。一种奇异的和谐,它比生理世界中所有的和谐还要壮丽一百倍!”(恰达耶夫1999:18)
欧洲民族以天启思想为指导,因此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想分道扬镳地走自己的路,他们仍然持续不断地相遇在同一条道路上,这就是实现上帝之国的道路。天启的思想高于任何单个欧洲民族的具体利益,将欧洲各民族联合成一个基督教大家庭,使它们处于无限进步的运动状态。欧洲社会包含着无限进步的开端和因素,这一切都是实现上帝之国所必需的。他甚至谈到,欧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帝之国的统治。可见,上帝之国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最高、最完善的状态。
受到上述基督教统一原则的统摄,欧洲民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形成了稳定的规则。在此,恰达耶夫指的是欧洲国家存在的“生活的必需的框架”,即有关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思想,它们构成西方的氛围,成为欧洲民族的意识习惯,在欧洲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是基督教在欧洲发展的结果。然而,同为基督教的俄国却没有这么幸运。
恰达耶夫处于19世纪初期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转型时期,其思想是转型时期俄罗斯民族认同危机的突出表现。该时期的民族认同包含着许多内在矛盾。
4 19世纪初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内在矛盾和困境
共同的集体记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历史的连续性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认同的连续性是认同观念形成的关键性成分之一。所谓认同范畴中的连续性成分,指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一种时间和空间意识。连续性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在集体那里则体现为一种历史感,即如何在时间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具有一种历史感。(王成兵2004:151-152)历史的连续性保证认同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中的动态一致性。反之,历史失忆和断裂妨碍民族自我认同的形成。俄罗斯历史发展状况印证这一观点。罗斯基督教化、鞑靼统治、彼得改革使俄罗斯历史呈现出”间断性”特点,使俄罗斯文明时而面向西方,时而关照东方,民族认同在面对这种跳跃式的历史发展中显得尤为紧张和彷徨。
从民族认同的心理学角度看,民族心理认同的结构主要包括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4个层次(任新民周文2011)。认知是个体对自我形象和群体形象的认知以及个体对本民族的起源、历史、价值的了解;评价是个体与民族身份相关的积极和消极评价,积极评价产生自尊而获得归属感;情感是在对民族身份积极评价的基础上对本民族产生依恋和归属;行为是个体参与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是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和文化行为。
从彼得改革时代开始,“俄罗斯与欧洲”的问题突显出来。彼得改革的特点是覆盖面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改革以横扫一切之势更换所有的“符号体系”,给世人造成的印象似乎要在新俄罗斯与古代罗斯之间掘出一道鸿沟,给人以明显的新旧之分。所有新的都是欧洲的,所有旧的都是古罗斯固有的。这样,判断标准发生变化,不再是好与坏,而是你的与我的之分、本土的与外来的之分以及彼得之前的罗斯与彼得的罗斯、俄国的与西方的之分。这样,“俄罗斯与欧洲”问题就自然浮出水面,造成群体形象认知的内在张力。
从行为文化角度看,从彼得开始,俄国上流社会在生活方式上“欧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在语言、服饰、交际和礼仪等“民族认同的外在符号体系”方面,彼得都有一套严格的欧洲方案。更重要的是,彼得创建的世俗学校用西方的头脑武装贵族子弟。贵族子弟从外在的仪表举止到内在的思想都明显欧化,变成“在俄国的欧洲人”。他人的范式成为自我行为的标准。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贵族知识分子,无论是在个人身份界定上还是在国家形象的认知上都显得力不从心。这是俄罗斯民族认同主体的困境。恰达耶夫的历史叙事显然是一种对民族身份的消极评价。在消极情绪的感染下,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产生负面情感也合乎逻辑。不难理解,19世纪初期出现大批俄国人放弃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识——东正教,自愿转向西方的天主教(Чимбаева 1999:55)。
5 结束语
文章从分析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русск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этнос和 нация 几个术语出发,考察 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在我们看来,民族自我意识是特定民族及其组成部分——人的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是俄罗斯人组成部分。因此,通过术语(语言)考察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就是通过俄语揭示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任务。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J].世界民族,2003(4).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J].民族研究,2002(1).
恰达耶夫.箴言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任新民周 文.民族心理认同的结构及建构[J].思想战线,2011(6).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张建华.俄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Martin,D.The Choice of Identity[J].Social Identity,1995(1).
Бромлей Ю.В.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этноса[M].М.:Наука,1983.
Кознова И.Е.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J].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07(1).
Чаадаев П.Я.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в 2-х томах.Т.1 [C].М.:Наука,1991.
Чимбаева Е.Н.Русский католицизм.Забытое прошло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M].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