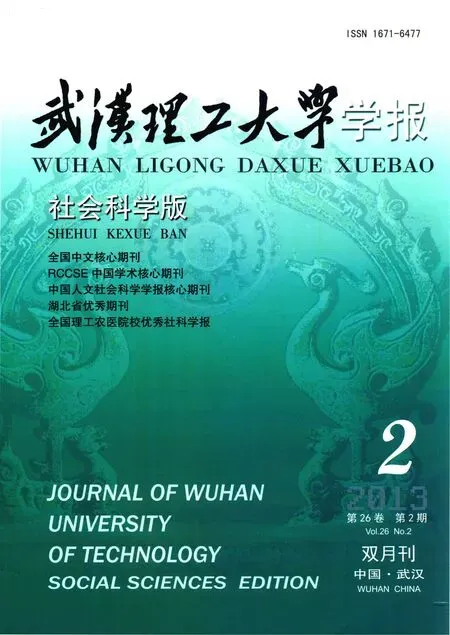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刍议
马建华
(西安科技大学 思政部,陕西 西安710054)
袁世凯一生引以为荣的两大志业:一是练兵,二是办学。袁世凯以练兵起家,但办学可能在袁世凯心目中比练兵的分量更重。晚清时的袁世凯曾经联袂张之洞等人向朝廷连上奏折,最终促使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并在山东、直隶等地大办新式教育。不过,清季袁世凯出于富强目的,特别着意于西方新式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持保留态度。到了民初,随着袁世凯个人地位的变化,其教育思想与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大体上看,1914年5月后,袁世凯废国务院,设政事堂于大总统府,称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一切政务,均由总统裁决,教育部也直属总统管辖,故真正能够体现民初袁世凯本人教育思想的文本实际上是1915年初袁氏相继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两个文件。本文拟以《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以下简称《要旨》和《纲要》)两个教育文本为中心,对民初袁世凯的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析。
一、教育宗旨的确定
教育宗旨是一个国家长远的教育目标和根本指针,它体现一定历史阶段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中国古代政教合一,教育一直未能从政治中独立出来,教育宗旨往往包含在皇帝下发的政令之中。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范围和深度的日趋扩大和加深,中国开始有了明确和独立的教育宗旨。戊戌之前,晚清的个别学堂中已有近代化的教育目标,然尚无整体性的教育宗旨。戊戌之后,各省纷纷仿效京师大学堂以“中体西用”为宗旨。1903年,张之洞等人在上呈《奏定学堂章程》时,提出了以忠孝为本,西学为用,造就国家通才的教育宗旨。然上述宗旨,在德育方面缺乏现代国民应备的基本特质,在智育方面也不够确切,与其说是教育宗旨,不如说是教育原则。
稍后,王国维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1]。王氏认为教育宗旨当涵盖德、智、体、美四育,但这是就教育的内容而言,且各人对德、智、体、美四育内涵的理解有可能人言人殊,故王氏所言失之笼统,不足以为教育宗旨的标准。1906年,学部审度中外情势,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2]220,该宗旨系教育家严修以日本教育思想为蓝本拟定而成,其中前两项为中国固有,考虑到教育的民族性;后三项为中国所缺,体现了时代性,且该宗旨切合实际,也易于贯通。“忠君、尊孔、尚公”讲的是德育,“尚武”属于体育,“尚实”指智育。道德教育是立国精神,体育和智育是强国之道,从体用关系看,此宗旨俨然属于张之洞所说的“中体西用”。
民国建立以后,由于政体改为民主,“忠君、尊孔”不合时宜。191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改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226然上述宗旨主要是教育总长蔡元培个人的主张,其中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体现了时代要求,但道德教育、美感教育有空泛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很难实施,加之蔡元培在该宗旨颁发前两个月已辞职,故国内并未奉行。
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废除了蔡版教育宗旨,重新颁布教育宗旨,鉴于蔡版教育宗旨中“美感教育”空泛而不切实用,且实施困难,因此首先废除美感教育一条,而保留军国民教育与实利教育两条。袁氏尤其重视道德教育,一方面恢复了晚清尊孔(法孔孟)外,并增加诚心、爱国、尽责任、戒贪争、戒躁进等五条,以充实其内容。此外,为配合当时地方自治的要求,又增加“重自治”一条。不久,袁氏又于《特定教育纲要》中重申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实用。”又进一步规定“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为体,以实用教育为用。”[2]258-259
袁氏特重道德教育,与清末民初革命风气的盛行有直接关系。革命注重破坏,然民国建立伊始,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当时社会风气却是“有奔突,无控止,有进发,无回旋,有私愤,无公理,健者躁进,懦者盲从,黠者鼓吹,愚者附和”[3]27。袁氏之所以重新恢复尊孔主张,因孔孟仁义之教是中国几千年来广大国民的处世程轨,用其来扬国粹以整合人心,这显然是考虑到了教育宗旨的民族性。当时的学风“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4]。
尚武为甲午战争以来文武合一教育的加强,也是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先驱,加之当时日本以“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故袁氏特定“尚武”为教育宗旨之一。尚实是西洋思想的发扬,提倡实用、科学与职业教育,袁氏将其视为中国富强的根本。无论袁氏有多少诚意,其提倡的教育宗旨能针对当时的教育缺失与社会需要,则为事实。对教育宗旨性质和特征阐述最完整的是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余家菊。余氏认为:“教育宗旨须具有五种性质,方能生其作用。五种性质为(一)时间性,合于此时之需要也;(二)空间性,合于此地之需要也;(三)历史性,合于此民族之需要也;此三者合名之曰国家性,(四)透彻性,可以贯彻于各项教育活动者也;(五)确定性,可以明示教育者以努力方针者也。于此五者,有一不合,即不足以为教育宗旨。”[5]实际上,余氏所说的教育宗旨的五种性质或特质可归结为民族性、时代性、可行性三种特征,即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旨要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可行性三个要素。从1915年袁版教育宗旨的内容来看,其与余家菊对教育宗旨标准的界定庶几近之。
二、从《纲要》看民初袁世凯的教育思想
1915年2月,袁世凯为进一步贯彻袁版教育宗旨,特意颁布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教育计划书,即《特定教育纲要》。从内容上看,《纲要》带有明显的袁氏色彩,体现了袁世凯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假若我们不因其人而废其言的话,其中也颇有一些令后人借镜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纲要》具有的两个特点上。
一是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起来。民初的袁世凯作为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特别注重利用中国传统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他意识到,孔孟思想支配中国国民心理数千年,如仓促废弃,民心必无依归,且一国的立国之道,必有所本,断不能完全剽窃异邦文化典章,而中国的立国之本即孔孟思想。在教育宗旨中,他在恢复清季“尊孔”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法孔孟”的主张,即将孟子与孔子并列。袁氏认为,孟子之所以言义利之辨,因战国时人人逐利,故以义济之,在他看来,战国时的情况正与民初的世风如出一辙,故尊孔的同时也需尚孟。在崇尚孔孟的同时,袁氏要求中小学教员特别要学习陆王心学,因陆王心学注重心性培养,实为教育国民必不可少的趣旨。在继承传统的民族道德教育的同时,他还放眼世界,提出师法他国在德育方面的长处。他认为,英美两国在德育方面注重感化,而德国崇尚严格,中国应在感化主义和严格主义两者之间调和兼用。他看到中国传统在德育方面的长处,但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其在富强层面的不足。他说:“吾国学术,推孔孟为极,则抽绎其书,体国经野之道,无非布帛菽粟之言。末流递降……愈变愈空,由智力破碎以至于浅薄虚浮;治身犹病不足,何以治国!”[3]29如对于绥远都统潘矩楹将《孟子要略》一书定为陆军中学教材的建议,袁氏就予以拒绝,他指出:“该都统自系为……振励人心,挽回颓俗起见,用意亦未可厚非。惟陆军学术重在增进军事智识,虽亦以道德为根本,究不尚心性之空谈。况现在各学堂功课门类甚多,授受时间已无余暇,若再添此项课本,转恐有妨正课,所请颁发之处应毋庸议。”[6]
在教育方法上,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主要为注入式教授,其特点是整齐严肃,通过采取强迫、灌入的方式,对学生采取严厉的管教措施以控制学生的言行,其最大的问题是养成学生的依赖性。晚清以降,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方法进入中国,尤其是法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提倡的自然教学法深受国人青睐,该法主张顺依儿童的个性使其自然发展,其优点是能够养成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袁氏在《纲要》中指出,学校教员一方面宜用注入教育,造就器使之人物;一方面又宜用自然教育,培养学生个性的陶冶,奖掖其良知良能,并养成其自动力。他要求教职员平日多研究生理、心理及各教育家学说而应用之,在教学时,对学生善诱善导,使其有迎刃而解之领悟,他尤其认为,养成学生的自动力,为教育要道。他虽未对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一揽子打死,然在教育方法上更注重借鉴西方自然教育方法的长处。
总体上看,袁氏对中国传统民族教育思想的继承是有选择的,对西方近代教育长处的吸收也不是盲目的,这主要来源于其对近代以来中西新旧关系的认识。清季以来的国粹与欧化(中西新旧)之争到民初时,已逐渐覆盖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教育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面相。对于中西新旧的关系,袁世凯的态度是“至国粹欧化,各走极端,中流一壶,正资舟楫,曰稽古训,执两用中,只有是非,并无新旧”[7]。
二是将政策的原则性与现实的可行性结合起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故国家政策要真正落实到位,必须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政策要有一定的伸缩性,庶几才有实际的可行性。长期的军政生涯使袁世凯对国情民风的认识较为实际,从而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态度上持比较稳健的态度,能够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上既考虑到长远目标,又能注意到实际上的可行性,而不盲目地求进求快。对于1912年蔡版教育宗旨中的“美感教育”一条,袁氏因其渺远不切实用而弃之。在学制方面,我国原有的五级学制,没有明显的衔接关系,教育功能完全为科举制度所统摄。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因缺失太多,没有实行。次年,在张之洞主持之下,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中国开始才有了明确的学制。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开始革除前清学制,结果仍以日本学制为基础。但袁氏认为,中国在普通教育方面,单纯借鉴日本的学制与国情不合,他指出,小学只有一种,在只求识字之平民子弟与有志深造之士族子弟,受同式之教育,于人情既有未顺,于教育实际亦多违碍,他建议师法法国和德国学制,改小学为两种:一为国民学校,纯为义务教育而设,一为预备学校,专为志在升学者而设;在中学学制方面,现行中学校学制,自初小、高小以至中学课程,迭次循环,重复太多,这与造就社会中坚人才与高等教育的准备,均有不济之处,故应取法德制,分为文科、实科二种,或分校,或一校兼备二科,视学生的个人志愿入学,不仅适应个性,而且学科有所偏重,可养成专门人才,即将来升入专门大学较易深造;在高等教育建设方面,我国自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开始有了高等教育,然直到民初各大学一直采用综合制,结果形成每办一校必设多科,博而不专,而且力难兼及,袁氏认为大学校应实行单科制与综合制并行。学制是一个国家依据教育宗旨、目标以及政府财力,将学校教育以程度与性质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有一种或数种不同功能的学校,而各学校上下左右之间,均有一定联结及互动关系的制度。学制之有否与好坏,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教育的品质与多寡。袁氏对普通学制的看法在横向上既注重到国情的复杂性,同时在纵向上又兼顾到各级学制的衔接性,其设想虽未实现,但其看法既有一定的前瞻性,又有切实的可行性。
三、时人对《纲要》的看法
1916年8月,袁世凯去世后不到两个月,教育部参事室针对《纲要》的存废问题征求部内同仁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纲要》不过是袁氏对于教育的一种政见,其中内容多与旧式思想相合,而与教育原理颇多不符,故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纲要》。然也有极个别人注意到《纲要》中的积极作用,如王第祺就援引《纲要》第五条中“各地方固有学款,宜分别保存,不得移作他用”等语在保护地方学款方面的积极意义。其实,教育部参事室在针对《纲要》存废问题提出的讨论主张中指出,鉴于“法令随政局变更,易失遵守信仰之力”及“新旧之见未融,改革过骤,恐滋反动”[3]47等,建议对废除《纲要》一事缓议似乎比较稳妥。教育本可以转移政治,然其力量未至时,则常为政治所转移。实际上,大多数主张废除《纲要》者的一个共同的理由是:《纲要》是一种“政见”。然反思他们主张废除的理由,实际上也是基于对袁氏一种政治成见而已。近代中国青睐政治层面的太多,关注技术层面又太少。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然由于时人的政治成见,《要旨》与《纲要》中的积极因素一直湮没于历史之中。几年之后,教育家余家菊在总结我国革新事业成效甚微的原因时说,国人“喜欢另起炉灶,而不愿将计就计;肤浅的更张多,彻底的实验少;吾国革新事业之无成,其亦有受病于此乎”[8]。
[1]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M]∥王国维论学集.傅 杰,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73.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袁世凯.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1913年6月[M]∥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5]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M].台北:慧矩出版社,1997:361.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政府公报:1915-07-30[Z].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8.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政府公报:1915-02-07[Z]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8.
[8]余家菊.进一步讨论学制[J].教育杂志,1922,14(号外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