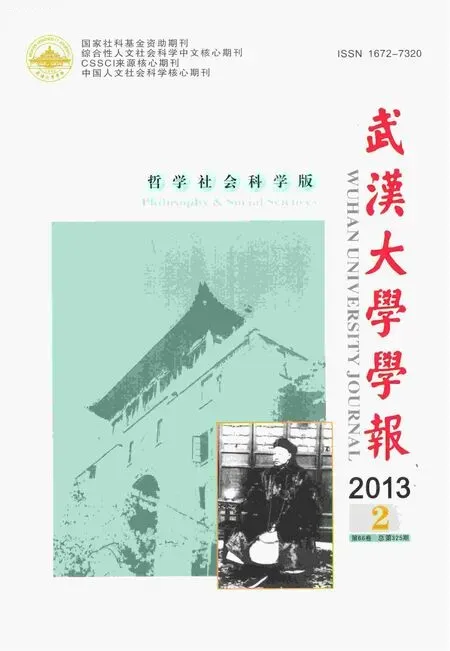论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及其解决机制
祝 捷
一、本地化的澳门法律与两地法律差异
1987年,中国和葡萄牙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对澳门回归及过渡事宜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法律本地化。为此,葡萄牙积极扶持澳门立法会加强本地立法,除非确有必要外,已经不再为澳门立法,也不再将其法律延伸适用至澳门①邓伟平:《略论澳门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过渡》,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来自于内地和澳门本地的法律专家在过渡时期共同努力,于法律语言中文化、去殖民化和司法本地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1999年澳门顺利回归时,澳门法律本地化在形式意义上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立法本地化和法律语言中文化基本实现,司法本地化也逐渐深入。回归以来,澳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域已经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法律体系,并得以作为与内地法律体系相并列的体系。
澳门法律本地化,不仅使得澳门法律逐渐“去葡化”,而且推动澳门成为独立于内地的法域,澳门的法律体系也相对地独立于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论域内,内地和澳门的法律随着澳门法律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而产生了两者相互比较和寻找差异的前提。法律规范的比较是法律比较的核心内容。法律比较的目的,就是探寻不同法律体系中具体规范的差异。而法律规范又是在特定的法律传统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在法律比较的论域内,支撑法律规范背后的法律传统又构成了比较的重要内容,是深入认识和理解法律规范差异的关键环节。具体到澳门的实际情况,由于澳门的法律文本长期以来由葡文书写,即便在本地化之后,仍然存在着诸多与内地不同的表述。因此,对法律语言的比较,也构成了澳门与内地法律比较的重要内容。
第一,法规范差异:“一国两制”下的规范差异。法规范差异,是指澳门与内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方面的差异。法规范差异是澳门与内地在法律差异方面的直接体现。根据《澳门基本法》18条的规定,全国性法律除附列于《澳门基本法》者外,均不在澳门实施,澳门的法律体系由《澳门基本法》、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且全国性法律适用于澳门,也需要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履行特定的公布或立法程序。基于《澳门基本法》第18条之规定,澳门具有相对独立于内地的法律体系。由于澳门法律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澳门与内地在法律规范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对于同一事项,澳门与内地不一定都有法律加以调整。澳门与内地都有法律加以调整的事项,法律规范的内容不一定相同。澳门与内地法律所规定的同一事项所遵循的法律程序也不一定相同。法规范的差异虽然仅仅是澳门与内地法律差异的外部表现形式,但也清晰而具体地体现了澳门与内地的法律差异,对于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实践亦有着直接的意义,因而需要加以着重关注。
第二,法传统差异:本土法传统与外来法传统的对撞。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澳门后,澳门与内地法律沿着不同的路径变迁和发展,构成了两地异质的法传统。内地法律在19世纪末西法东渐后,呈现出大陆法系的特征,当代中国的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在规范层面作了切割。在绝大多数内地法律规范中,已经难以找寻中华法系传统的踪迹。澳门法律体现为一种由葡萄牙法律、葡澳当局的法律、中葡法律、华南地区、尤其是澳门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香港的某些法律——特别是商法的一些领域——共同构成的多元法律文化的法律制度①米 健:《从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看澳门法律制度的未来》,载《法学家》1994年第5期。。澳门法律来源的多元性,决定了澳门法律传统的多元性。澳门实际上并行着两套规则体系:其一为以葡萄牙法律为中心的官方规则体系,其二为以当地习惯和风俗为中心的民间规则体系。澳门的官方法律传统以澳门成文法为基础,是葡萄牙法律在澳门的延伸适用,是文本被中文化的葡萄牙法律。对华人居民而言,法律是“法官的法律”,而并不是“民众的法律”,未被大众所完全认可和接受。为大众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民间的法律传统已经为澳门立法和司法体系所容纳,澳门民间规则因而并不是一套不为官方所认可的隐性规则。因此,蕴含中华法系传统的民间规则体系是澳门法传统之一,其地位和获得认可的程度甚至并不亚于以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传统。澳门与内地的法传统呈现出相合与差异共存的局面;一方面,澳门的官方法律传统与内地法律传统至少在技术上同属大陆法系,法律概念、原理、制度和司法体制上有暗合共通之处;另一方面,澳门的民间法律传统与内地法律所体现出的大陆法系传统又呈现出差异,并在以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民间交往占据主流的区域一体化中,澳门民间规则体系将适用于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两地法传统差异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对后者产生影响。
第三,法语言差异:表述差异、概念差异与效力差异的叠加。法语言差异是澳门与内地法律差异的重要表现形式。法语言的差异,在法律本地化之前,主要体现为文字差异,亦即内地法律以中文书写,而澳门法律以葡文书写。澳门法律本地化的重要工作是实现法律文本的中文化。然而,此种形式化的法律本地化工作固然可以解决法律文本的文字差异,但并不足以完全消除澳门与内地在法语言上的差异。在文字差异之后,由于法律译本、葡式法学理论以及澳门司法中的葡萄牙传统等因素,澳门与内地的法语言差异又在文字差异之外,体现出表述差异和概念差异叠加现象。在翻译葡萄牙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法律时,译者多采取了文白相杂的方法表述法律文本,与内地以白话文表述法律文本的方法有所不同,因而产生了两地在法律文本表述上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对于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并不构成困难,但对于多数并不熟悉法律语言文言文表述方式的普通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法律的理解困难。澳门特区政府亦注意到此问题,在法律中译的过程中引入了“中文习惯表述控制”的概念,逐步将文白杂用的法律文本过渡至接近于白话汉语的法律文本②陈轩志:《法律改革从形式到实质》,载《澳门法律改革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3页。。此外,尽管澳门法律已经实现了中文化,但支撑澳门法律的法学理论并未实现本地化。当前的澳门法律,尤其是从葡萄牙法律翻译而成的澳门法律,在概念上有着较强的葡萄牙色彩,因而产生了两地在法律文本所用概念上的差异。
二、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及其表现形式
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法律障碍,是指对两地区域合作产生阻滞作用的法律因素。前文讨论了澳门与内地的法律差异问题。澳门与内地的法律差异,是否必然构成两地区域合作的法律障碍?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澳门与内地在法规范、法传统和法语言上的差异,是否都构成了两地区域合作的法律障碍;第二,哪些法律差异可以产生阻滞作用,而另一些法律差异并不产生阻滞作用。
(一)法律差异与法律障碍:“不一致”的释出
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法律障碍以澳门和内地的法律差异为基础,法律差异构成两地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前提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差异都构成法律障碍。基于“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澳门之间某些法律差异不仅可以存在,而且是必要的。一些两地法律上的差异的存在,不仅不应消除,而且还构成了内地与澳门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不可逾越的界线。因此,用“法律差异”作为概括“法律障碍”的表述并不合适。本文提出可以用“不一致”来概括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表现形式。
“不一致”来源于《立法法》的表述。《立法法》在法律冲突上提出了“相抵触”和“不一致”两种类型。《立法法》所提出的“不一致”表述,有着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不一致”描述的是横向法律冲突,即处于同一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其二,“不一致”体现了包容性的法律思维,法律之间发生“不一致”,并不必然产生其中之一无效的结果。将“不一致”引入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论域,正是考虑到了其在《立法法》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
“不一致”在澳门基本法中虽然难觅踪影,但可以从其文本规范中推演出“不一致”的含义。澳门基本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澳门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第18条第2款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澳门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附件三的法律,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澳门基本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澳门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所允许继续适用原有澳门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三类。根据以上三个条文的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宪法第31条作为澳门基本法之立法依据外,其余法律并不自然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即便是附件三所列的全国性法律,也需要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布或者立法实施等法律形式予以接受,澳门具有与内地法律体系“不一致”的法律体系。在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背景下,“不一致”是指澳门法律体系与内地法律体系的不一致,类似于内地各地方之间因地方立法权不同而产生的“不一致”。
(二)“不一致”的类型化与不足
对“不一致”进行类型化,是解决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前提。以产生原因为标准,可以将“不一致”分为不必要的不一致、必要的不一致和无法取得共识的不一致。上述将“不一致”类型化的方法,有助于提出内地与澳门法律障碍的解决思路,进而形成相应的解决机制。
第一,不必要的“不一致”。不必要的“不一致”,是指本可以避免、但因两地在立法时未能沟通和协调,而没有消除的“不一致”。不必要的“不一致”一般出现在不涉政治事务、非属特殊经济管制事项和具有普遍性的风俗习惯、经济交往规则的法律之间。这些法律所规定的对象,一般是两地有着共性的事务,具有适用同一规则加以调整的可能性。不必要的“不一致”是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所应当极力避免和消除的情形,可以通过加强两地立法机关沟通、协调、达成两地统一协议等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必要的“不一致”。必要的“不一致”,是指因内地与澳门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的“不一致”。必要的“不一致”一般出现在涉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澳门特殊的经济产业政策(尤其是博彩业和娱乐服务业)、澳门特殊的经济管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具有澳门当地特点的风俗习惯、经济交往规则等法律之间。必要的“不一致”是“一国两制”原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在法律领域的必要结果。因此,必要的“不一致”不仅不能消除,而且有必要维护和保障其存在。但是,维护和保障必要的“不一致”之存在,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解决其对两地区域合作所产生的阻滞作用。必要的“不一致”,两地可以采取个案协商、制定区际冲突规范、进行两地司法协助等方式解决。
第三,无法取得共识的“不一致”。无法取得共识的“不一致”,是指在内地与澳门因各自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对于某一事务在协商后仍无法达成共识所产生的“不一致”。无法取得共识的“不一致”一般出现在涉及两地重大或者核心利益的事务上。由于出现无法取得共识的“不一致”时,常常意味着政府的失灵。因此,可以借鉴澳门社团社会的特点以及民间规则体系在澳门的特殊地位,引入民间治理的机制,补足政府失灵所形成治理漏洞。
尽管“不一致”已经可以容纳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绝大多数法律障碍,但仍有部分阻滞性因素并未为“不一致”所容纳。此类阻滞性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内地所盛行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潮,其二仍然是澳门法律中中葡文本的差异,但这一差异并非源自澳门与内地间的法语言,而是澳门在法律本地化过程中所遗留的内部问题。上述两个阻滞性因素,大多是因为两地的内部法律问题对两地区域合作的间接影响。因此,“不一致”只能对这类阻滞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概括,而无法直接概括这类阻滞性因素,不能不说是“不一致”的理论不足。解决以上两个阻滞性因素,需要内地与澳门两地长期的观念更新和实践累积,并不是单凭通过制度构建所能解决的。从此意义而言,即便“不一致”在直接概括以上两个阻滞性因素上存在缺憾;但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并不影响“不一致”作为概括性表述的重要意义。
三、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解决机制
法律在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中起着枢纽性的作用,克服法律上的障碍,对于两地区域合作有着重大意义。从更为长远的视域而言,解决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法律障碍,对于转变区域合作的方式,保障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亦有重要意义。当前,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有着较为明显的项目拉动型特征。项目拉动型的区域合作或许可以使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繁盛一时,但随着区域合作概念效应的消退和优惠政策普遍化,项目的热度和幅度都会出现下降和收窄的现象。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不同社会制度地区间合作的典范,除了推动内地和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外,还应当起着“示范区”、“试验区”的作用。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不仅是两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相互接近和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着法律意义的过程。结合两地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考虑到澳门法律体系的特点,本文提出构建内地与澳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内地与澳门的区际私法和内地与澳门社团合作机制等解决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机制。
(一)内地与澳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内地与澳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是以政府间合作面目出现,以满足澳珠两地民众福祉和秩序需求,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和综合性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内地与澳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将两地政府合作的结构、功能和程序以规范的形式加以确定,并在实践中实施被规范化的机制的过程。当前,无论是2003年粤澳双方高层建立的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还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所设计的以政治领导人和官方为主导的粤澳合作机制,都体现出科层式的样态。与此相比,内地与澳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应当按发挥之功能,呈现出由外围至核心之样态。
信息共享机制为第一层次,是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外围”。信息共享机制是澳珠两地政府通过信息交换而实现两地涉法信息共享的机制,其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消除因信息不畅而导致的不必要的不一致;其二,为立法协调和功能协议的制定积累必要的立法信息。法律协调机制为第二层次。法律协调机制是内地与澳门两地政府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通过沟通和协调的方式避免或合理解决两地法律不一致的机制。法律协调机制在本质上仍为两地相关公权力机关的磋商沟通机制。法律协调机制处于两地政府间合作机制的“中圈”,在机构设置和具体程序上宜继续沿用现行的联席会议制度,但应根据实际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功能协议形成机制为第三层次,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其意指内地与澳门两地政府通过协商和沟通,将某些共识制定成功能协议,以统一规范两地相关主体的行为。功能协议形成机制是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内核,其本质是两地的统一立法机制,以规范两地能够达成共识的事务,在消除两地不必要的不一致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促进两地法律融合。
(二)内地与澳门的区际私法
澳门的自法域性亦是“不一致”产生之前提,而因澳门和内地各自立法权的自治性和自洽性,也构成“不一致”的原因。由此可见,就产生机理上而言,内地与澳门的区际法律冲突和“不一致”系属同源。内地与澳门的区际私法是解决两地法律冲突的主要法律途径,但澳珠区际私法的范围小于国际私法,而是主要体现为内地与澳门两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关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法。
由于澳门和内地在区域合作上的特殊性,可以采取以“折衷制”类推适用国际私法为主体、以在特定领域的统一实体法和个案协调为两翼的构建方式,即“一体两翼”的多元化构建方式。所谓“折衷制”类推适用国际私法,是指由于作为区际私法核心内容的冲突规范并未受到“主权”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也与国际私法大部相同,因而可以类推适用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而对于属人法、识别、反致、公共政策、法律规避、外法域内容查明等问题,则应当建立一套与国际私法不同的规范①陈 江:《论用“折衷制”解决大陆与港澳间区际法律冲突》,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采取“折衷制”类推适用内地与澳门的国际私法是当前最具实践可能性的方式。当然,采取“折衷制”类推适用国际私法的构建方式,并不排除在比较成熟的领域制定统一实体法。内地与澳门也可以借助区际司法协作的途径,构建个案协调机制,发挥内地与澳门在解决法律冲突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三)内地与澳门的社团合作机制
澳门虽然为弹丸之地,但其法律制度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之路,体现为传统中华法系和外来大陆法系的冲突、交融、最终转型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别于中国内地,也有别于曾经同为外国殖民地的香港②刘海鸥:《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6期。。澳门法律殖民化的最大特色是在法律殖民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澳门华人的法律传统和规则,因而形成了澳门法律在殖民化过程中的二元化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澳门的社团治理成为澳门社会的一大特色。澳门社团具有良好的决策影响管道,足以影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决策,且澳门政治格局相对和谐,多数澳门社团与内地关系良好。澳门社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内地与澳门可以透过社团合作机制解决两地法律中的“不一致”。
但是,由于内地社团对内地政府决策影响力有限,且澳门社团数量过多,因而也导致了两地社团合作机制构建中的困境。为此,内地与澳门社团不妨借鉴海峡两岸所构建的“海协对海基”的“窗口社团”,建立以参与内地与澳门社团合作机制为任务的社团形式,克服澳珠社团合作所面临的困境。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内地与澳门的社团合作机制既要体现“窗口社团”的设计思路,又要保证一定的制度开放性,以便制度变迁所需。总体而言,澳珠社团合作机制可以包括澳珠社团协商机制、澳珠社团高峰论坛、澳珠社团信息交换机制等形式。
四、结 语
内地与澳门构建更加紧密的经贸往来以及粤澳合作的持续深化,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将跃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当前,由于两地的区域合作还仅限于项目合作,两地法律障碍在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中的阻滞性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然而,从创新“一国两制”下区域合作的模式以及探索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不妨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克服法律障碍和促进法律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