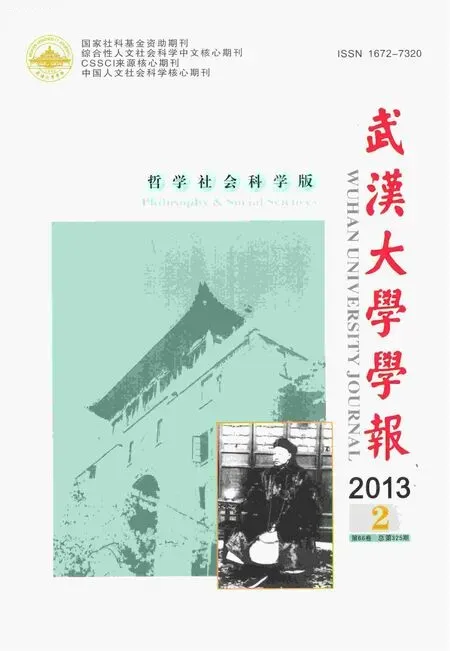协商民主在中国:从理论走向实践
叶娟丽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新理念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本是舶来品,1981年由美国学者提出,2001年由哈贝马斯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引发“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从政治学界到实务界,“协商民主”从最初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演变为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再发展为中国式民主试验的制度选项,直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成为制度建设的目标,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一些新特征,那就是:中国政治发展呈现更加开放多元的姿态,对理论的反应更加敏感快捷,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更加紧密,新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语汇相得益彰,政治学研究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路途正在缩短,中国政治学开始摆脱最初的注解诠释阶段,日益走向成熟。
一、作为舶来品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典型的舶来品。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协商民主”一词最早来自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下的多数原则》。在这篇论文中,毕塞特最先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认为美国宪政既尊重多数原则,又对大众的多数形成制衡,体现为一种协商民主①Joseph Bessette.“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in Robert Goldwin,William Shambra(eds.).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pp.102~116.。此后,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他们的研究从公民参与、合法性与决策等角度拓展了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②Bernard Mannin.“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Political Theory1987,15(3),pp.338~368;乔舒亚·科恩:《协商与民主合法性》,载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真正赋予了协商民主以动力”③陈家刚:《协商民主研究在东西方的兴起与发展》,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7期,第77~84页。。但不可否认的是,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对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才是协商民主迅速成为西方政治学热点话题乃至新的政治实践的重要原因。
协商民主,对应英文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指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协商、对话、讨论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①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总序第1页。。为了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相区别,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将其译为“商议性民主”。但是,目前较为通行的译法还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理论认为,代议民主已经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及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公民就自己关心的政策问题与政府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已成当务之急。具体地,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解读。
针对现代社会因职业分化、社会分层而形成的多元分化现状,罗尔斯提出了“理性多元论”,他“把各种相互冲突的无公度性学说之间的理性多元论,看作是持久的自由制度下实践理性长期产生特殊作用的结果”②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他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不可能依赖于强力,“要求利用国家权力的制裁来纠正或惩罚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左的人,是不合乎理性的或错误的”③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146页。。因此,必须寻找和平、包容、理性的能够消融矛盾和促进共存发展的新民主形式,这就是协商民主。理性的重叠共识、内涵公共正当性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是罗尔斯协商民主理论中的三个核心理念。尽管也有人质疑罗尔斯是否能被当作真正的协商民主理论者④迈克尔·萨沃德:《罗尔斯和协商民主》,何文辉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第108~114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正是在原初状态之下的无知之幕中根据理性进行选择的共同协商原则。
反思与重建现代性是吉登斯学术生涯的主题。他认为,现代性的过度扩张带来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为了摆脱现代性危机、追求更加道德与和谐的政治生活,他开出的良方就是对话民主。吉登斯认为,“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⑤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根据吉登斯的理解,“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折射回到它身上。处在全球化和社会反思的情况下,对话民主制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⑥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第116~117页。总之,吉登斯认为对话民主是克服自由民主缺陷的有效形式。
哈贝马斯也是在对竞争性民主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他的协商民主理论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已是一个非中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政治公共领域已经作为一个感受、辨认和处理影响全社会的那些问题的论坛而分化开来。”⑦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74页。除了国家的等级性规制和市场的分散性规制之外,也就是说,除了行政权力和私人利益之外,团结(Solidaritaet)和对共同的善的向往成为了社会整合的第三种来源⑧于根·哈贝马斯:《三种规范性民主模型》,载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根据这种新的民主概念,在规范意义上,存在三种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团结、权力与金钱。话语民主要求把重心从金钱、行政权力转移到团结上。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目标就是在多元分化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共享世界。
应该说,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古典协商民主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它“代表了一种复苏,而不是创新”,因为在古雅典民主制中,协商、讨论、争辩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雅典式民主也是导致那种将讨论批驳为诡辩或煽动性言辞的倾向的根源”⑨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2页。。进入当代,当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陷入合法性危机时,协商民主又成为了一种替代或者弥补方案,它预示着民主发展的新的可能。因此,在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后,协商民主开始走近实践,一些政治学家,为了验证、修正、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政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实验,包括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区域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和全球治理中的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为扩大公民权、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参与搭建了制度平台。其中,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形式——如参与式预算,比较具有典型意义。
所谓参与式预算,是指政府将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资金,交给公众讨论,并由公众决定,使预算编制更加公开、民主、透明。简单地说,“参与式预算是一个直接的、自愿的、普遍的民主过程,其中,人们能够讨论和决定公共预算和政策……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①UN-Habitat.“72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Participatory Budget”,Urban Governance Toolkit Series 2004,July.据考证,世界上最先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是巴西。1989年,巴西的阿里格雷港市率先实行参与式预算,后来发展到100多个市政当局都通过参与式预算来确定支出优先性和配置预算资源。参与式预算目前已经在拉美、中东欧、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次中央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实施,成为走向更广泛的政治包容和更普遍的社会公正的重要步骤。与参与式预算一样,美国等地的市镇会议(或市镇委员会),加拿大温哥华的公民议会,丹麦的共识会议等,都是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验或者实践的重要形式。
此外,区域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如欧盟议事规则,无不体现了开放、包容、可持续的特征,欧盟体系内一系列通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范,都是在平等的沟通、协商过程中得以确立的。至于全球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气候问题谈判了。为了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核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新问题,各个国家为了全球共同的利益,被迫坐下来,在忠诚于自身民主实践和价值的基础上,倾听各种利益表达,沟通谅解,以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为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民主化的道路。
应该说,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在西方的兴起,正是为了破解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但它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离开这样的前提去看待协商民主,可能会偏离历史的真实②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总序第2页。。
二、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
根据浦兴祖的看法,“协商民主”的概念传入中国是在1990年。当年出版的黄文扬主编的《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一书,已经提到了耶鲁大学利基法特·阿伦的著作《民主:21国的多数人政府模式与协商政府模式》。而在利基法特·阿伦的书中,他已经系统比较了多数人民主与协商民主,甚至有一节的标题即为“协商民主模式”③浦兴祖:《试论有关“协商民主”的三个关系》,《联合时报》2011年9月7日;黄文扬主编:《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中华人民大学1990年,第423~452页。。但不知何故,当时黄文扬的这一引介并未引起学术界其他人的注意。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协商民主”传入中国,是源于哈贝马斯2001年访华。2001年4月15-29日,哈贝马斯访问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做了8场演讲,还在一系列座谈和聚会中与中国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交流,引起轰动,并被媲美于1919年的罗素访华、1920年的杜威访华以及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哈贝马斯做了题为《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关于协商政治的概念》的精彩演讲,首次将“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这个词带给中国④薛利山:《2001——哈贝马斯访华引起的争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政治,就是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议会中利益的妥协,也包括政治公共领域的公民自由协商。通过公民的自由协商,非正式的意见可以转化为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决策,公民因此可以通过话语交往参与社会意见以及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就这样,交往权力就转换成了行政权力。据此,公共权威也就获得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公共权力领域就与公民社会领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⑤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载《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9~293页。。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实质民主,而达成实质民主的具体路径,就是协商民主或者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不仅带来了“协商民主”的理念,更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重新思考与理解民主的当代形态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了解、引进与解读“协商民主”理论的进程。资料表明,国内首次见诸文献的“协商民主”研究,是俞可平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载《理论参考》2003年第1期),该文概括了西方政治学家们提出的一些新的政治学“话语”,其中就包括远程民主与协商民主。而林尚立的《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一文,则开始利用“协商政治”的概念来解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未来可能途径。但是,真正以“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为标题的学术成果,首见于刘晔的《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文章通过对上海的街道与居委会的实证研究,提出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有利于实现党、政府、社会的权力互强,从而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一个方向。应该说,他的这个结论与西方协商民主实验首先出现在地方治理中是不谋而合的。
从2004年开始,协商民主理论开始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重镇在北京和上海。但这时期,“协商民主”还没有引起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兴趣,参与的学者比较高端,也比较小众。具体地,在宣传译介“协商民主”理论中功不可没的著名学者是中央编译局的陈家刚,他不仅亲自编译了几部主要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著作,更重要的是在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适时地有相关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成果,引导着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的发展。从资料来看,国内最早召开“协商民主”研究专题研讨会的是浙江大学①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政府系于2004年11月18—20日联合举办了“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最早以“协商民主”命名的学术研讨会。。最早开辟“协商民主”研究专栏的期刊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②如2004年第3期集中刊发陈家刚的《协商民主引论》和乔治·M.瓦拉德兹的《协商民主》。。最早的著作是陈家刚选编的《协商民主》③200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涉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协商民主的内涵、条件、制度建构以及协商民主与多元文化社会的关系、协商民主面临的困境与选择等等。但在2004年,中国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重视显然还非常不够。从中国知网的搜索情况来看,2004年以“协商民主”为题的报刊论文还非常少,仅有5篇。到2005年,相关报刊论文增加到17篇,杭州成为新的“协商民主”研究重镇。《浙江社会科学》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连续编发研究“协商民主”的稿件,尤其是后者,在2005年第5期集中编发了何包钢、陈剩勇、James S.Fishkin和John S.Dryzek四位学者的稿件,将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小的高潮。至2006年,以“协商民主”为标题的报刊论文发展到61篇。但遗憾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继续以专题的形式推进“协商民主”的研究外,多数论文都是一些跟风的注释文章,更有甚者,完全相同的同一篇文章在2006年内竟然连续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16次之多,这种一稿多发的现象,姑且当作“协商民主”研究热潮中的不和谐之音吧。
应该说,2006年,对于中国“协商民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剩勇、何包钢主编的《协商民主的发展: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收录了20多篇文章,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维度,对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西方的实践、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当时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但是,真正对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起到动员作用的是中央编译局的两套“协商民主译丛”。第一套出版于2006年,第二套出版于2009年。第一套译丛由俞可平、陈家刚等主编,陈家刚亲自领衔翻译,共出版《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和《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等4部著作④[美]博曼、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南非]登特里维斯主编:《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王英津等译;[澳]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等译。,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论及其产生过程,充分展示了这一理论对现实民主困境的解释力,同时也对这一理论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其中,《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为西方学者学术论文的汇集,收录了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学者例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等人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探讨了关于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理论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根据协商理想思考民主的丰富成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被称之为前沿、经典、准确⑤贾宇琰:《前沿·经典·准确——〈协商民主译丛〉出版》,载《出版参考》2007年第10期,第42页。。前沿表现在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展现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认知;经典表现为其学术定位,观点上的兼容并包,国别上的多方涵盖,重点是填补理论空白;准确表现为其较高的翻译质量,正如出版者所期待的,这套丛书的出版给中国学术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第二套译丛也包括4部著作,它们是《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协商民主论争》和《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①[美]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周艳辉译;[美]本哈比主编:《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等译;[美]菲什金、[英]拉斯莱特主编:《协商民主论争》,张晓敏译;[美]里布:《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朱昔群等译。,这是在协商民主已成国内政治学研究热点的2009年出版的,更加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丛书不仅涉及了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系统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的渊源、论题、概念、意义、内涵、形式、争论等,还涉及协商民主的现实操作问题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应该说对协商民主这一产生于西方的理论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评介。
在这两套译丛的推动与指引下,中国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明显的标志是,报刊论文大幅度地提升。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直接以“协商民主”为标题的报刊论文,2007年是128篇,2008年是164篇,2009年是166篇,2010年是154篇,2011年是122篇,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是151篇,十八大召开后是62篇②另外值得关注的专著有:罗豪才:《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高建等:《协商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韩]李允熙:《从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民主——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戴激涛:《协商民主研究:宪政主义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陈朋:《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温岭案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数据是一种直观的表征,尽管它并不一定完全科学合理,但上面的数据还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2006年以后,“协商民主”研究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热点,以至于很多学者都无法回避它。当然,在这一研究热潮中,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有质量的成果或者说权威的结论还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样的期刊、中央编译局这样的机构以及俞可平、陈家刚、何包钢、陈剩勇等少数作者身上。从这些海量的论文的参考文献来看,引用频次较多的是上述两套译丛以及上述4位学者的成果。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深思的理论现象。
三、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理论先行,有时却是实践在先。在中国即是如此。在“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前,中国已有自己的协商民主制度,典型的就是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信息聚合、慎重讨论、沟通交流、政策表达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显然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引进无关。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参政议政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即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中国建立起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政治协商制度逐渐升华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形态,尽管还未提出“协商民主”这样的专有名词。如在1991年,江泽民即已经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提法呼之欲出。到了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与当时中国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相呼应,中央文件再次表达了协商政治或者协商民主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紧接着,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并强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这是“协商民主”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当中。以此为基础,十八大报告直接将“协商民主”由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成为我国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至此,“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John Dryzek认为,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三个层面,即国家制度、各种公民论坛以及公共领域。每个场所的实践都可以构建一个协商民主。根据中国国情,最有希望的是在公民社会中发展出协商民主③John Dryzek.D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6.,具体地,如在地方层面发展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协商民主政治。正如陈剩勇等所指出的,“即使中国能找到使人民协商制度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的某些方式,即使人民协商制度在国家层面上能被采用,它首先需要在地方社团层面上试验,这对于在一个政治的实质结构转型中保持一种完美理想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只有这样,民主协商的理念才能成为现实。”①陈剩勇、何包钢:《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事实也是如此。近年来,除人民政协制度外,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协商民主制度形式,包括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参与式预算等。基层发展起来的这些协商民主形式,成为新的协调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程序和途径,从而使得由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得到反映与保护。应该说,在中国,协商民主已经超出了政治协商的一般范畴,如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以及其他领域的各种听证会,已经与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一道,成为我们探索协商民主的杰出成果。
关于参与式预算,前面也已谈到,它首创于巴西,目的是通过公民及其组织对地方政府预算程序的理性参与,促进地方政府公共预算与公共决策理性化,以保障公共资源分配的公正与效率。后来这一民主形式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②陈家刚:《参与式预算的理论与实践》,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2期,第52~57页。。温岭2005年以来的参与式预算与之有理论上的关联,但更多地是基于中国的民主探索实践。1999年,浙江温岭便开始了基层政治“民主恳谈会”的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2005年7月,温岭新河镇政府将民主恳谈会的形式应用于镇年度财政预算的制定、审议,从此开始了参与式预算的实践。2008年温岭参与式预算又拓展开来:横向推广到市内泽国、箬横等镇;纵向则从乡镇推进到市级交通部门预算。根据温岭参与式预算的运作模式,它是由基层人大负责组织,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参与,对政府及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民主恳谈,从而实现实质性参与的预算审查监督。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基本逻辑围绕着基层民众的预算参与、政府预算方案的商议和改进、基层人大对政府预算方案的审议而展开,将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导入现代政府的核心领域,即财政预算和公共决策③李 凡:《从新河镇的公共预算改革看中国人大改革的路径》,载李 凡:《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6-2007)》,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第25~33页。,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合作关系。
自浙江温岭试验后,哈尔滨、无锡、焦作等地纷纷效仿。从参与目标来看,我国目前基层实行的参与式预算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的参与式预算,其典型是上海南汇区汇南镇的“代表点菜”模式;二是“以提升政府行为合法性为目标”的参与式预算,代表是浙江温岭的“预算民主恳谈”模式;三是“以增加公共服务可接受性为目标”的参与预算,上海浦东新区街道、无锡市各区县街道以及哈尔滨道里区的各街道所使用的“项目预算支出选择”模式可以归为这一类。三种参与式预算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通过尽可能扩大公民参与范围、数量,最大化地满足公众知情权,从而提高了整个预算的透明度,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当然,毕竟是民主探索,参与式预算与民主恳谈会在实践操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如民主恳谈会的代表性问题,参与式预算的制度化问题,都是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需要正视且加以研究的问题。就目前各地的参与式预算模式来看,各有所长,只有相互借鉴,才能使参与式预算的制度程序在现有的经验基础上得以完善④徐 珣:《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除了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外,在我国还有一种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就是听证会。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在中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已经有些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也进行了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听证会的意义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然后在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的共识。当然,由于各种其他配套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的缺陷是显著的,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拘束力,导致听不听一个样;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不够,听证代表很难充分恰当地表述意见,而且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也不可能形成事实上的约束;至于饱受非议的各地的价格听证,那更是形式大于内容,有时由于听证会组织者的独立性不足,听证参与者的结构缺陷,有些价格听证会反而沦为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价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的工具。
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协商民主形式,如公共讨论、网络论坛等,也在一种程度上行使着协商民主的功能,成为公民互相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日益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西方协商民主更多的还主要停留在学术层面,还只是一种民主理想;而我国的协商民主早已经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种组织形式在实施,而且在实践中,还探索出了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等多种新的协商民主形式。这是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智慧与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当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其发展道路还很漫长,如何在制度上划分各类协商民主形式,确定其范围,明确其主体,清理其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如何认识与处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相互关系,如何通过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或者通过选举民主保证协商民主,都是今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任务仍很艰巨。事实上,我们目前的一些协商民主形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经验要提炼为规律,实践要升华为理论,中国政治学界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四、结 语
理论服务于现实,是由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所决定的。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术,通过实验或者实践,来参与公共决策。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在建构国家能力上起了巨大作用。中国同样必须思考用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国家能力,特别是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建构基层国家执政能力①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协商民主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既不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由民主的补充,也不如激进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由民主的替代,它更多地是代表一种走向民主化的新的可能。自由民主更多地是追求对民意的代表;而今日中国更多地是需要达成共识和维持秩序,因此协商民主理论比传统的自由民主更有意义。或者说,它更加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既没有完全实现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实现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者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模式对我们可能更有价值。他认为民主是一种对公共政策进行讨论、协商的制度,强调决策源于广泛的协商而非金钱和权力的较量;同时,他强调协商过程中的尽量平等和广泛参与,这对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民主机制的中国而言,对中国民主化道路和战略选择是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的②Ethan Leib,Baogang He(eds.).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New York:Palgrave 2006.。
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是个新东西,但协商政治实践却并不新鲜,以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政治,在中国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如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新形式,不断地丰富着中国特色的协商政治的内容,验证、完善和发展着协商民主理论,中国的协商政治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世界政治文明做出贡献。事实上,除了“协商民主”这一热词外,党的十八大报告还首次用到“政治发展”的概念。“政治发展”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已是耳熟能详,它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于80年代传入中国,一度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今天它在十八大报告中亮相,还有“协商民主”概念的初次运用,都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与实践的距离在缩短,中国政治学理论日益体现其公共性功能,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的稚气,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