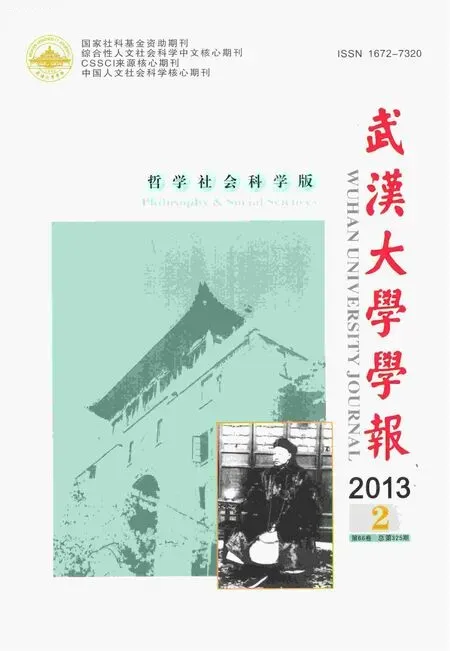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伍华军
我国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规定,使“一国两制”这一理论构想上升为关涉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原则。迄今为止,“一国两制”理论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功在港澳地区付诸实践,两部《基本法》也已实施十余年。但是,作为“一国”基础的宪法在港澳地区的效力和实施问题,至今仍未取得共识。
在港澳地区,因宪法实施产生的一些争议,经常被湮没于基本法的讨论当中,没能得到宪法层面的充分讨论。
这突出反映了我国宪法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的认识障碍,也更加体现了宪法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的迫切需求。
一、宪法应毫无例外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实施,这不仅体现了坚持“一个国家”原则的根本要求,也回应了一个国家宪政体制的根本问题。
(一)只有宪法得到普遍实施,才能更加有效地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权
主权(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其本意就是最高权力或最高权威。如果主权没有了最高权威性,它就失去了在政治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主权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对内最高权,也就是在国内作为政治统治的最高权力,不受其他权力的支配,它的意志全体公民和机关组织都必须服从和执行。对外独立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的各种事务,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①秦前红:《新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这种最高性和独立性,使得主权事务应当首先由宪法加以明确规定。换言之,主权问题应当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
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归属问题是清楚、明了的。众所周知,香港和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开始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虽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甚至在特定领域内处理有关对外事务的权力,但这不过是事权问题,而绝不意味着特别行政权享有独立的主权。
宪法规定了国家主权最核心的内容,如果宪法不能得到实施,主权的尊严根本无法得到真正彰显。笔者注意到,在香港、澳门回归之时,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享有众所周知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宣示,这包括主权交接仪式、驻军。在这个过程中,宪法似乎没有明确出场,但一切宣示主权的方式都是以宪法为基础的。以主权交接仪式为例,代表中国出席主权交接仪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主权交接过程中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等事实,反映了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得到实施的实际状况。
(二)只有宪法得到普遍实施,才能更好地塑造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公民认同、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
所谓认同,是基于认知而产生的一种趋同的心理状态。在现代国家,公民应当产生的认同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这些年来,港澳居民在这三个方面的认同都存在一定偏差与困境:
第一,居民身份认同经常超越公民身份认同。所谓公民身份认同,指的是“公民个体对其自身所着落时空之脉络的认知与认可”①江国华:《宪法与公民教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4页。。当一个香港、澳门居民被问及身份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澳门人”,这个问题最能够直接地反映香港、澳门居民的身份认同。然而,近些年来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的认同感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不够牢固。
第二,地区认同经常超越国家认同。港澳(特别是香港)缺乏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感。以最近的一个事件为例,2012-10-10,(A19),香港立法会的黄毓民议员在宣誓就任时,竟然假装咳嗽,咳走“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字眼;即使他在第二次重新宣誓时,则采用另一种“极不尊重的”方式,以表达对政府及立法会的蔑视。这样的人能够当选为议员,而他在当选为议员之后,胆敢以违法的方式哗众取宠,只能说明香港存在此类政客的活动舞台,也说明香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区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问题②郑治祖:《未依法宣誓,黄毓民认衰“补镬”》,载香港《文汇报》2012-10-13,(A19)。。
第三,宪法认同让位于基本法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这是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的。然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依据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这种道路差异,使得宪法在香港、澳门的政治生活中持续缺位,也就很容易使港澳居民产生“中国宪法是大陆的宪法,效力不及特别行政区”的认识。
要进一步巩固上述三种公民认同,首先要明确三种认同的目标:“公民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国家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所具备的功能目的和职权职责;宪法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所包含的价值精神和规范体系。”③朱道坤:《论法治文化的发展——以法治生活之实现为视角》,载《文化强省建设与湖北跨越式发展(2012·湖北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可见,宪法认同是这三种认同的枢纽。要建立起有效的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就必须做好宪法的教育和实施。只有了解宪法,才能让公民真正产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只有实施宪法,才能让国家真正转变为一个凝聚、巩固的共同体。
二、宪法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讲,特别行政区内宪法实施的具体方式是不一样的。特别行政区是根据宪法第31条设立的地方单位,享有高度自治权。实施高度自治权,践行“一国两制”的宪法规定,就是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宪法的表现。而在实践高度自治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毕竟是国家的根本法,虽然其中的一些条文在特别行政区并不适用,但仍应在特别行政区发挥重要作用。
(一)宪法没有部分实施的问题,宪法的普遍实施就是宪法的全面实施
特别行政区没有实行现行宪法中规定的许多制度,如人大会议制度、人民法院制度等等。有人因此就认为,宪法的条文只是部分适用于特别行政区。这实际上没有认清宪法作为规范体系的特性,也没有搞清基本法的性质,认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基本法本身就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的下位法。宪法的效力,就是通过基本法得以实现的,实施基本法,归根结底就是实施宪法①也有学者主张,基本法是宪法的特别法,宪法(典)乃是通过其特别法对特别行政区发生法律效力,只要作为宪法特别法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意味着宪法对特别行政区发生了法律效力。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我国宪法第31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在特别行政区问题上规定的例外条款。正是根据这一条款,我国制定两部《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的“序言”也表述得非常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基本法。”
第二,宪法作为一个规范体系,本身具有完整性,实施基本法,不意味着宪法的部分实施。我们认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并不存在所谓部分实施的问题。只是基于宪法31条的特殊规定,特别行政区才具有高度自治权,并且无须进行宪法的实施。宪法是一个规范体系,它既有原则规定,也有但是、例外。虽然我国宪法的一些条款在特别行政区没有得到适用,但是,宪法作为这样一个规范体系,在特别行政区仍然得到了实施。认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只是部分实施的观点,实际上割裂了宪法作为体系的完整性。与之相类似的是,我国宪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结论,在非民族自治地方,宪法也只是部分实施了呢?这个结论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不应违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建立其他有关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②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政治运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内地,其不设立人大机构,地方人大的立法职能、监督职能、人事职能、财政职能等均由以立法会为主的其他机构行使。
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还是坚持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港澳居民参与国家决策。他们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也特别注意倾听市民呼声,已经成为港澳居民与中央的纽带。一位香港人大代表就曾指出,“香港人大代表的实际工作是有成效的,包括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中参与了意见,以及有效推动了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同时反映了香港民意、转达申诉和帮助解决疑难,为市民办了实事”③曾德成:《“一国两制中的香港人大代表》,载《中国人大》2007年第12期。。
港澳人大代表的选举,反映了香港、澳门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组成的宪法地位。但近些年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上的不同派系,罔顾现实,对人大制度在香港的运行无端指责。针对这一指责,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曾于2009年4月20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表示,在基本法之下,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除担任选举委员会委员以选出行政长官外,在本地事务方面并无担当任何特定角色。
而曾经担任或正在担任人大代表的议员则纷纷表示,不应矮化人大代表在香港事务中的角色。叶国谦议员曾担任人大代表6年,他表示,基本法第21条规定,人大代表根据由人大确定的代表产生办法选出。当选的人大代表须研究如何可更有效为香港人服务,务求达到选民的期望。他强调,大家不应“矮化”人大代表在本港涉内地事务方面所担当的角色。何锺泰议员强调,人大代表的角色是充当香港人与内地当局之间的桥梁,并没有担当干预的角色④《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纪要(2009年4月20日)》,立法会CB(2)2403/08-09号文件。。
(三)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不得影响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我国奉行的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特别行政区是单一制国家的一个地方单位,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不能破坏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就国家结构形式与港澳事务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个突出的争议问题就是所谓的“剩余权力说”。1986年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港方起草委员李柱铭等人提出了“剩余权力”问题,其主要观点是:在即将建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由中央政府行使国防、外交事务的权力,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权力作为“剩余权力”,应该概括地由特别行政区行使①李元起,黄若谷:《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这是所谓“剩余权力”问题的起源。
这一观点遭到了学界的普遍反对,其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完全是联邦制国家的问题。最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明确指出了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
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43条还具体规定了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
在基本法解释问题上的细致处理,实际上体现了基本法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谨慎态度:一方面,要维护全国解释法律的宪法权力,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理应由全国人大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要尊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司法环境,特别是香港沿袭英国的普通法系传统,由法官解释法律,已成为香港的司法习惯。
可以说,香港基本法最终的立法选择,已经抛弃了“剩余权力”理论。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再次得到香港、澳门民众的普遍关注。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学、宪法学上的理论思考,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将来的拉锯式的反复,我们最终还得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问题着手,从维护国家宪政体制的角度展开分析。
三、规范“一国两制”应当成为宪法实施的基本问题
“一国两制”一直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不明确、不明朗的表述,如“井水不犯河水”、“五十年不变”等等。这些不明确的表述,在政治谈判的过程中,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然而,香港、澳门回归至今,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实践日趋复杂,这就迫切要求我们从宪法实施的角度入手,将这样复杂的政治问题变得稳定化、法律化。
(一)维护中央与港澳关系的稳定性
中央与港澳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近些年里,港澳居民经常会因为一些中央的一些风吹草动而大惊小怪。例如,2008年,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撰写了《“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文章指出,香港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两支队伍。其中有一支体现“一国”原则、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宪制权力但不干预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管治队伍,这就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②曹二宝:《“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载《学习时报》2008-01-28,(5)。尽管该文在行文上已经颇为小心翼翼,但文中提出的“第二支管治队伍”的说法最终还是引起了香港方面的关注,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4月对此进行了讨论。
实际上,曹文观点并不存在违背基本法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央对香港享有宪制权力,应由一定的机关行使,中央应当建设好干部队伍,依法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特区的宪制权力但不干预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为避免误会,作者在文中也一再强调,香港的内部事务是香港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地官员不应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香港立法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制权力”概念的不明确:什么是宪制权力?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权力到底是什么?宪制权力和香港内部事务的界限在哪儿?学界观点很模糊,政府态度也不甚清晰。再加上曹二宝先生的中央官员身份,以及该论文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上,更是触动了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的敏感神经。
此外,中央在这些年采取的一些涉港、涉澳政策,经常遭到港澳居民(特别是香港)的抵制。我们认为,其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于中央采取的这些政策到底是好或不好,而在于中央与港澳关系尚缺乏足够的稳定性,港澳居民也极可能因此会对中央的举措过分敏感,而将一些风吹草动当成中央和港澳关系变化的前奏。笔者认为,要让中央与港澳关系变得更加稳定,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央与港澳关系纳入宪政体制之内,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中央和港澳的关系明确化、稳定化。
(二)实现“一国两制”的法律化
“一国两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术语,它早已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得到了表述。然而,“一国两制”概念的模糊性,造成了实践过程中的诸多误解。比方说:哪些事项是“一国”的问题,哪些事项是“两制”的范畴?要消弭误解,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一国两制”的法律化,换言之,就是去政治化,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不仅是促进中央与港澳关系更加稳定的重要方式,还是避免纷争、弥合矛盾的重要手段。
目前,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宪制方面的交流仍然不足,一些问题仍然集中于政治层面,而无法最终法律化。这就造成了部分港澳居民的疑惑——中央是否不愿意将港澳问题法律化?而港澳的未来是否存在着在改弦易辙的风险?应对这些问题,就应当更好地实施宪法,根据宪法将一些重要问题法律化,从而避免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观望、犹疑。
实际上,基本法就是关于港澳的法律,也是关于港澳的总体规则。但是,基本法如何实施,如何区分中央管治事务和特别行政区的管治事务,尚需进一步明确。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了数次基本法的释法工作,其中,只有最后一次释法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出的。有人就认为,前三次释法,违背了基本法的要求。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宪法问题,最好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予以处理。将这样一些问题政治化,只会带来港澳法制的更加不稳定,最终不利于港澳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