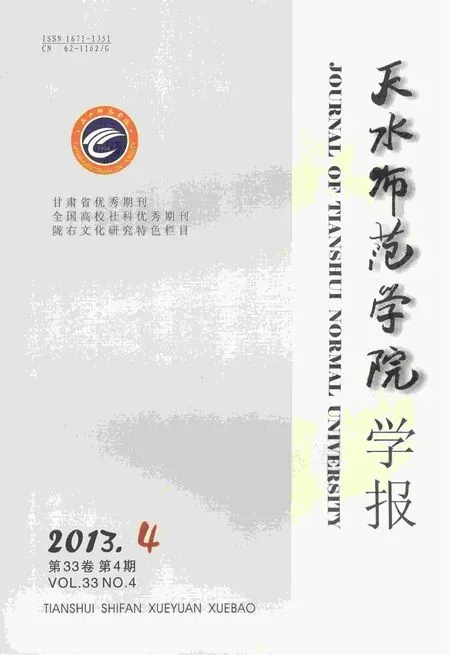论后殖民视角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的陌生化张力
王 博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以关注权利和身份、批判文化霸权、反思殖民体系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其当下影响等为重要内容的多元文化理论。作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较为激进的理论,后殖民理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鸣,其自身在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矛盾与局限,也是一直遭人诟病的焦点。本文力图克服后殖民理论的局限性,只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关注藏族当代作家“边界写作”的审美特质。
一、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边界写作”
“边界写作”是从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派生出来的。“‘第三’这个定语在英文中往往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它突破了传统的二元论,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既是A又是B、既不是A又不是B的模糊不清的‘临界状态’。……‘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这里所说的‘翻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任何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建构’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1]而“边界写作”无疑具有“第三语言空间”的特征。丹珍草将“边界写作”定义为:“具有多重族籍身份和多种语言能力的作家或诗人,用主流或强势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传达一种处于边缘或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文化特质;同时又立足于‘边缘化’写作的优势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一种崭新的语言突破与变革。”[2]
显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是符合“边界写作”特征的。他们面对两个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文化范畴,自由地穿行于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然而始终无法被任何一方完全接受。正如巴赫金所说:“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它们既不会彼此完全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3]“边界写作”者承受着巨大的内心矛盾冲突,但同时也实现着双重超越,呈现给我们一个更为丰富惊艳的世界,就像一片妖艳的罂粟花海。
二、“杂糅”:藏族文学的陌生化张力
藏族的“边界写作”者大都深受汉藏双重文化影响,他们的创作必然呈现出多元文化“杂糅”的特点。而两种乃至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杂糅”,从某种角度上讲,具有使习常的审美感受变成陌生审美感受的独特功能。“民族、时代、地域的区别性自识,导致审美价值发现:此民族陌生于彼民族,非主体民族陌生于主体民族,高原雪域边陲山区陌生于无垠平原。民族的地理、生理、心理、文化的交界就是习常和陌生的交界。它们作为文学内容和形式,本身就符合艺术原则,具有审美效应。”[4]可以说,在藏族文学或者说任意两个可以发生语言文化交流的民族文学之中,“杂糅”是使习常与陌生这种二律背反的机制发生转变的内在推动力,也是将习常和陌生置于同一层面形成张力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杂糅”为边缘文学创造了一份独特的审美感受,即陌生化张力。
藏族作家中的“边界写作”者他们大多生活在文化的过渡地带,如阿来、扎西达娃、央珍、梅卓等人都生长在藏区,同时他们又都曾就读于高等学府,接受过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且能自由地运用汉语写作。因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汉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汉藏文化的“杂糅”的独特的景象。
首先,藏族文学在内容上呈现的“陌生化张力”。藏族文学作品自然是反映藏族独特的生活内容:民族风情、宗教仪式、自然风景、奇珍异兽、崇尚禁忌等等。而这些对于有着地理文化差异的我们,天然具有文化陌生的审美价值。《尘埃落定》描写的是川西的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家族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浓郁的藏族风情、土司家族的生活、神秘的巫术和信仰等。例如,小说中提到了水葬、火葬等,奶娘的夭折的儿子就是“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而战死沙场的勇士们则是火葬,“焦臭的烧骨头的气味在初春的天气里四处弥漫”;还提到了藏族的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小说中也有关于藏族建筑描写,“门楣、窗根上,都垒放着晶莹的白色石英;门窗四周用纯净的白色勾勒。高大的山墙上,白色涂出了牛头和能够驱魔镇邪的金刚等等图案;房子内部,墙壁和柜子上,醒目的日月同辉、福寿连绵图案则用洁白的麦面绘制而成”;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写到藏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藏医藏药,当土司的傻儿子得了雪盲,专攻医术的门巴喇嘛“燃了柏枝和一些草药,用呛人的烟子熏我,叫人觉得他是在替那些画眉报仇。喇嘛又把药王菩萨像请来挂在床前。不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我就安静下来。”由于地理文化的不同,这些对于他者就是陌生而神秘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发生传递时,就意味着从发出者的习常转为接受者的陌生。也可以说,藏族文学的神秘感源自两种异质文化以及两种文化的审美差异之间涌动的审美张力,因而藏族文学中无处不在的神秘感正是在审美接受过程中读者体验到的陌生化张力的审美感受。
其次,审美的“陌生化张力”还体现在文学语言上。在文化的过渡地带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而“交流自然离不开语言,于是在文化的‘接触地带’与文化的‘中间地带’就出现了文化的‘接触语言’,‘接触语言’往往是不同文化之间出现的混杂语言。”[2]汉藏文化的交流带来汉藏语言的“杂糅”,但藏语作为本民族的母语是根深蒂固的,因而这种语言“杂糅”实际上是汉语对藏语的直译,藏语成为现实语言的底层,汉语作为表层语言覆盖其上。但是每一种语言本身都蕴含着独特的审美因素,无论是在语音、节奏,还是象征、形态上,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因此,藏族作家在用汉语写作的过程中,面对藏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转换时,必然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独特的美的资源。在汉语的叙述背后自然融入藏族的叙述方式,正如阿来在演讲中所说:“找不到适当的形容,就想到藏语的对话,如觉得好就借用,把藏语对话变成汉语,汉语对话必然隐藏着藏语的思维模式。”藏族独特的思维方式、独有的意象及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表意体系相互叠加,呈现在文本中的即为藏族的内在与汉言“杂糅”之后的语言表现形式。这种带着藏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语言表达形式使我们所熟悉的汉语变得些许陌生,使文本接受者“眼前一亮”。
(一)“言外之意,象外之旨”
藏族日常口语本身就具有幽默诙谐、形象直观、善用比喻的特点,所以藏族文学的传统语言风格也如此。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不似主流文学大多采用“赋”的叙述方式,而多用“比”“兴”。受藏族传统文学影响,当代藏族文学作品也多用隐喻、象征、比喻、拟人等表现手法。寓言式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在当代藏族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比如在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里,塔贝和琼在寻找香巴拉途中,塔贝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好奇,琼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背叛了她的神但最终又回到塔贝身边,这种种行为都是设计好的一个个隐喻系统,最终指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再如,在《尘埃落定》中,僧人翁波意西两次被割掉舌头,就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第一次被割掉舌头,他从一名虔诚的传教者变成记录历史的书记官,但是他并不甘心失去话语权,因而奇迹般地又能开口讲话了,但他一开口便就彻底地成为了历史的旁观者,对真理的坚持使他第二次失去舌头。在这里,失去舌头意味着失去话语权,失去话语权意味着退出历史。还有一些比喻句随处可见,如,“被瞄准的感觉就像被一只虫子叮咬,痒痒的,还带着针刺一样轻轻的疼楚”,“我只一伸腿,绸缎被子就水一样流淌到地板上”等等,通过非惯常的本体和喻体的搭配达到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在接受者内心生成陌生化张力的审美感受。当代藏族作家继承了传统藏族文学中擅喻的审美特征,其作品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隐喻象征系统,小到句子大到整部作品的构思。寓言化、象征化的美学倾向使读者在审美接受过程中产生阅读延宕,从而形成陌生化张力。
(二)多语言“杂糅”的叙述
对于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而言,多语言“杂糅”是指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母语藏语与写作时使用的汉语的混合“杂糅”,形成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审美价值的汉语,是对汉语的“重新建构”。如阿来所说,“汉族人使用汉语时,与其文化感受是完全同步的,而一个异族人,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但在文化感受上却是有一些差异存在的。”[5]因而,藏族人使用汉语是与汉族人不同的。他们说汉语时,“言辞本真,直指人心,自由随意,形象直观,不尚修饰,平白质朴,‘随物赋形’,大巧若拙,能抓住人物一瞬间的直觉和感受,并使读者产生阅读通感。”[2]在《尘埃落定》中具有如上特点的句子比比皆是。例如:“回信又来了,言辞有点痛心疾首”,“喇嘛的泻药使我的肠子唱起歌来了”,“一串风一样刮来的马蹄声使人立即就精神起来。一线线阳光也变成了绷紧的弓弦。”等等。多语言“杂糅”的叙述方式违背了汉语的常规用法,但是使汉语回到了一种天真的状态,具有最原初的力量,给对汉语再熟悉不过的读者内心最大的冲击。
(三)富含不确定性和哲理性
藏族传统文学多采用“比”“兴”手法,且小说语言简洁,有着精美的情致与内在韵律。比如在《尘埃落定》中:“爱就是骨头里满是不断冒出来的泡泡”,“命运不能解释”,“从床上看出去,小小窗口中镶着一方蓝得令人心悸的天空”。语言简洁但有一种韵律美,并且在如此简洁清新的语言之下蕴含着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在语言与含义之间生成张力。比如,在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中,当老次仁吉姆去世的时候,空中掉下一串佛珠,并且有一个声音说,“每一颗就是一段岁月,每一颗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作者给每一个女人都取了相同的名字,这种刻意的重复代表着他对人类命运和生活的思考,并不是无意义的。这样独特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接受体系,具有不确定性、丰富性以及哲理性,言简但意无穷,冲散了惯常的铺陈其事的小说风格。
三、结 语
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研究认为,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当代藏族文学“杂糅”的必然,从而通过分析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杂糅”,并推及深深扎根于文化土壤的文学,认为“杂糅”是文学陌生化张力的深层动力,而陌生化张力是“杂糅”的外在表现,也是藏族文学作为“边缘文学”独具的审美特质以及审美价值。在全球化趋势和文化趋同的背景下,随着文化交流的便捷更加频繁,“边界写作”必然得到更多的关注。因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探讨当代藏族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揭开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纱,进一步探索藏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1]史安斌.“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的建构:扎西达娃和拉什迪的跨文化“对话”[J].民族文学研究,2004,(3).
[2]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0,139,153.
[3]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65.
[4]向云驹.陌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基础及价值定向[J].民族文学研究,2001,(3).
[5]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J].当代文坛,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