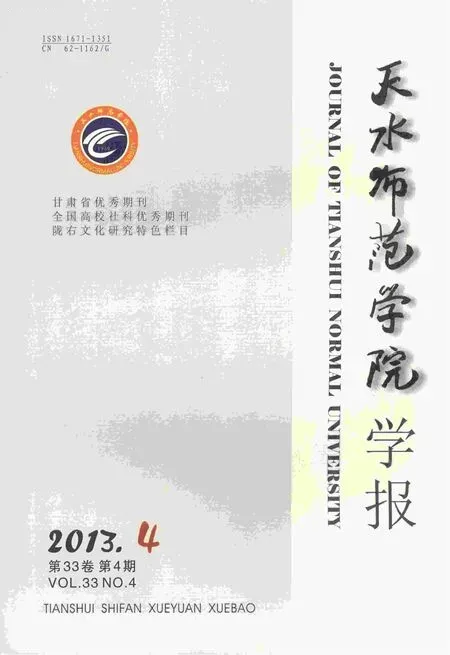启蒙视域下赵树理小说的民俗文化表现
王怡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赵树理的小说写作多以农民生活为其表现的题材,浓郁的民俗文化风味便成为赵树理小说写作极为重要和显著的美学标志。
赵树理的作品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俗文化?参照具体的文献史实,对于赵树理从事文学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基本的理解: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作家,加之对于中国民间社会和底层民众远较他人真切的理解,他的写作自然顺延或者说承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存有通过思想的教育而唤醒民众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真切思想启蒙动机和意图;一方面,因为失望于五四新文学与底层民众的隔膜,加之感恩于政治革命对于自己生活的振救而起的主动的政治革命责任承担,他的写作亦表现出了按“领导的授意来写”,“和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1]的解决“工作问题”的明晰政治动机和意图。这两种动机和意图在他的写作实践之中不断交织、冲突,不仅构成了他复杂和生动的精神存在图像,而且也深深地营造了他作品的面貌和品格,所以,从启蒙视域观照和审视赵树理小说中的民俗文化表现,是能契合作家创作实际且可以较为深入地进入到对赵树理和民俗文化关系的理解。
因为与现实的政治革命所保持的极为紧密的关系,加之对于五四新文化思想和中国乡村社会普通民众之间“天悬地隔”的分离状况的真切体察。所以赵树理的小说写作和以“启蒙主义”为其目的的鲁迅等新文学大家的写作是有明显差异的。
一
赵树理本人的人生和文学觉悟原本就是一种思想启蒙的结果。
赵树理小名叫“得意”,这个名字是他先前经商、壮年之后又返乡务农且粗通文墨的祖父取的,真切而又生动地表现了在数代单传之后一个小男孩的到来给一个家族所带来的巨大的喜悦。他出生的村子叫尉迟村,虽然时代已经到了新的纪元,但是在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四时节庆并及尊卑长幼和婆媳关系诸多方面,这里的规矩和讲究却还“和前清光绪年间的差不多”。[2]母亲及其舅舅一家信奉一种叫“清茶教”的小型宗教,她们认为“神在柜中,柜中放两半盆清水,清水上放筷,平时不开。教徒不用烟酒葱蒜。每天查一次水缸,缸里若有什么东西,如蜘蛛等,认为是得罪了神。柜里的筷子受到震动开了叉,也认为是得罪了神”。[1]父亲则虔诚于“准宗教”式的阴阳八卦术,一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生长于这样的环境,受到其日常化、细节化的长期影响,所以,在1925年夏进入山西省省立长治第四师范读书之前,食素戒荤,敬惜字纸,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赵树理自然也保持着和其生存环境高度一致的保守、愚昧和迷信习惯特点。但是,他所保持和信崇的这些东西,在进入到长治师范——准确点讲,在接触到了以同学王春为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之后,经过和他的辩论,“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于是崇奉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1]在他的引导下,不仅慢慢破除了笼罩在他头顶的迷信雾霾,开始认同并主动了解五四新文化思想,而且也“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喜欢鲁迅、郁达夫的作品,一如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等。学着写了新诗新小说,学习欧化。”[3]
因为自己的这种“被启蒙”而后得以觉醒的经历,又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思想,运用新的眼光对于“天聋地哑”的中国偏僻乡村社会进行了重新观照,赵树理事实上也便认同了五四主流文化所主张的“思想启蒙”观念。在长治师范上学期间,每逢回家探亲,深感于家乡时时处处的迷信重重,他便有意识地将学校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用于周围亲人生活的改造,虽然结果不过是碰壁,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不断碰壁,所以当他拿起笔大声地对底层民众说话时,希冀通过鲜活生动的故事讲述,揭示乡村百姓在无意识状态下为落后的风俗习惯所蒙蔽因而不能自觉到其为人所欺辱和剥削的真相,从而能够达到教育百姓、促使其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的目的,也便成为了赵树理小说写作贯穿始终的潜在而且重要的主题。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本来不装神弄鬼,但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又不愿接受公公和丈夫的管教,且意识到了借助于人们对于神的崇信,不仅可以光明正大地摆脱公公和丈夫对于她的管教,而且也可以赢得村子里年轻异性对于自己的追捧,所以,在邻家一个老婆“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之后,“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很显然,她的装神弄鬼,并不是别人强迫她接受的,而是她自己主观上意识到了这样的接受可能带给她本人的现实利益,所以将原本外在于她的民间崇神信仰和巫术内化于自己的日常行为,且于长期的演化操作之中,自己俨然成为一种神的化身,不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使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应该有的本相。
二
相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民俗生活总是显现出了明显的先在性和给定性,换句话讲,也就是一个人一俟降临到人世,他所置身的环境总是会先在地给他提供一些群体所共同持存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个体若要顺利进入群体,和周围世界保持一致,他或她也便自然需要信崇和修习这些民俗文化和生活。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在事情的另一方面,具体的个人又总是有着自己鲜明和独立的主体性的个体,所以,其对环境所先在给予的东西,事实上又可以根据自己成长的设计富有选择性地接受。缘此,个体与民俗生活之间的关系,即如民俗文化研究者高丙中所言:“民俗生活是人的生命在情境中遵照意向在民俗模式中的呈现。作为人的一种活动过程,民俗生活是人的这一活动主体的现实表征。由此看来,民俗生活是由民俗模式、情境、意向和生命所整合而成的活动,所整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过程。民俗生活是主体的实现,在这活动和过程中,体现着主体的参与和投入,贯穿着主体的做为。”[4]因此,民俗文化和生活的接受,无论怎样强调先在的环境给定性,但本质上是由主体决定并且归根结底应该由主体负责的事情,所以,当其所要接受的民俗文化和生活如果业已显现出某种腐朽或者负面效应,可是接受的主体却没有警觉,相反却自觉地选择顺从和认同之时,便如《登记》中张木匠的母亲,自己年轻时深受“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的陋俗的苦痛,然而自己熬成婆婆之后,她却不仅不思改变,相反却变本加厉地信崇和操持这一陋俗,怂恿自己的儿子欺辱自己的媳妇,显见其精神、思想上的麻木和深受毒害。
和这种民俗文化接受的主体性相一致,当意识到了外在的民俗文化要求一旦内化为生命个体的主体认同即会成为其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之后,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之中也便给读者深刻地揭示了民俗文化存在的日常化、细节化实质,从而藉此说明了深受旧思想、旧习惯毒害的老派乡村人物,是怎样在愚昧落后观念的制驭下,一言一行都不能自主的情形。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迷信阴阳八卦,所以抬手动脚便“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种地时要翻翻黄历,看看是不是黄道吉日,适宜耕种还是不宜耕种;二黑和小芹好上了,别人前去提亲,可他却死活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一是“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即人们忌讳的“破月”,不吉利;而小二黑被金旺和兴旺抓到区里之后,他先是讲自己今年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但不巧的是前天早上上地,才上到岭上,偏偏就碰上了一位穿了一身孝的骑驴媳妇。而后又说“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传家宝》中李成的娘也是,她按照老习惯心理预先形成了“媳妇要有个媳妇样”的模糊观念,然后在这“媳妇样”的模糊观念驱使之下,她内心的“老婆婆”对媳妇的定见便时时处处表现出来:媳妇单手提一桶水她觉得和自己不一样,是不对的;媳妇用大瓢往锅里舀水,而自己一直是用碗舀的,她也觉得是没有个媳妇样;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而媳妇却要用半桶水,这也“不象女人”;破箱子的位置不能动,喜欢到地里劳动也是错,做饭多放点油是“耍派头”,赶集买双鞋、裁缝铺里做件衣服,也抱怨说“不嫌败兴!一个女人家到集上买着穿!不怕别人划她的脊梁筋”。二诸葛神课出的黄道吉日到底有什么道理?李成娘所以为的媳妇到底怎样了才像个女人?他们并不深思,但是他们心里内化极深的讲究和规范,作为一种极富渗透性的理念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也便于不经意之中织造出了一张细密结实的网络,套住了自己,同时也不断想要束缚别人。
落后、腐朽的民俗文化的日常化、细节化以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形式,遍植于人生活的各个环节,使个体在与既定的对象——多半是一些具有一定势力的人,如长辈、手握权力的人等——交往之时,不是动辄得咎就是终了归顺,从而在层层制驭之中或被别人控制,或将他杀变成自杀,在他人对自己进行控制之前完成自我的控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老一代落后农民对于年轻人追求自由、进步的压制,其作用往往与欺辱着他们的封建势力和腐朽政权的期望之间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换句话讲,在对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态度上,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事实上不自觉地和金旺、兴旺一类的人成为了同盟军,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金旺和兴旺他们始才得以有恃无恐地施展其淫威。
三
和这种日常化、细节化的民俗文化表现相比较,赵树理在他的小说写作中亦说明,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历史承袭性,其实对于个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解放具有更大的控制作用。
《登记》中张木匠的娘年轻时也有过和她的媳妇小飞蛾一样的爱情追求,但她的追求不合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不被周围环境所允许,所以老张木匠依据惯常做法给予了武力的打压,迫使她放弃追求,成为了被习惯所驯服的奴臣。这样的经历,本来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悲剧,但问题的可怕性却在于当张木匠的娘从媳妇熬成婆婆之后,她不仅不对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媳妇给予必要的同情,相反,因为知根知底,所以也便更为冷酷地怂恿自己的儿子:“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为什么会这样了,叙述人解释说:“原来他妈当年年轻时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
腐朽落后的民俗文化的这种历史传承性表现,在《孟祥英翻身》一文中是以“传家宝”的象征形式加以生动演示的。孟祥英的婆婆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针线筐是柳条编的,红漆漆过的,可惜旧了一点——原是她娘出嫁时候的陪嫁,到她出嫁时候,她娘又给她作了陪嫁,不记得那一年磨掉了底,她用破布糊裱了起来,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层,现在不只弄不清是什么颜色,就连柳条也看不出来了”;“装这些东西的黑箱子,原来是李家的,也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留下来的——榫卯完全坏了,角角落落都钻上窟窿用麻绳穿着,底上棱上被老鼠咬得锯齿一样,漆也快脱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就这些东西,——看不清什么颜色的,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留下来的东西,李成娘却想着早给李成娶上个媳妇,“拿她的三件宝贝往下传”。在娶上了媳妇之后,更是时时处处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穷讲究和老规范要求和制驭媳妇,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的一种延续,并因此时时处处发现和感觉到媳妇的不顺心和不合意,不知不觉就成为了新生活的对立面和阻逆者。
旧筐子的不断修补和老箱子的一代一代传承,其首先显现出的结果,便是新生活的难以立足,新人物成长的不易和艰难。二黑和小芹明明是你看上我,我喜欢你,你情我愿,但二诸葛在所修习的传统阴阳五行理念的驱使下,对于孩子们自主的婚姻追求却始终不肯认同,即使政府都同意了,他还是要反对,对区长发急说:“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作为媳妇,金桂和孟祥英虽然对于自己要做的事务都处置得不错,然而依从说不清道不明的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观念,她们的婆婆还是觉得她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没有一个女人样,她们所要进行的新生活建设工作,由是显得格外沉重。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落后习俗这种可怕的历史因袭或传承特性,所以当小飞蛾无意中发现了女儿艾艾用自己的戒指换了罗汉钱之后,对于女儿行将展开的前途命运也便充满了恐惧。“我娘儿们的命运为什么这多一样呢?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鬼跟上了我,叫我用一只戒指换了个罗汉钱,害得后来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直到现在还跟犯人一样,一出门人家就得在后边押解着。如今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真是冤孽:我会干出这没出息事,你偏也会!从这前半截事情看起来,娘儿们好象钻在了一个圈子里。傻孩子呀!这个圈子,你妈半辈子没得跳出去,难道你也跳不出去了吗?”
小飞蛾所恐惧的这种前后两代人跳不出去的“圈子”,其实即是民俗文化的历史传承所体现出来的旧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超稳定存在形态的象征性表达。从纵向的时间视域审视,这种圈子即是旧规范旧习惯的“历史轮回”,时代在发展,新人不断出现,但是经由父子、母女的代代因袭,老旧的意识观念依旧成为新生活的现实内容构成,且作为深层的公共价值规范,全面并细节化地对新的生活的建构和新人的日常言行进行干预。“社会上多数古人传下来的模模糊糊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但是其“却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5]鲁迅所感叹的这种事实,同样具体且生动地表现于赵树理所描写的人们的生活,“从来如此”,或者“先前就是这样的”,太多的古旧习惯,历史轮回的这种圈子的束缚,不仅使外在环境往往借助于传统和数量的优势,迫使个体接受这些外在的规范,最终在“貌似无事的悲剧”形式展开之中,使新人迅速老化,即如赵树理所刻画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如三仙姑、小飞蛾婆婆、李成娘、金桂婆婆等,通过自我的阉割和改造,成为封建思想观念的承载和传播者,阻逆或者延滞个体的觉醒和新生化展开的速度;而且也诚如鲁迅所言,旧的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一如病毒的遗传,“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6]“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7]
鲁迅所讲的后一段话中的情形,典型地体现于赵树理所写的蜕化变质的新一代青年,像《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像《邪不压正》中的小昌等。小元本是老槐树底下小字辈的代表,是和村西头的作为封建旧势力代表的恒元等人站在对立面的,但是当他被小字辈们推举领导之后,架不住恒元、广聚、家祥等人关于领导应有派头的意识灌输,在旧习惯和讲究的渗透之下,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从此之后,小元果然变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成为旧势力恒元一派的同盟军;无独有偶,小昌原本也是革命的积极分子,但是当革命成功做了农会主任之后,因袭旧有的落后习俗和意识,在分了地主刘锡元的房子、土地之后,不知不觉又成为底层民众新的主人。旧有习俗和意识理念在新一代人身上生动具体的传承演化过程之中,通过新的蜕变或者新旧的掺杂,使赵树理从一个至深的层面上,延续了鲁迅曾经所揭示的启蒙主题,告诫人们必须时刻清醒封建思想借助于传统习俗和意识的历史因袭,“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创造新的生活。”[8]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具有着鲜明民族特色的乡土写作者,在中国文学力求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世界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内涵建构之时,于新文学思想启蒙的主题表现之中,赵树理在其小说写作中对于民俗文化的对待和处置,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因其本身作为“赵树理方向”所发生的历史影响,以及话题本身所牵涉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个人、文人与民间、启蒙和文学等复杂关系,所以对于它们的研究,自是可以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引向一个极为深广的天地或空间。
[1]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M]∥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1777.
[2]孟祥英翻身[M]∥赵树理文集:第1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195.
[3]赵树理著作年表[M]∥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1940.
[4]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1.
[5]我之贞烈观[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4.
[6]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4.
[7]十四年的“读经”[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0.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