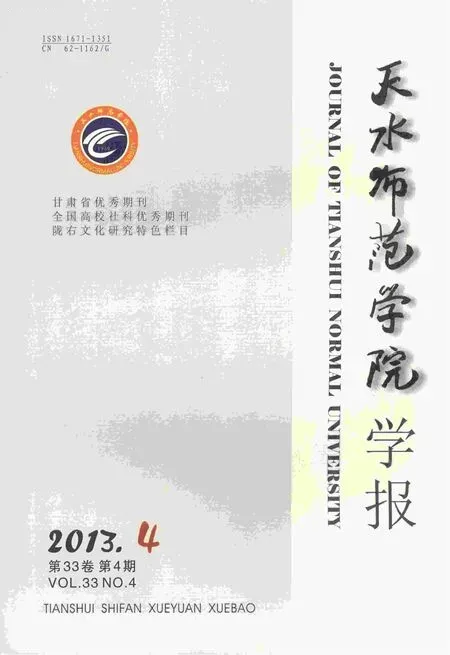试论生态文明观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陈彩棉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室,福建 泉州 362000)
生态中心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在反思人与自然之尖锐冲突中产生的一种绿色思潮,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主要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的“深生态学”。在很大程度上,生态文明观也是我们党为了应对并缓解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而提出,但由于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旨趣和致思路径不同,它提出了与生态中心主义迥异的观点与主张。在价值观、工具论以及伦理学三重维度上,生态文明观都实现了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本文拟就这些超越进行简要探析,以加深人们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认识,并增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一、价值论意义上的超越
在环境伦理学中,在大自然中是否存在中心以及何为中心的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中心之所在。与之相对另一派是生态中心主义。其中自然价值论者明确地对人之自然中心地位予以否认。正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言: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大自然是一个由没有等级差别的不同器官构成的机能性整体,其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中心;人类在生态群落中没有什么特权,只是自然有机整体中平等而普通的一个成员,其超越于“非人”的各种能力既不能成就其“处于环境的中心形象”,也不应成为其野蛮统治其他事物并掠夺自然的理由。[1]240以阿伦·奈斯为代表的深生态学者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观点:生物圈乃至整个宇宙是一个呈现为“无缝之网”的生态系统,其中的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人类和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都不过是这一“生态之网”上的一个“节”,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不在自然之外,更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2]28更有甚者,大地伦理学者不仅否认人类之自然中心地位,而且还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当前日趋严重的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终极根源正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分张扬;出于这一认识,为了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主张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代之以更为整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进而走入非人类中心主义;他们同时强调,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关键与重点在于人类改变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角色和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为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3]241
显而易见,尽管各种生态中心主义流派都主张大自然中不存在一个中心,但透过它们对自然尊重的强调,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实质上无疑是将自然置于了价值中心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称之为生态(价值)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中心主义。它们的论证逻辑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生态危机,因而就应该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而采取与之相对的生态中心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因为,正如戴维·佩珀所言:“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犯有傲慢、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而且,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遗传物质或者像在原罪中的腐败:现行的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4]354-355换言之,人并非天生就对大自然有害,而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使然。可见,生态中心主义是反对错了对象,生态中心主义从错误的论证逻辑出发,所得出的观点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是把人放在中心地位,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的主人,那无疑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和神秘化。事实上,人类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人类只能从自己意识的角度去观察自然;而且对自然环境以及生态平衡的界定并没有客观标准,而是依从人类自身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等主观尺度而做出的,因而明显是专属人类的行为。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赞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我们党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生态文明观是全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相一致,生态文明观之所以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是因为它“关系人民福祉”,能够“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尤为值得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旨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且还着力于“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可见,我们党所倡导的的生态文明观是真正以全人类为价值中心的。另一方面,生态文明观意在真正实现人类的价值中心地位。毋庸赘言,要想实现人之价值,必须首先得活着;而人要想活着,就必须使作为“人之无机身体”[5]45,第1卷及其“赖以生长的基础”[5]222,第4卷的生态自然的健康持存。有鉴于此,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可见,生态文明观不仅坚持人类的价值中心地位,而且还强调应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事实上,正是由于其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对人(类)之价值中心地位的确认,生态文明观对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了价值观意义上的超越。
二、工具论意义上的超越
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伦理道德观念也必然会不断扩展;而“一种伦理学,只有当它对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了某种恰当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6]6他们据此断言,传统的伦理学是一种不完备的、偏狭的伦理学;因为在这种伦理学的视野中,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权利,才是道德关怀的惟一对象,除人类以外的一切都没有被赋予主体资格,都被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他们进而认为,正是在这种有着极度偏狭性与偏执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支配下,人类才倾向于对大自然进行粗暴奴役和无情破坏,进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及生态危机现象的发生。出于这一认识,生态中心主义主张,要缓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就必须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进行改造。其改造方案是:必须突破对人的伦理偏爱,拓展伦理道德关怀的阈限和范围,以使一切非人类生物都能纳入伦理关怀的体系范围中,把道德关怀的界限和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所有存在物——尤其是生物——上去,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承认各种非人生物物种的“道德权利”。这就是说,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还要对非人类生物讲道德;惟其如此,才能为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提供确定基础和内在动力。[7]他们强调,尤其是在当前人与自然之冲突不断彰显的状况下,人类更应该把伦理共同体的范围扩及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从大地的支配者变为大地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8]209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生态中心主义对传统伦理学的指责是否妥当,单就其将伦理学改造指认为缓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有效途径而言,则是极为荒谬的。这是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特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是其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体现与反映;而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又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要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单靠伦理学改造是远远不够的;而只有溯及特定伦理观得以产生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充分的共同基础。”[9]43
可见,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不仅要形成确当的生态伦理观,而且还必须将这种伦理观的形成置于对自然予以伦理尊重的现实实践中。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要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不增长就死亡”的生产方式、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异化消费”等对“环境不友好”的特质。[4]134对我们的论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对已实现了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要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就必须象生态文明观所要求的那样,“……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并在这一现实实践中,使得“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0]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现问题上,生态文明观不仅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而且还强调要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形成有利于保护生态的生产方式,从而构成了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三、社会学意义上的超越
在其原初的意义上,伦理学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有着鲜明的社会维度。因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因为它所调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论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所应具有的社会维度,它所强调的不过是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和践行。在罗尔斯顿看来,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就必须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并培养尊重自然的意识;这就是要求个体进化出一种能与自利主义同时并存的利他主义倾向,进化出一种不仅指向其物种、而且还指向生存于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物种的“恻隐之心”。[4]26生态学更是明确地将其希冀寄托于个体意识的转变之上。在他们看来,个体意识的转变是个人的和文化的双重转变,是个体从个人和文化的角度转变自己,从而进行“自我实现”或“自我认同”。他们同时强调,“自我实现”的过程的关键与核心在于自我省悟,借以将自己理解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并自觉地在道德情感上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甘苦与共。[1]253可见,生态中心主义——尤其是深生态学——将生态环境改善的希望寄托于每个个体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因而所予以建立的不过是个人道德,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社会维度的伦理。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态中心主义不仅将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的希望寄托于伦理学改造,而且所予以改造的还是个体意义上的伦理学,因而这一方案是远不能奏效的。与之相对,生态文明观不仅将这一希望置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之上,而且还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这是因为,作为其倡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344第1卷这就是说,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必须首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由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344鉴于此,为了实现科学发展所要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就必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12]
可见,生态文明观不仅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尤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有着生态的维度,同时还涵括社会的维度。在这一意义上,生态文明观构成了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主要侧重于从伦理价值批判层面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并把解决环境问题的良方寄托于借由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来拓展生态伦理,以及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由此显现出实践立场的偏失和社会批判视野的空场。与之相对,生态文明观则更强调从社会现实层面对环境问题展开分析,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冲突的环境问题归结于一个社会问题,并主张借由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来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由此不仅获得了更为宽广的理论视界,而且还直击导致环境问题现实层面,从而全面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
[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AI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M].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66:241.
[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JOHN BELLAMY FOSTER.A New War on the Planet[J].monthly review,2008(6).
[7]王云霞,杨庆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与出路[J].南开大学学报,2009,(4).
[8]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16(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