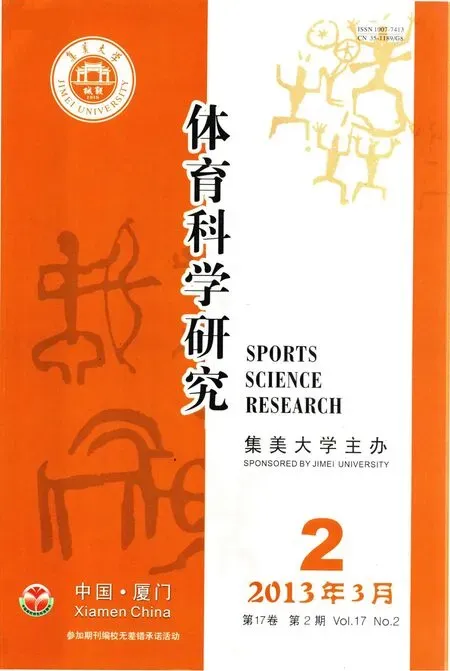竞技体育本质的多重解读与概念重塑
李传兵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体育科学系,福建 福清 350300)
人在认识和改造自我与自在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挖掘事物的本质来不断深入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而事物的本质通常是不能被直接认识,它既隐藏于事物外在现象背后,又深匿事物之中,要真正透视事物的本质,就要通过事物的不同表现形态,寻找隐匿于其中的共同属性。竞技体育本质探求一直是学界长谈不衰的话题,竞技体育在当今社会中的表现形态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多样化,学者们对其赋予不同的认识视角时,就产生了风格各异的本质论点,具有代表性的有游戏论、宗教论、决斗论、活动论、创化论和表演论。笔者对不同竞技体育本质论观点进行解读,在沿袭和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竞技体育本质深邃的解读与重塑征途。
1 竞技体育本质多重解读
1.1 游戏论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顺着“游戏”这一源头对竞技体育的本质展开了没有休止的争论。荷兰学者约翰·胡伊青加(John·Huizinga)从文化论的角度系统考察了游戏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于1938年出版了专门研究人类游戏的专著《人:游戏者》,其惊世观点正如其书名:人是游戏者[1]。在胡伊青加看来,游戏与竞赛具有本质同一性。德国学者笛姆(K·Diem)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游戏,从狭义上来说,竞技运动是有组织的身体性游戏。[2]”美国学者托马斯(C·E·Thomas)指出:“竞技运动具有游戏的要素,但在规则、组织性和对结果的评价等方面却超出了游戏的范畴。[3]”日本学者今村浩明主张:“竞技运动在广义上与游戏同义,狭义上是游戏的诸形式之一。[4]”
国内学者周爱光从对胡伊青加、凯洛易和威斯等人的游戏理论与竞技特征内涵进行分析比较的视角深度阐述了游戏与竞技体育本质的紧密关系[5]。卢元镇将竞技体育比喻成为游戏与工作之间的游标,认为游戏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本原,同时他也指出随着竞技体育的不断政治化、商业化和职业化,将奥林匹克运动抹得色彩斑斓的同时,也使得这一游标不断向工作靠拢[6]。张军献更是从本质主义的视角直截了当的提出“竞技本质游戏论”的观点,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深入、淋漓地论证阐述,最后将竞技定义为:“身体活动性游戏。[7]”竞技体育与游戏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从手段论的视角出发,原始游戏与竞技体育都是依托身体活动来达到目的。它们都强调一定的规则、时空限制,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是游戏与竞技体育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游戏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而竞技体育则日趋组织化、制度化,尤其是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轮廓更是越来越清晰化;其次,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乐趣,离开乐趣,游戏将不能再谓之游戏,而竞技体育则不然,即使痛苦,竞技体育也要进行下去,更何况绝大多数竞技体育都是在经历了痛苦地努力、拼搏和磨练后才得以实现其目的。刘欣然以“语言屏障”、“语言游戏”、“文化游戏”为依据对张军献的“竞技本质游戏论”进行了反驳,认为“竞技本质非游戏”[8]。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游戏的理解已经不能再囿于狭义的原始游戏,现代游戏可以分为原始游戏和文化游戏,两者合成现代广义的游戏。原始游戏需要身体的参与,而文化游戏则不然,游戏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的扩大和泛化,所以竞技体育本质游戏论的观点受到了质疑。
1.2 宗教论
竞技体育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宗教的色彩;而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或多或少都充斥着迷信色彩的身体活动,使得竞技体育与宗教的关系甚为密切。首先,古代希腊人将竞赛活动与希腊众神完美地结合,表达对希腊众神中最伟大的宙斯的敬意,以象征他们生活中的普遍力量。这为竞技体育在这一时期得以繁荣发展奠定了相对自由的宗教文化根基。
而后来古代奥运会禁止举办的矛盾实质是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与在精神上的信仰相比,更多的是一种身体崇拜。传统的宗教竞赛活动表现在他们对诸如美的身体姿态的追求和对强劲膂力的展示上。其次,中世纪由于“灵肉分离”的宗教思想逐渐盛行,基督教在继承了古希腊的身心二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精神的作用,以否定世俗、弱化肉体的方式来求得灵魂的超脱[9]。
这一时期的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us)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以人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为理论依据(即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组合),将世界化为两个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分别象征着光明与黑暗。作为用灵魂来生活的世界里的公民,就活在“上帝之城”中;而用肉体来生活的世界里的公民,则栖息在“世俗之城”,其实质是让人们远离罪孽深重的世俗生活,超脱束缚灵魂的肉体之身[10]。这一宗教思想的盛行以及基督教与古希腊、古罗马信仰的多种教义之间冲突导致竞技体育的发展进入了“黑暗时期”。
但是这种虚空的“精神至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让竞技体育彻底消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等思想运动的兴起对“身心二元论”进行了批判,使得“灵”与“肉”二者再次结合。这期间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Valla),他提出了“身心一元”、“灵肉一致”的观点。随后,高举文艺复兴大旗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了以人为中心地位的观点,并认为人的本质并不在“灵肉分离”的彼岸世界,而是在“灵肉一体”的世俗世界之中[11]。在反对封建势力的过程中,他们倡导以“人”而非以“神”为中心的文化,主张以“人权”代替“神权”基本思想,这种“人的重新发现”便为古希腊式的竞技体育复苏奠定了思想前提。与此同时宗教改革者们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抨击,强调“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12],这一时期人们对个体自由的追求、身体性的凸显以及竞争意识的形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古奥林匹克运动在沉寂千年之后再次复苏,并以全新的面貌展示。虽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再带有明显的宗教功能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进取精神,但它始终还是沾染着一些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我们经常会看到运动员进场时会摸一下场地,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架,向上帝默默祈祷;各大足球联赛中的“德比大战”,其实也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碰撞,激起了球迷的疯狂和失声竭力的呐喊,这种“泛宗教”类型的狂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竞技体育迷、粉丝团、协会,甚至各种教会(如“马纳多拉教”)。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竞技体育深受宗教发展的影响,但两者很显然不具有本质同一性,它们各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研究范畴,宗教不仅研究“人”的活动,还研究“神”的象征,而竞技体育本质是根植于人的,不会是神,也不能是除人以外的其他动植物。
1.3 决斗论
决斗,作为人类原始野蛮生存流习的延伸,其起源有三:一是雄斗雌决的搏斗行为;二是为争夺食物而进行的格斗行为;三是为争夺或保卫领土而进行的群体战斗行为[13]。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近代欧洲,竞技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而斗争更是根植于人类原始野蛮生存流习,展现着人类本能的野蛮和魅力。
实际上,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决斗与竞技的联系源于文化的交织发展,文化与文化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继承。古希腊人对体育的“欢娱精神”与古罗马人相互对体育的“实用主义”是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化,却也是继承的关系。恩格斯曾说:“没有希腊就没有罗马,没有罗马就没有近代欧洲。”罗马人在有意无意中继承了希腊的某些文明,但是对于文明的甄选是一种源自于民族性格的特征,罗马人将希腊人的“体育”和埃特鲁斯坎人的“角斗”相融合,并将两者结合成为罗马人特有的角斗竞技表演活动[14]。
然而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后,对于体育运动的钟情发生了异化,人民已经不再喜欢自己裸体的奔跑,而是钟情于观赏他人生命的决斗。这种方式传达出古罗马人对勇气、力量和胜利的渴望,角斗士精神就是古罗马人对于强力征服的欲望,这是维系罗马精神的支柱之一。随着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角斗竞技表演也就此散场,但是这种“决斗精神”却并未因此消失,决斗作为一种明确风行的文化,以“骑士精神”和“决斗风范”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包括拳击、击剑、斗牛等现代竞技体育,都是“决斗”文化的缩影与遗存。决斗发展到近代以后,已被近代理性主义者所取缔,但是,决斗并未消亡,恰相反,就好像任何一种古典时代人类的社会选择一样,决斗的精神与尊严、理想与价值,仍然感召着世界上众多的人[13]。决斗者必须发挥自身所有的潜能来战胜对手,而竞技体育中竞技者,也要发挥自身所有的潜能来战胜对手或者夺取优胜,在这一点上,决斗风范与竞技精神不谋而合。
有鉴于此,竞技体育便慷慨地收留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遗产,并将其熔铸到了竞技体育的精神内涵之中。竞技者们通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不断提升竞技能力,形成和发展竞技状态,在约定的竞技赛场,与其他竞技者一决高下,争取战胜对手或者夺取优胜,这不就是决斗的原型吗?现代各种职业体育赛事,如英超、意甲、德甲、西甲、法甲、欧冠、世界杯、NBA、拳击等等,之所以让人们如此热衷痴迷,源于人内心的“决斗情结”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决斗如同游戏一样,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决斗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需要身体参与的原始决斗,文化决斗的发展使得决斗的内涵和外延也得以深入和扩展。另外,决斗精神并不是仅仅体现在竞技体育中,而是体现在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之中。核弹头是科技竞赛的结晶,发展航天技术的首要目的是争夺宇宙空间。影视作品中所谓的戏剧高潮,无非是对立双方对抗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突然由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将对立双方提炼成两种绝对力量,使之硬性对撞,最终决出胜负[13]。决斗必争胜负,而竞技则超越胜负,更侧重于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两者属性有类似,但本质有别。
1.4 活动论
竞技体育本质活动论有三个版本:一是身体活动论;二是竞赛活动论;三是社会活动论。“身体活动论”认为竞技体育就是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Frank Galligan[15]对竞技体育的界定是指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周爱光[16]将竞技的概念定义为:一种具有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挑战性以及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
其中“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和不确定性”是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而“身体活动”则是竞技体育的本质,这是侧重于以手段论的方法来给竞技体育下定义,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探析竞技体育的本质,最后将其定论为身体活动。“竞赛活动论”认为竞技体育是通过专门有组织、有计划的训练,逐渐提高人的竞技能力,培养和发展竞技状态,最后成功参加竞赛,完成竞技目标的活动。
胡亦海[17]在其著作《竞技体育训练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将竞技体育定义为:通过专门的运动训练,在最大限度挖掘和发挥个人和集体体力、心理、智力等潜力的基础上,以在比赛中创造最高运动成绩为主要目的的活动过程。全国体院版的《运动训练学》教材[18]将竞技体育定义为: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
这些观点认为训练和竞赛是竞技体育的主要过程和内容,“优胜”、“夺冠”等是其主要目标。“社会活动论”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现代竞技体育之所以成为一项影响巨大的社会实践,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除它以外任何其他形式均不能替代的体育产品。由此,肖林鹏[19]认为:竞技体育是指运动员以比赛竞争为基本手段,以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这一观点是在对“竞赛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侧重从竞技体育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诠释竞技体育的概念,以此来探析竞技体育的本质。
上述三个版本的“竞技体育本质活动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对竞技体育的本质进行阐述,都有各自的理论基础,但三者也都是不全面的。“身体活动论”将身体活动视为竞技体育的本质遭到质疑,作为身体活动本质说的反对者,于涛[20]认为:依照现代哲学对身体的理解和身体一词的使用来看,所有的活动都是身体活动,“身体性”已不再为体育所独有,所以把“身体性”看做体育的本质有些不妥,比如劳动实践、艺术动作等也是身体活动,但它们不属于竞技范畴。“竞赛活动论”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竞技体育简单理解为了高水平竞技也是有失偏颇。周爱光[16]认为把竞技运动概念只解释为高水平的选手竞技体育是不妥的,这样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竞技运动这一概念的外延。另外这一观点将竞技体育的目的理解为“优胜”、“夺标”、“争冠”等等也广受质疑。现代竞技体育的内涵早已超出了“优胜”、“夺标”、“争冠”等表面形式,如有时基于政治、交往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竞技体育中有时故意放弃或输掉比赛的现象比比皆是[19]。“社会活动论”重点诠释了竞技体育“社会属性”层面,而忽视竞技体育中竞技者“主体参与”的价值诉求,前者必须是在后者得以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同时这一观点也不能明确体现竞技体育与其他体育活动之间的“种差”。
1.5 创化论
在19世纪与20世纪新旧哲学交替之际,法国著名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1927年以其著作《创造进化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柏格森[21]的“创化论”以生物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批判刻板的机械论和传统的理性主义,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派生的,派生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事物的千差万别。
在这万千的派生方式中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者说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即他的向上喷发,他产生一切生命形式;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向下坠落,他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这两种倾向根本对立、互相抵制。生命冲动的向上运动总是企图克服向下坠的倾向,克服物质事物的阻碍,而生命冲动的向下坠落也必然牵制其向上的喷发。在生命冲动受坠落的物质牵制而发生“停顿”与物质交接的地方,产生既有生命形式又有物质躯体的生物有机体。不仅如此,柏格森还把上至人的感情意志活动、下至无机物的存在,都当作生命冲动的产物。他认为那些沿着生命冲动的自然方向前进未受阻拦的生命构成了精神性的事物,例如人的意志、灵魂。而那些作为生命冲动的逆转而未获得任何生命形式的东西则构成了无机自然界,即所谓惰性的、物理的物质。柏格森认为生命是意识的绵延,是心理的东西,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生命冲动与意识绵延[22]。邰峰[23]和杨韵[24]沿袭这一理论视角,认为竞技体育究其深邃,实际上也是生命进化的发展过程,始终是以传承人类文明,追求生命价值,推动生物进化与发展为目的的“人”的修炼过程。只是人们对社会认知程度的改变与提升,对利益与物质需求的不断增加,已经异化了竞技体育的本质。致使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已经忽视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追求,背弃了物种进化的生命意义;背离了平等、自由、和谐的价值观体系,反之使其成为了追逐名利的工具;成为了政治化的手段;成为了满足利益欲、物质欲的生活方式。
依照机械论的逻辑关系来计算竞技体育成绩的获得,是将训练能力值与比赛经验值相加就可以推算出来的最终结果,从而忽视了人类生命的创造性,潜能的激发性,灵魂对肉体的驾驭性,精神与意志的超越性,竞技体育的偶然性以及人类对价值、情感、责任的不懈追求,而显现的更近于“一种纯粹的理性虚构”。
然而,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生命进化过程,其发展正好比机械论的思想桎梏与困惑那样,似乎是被某种“物质力量”拖拽住了一样,偏离了生命本质进化的发展轨道,背离生物自然发展进化的规律,脱离了竞技体育存在的本质涵义与科学内涵。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竞技体育本质创化论者认为竞技体育的本质是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和意识的绵延与自由。这一竞技本质论的理论追述到了生命的源头,也为呼吁重视竞技者的“生命存在”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生命冲动和意识绵延并不尽集于“竞技体育”一身,这一问题类似于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全在于“体育”一家,不免会让人觉得有些扯着“生命哲学”的大旗,鼓噪其理论先天优越的意味。体育作为人类文明之一,在促进人体身体健康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独臂是难以完成人的全面发展之大业的,同样,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分支,在展示人类生命力量方面是能得到认可的,但是其单肩是不能挑起整个生命之重担的。
依照柏格森的创化论,生命冲动的派生方式多种多样,竞技体育如果作为一种生命冲动的派生,那么它是一种纯粹的生命形式,还是生命和物质的共同体或者其他形式?竞技体育是伴随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人类生命本身就是意识与物质的结合体,笔者认为将生命冲动和意识绵延视为竞技体育的本质则难逃质疑,而且使得竞技体育的本质泛化,无法凸显竞技体育的独特性。
1.6 表演论
表演,在古汉语中是以“表”和“演”分开形式存在的,李政涛[25]对“表演”进行了词源考察,认为“表”和“演”都具有由内向外、向他人传达消息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表演”的内涵更加丰富:演示性的动作、情节、技巧或者戏剧、舞蹈等等。随着“表演”内涵的不断拓展,它已经逐渐的形成一种理论体系。理查德·谢克纳[26](Richard Schechner)于1977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的《人类表演理论》和《人类表演学导论》,为“表演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也促使“表演学”成为一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和视角,如果从这一视角来探视竞技体育,会发现竞技体育充满了表演韵味。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开始,竞技体育就与表演结伴而行了。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和表演都还处于朦胧和雏形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竞技”与“表演”,当时的竞技是宗教活动中的一种竞技赛会,是用来祭祀希腊各城邦众神的庆典,而且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大大小小有近200个,每一个城邦几乎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他们都会举办竞技赛会来祭祀自己的守护神。其中人们祭祀众神之父宙斯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祭祀太阳神阿波罗的“皮提翁竞技赛会”、祭祀海神波赛冬的“伊斯玛斯竞技赛会”和祭祀大力神海格斯的“尼米亚竞技赛会”是古希腊时期最著名的四大竞技赛会[27]。实际上,在这些祭祀活动中,除了竞技赛会,还有歌剧、舞蹈、诗歌等等其他活动。但这些活动都充满着宗教仪式的色彩,从谢克纳的表演学视角来看,这些活动可以被称为“仪式表演”。这一时期希腊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而战争需要强健的士兵,所以竞技赛会是非常受推崇的活动,加之当时的宗教信仰大背景,使竞技赛会作为“仪式表演”得以盛行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战乱纷争,使得希腊国力大减,以致被马其顿吞并。在马其顿君王菲利普时期,“赛马”做为一项竞技体育甚为风行,菲利普君王也亲自参与。不过,这一时期古奥运会精神已大为减色,并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因此,古奥运竞技赛会作为“仪式表演”也走向衰败。古罗马帝国统治希腊后,更是导致古奥运由衰败走向了毁灭。取而代之的是的“角斗竞技表演”,角斗场是表演的舞台,角斗士就是表演者,随着观众一声声呐喊、呼唤和叹息,一次次欢呼、跳跃和喜庆,血液在流淌、在沸腾,这是一种“异化表演”,充满了血腥、残冷、野蛮。然而这种“异化表演”却正象征着罗马人对勇气、力量、征服和胜利的渴望。我国古代的典型竞技运动如“蹴鞠”、“马球”、“捶丸”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表演,只是表演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皇宫贵族们的娱乐需求,因而观看席设置规模并不大,而民间竞技项目则由于其竞技场具有随意性、流动性等特点,使得这种竞技表演散落在民间,没有形成规模。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品性决定了我国竞技场不可能形成与西方竞技场相当的规模[28],但是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展现了竞技体育的表演性质。历史长河流长的脚步是无人能够阻止的,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必然的,竞技体育与表演的交织发展铸造了现代竞技体育表演的璀璨和辉煌,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表演”或称“大众表演”。袁旦认为近代以来在“小体育”向“大体育”演进过程即体育的社会化过程中,为满足人们通过观赏竞技表演获得特殊审美享受的需要,产生了以竞技体育表演为谋生手段的职业。竞技体育运动中的竞技者运用高超的身体技艺向外传达信息、向他人展现自我,使得现代竞技赛会成为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盛宴和视觉大餐。
方千华[28]从身体语言、身体体验、身体真实、身体文化、身体呈现、生命确证六个方面淋漓地论述了竞技体育的表演内涵。并认为现代意义的“表演”具有泛表演的内涵,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词汇,成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或研究方法[29]。表演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应用于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中。谢克纳认为社会表演可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表演,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可以归于社会表演,只是表演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2 竞技体育本质探邃与概念重塑
2.1 竞技体育本质探析
要探究竞技体育本质,就要弄清“本质”是什么?哲学范畴中的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本质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是一个事物和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所在[30]。例如,化学运动的本质是由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矛盾决定的。与“本质”对立存在的是“现象”,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与现象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真象是从正面直接地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假象是从反面歪曲地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要真正透视事物的本质,就要通过竞技的不同表现形态,寻找隐匿于其中的共同属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亦称矛盾规律。这一规律指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31]。不同的事物包含的矛盾都有其自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32]。既然本质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是一个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根本。那么竞技体育的本质是由什么样的特殊矛盾所决定呢?这是在竞技体育本质探邃中要回答的问题。
本质不能与主体分离,外在于主体的事物是无意义的,事物本质的发掘与对主体的深入认识密不可分。竞技体育本质是根植于“人”这一主体的,离开人这一主体,竞技体育本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人有很多方面,很多矛盾。竞技体育关于人这一主体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根据袁旦[33]的“三维体育观”,即“生物、心理、社会体育观”。我们在思考体育问题时,要运用“生物、心理、社会三维系统体育科学思维模式”来进行思考。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者在生物维度的差距在缩小,使得心理、智力、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能力优势更显重要,尤其围棋、象棋、桥牌等非传统意义的竞技项目加入到竞技体育行列中来,不能再将竞技体育理解为单纯的生物性、身体性活动,而是身心并重的活动。所以竞技体育关于人这一主体的矛盾就集中在人的身心方面,而矛盾的具体形式或内容就是人们在体育活动中发挥人体生理、心理和智能等方面最佳或最大能力的理想与人体身心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是一方面挖掘人体生理、心理和智能等方面的潜能,一方面提高人体身心现实能力水平,前者的挖掘提高了对后者的要求,而后者的提高也为前者筑构了坚实的平台。而这一挖掘和提高过程都离不开运动训练(这里所说的运动训练并不限于高水平的专门训练),要求竞技者要遵循科学的训练原则和规律,合理地挖掘和提高人体身心能力,最终通过以体育竞赛为主要形式的活动表现出来。
2.2 竞技体育目的界定
国内外关于竞技体育目的的争论大多聚焦在对“优胜”、“夺标”、“争冠”之类目的的质疑,例如在有些竞技体育活动中竞技者基于某些政治或商业目的“故意”输掉比赛的行为来予以质疑反驳,笔者也赞同类似观点。当今竞技体育由于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商业利益的驱使,使其受到强烈的政治关照、巨额的经济投入与回报以及狂热的媒体卷入[34],从而也使得竞技体育逐渐物化、异化。实际上,从竞技体育主体参与的价值诉求角度来看,我们要关爱和呵护竞技者,重视竞技者作为“人”的生命存在[35],竞技者在运动中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生命力量,从竞技体育观赏的社会属性层面来看,人们通过参与和欣赏竞技体育,在满足了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发展资本。因此,可以将竞技体育目的界定为:展示人类生命力量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
2.3 竞技体育种差辨析
国内比较公认的体育分类方式是认为竞技体育隶属于体育活动范畴,是体育“三分”中的一支,而体育活动实际上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36]。因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活动层面,体育是一种文化活动,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活动层面,体育又是一种社会活动。随着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其社会属性也在不断凸显,甚至有突破体育的范畴另立门户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文化活动”就是竞技体育的“属概念”,如果要给竞技体育下定义的话,还必须找出其“种差”。这样就符合“被定义项 =邻近属概念 +种差”的定义法则[37]。卢元镇曾经指出体育教育与竞技运动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描述和构造未来人类的特征。体育教育侧重说明各种特征的必要性,而竞技运动则侧重探索各种特征的可能性[38]。具体一点说,与其他体育活动相比,竞技体育更侧重于不断的探索人在生理、心理和智能等方面潜能的可能性。
2.4 竞技体育概念重塑
最后,笔者结合前述分析将竞技体育定义为:以运动训练为主要手段合理挖掘人体生理、心理和智能等方面的潜能,以体育竞赛为主要表现形式来展示人类生命力量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社会文化活动。
3 结束语
在竞技体育异化饱受批判的现实下,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辨析和理解竞技体育的本质,有利于拓宽视野,打开思路。与此同时,在对竞技体育本质不断进行探析的过程中,吸取各研究观点的精华,更新对竞技体育概念的认识,有利于竞技体育的准确定位和统筹发展。
[1][荷]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2][德]笛姆.竞技运动的本质与基础[M].福冈孝行,译.日本:政法大学出版局,1974:31.
[3][美]托马斯.竞技运动哲学[M].大桥道雄,译.日本:不昧堂出版社,1992:20.
[4][日]今村浩明.竞技运动文化与人类[M].日本:大修馆出版社,1979:28.
[5]周爱光.论“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从游戏论的观点出发[J].体育科学,1996,16(5):4-12.
[6]卢元镇.还奥林匹克的游戏本原[J].体育文史,1996(2):52.
[7]张军献.竞技本质游戏论——本质主义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0,17(11):1-8.
[8]刘欣然,余晓玲.竞技本质非“游戏论”——就本质主义立场与军献兄商榷[J].体育学刊,2010,18(3):7-13.
[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43.
[10]AUGUSTINUS.The City of God[M].Translated by R·W·Dyson.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
[11]孙玮.历史视域下的“宗教竞技”及其与游戏属性的勾连[J].体育科学,2011,31(5):86-90.
[12]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49.
[13]路云亭.竞技的本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22(6):461-464.
[14]刘欣然,蒲娟.文明的选择:古罗马角斗竞技的体育思想溯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10):30-34.
[15]FRANK GALLIGAN.Advanced PE for Edexcel[M].Heinemann Educational Publishers,2000:15.
[16]周爱光.对竞技运动概念的再认识[J].中国体育科技,1999,35(6):5-6,10.
[17]胡亦海.竞技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0.
[18]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
[19]肖林鹏.竞技体育本质及发展逻辑[J].体育学刊,2004,11(6):1-3.
[20]于涛.体育哲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31-38.
[21][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1.
[22]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33.
[23]邰峰,何艳华.哲学视野下的竞技体育本质解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9):120-123.
[24]杨韵.体育的生命冲动与绵延——基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体育本质解读[J].体育科学,2011,30(11):87-92.
[25]李政涛.生活的表演——人类行为表演性的教育学考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5-7.
[26]RICHHARD SCHECHNER.Performance Studies-An introduction[M].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02.
[27]赵岷,李翠霞.人类表演学视角下的古希腊祭祀竞技赛会[J].成都体育学院报,2010,36(1):21-23.
[28]方千华.表演视域中的竞技运动诠释[J].体育科学,2008,28(6):78-96.
[29]方千华.竞技运动表演论[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10-17,87.
[30]邢辉生,吕晓东.哲学基础[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62-63.
[31]郭学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5:100,154.
[32]高铭鼎.从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谈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J].体育教学与科研,1987,16(5):4-12.
[33]袁旦,谭卫和.论体育观和体育科学思维模式的几次重大变革[J].体育科学,1987(1):76-82.
[34]卢元镇.竞技体育的强化、异化与软化[J].体育文化导刊,2001(4):19-20.
[35]方千华.生命视野下的竞技教育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9):1256-1259.
[36]鲁长芬,陈琦.从当代体育价值观的转变透视体育本质[J].体育文化导刊,2006(6):26-28.
[37]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
[38]卢元镇.论学校体育与竞技运动的关系[J].体育科研,2000,21(3):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