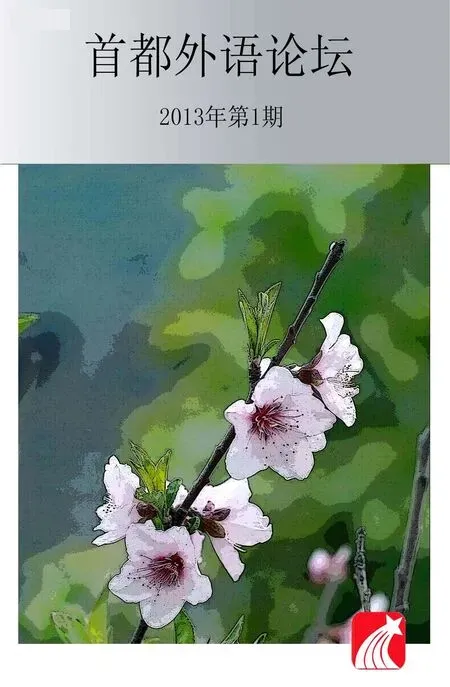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与意境美学
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 杨波
一
海德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之所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原因在于他突破了长期统治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此种区分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到笛卡儿那里便有了确定的形式,即“主体性原则”,而终于至黑格尔达到了顶峰。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人的认知能力被抽象出来作为认识的主体,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都被放置到主体的面前,成为主体的认识对象。于是,整个世界都成为外在于主体、对象化了的客体。此种思维模式正是列奥塔所说的“表象形上学” (representative metaphysics)。与表象形而上学紧密相联的是传统存在论,即认为在万事万物的背后有一个最高的终极的“存在”,此“存在”的“本质”也可以用主体的逻辑范畴去把握。哲学的目的就是把握“存在的本质”。形而上学与传统存在论相结合的结果,是造成统治西方思想数千年的旧存在论哲学传统,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形成了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关系的宰制。在科技理性精神彰显的同时,人并没有感到满足,而是感到一种深切的失落,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日益感到“无家可归”。
海德格尔认为,要扭转这种思维与存在二分的局面,必须回到古希腊早期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所谓“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基本思想。海德格尔警告我们,在这里不能用通常的模式来理解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以为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客体,从而认定思维与存在同一就是表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主观的,这乃是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学说,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学说,“使我们难于理解巴门尼德所说的原始希腊语词的真正意思。”①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7 页。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人是“用极其原始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关系的,因为这是哲学的开端,而且他们缺乏认识论方面的训练。”②同上,第136 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与巴门尼德对立的赫拉克利特在这方面与巴门尼德的观点是一致的。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聚集,采集”,也有“说”和“听”的意思。而“聚集”、“说”、“听”,都是使事物内在地联结起来,从而使之明白起来和显示出来。这样,“逻各斯”也就有了存在的意思。巴门尼德的存在也是出现、显示之意,而巴门尼德的“思”并不是指人的属性或能力,而是指人的出现过程,这样,“思维与存在同一”,实际上不是说的主体与客体同一,而是说存在通过人的活动显现出来。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无主客二分的思想,他们都把人和存在看成浑然一体,都把人看成是存在的显示、去蔽。“就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已经很明显的是,存在的问题必然包含此在的根基。”③同上,第174 页。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又译作“亲在”)实际上是指的人。人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世界通过人而显示出来的关系:“此在”是“存在显露自己的场所”。④同上,第205 页。没有“此在”,“存在”不能显露自己,因而存在是无意义的。当然“此在”也离不开“存在”,因为“此在”的最基本、最原初的状态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In-der-Welt-sein),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就是“人生在世”。“人生在世指的是人同世界浑然一体的情状,”①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406 页。而不是把“世界”当做外在于“我”的对象。“人生在世”,首先要和世界万物打交道;至于人作为主体来认识客体的关系,那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后来衍生的。认识必须走向“在世界之中”的源认识,才能破除主客二分对认识的限制,走出形而上学思维习惯的误区。
二
海德格尔超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美学有重大的突破意义。柏拉图把文艺摹仿现实贬低为“照镜子”,认为文艺是理念的“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着三层”,并据此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虽然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肯定了文艺摹仿现实的真实性,但是也更加坚固了摹仿论的基础,从而确立了摹仿论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统治地位。这一统治地位直到浪漫主义时期才遭到质疑。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源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强调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和“自我”的独立性,认为“自我高于一切”,反对理性的无上统治和将情感屈从于理性的做法,主张文艺应表现人的主观情感和思想。浪漫主义反对现代机械文明,要求返回自然淳朴的原始生活和人的自然情感。例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主张远离城市文明,到自然中去寻找“自发的智慧”(spontaneous wisdom),这和中国古典山水诗“天人合一”的理想颇有相似之处。然而,正如叶维廉先生在“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一文中所指出的,华氏虽然提出Wise Passiveness(意为保持一种聪悟的被动,近乎道家之所谓“虚以待物”)的名言,但是他诗中用了大量解说性、演绎性的文字,和“景物不知不觉进入他脑中”的观物理想相违。事实上,浪漫主义诗人“常常有形而上的忧虑和不安,因为他们,像康德一样,认为纯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认识论必须包括诗人的想象进入本体世界的思索,必须挣扎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跃入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②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李达三,罗刚:《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 页。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力图解决主客观之间的对立,使人与自然获得统一,但是他们的诗歌中主客始终是分裂的,并且时时流露出试图弥合此种分裂的挣扎焦虑的痕迹。
真正实现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批判了历史上那种把“我思”客观化的做法,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海德格尔通过对玫瑰的体验来告知这种思的独特:
对于更宽泛意义上的物的日常经验既不是客观化的,也不是一种对象化。譬如,当我们坐在花园中,欢欣于盛开的玫瑰花,这时候的我们并没有使玫瑰花成为一个客体,甚至也没有使之成为一个对象,亦即成为某个专门被表象出来的东西。甚至当我在默然无声的道说中沉醉于玫瑰花的灼灼生辉的红色,沉思玫瑰花的红艳,这时红艳就像绽开的玫瑰花一样,既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物,也不是一个对象。玫瑰花在花园中,也许在风中左右摇曳。相反,玫瑰花的红艳既不在花园中,也不可能在风中摇曳。但我们却通过对它的命名而思考之、道说之。据此看来,就有一种既不是客观化也不是对象化的思想与道说。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1 页。
因此,那种认为“我思”必须客观化和对象化的想法是一种误解。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是非客观化、非对象化的“思”展开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让美走到前台,或者说这个世界就是美的世界。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海德格尔反对将语言当成是逻辑演绎、表达事理的工具,认为此种观念掩盖了语言的本质来源和美学意蕴。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在其本质中澄明着人类生存的境遇。海德格尔写道:“语言之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这一规定全然没有触着语言的真正本质,而只是指出了语言之本质的一个结果而已。语言不止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②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页。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话”不是抽象的精神、思想,而是在万物中留下(刻出)存在的“痕迹”,使事物本身“明朗化”。语言不但保存着存在之敞开状态,还赋予人通达存在的道路。所以海德格尔说, “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在语言中安然栖居于存在的家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之思才开启出世界,这种世界不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世界,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是一种生存的境界,是“实际上的此在作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76页。海德格尔把这个世界加以具体化,他说:“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具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④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188 页。这里的纯一性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而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这四重整体的统一性就在于说到其中一方,其他三方也必然包孕其中。人生存于大地之上、苍天之下,承纳着神性的恩爱,因此而构成了世界存在的原初的一。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以“此在”的存在为基础,以诗意的栖居为旨归的哲学思路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而接近东方的哲学精神。叶维廉在“道家美学·山水诗·海德格”一文中,说海德格尔所致力的回到苏格拉底以前的原真状态,力求呈现“存在的具体性”,重建与世界的直接、原始的接触,与道家美学大有共通之处。他说:“要消除玄学的累赘、概念的累赘也可以说是海德格哲学最用力的地方。像道家的返璞归真,海德格对原真事物的重认,使到美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①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第169 页。关于海德格尔和道家思想的亲缘性,前人已经作了不少研究。这里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只想谈谈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美学范畴中的“意境”的共通之处,这一方面也许可以在“意境”的理解上提供些许启发,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有助于在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作些沟通和交往。
三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核心范畴,高度凝结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意境”是从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意象”发展而来,其作为概念首次被提出来是在唐代,近代王国维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总结和揭示,并使其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和艺术内在本质的最高理论概括。关于“意境”的理论内涵与本质,众说纷纭,缺乏定论。但“意境”有两个基本特征已经是共识,即“意与境浑”和“艺通于道”。“意与境浑”强调艺术和诗歌创作中主客合一的艺术体验,“艺通于道”则是强调艺术是宇宙人生之道的显示。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意境美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都具有共通的理论向度,从而为中西美学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契机。
“意与境浑”或曰“意与境偕”,是意境的基本结构。王昌龄《诗格》说:
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8 页。
这里说的是诗歌意境产生的三种情况。“思”是刘勰所谓“神思”,也就是艺术灵感和艺术想象。 “心”是审美活动中的主观因素如诗人的情意,“境”则是审美活动中的客观方面。“心偶照境”、“心入于境”,都是强调艺术灵感和艺术想象不能脱离客观的“境”,而要依赖审美观照中“心”与“境”的契合。《诗格》中另有一段话对这个意思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②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 页。
意境的创造要依赖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的契合,没有达到物我交融、心境契合的状态,就不能有意境的创造。这是意境说的基本思想。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说的“思与境偕”,以及明王世贞的“神与境会”、“兴与境诣”,都是对王昌龄上述思想的概括与发展。
艺术意境的创造有赖于意与境浑的艺术体验,这和海德格尔突破二元分离的表象性思维的观念是一致的。在审美观照中,人并非把事物当作是外在于人,对象化了的客体,对其进行逻辑性、概念性的剖析,而是进入一种类似“游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忘记了自身”而被“聚集到他的此在的根基上。人在其中达乎安宁;当然不是达乎无所作为、空无心思的假宁静,而是达乎那种无限的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③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9 页。艺术体验之思不是一种概念性思维,而是根源性的存在之思,是“至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是在“天、地、神、人”四方都到场和敞开下的“映射游戏”;同样,对于物来说,也不是独立于人的、外在的物,而是“物居留四重整体”,即“物物化世界” (Das Ding dingt Welt)中的物。
王国维把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过’。‘可堪孤馆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④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 页。叶维廉先生借用了“以物观物”的概念来归纳中国艺术意境的创生方式,并指出其特点在于“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①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李达三,罗刚:《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第186 页。此种感应宇宙万物的方式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来的“以我观物”的方式是迥异其趣的。“以我观物”主张艺术家从自我出发,把自我的情感外射到自然物象上,从而在人与物、情与景之间找到契合点,达到一种以艺术家的主观情感为中心的情景交融。而“以物观物”以及所达到的“无我之境”,则是审美主体在超脱世俗尘想,在“心凝形释,与万化冥会”的状态下,把自我融会到自然对象中,体悟出宇宙自然的内在精神律动,最终形成物我两忘、物我合一、“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化境。
“以物观物”、“无我之境”的思维方式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泰然自在”(Gelassenheit)之思是完全一致的。海德格尔写道:“思想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同时超越一切实践的行为。思想耸立于行动和制造之上,并不是由于它的功劳伟大,也不是由于它的作用成果,而倒是由于它的毫无成就的完成微不足道。”②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6 页。可见,“泰然自在”之思不是形而上学的技术型思维,而是类似于道家的“无为”;它从不急切地把事物的本质加以剖析、计算和探究,而是以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保全了存在的本质;它要求破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偏执,不以人为的分化和计算去破坏万物的本来面目,而是顺天自化、天人合一,保持宇宙万物的天然生机和完整意趣。
体现在艺术意境上,它追求一种清静无为、自然天成的境界。 “泰然自在”,即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不动声色中使诗意涌现,使存在得到澄明。在《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一文的开头,海德格尔指出,如果想真正进入荷尔德林的世界,就必须“把我们惯常的表象方式转变为一种质朴的、异乎寻常的运思经验。”任何与思背道而驰的方式,都不利于诗意世界的呈现,“对于这个诗人世界,我们依据文学和美学的范畴是决不能把握的。”③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5 页。
四
海德格尔美学与中国意境美学会通的另一个理论向度在于二者都强调“艺通于道”,即认为艺术是对人生宇宙真理的体悟。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Entbergen),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①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 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既不是对现实的摹仿,也不是主观的表达,而是为了彰显存在的真理,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敞开”。②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5 页。海德格尔认为艺术这个词的原义涉及古希腊人特有的认知方式,即将在场者作为非现成的在场者带到揭蔽状态中来的认知方式。它是以一种非普遍化、抽象化的方式揭示存在的境域。与之类似的,中国意境美学同样强调艺术应该超越对于具体物象的描绘而进入一种更阔大、更深远的原发生意义的境域,即“道”的境域。
叶朗先生说:“从审美感兴活动来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受。”③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2 页。这段话概括出意境的一个根本特点: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此种超越体现在中国哲学中就是对“道”的追求。宗白华先生指出:
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④宗白华:《意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9 页。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诗的意境必须表现这个本体和生命。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例如:“俱道适往” (《绮丽》),“由道返气”(《豪放》),“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委曲》),“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形容》),等等。这些话都是说意境必须表现“道”。“道”是无限的,而“象”是有限的,。因此要追求“道”就必须突破具体的“象”。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皎然说诗境要“采奇于象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从本质上说都是根源于文学是“道”的显现的观念。
具体到诗歌创作上,意境美学强调“无”和“虚”的作用,讲究虚实相生之妙。司空图的“返虚入浑”(《雄浑》)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严羽的“镜花水月”之“妙悟”说,以及王渔洋的“神韵”,都认为艺术意境的创造在于发挥“虚”和“无”的作用,使人在似有似无、虚虚实实之间,体会到无穷的美感享受。
海德格尔哲学虽没有明确开启艺术意境中“象外之象”这一课题,然而其对于“无”的强调在西方哲学中也可谓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直逼东方哲学和美学的精神。《形而上学导论》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而没有无?”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无”的地位。传统哲学从不追问“无”的问题,因为其思想的前提是“有”而不能是“无”。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对“无”的忽视导致了存在的遗忘。因此,“无”的发现是开启存在世界的关键。“只有当人的生存把自己投入无中,人的生存才能与现实存在物相关”。①海德格尔:《什么是形而上学》,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41 页。在海德格尔看来,投入无也就是从人的日常“沉沦”状态及“非本真状态”返归到“本真状态”。人在日常生活中,被一切人和世俗牵着鼻子走,只有当面对“无”时才能体会和发现自己的“本己”,达到最无拘束的自由境地。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达到“无”和“存在”的途径。他说:“对科学来说,讲无总是一种可怕的和荒谬的事。除哲学家之外,只有诗人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并不是因为像普通常识所设想的那样,诗没有严格的规律,而是因为诗的精神(这里只是指真正的、伟大的诗)本质上优于一切单纯科学中流行的精神。”诗之所以优于科学精神,是因为诗摆脱了世俗的羁绊,而显示存在的真意。
这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和中国意境都强调通过诗的途径以返回本真,都可归结为“超然”哲学(美学),其核心都在一个“无”字,意识不到“无”,就谈不上“超然”,谈不上“返回本真”。然而此种“超然”又并不以对现实存在物的否弃为前提,不是脱离现实存在物而去追求高高在上的“理念”。“无既不自己独立出现,也不在现实存在物之外出现,它似乎粘附着现实存在物。”②同上,第35 页。海德格尔反复吟诵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作为对这句诗的注解,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③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1 页。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对某种更高的、终极的实体的追求,而在于从眼前的现实存在物中去体悟“存在”的真意。“名教中自有天地”,超现实的精神境界的获得,无须从虚无缥缈中去寻求。陶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人境本是喧嚣纷扰之地,居人境而不觉车马之喧,关键在于“心远”,即对世界对生活的一种超然的态度,此种超然,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是禅宗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智慧。
张祥龙指出,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观(包括禅宗)在最关键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一种源于(或缘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纯境域构成的思维方式”。①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13 页。称之为“境域”,取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即“终极既不是任何现成者,而又活生生的在场,使我们领会当下涉及的一切可能”。②同上,第359 页。艺术也好,诗歌也罢,都是此种终极境域的显现,是来自此种境域的消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此种消息既浑厚无比,又似有似无,人的观念思维接受不到它,只有在艺术和诗歌的世界中,我们才能感知这终极境域的消息,从而浑然天成的“敞开”,达到“思无邪”。
五
本文考察了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和中国意境美学的共通之处。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主张回到苏格拉底以前人和存在浑然一体的状态,力求呈现“存在的具体性”。中国意境美学所强调的“意与境浑”也是一种超主客二分的艺术体验,强调艺术创作中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特点,和海德格尔的思路一致。海德格尔从存在的开显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本源,反对形而上学的艺术真理观,这和中国意境美学的进路也是共通的,二者都是主张“艺通于道”,即艺术创作是对人生宇宙真理的体悟,但这种体悟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相对真理的表象性思维的认知,而是一种自然天真,一种本体与现象的体用浑然。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和中国意境美学的背景是大不相同的。海德格尔的哲学系针对西方形而上学思维和科技理性的弊端而发,乃是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反叛和超越,而中国意境美学则是以老庄道学、魏晋玄学以及禅宗佛学为其哲学根源,是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底蕴孕育出来的花朵。如果说后者是尚未达到主体性原则之前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前者则是在经历了长期主体性原则之后,在意识到主体性原则的弊端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超越,重新回归天人合一。在此笔者无意于评价两者的优劣,应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因为背负了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重压而充满厚重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意境美学则由于少了如许的理论负担而显得更加轻盈和空灵。或许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各种价值体系与存在基础纷纷崩解的后现代大潮中,海德格尔以“此在”的存在为基础、以“诗意的栖居”为旨归的哲学和美学究竟给人们开启了怎样的可能性?正如张祥龙先生所指出的,海德格尔的生存境域“不同于实用主义和各类无根的‘后……主义’,因为它取得了一种尽管是非实体的、却浸润到了人生最深处的终极理解。”毕竟,“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后冷战’、‘后哲学’的时代,反形而上学是个赶滥了的时髦,而真正的难处在于不避开终极问题的消解掉形而上学、包括宗教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增进我们对于人生在世本身的领悟。”①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0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与中国意境美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是关乎存在的意义本身。说到底,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有限的、夜露残宵般的个体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意义,如何超逾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由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