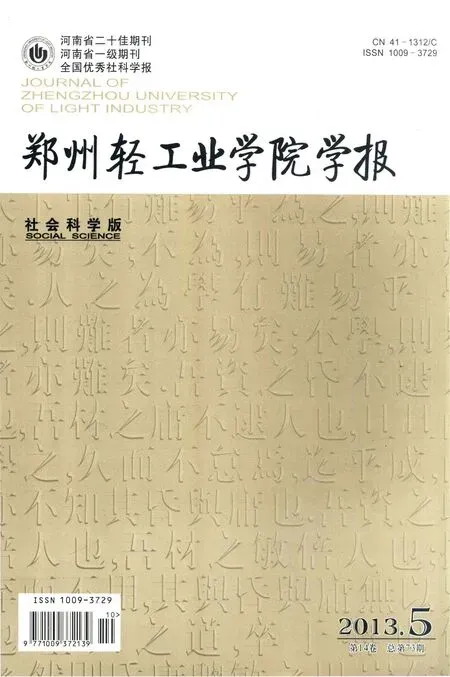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232007)
现代新儒学即将落幕之际,大陆新儒学悄然兴起,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中的所谓大陆新儒学,是指现代新儒学式微之后,大陆地区兴起的新的儒学体系重构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致思路向,有的汲汲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的热衷于现实的政治进路,有的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有的尝试于儒学的宗教进路,其代表人物有蒋庆、黄玉顺、陈明、张祥龙等。虽然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宣言,但它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儒学思想的再度复兴。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1](P39);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2](P55);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才是儒学发展的现实路径[3]。纵观大陆新儒学研究之现状,学界对此领域尚未展开系统的学理疏解。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几种理论体系进行初步分析,以管窥大陆新儒学的内在特质和基本风貌。
一、儒学的消沉与落寞
对于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 世纪是一个喧哗与骚动、震荡与激变、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蓬勃涌现,围绕“中国走向何处”“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与争鸣。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命运与未来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首先是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儒学解体的原因,余英时认为首先是“硬件”方面已体之不存,即持续2000 多年的帝王制度的崩溃,使其丧失栖身之所[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即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种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虽因佛教、道教的冲击与挤压而曾经遭到过冷遇,但始终未能动摇其主体地位。然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帝制王朝的分崩离析使儒学失去制度层面的支撑,儒学日见式微,走向衰落。帝制崩溃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亦使儒学失去长足发展的内源动力。科举取士是为统治阶级网罗人才,考试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过科举出仕的士大夫对传统儒学的研读和发挥,无疑为儒学的持续发展输送了绵延不绝的新鲜血液。1905 年,清廷取缔科举转而采取新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显然切断了儒学与读书人之间的直接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解体之后并未因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获得些许生存空间,反而在经历20 世纪数次激烈反传统浪潮之后,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清算和荡涤,曾经显赫数千年之久、作为独立文化形态的儒学,其时“似乎成为一堆万劫不复的死灰”[5]。
其次是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五四新文化派对儒家传统的无情批判,激起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度思考。1921 年梁漱溟推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它基于现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拉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序幕。尽管现代新儒家认同民主与科学,但与新文化派迥异的是,他们认为传统儒学早已蕴含科学、民主的因子,并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即“内圣”可以开出新的“外王”事业。为此,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和未来,通过消融西方文化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力图寻找到儒家思想新的慧命。现代新儒家四代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立而行道”,但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始终没有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改变“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现实窘境,而且当时一流学者很少关注儒学。1995 年,牟宗三的遽然离世,标志着现代新儒学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走完了这个现代新儒学的圆圈全程”。李泽厚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这个圆圈是无可怀疑地终结了。”[6]时光流转,梁漱溟曾以几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精辟解答,也早已被人遗忘了。这并不是因为梁漱溟的观点不够深刻,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在很短时间内仅凭学理探讨就能解决的。面对新的时代,现代新儒家的孤寂与落寞并非偶然,而是古老的儒学应对乏术,无法搭建一条沟通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桥梁。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已有百年之久,唯其独尊的时代早已远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民主政治也成为当今主流的政治安排,但随之人们又患上了现代性焦虑症。于是,挣扎于现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儒家文化,这又为大陆新儒学的勃兴提供了时代机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几成儒学展开的基本向度,于是大陆再现儒学复兴的迹象。
二、大陆新儒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新儒家纷纷移居港台及海外,留在大陆的老辈学人也基本上停止了儒学研究,转而关注马克思主义。19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文化研究热潮的勃兴,儒学传统及其现代命运才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力的提升,大陆儒学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新的儒学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里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人文儒学为例加以解析,以探究其底蕴。
1.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的产生与现代新儒学的致思路向密切相关。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乃是源于其自身的理论偏误,可将其归纳概括为个人化倾向、形上化倾向、内在化倾向、超越化倾向。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只深掘儒学的心性和生命面向(蒋庆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忽视了它的政治面向(即“政治儒学”)。基于对新儒家的这种认识,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当代儒学的发展应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1](P11)在他看来,政治儒学可以弥补心性儒学现实层面之不足。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政治实践,这无疑彰显了儒学的政治理想。由于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政治儒学从一问世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引起学界热议。
那么,政治儒学到底有何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其内在特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析。在理论阐释上,蒋庆从历史深处入手寻找原始依据。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源于儒家之经学,其源头可追溯至周礼与春秋。在先秦,能将周礼与春秋之微言大义发扬出来的,唯有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它源于孔子、兴于公羊、成于荀子、光大于两汉(董仲舒)、复兴于清末(康有为)。这条一脉相承、有别于心性儒学的儒学传统,即是儒学的政治面向[1](P28)。有识于此,他认为政治儒学不屑于形上体系的建构,而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认为道不在抽象概念的推演中,而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1](P42)。所以,蒋庆试图改变现代新儒家以个体生命为关怀对象、以道德理性为理论依据的致思路向,转而以社会政治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理性为理论依据,并致力于政治实践的具体落实。
实践上,蒋庆结合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提出“三重合法性”构想,并将其发展为“议会三院制”。首先,蒋庆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三重合法性”的构想。具体来说,他把《中庸》“王天下”之“三重”的“议礼”、“制度”和“考文”,改造成“天道”、“历史”与“民意”三项,以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三重维度,这是其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蒋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挥仅至于此,那么“三重合法性”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此论所以引起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驳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融摄,进而以“议会三院制”实践其政治维度。所谓“三院”,即庶民院、国体院和通儒院,其制度设计为:庶民院代表公众民意,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通儒院代表儒教价值。凭借“三院制”,蒋庆构建的“天道”、“历史”、“民意”之“三重合法性”便辐射到政治生活中。这种路径设计充分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庆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实践“议会三院制”的目标就是儒学国教化[7]。而儒学国教化正是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所倡,目的在于重构国民的儒学信仰,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剖析,可以感知政治儒学浓烈的政治化倾向。尽管康有为等人的儒学国教化没有成功,政治儒学也难免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但都没有动摇政治儒学的立场。
2.生活儒学
关于生活儒学,学界现有两种不同提法:一是大陆学者黄玉顺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二是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日常生活化的儒学。前者热衷于儒学体系的构建,后者致力于儒学的大众化。因本文主要探讨大陆新儒学,故后者略去不谈。关于生活儒学的体系建构,黄玉顺本人曾多次撰文,就其概念内涵和构建思路展开论述。
一是概念内涵。何谓“生活儒学”?黄玉顺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先对“生活”和“儒学”加以界定。先说“儒学”。提及儒学,大家肯定会想起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之类的话语,但到底“什么是儒学”?即便儒学界给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似乎与儒家传统隔膜甚深。黄玉顺认为有必要回到原始儒家,涤荡其理论构架,夯实其理论根基,重构新的儒学体系[8]。再说“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因为一说起“生活”,人们必定想到现实生活,自然也就把生活儒学理解成将儒学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消除误解,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之“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关于“生活”的观念;二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存在”的阐述。海德格尔厘清了“生存”与“存在”的关系,认为人的生存只能是此在[9]。倘若我们将这个“此在”去掉,回到“此在”之前,那么“生存”等同于“存在”,也就叫“生活”(life)。基于这种认识,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就是以生活为本源,面向生活的儒学。[1](P55)
二是构建思路。回顾20 世纪的儒学发展,黄玉顺认为它始终没有超越“西学东渐”的理论预设,当代儒学体系的构建应当避免这种倾向,创设具有当代思想视域的新儒学。为此,他从3 个层面构建理论体系:其一,回归生活本源。黄玉顺承认,生活儒学受到海德格尔的启示,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区别开来,黄玉顺以“生活”指称“存在”或“生存”。在他看来,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并对“生活”作了如下界定:“生活”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它只是存在本身;而具体的生活方式,则只是“存在的生活”的一种显现方式。在他看来,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只有回归生活本源,才能阐释其形上与形下的可能性。其二,重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显然无法回避形而上学。但问题是怎样重建?黄玉顺坦言应秉持中道立场,既拒绝现代新儒家的纯粹哲学思辨,又拒绝大陆新儒家的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形而上者的源头在于人们当下生活中的生活感悟。在形上体系的创设上,他把重建主体性和范畴表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后者视为形上与形下的过渡环节。其三重建形而下学。学界关于形上与形下的划分,一般常用佛教术语“此岸”与“彼岸”加以区别。由于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儒家自古以来注重此岸,具体表现在制度伦理和正义理论上。黄玉顺指出,儒家正义伦理具有两个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在他看来,通过提炼正义伦理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当代儒学构建回归生活的诉求:如果说正义性所挺立的制度规范的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适宜性所奠定的制度伦理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存在的再度显现,那么可以说这两者均来自生活,且归于生活。[8]
综观上述,生活儒学打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模式,构建“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下学”的框架,不仅夯实了儒学本体形态的理论根基,还为当代儒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向度。
3.人文儒学
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上,人文儒学既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没有透过西学阐释儒家传统。通过对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钩沉,李承贵发现人文主义才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并将人文儒学确立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
人文儒学何以成为儒家的本体形态?李承贵提供了五点理论支撑。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其一,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儒学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在特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内涵虽有争议,然其核心义理大体相同,即肯定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价值及意义,追求个性解放,崇尚人格尊严。孔子提出“仁”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肯定了人的价值及人生意义。这样的例子普遍存在于儒家典籍中,说明人文主义无疑是儒家思想基本内容。
其二,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生长之源。这里的“生长之源”是说,人文主义是儒学生成与发展的源头或种子。首先,“仁”是儒家思想生长的源头。在儒学体系的众多核心概念中,“仁”最具生命力也最具创造力,儒学的历次更替与创新,无不从重新释“仁”开始。其次,儒学的丰富和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在儒学发展史上,无论是生生思想,还是自强精神,抑或厚德意识,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其三,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开掘之匙。此处的“开掘之匙”意指,人文儒学是诠释和评价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并为20 世纪儒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举例来说,无论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还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抑或当代大哲张岱年,不仅肯定了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运用人文主义方法对儒家人文理念进行整理、诠释和评价。
其四,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学科化之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学从传统儒学悄然转向人文儒学,致使原本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被分别纳入中文、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范畴之中。如此以来,传统的儒家体系就不复存在,但人文儒学由此凸显。所以说,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现代学科化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儒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这恰是儒学确立身份,使其走下独尊的神坛,重新挺立儒家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机缘。
其五,人文儒学是儒家应对挑战之法。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李承贵认为,若从人文儒学角度思考,可使儒学成功应对挑战。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功能过多所致。由于传统儒学体系过于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功能方面有着广泛的诉求。而人文儒学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化解儒学的生存危机。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二是,儒学外王事业所致。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乃是现代新儒家的毕生祈愿,却终究未能实现。但对人文儒学而言,开出科学与民主,是内在的诉求;开不出科学与民主,也是它的特性所规定。[3]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三是,质疑儒学价值所致。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受到国人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与科学、民主相悖。作为由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儒学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人文儒学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个体尊严的维护,显然与民主观念兼容不悖。
经过以上5 个方面的学理疏解,李承贵说: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担当起儒学的现代使命,人文儒学是儒学当之无愧的本体形态。[3]乍看之下,似无疑义,但细心揣摩,会觉得人文儒学的根基不够牢固,因为人文主义显然无法作为本体撑起体系庞大且内容繁杂的儒学。所以,此论一出即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纷纷著文与李承贵展开论争。依笔者之愚见,人文儒学的论证和推理不乏精湛之处,但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更无法展开社会实践。
三、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不管认同与否,近年来儒学复兴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的探索。除了上述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与人文儒学,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化儒学(陈明)、制度儒学(干春松)、公民儒学(林安梧)、经济儒学(盛洪),以及近来郭齐勇关注较多的民间儒学。这些儒学体系的构架,是否表明儒学已经度过近代以来的持久落寞,再现昔日的辉煌气象?笔者认为尚需历史作出理性的评判。细致阅读大陆新儒学倡导者的学术论著,笔者就当前的儒学复兴思潮略谈两点浅见。
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厘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儒学对当代社会究竟有无价值,其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儒学复兴的意义及前景所在。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虽然有过广泛的研究,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袁伟时先生曾发出疑问“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10]大陆新儒学家们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他们显然是肯定儒学的现代价值的。可是仅止于此还不够,对于新儒学提倡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倾心于儒学体系的构建,而是彻底理清儒学的现代意义到底体现在哪些领域,其未来前景又当何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当代社会为它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安顿之所。
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儒学复兴的现实路径是什么,是否如大陆新儒学所描绘的那样?大陆新儒学虽然已经初具一定的理论形态,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政治儒学的政治诉求带给儒学的也许是毁灭性打击,生活儒学回归原典重构儒学体系可行性不大,而人文儒学将人文主义作为儒学的本体形态根本就不成立。关于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笔者赞同杨庆中教授的观点,即充分利用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回归原典、开发原典,是否构建儒学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所谓“回归”,就是基于新的时代特征重新诠释原典,以此确立历史与现实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之所以回归原典、重释原典,是因为原典是一个民族最基本存在形式的最经典的诠释文本。[11]儒学复兴虽不是喊几句简单的口号、掀起几场读经活动、构建几种理论体系就能实现的,但儒学复兴的曙光毕竟已经出现:表现之一是单独的西学或中学解释不了当前国人的生存形式,表现之二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未来前景的形上思辨为儒学复兴作了有力的理论尝试。
[1] 蒋庆.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3] 李承贵. 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J]. 学术月刊,2009(12):34.
[4]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
[5] 封祖盛.当代新儒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30 -331.
[7]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EB/OL].(2012 -12 -23)[2013 -09 -01]. http://culture. people. com. cn/GB/27296/3969429.html.
[8] 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J].学术月刊,2012(11):41.
[9]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虚无[M]. 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2.
[10]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EB/OL].(2013 -05 -06)[2013 -09 -02]. http://cul. qq. com/zt2013/ysdjt216/index.htm.
[11]杨庆中.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