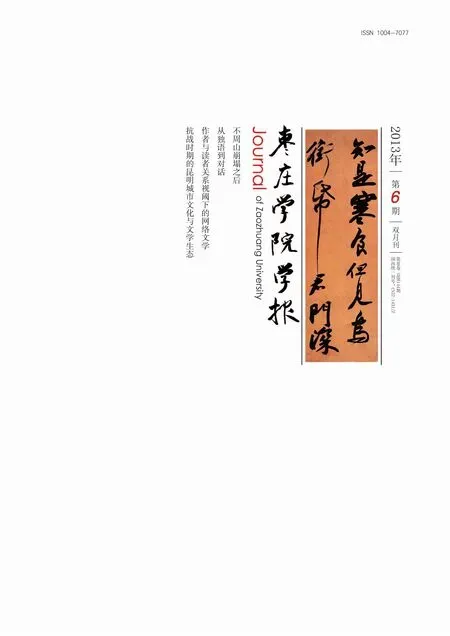虚实、动静中的灵魂拯救之旅
——评亚历克斯·米勒《别了,那道风景》
张晓菲
(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22)
虚实、动静中的灵魂拯救之旅
——评亚历克斯·米勒《别了,那道风景》
张晓菲
(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22)
《别了,那道风景》是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最新力作。小说以崭新的视角讲述了纳粹后人因心怀与父辈“共谋犯罪”的深深的负疚感,完整人生的构建异常坎坷的故事,从而论证了战争和屠杀是全人类共同的悲剧。小说语言平实,情节简单,但作者高超的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小说艺术使得人物复杂的心绪跃然纸上,主人公的精神重生也显得异常艰辛和引入深思。
大屠杀;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人生的意义①
亚历克斯·米勒是澳大利亚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两度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米勒在《别了,那道风景》中,勇敢地反思大屠杀和战争爆发的原因。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足以给和平时代的人们以警醒。另外,这本小说更在深层次上涉及了人类共同的话题——找寻存在的意义,求得内心的平静。
秉承澳大利亚文学的写作风格,该小说情节简单,人物心绪却错综复杂。主人公人生意义的找寻杂糅在梦幻与现实,孤独与友情之间,显得异常艰辛。小说的语言朴素平实,但谋篇布局和描写却虚实相生、动静结合,并缀以生动的隐喻,将人性的善良和罪恶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引人深思。妻子威妮弗雷德突然离世后,德国历史教授马克斯认为自己失去了人生的全部意义,企图自杀。然而,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学者维塔及其叔父道佳尔德的帮助下,通过对自己逃避了大半生的与父辈“共谋犯罪”的负疚感的反思,终于得以直面父辈纳粹的罪行,并积极寻找证据,以公之于世,以警示后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内心也最终得以平静。
一、流放于现实,归属于梦幻
战争和屠杀无疑惨绝人寰,对受害者而言尤为如此。但鲜有人关心战争和屠杀发动者后人的感受。对先人残酷的行径,他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代却饱受与先人“共谋犯罪”的负疚感,不敢面对历史,难以构建完整的人生。米勒匠心独运,从纳粹后人马克斯的视角,让我们体会到战争和屠杀是全人类共同的悲剧。
马克斯清楚,他的父亲“不可能清白无辜”[1](P45),但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全家不陷入痛苦的深渊,在德国社会对战争坚守沉默的巨大压力下,直到父亲去世,马克斯都没有鼓起勇气问父亲到底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作为纳粹的后裔,对于自己同样有罪的认定,将他活生生地流放在现实生活之中。可人类有追求幸福的本性,于是他在饱受来自时代和社会的压抑时,转向其他领域寻找发泄口。他沉湎于十二世纪的历史文献中不能自拔,并将幸福感紧紧地与妻子威妮弗雷德捆绑在一起。当妻子过世,几十年的幸福生活突然结束,他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试图自杀。
选择沉默也就摒弃了生活,但这并不能磨灭马克斯“共谋犯罪”的罪恶感。精神分析学认为,“那些似乎已不在记忆范围内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的组成部分,而且时常会在睡梦中呈现出来。没有什么事情会被人真正遗忘。”[2](P129)他试图自杀前对着醉酒睡着的维塔自说自话,不是怀念与威妮弗雷德的美好生活,而是倾吐“共谋犯罪”的罪恶感如何将生活鞭打的伤痕累累,而他却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真实的历史和沉默态度的沉重感使得马克斯常常游离于现实之外,在梦幻中寻求归属和安宁。他常常想起舅舅,回忆童年。他写下了小时候在舅舅农庄住的时候,对床边墙上的一个小窟窿的恐怖幻想。小窟窿代表着一种黑暗,“在那里,暴力和对人的折磨,埋葬在沉默之中”[1](P95)他明知这是自己的幻想,却无法抵挡于愈演愈烈的恐惧的侵扰。对父亲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的怀疑,对父亲正直人格的不信任,使他小小的心灵饱受摧残。马克斯对小窟窿的恐惧让人想起《黄色墙纸》中女主角对墙纸的一系列癫狂联想。他们都饱受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压抑,独立人格遭受了一定的扭曲,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发泄无奈和沮丧,只能将自己流放,转向梦幻世界寻求出路。不同的是,《黄色墙纸》的女主角最终精神崩溃,而马克斯则在担心自己也走向人性恶的一面的恐惧中惶惶长大。
成年后的马克斯依然在现实的夹缝中给自己的幻想大开其路。他在考虑问题时,总想象有两个自己。一个勇敢而感性,另一个理智而冷漠。“我们相互排斥,我和他。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相互排斥,看不起甚至讨厌对方。然而,在骨子里,内心深处,我们却是一体的,是同一个人,有同样的信仰。”[1](P225)两个“自己”纠结缠绕在一起,感性总是获胜,然而遇到挫折后理智再把自己狠狠嘲笑一番。马克斯依靠幻想应对生活,显然是对历史的负疚感使然。这种梦幻与现实的交锋和融合,在他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武士戈纳帕领导的一场对白人殖民者的屠杀的记录中迎来了高潮。
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顾问道佳尔德在充分信赖马克斯之后,拜托他将曾祖父戈纳帕带领其他原住民将强占他们运动场的19名白人殖民者全部屠戮的故事记载下来。虽然颇有难度,但这对马克斯而言,是个千载难逢的直面大屠杀的机会。国籍、人种和文化的差异并不妨碍马克斯体味人类共同的道德难题。因为“道德得以产生的根据,是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性。”[3](P72)人性总是相通的,也无外乎人类历史到处可见惊人的相似。而马克斯“越是深入到故事情节中,道佳尔德故事的精神和我自己故事的精神在我的想象之中越融合在一起变为一体,直到我就是武士戈纳帕,他就是我。”[1](P153)马克斯很快又将历史与梦幻揉合在一起。他幻想在写自己的故事,或者自己崇拜的为正义而战的英雄的“光辉业绩”。几十年来压抑下来的与父辈“共谋犯罪”的负疚感喷薄而出,一场过往的大屠杀跃然纸上。
澳大利亚原住民至今仍将“梦幻”作为和先人沟通,获得神秘力量的方式。在梦幻中,戈纳帕感到自己的灵魂与白人殖民者族长的灵魂融为一体。他体味着族长的思想、情感及他死去时的痛苦和回忆的所有细节。他认定自己和那位族长是“兄弟”。亲切、熟悉,“对他很重要”,但同时他也明白,对付这一群亵渎并占领他们祖先留下的神圣的运动场的白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白人族长在临死前也大喊:“不,戈纳帕,我的兄弟!”[1](P181)梦幻变成了现实,尽管充满悲伤,戈纳帕还是将长矛刺进了族长的骨盆。戈纳帕与族长的关系让人不禁联想到《圣经》里亚伯和该隐的故事。该隐杀害了亲兄弟亚伯后,被罚永远流亡。戈纳帕不愿意自己和族人“充满仇恨和耻辱,在自己的土地上过流亡者的生活”[1](P172),可是血腥的杀戮使他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生活,他只有将自己流放,离群索居,孤老一生。他希望族人今后可以明白自己和白人族长是兄弟的真正含义。原住民与白人殖民者之间的互相残杀,是全人类的悲哀。“杀死的人是另一个自己——这等于为种族屠杀是人类共同悲剧的主题,做了感性的铺垫。”[4]
在《大屠杀》一章中,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却意义重大。族长深爱的妻子也叫威妮弗雷德,与马克斯的亡妻同名。在梦幻中,戈纳帕看到了族长对妻子深深的爱,正如马克斯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动作的细节都是那样的温馨和美好。族长和马克斯都对妻子的死亡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却又无可奈何。戈纳帕在梦幻中与白人族长连结在一起,知晓自己要屠戮同类,只感到无尽悲凉,哭泣了三天三夜才行动。而马克斯也脱离了现实,在梦幻中将自己和戈纳帕融为一体,从而在写下人类共同的悲剧的时候,尽情抒发内心深处浓浓的悲哀。
同样将自己流放于现实生活,转向梦幻寻找归属和人生意义的还有道佳尔德。尽管不顾自己恶化的健康状况,投身于为原住民解决各种问题,道佳尔德还是将自己的根定位在回忆先人和远方的家乡中。为了警示后人,他豁达地让马克斯将他先人犯下的大屠杀记录下来。随后,毅然带着马克斯探访戈纳帕生活的远征岭。经年未归,那里却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和归宿。瞻仰戈纳帕的遗骸之后,道佳尔德终于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与马克斯相视而笑。
他们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穿梭,终于找到了自己归属,以归属为基点确立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回到现实去实现它。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也体现在作者对两次屠杀的处理上。米勒对德国在战争中的屠杀与罪恶采取了虚写的方式。现代读者对德国在上个世纪的世纪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心照不宣,如此虚写避免了文本拖沓,也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在马克斯“共谋犯罪”的负疚感上,使读者更好的体会屠杀的双方都是输家的主题。虽然道佳尔德的先人对白人殖民者的屠杀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二战,却方便米勒详尽地描写了屠杀与被屠双方前前后后的想法,屠杀的因由,过程,结果,当地的风景,干活的场景等等。对这次屠杀事无巨细的实写则吸引了读者细细地体会大屠杀的血腥和罪恶。也为马克斯卸下身上沉重的历史负担,摆脱精神阴影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出路。
二、孤独中求索,友情中求生
除却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展现小说人物复杂的心绪外,米勒的笔触还悄然结合了动与静,以静显动,以动衬静,使得小说的节奏时快时慢,时紧时松。“静”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孤独的心态和状态中,“动”则体现在人物之间友谊的形成和发展上。在米勒的笔下,孤独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马克斯、维塔和道佳尔德无不是在孤独中坚守自己,探寻人生的意义。但帮助他们找到内心平静与安宁的却是彼此间的理解、信赖和深厚的友谊。
米勒“描绘的人物即使是农民或是武士的身份,也都倾向于孤独和内省,凸显内心世界的沉重和伟岸;作家用现代派的感觉书写,细微地传达澳洲历史当中人物的孤独和困惑。”[5](P117)直到马克斯获得精神的重生之前,孤独弥漫在小说几乎每一个人物身上。孤独,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圆融的心理。不管是身处喧闹的德国大城市汉堡,还是偏僻的澳大利亚尼博山小镇,被孤独侵蚀心灵的人,却反而得以在一个清冷的环境中审视自己,自由地呼吸。徘徊在无声的孤寂中,心灵深处的渴望却愈加灼热,喷薄欲出。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一个真正的自己终于浮出水面,痛苦的症结和生命的热望变得无比清晰,只待走出孤独,去努力解决和实现。马克斯在丧妻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妻子威妮弗雷德走了,也带走了他几十年来幸福的寄予之处。在绝望中,他压抑了大半辈子的“共谋犯罪”的负疚感愈演愈烈,不吐不快。但是他不知晓如何发泄,如何求生,于是决定在宣读一篇关于大屠杀的论文后自杀。维塔及时的友情拯救了茫然的马克斯,道佳尔德的对待历史的豁达和崇高的责任感则使他直面“共谋犯罪”的痛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重拾活下去的勇气。
维塔告诉他,对父辈骇人听闻的罪行保持沉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年老不是借口,行动起来,直面伤口,揭示真相,才是问题的答案。一味逃避只能让他失去生命的意义。维塔带马克斯去见丧妻多年,固守在别人遗弃的家园的道佳尔德,两人一见如故。在默契的沉默不语中宛若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兄弟。书写戈纳帕领导原住民屠杀白人殖民者的历史的时候,马克斯深刻感受到了屠杀事件前后人性善恶的碰撞,为直面自己父辈犯下的罪行做了充分的铺垫。
在同样孤独的尼博山,马克斯回忆起了小时候遇到一个屠杀中逃跑的饥饿的吉普赛小姑娘,当时他没能帮助她。在远征岭跌落后的梦里,他意识到他“一生中最珍惜的就是和她短暂相逢的那一刻。它预示了我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1](P232)那一刻,标志着马克斯一生的纠结所在。他心地善良,想帮助小姑娘,却因顾忌太多最终爱莫能助。但是没能帮助到她却成了马克斯几十年来的心灵之殇。是自己的父辈杀害了她的家人,逼她小小年纪亡命天涯,那一刻他却什么都没有做。那一刻,他的无力和懊悔及对父辈罪行的逃避和恐惧融为一体。明白了那一刻对他生命的重大意义,他终于可以走出孤独和“共谋犯罪”带来的窒息感,勇敢的面对生活,面对历史。
另外,小说“动”与“静”的结合还体现在小说的节奏上。起先读者在透过老教授马克斯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无论是学术演讲,还是他冒着危险试图给山羊一个体面的葬礼,处处弥漫着一种老者透视世事的淡然,以及马克斯对“共谋犯罪”负疚感挣扎了大半辈子的疲惫、无力和绝望。小说的叙述处处透漏出一丝丝静态。直到小说进行到《大屠杀》一章,紧凑的文字迸发出了炙热的心绪和强烈的动感。《大屠杀》一章与全书其他章节的写法不尽相同。故事结构更加紧凑,语言充满诗性,隐喻丰富,梦幻与现实犬牙交错,漂浮着圣经和宿命论的味道。甚至语调都不再平和,而是充满活力与激情。因为马克斯在写作时,完全将自己与戈纳帕融为一体。他不再是个失去生命意义,哀叹额头上的老年斑的丧妻老教授,而是英勇无畏、善良正直的青年原住民领袖戈纳帕!是他“小时候从卧室墙壁上那个小窟窿焦急地向外面窥视时渴望成为的勇敢、善良的好人。”[1](P153)这种语言语调间游刃自如的转换,足见米勒高超的小说艺术。之后的短短几章里,马克斯的精神终于获得了重生,生命重获活力。小说的叙述也注入了更多的动感和对生命意义的渴望。小说节奏总体而言前松后紧,前静后动,作者的笔触随着马克斯对自己的认识,对生命意义的体会和找寻跳动得时快时慢,奏出一首引人入胜的生命之歌。
三、结语
《别了,那道风景》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了战争和屠杀是全人类的共同悲剧。作为纳粹的后代,为了不使自己和家人陷入痛苦的漩涡,对于父亲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斯始终没能问出口,而是坚守沉默。怀着与父辈“共谋犯罪”的负疚感,马克斯大半辈子都将自己流放在真实生活里,活在怀疑之中。丧妻之后,孤独和绝望吞噬了他,他转向梦幻寻求归属感和人生的意义。最终在友情和榜样的力量的帮助下得以正视历史,决心将他的余生贡献给揭露父辈犯下的罪行,给世人以警醒的事业上。找到了归属和人生的意义,他终于获得了精神重生和活下去的动力。
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激烈的场景描写,但其对屠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却足以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引起中国读者的深思。作者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叙述和谋篇布局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主人公马克斯切实、感人的灵魂拯救之旅。逃避只能使痛苦持续得更久,对罪恶保持沉默也就做了人性之恶的帮凶。只有正视历史,正视人类犯下的罪行,才能避免屠戮同类的悲剧再次上演。
[1]亚历克斯·米勒著,李尧译.别了,那道风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阿尔伯特·莫德尔著,刘文荣译.文学中的色情动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3]刘晓文.多元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李霞.反省的道路—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 [EB/OL].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3683.2009-04-25.
[5]刘云秋.心灵的自我拯救之旅—解读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J].西华大学学报,2010,29(5).
I106.4
A
1004-7077(2013)06-0058-04
2013-11-12
张晓菲(1987-),女,河北张家口人,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张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