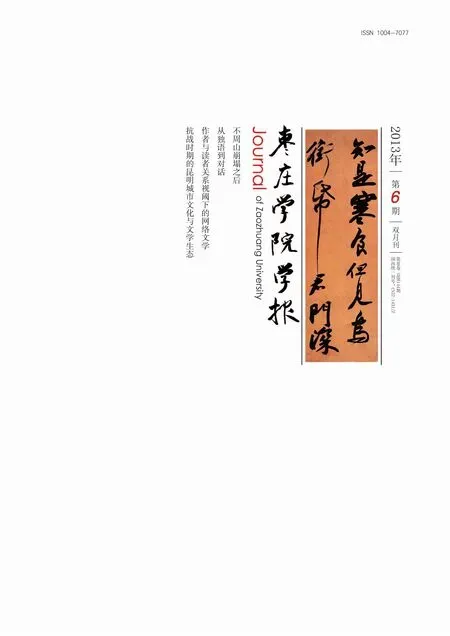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与文学生态
高兴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目前的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视野尚嫌狭窄”,“北京、上海、桂林、重庆、武汉抗战文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他地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1]等等。昆明是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城”之一,但昆明抗战文学的研究“和四川、桂林等地区比较,差距是相当明显的”。[2](P7)本文主要从昆明城市文化的视角探究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学生态。
一、昆明城市文化视角下的抗战文学研究
当代学术界日益呈现“空间转向”的研究态势,文学“现代性”的审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城市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分析均体现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3](P160~162)秦弓较早提出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应该注意“重庆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对创作的影响”。[4]靳明全主张为了“克服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欠缺”,应当“加大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力度”,以重庆为例,需要“结合重庆的地方特色,重庆的风土人情,重庆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研究”。[5]从区域文化的视角不断深化抗战文学研究,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地带,该现象的出现固然基于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转变以及上海的法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优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上海都市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造成了很多奇妙的效应:“先进的现代传媒、发达的文化市场对于上海各类文人的文学产生活动都会造成一定作用,比如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境、文体选择、写作速度等因素必然会受到上海文化场域的不断调适”,导致“各类作家群在写作方式和美学风格上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差异”。[6](P343)抗战之后,上海文化场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城市获得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机缘,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冲击。抗战文学研究不能忽略“城市文化”这个重要因素。
关于抗战与云南文化发展的关系,楚图南曾有全面概括:“由于对日抗战的发生,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历史课给云南以最伟大的责任。所以过去的地理的限制,被打通了,社会的以及一切无形的壁障,也要被打通了。难民、文化人、学者、学校和文化机关,不断的如同潮水一样的向着昔日被视为畏途的山国地方涌来。”[7](P171)昆明作为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迁滇文化人的首选之地。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昆明这座城市对整个中国现代作家的空间分布格局造成了影响。但正如上文所述,在抗战文学研究方面,昆明与桂林、重庆、武汉等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规模较小,也表现在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探讨了单个、零散的作家活动与昆明城市文化的关系,很少见到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作家群落与“大后方”城市昆明的文化空间、文化场域双向作用的精彩论著。
在研究城市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方面,很多学者倾向于从“文学生态”这一理论视点进行剖析。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寄寓在不同的生存空间里继续他们的文化追求,除了服从抗战主题之外,其文学实践也存在一些差异。中国抗战文学并没有彻底阻断各文化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融,随抗战而起的人员迁徙与流动是战时的一种常见现象,这无形中为各区域文化的融会与交流创造了历史机遇。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城市文化与文学生态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这方面,桂林具有代表性:“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等历史条件造就桂林‘文化城’蓬勃多元的文学生态,‘文化城’中的作家群具有强大的精神合力,文学生产呈现出丰富的美学蕴含。”[8]与桂林相似,抗战时期的昆明也是“大后方”的“文化城”之一,大量外省作家与滇籍文人云集昆明,使昆明的文学生态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作家生活在昆明的城市空间中,并且在昆明城市文化场域中求得适应,因而昆明城市文化对该城市的文学生态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规约。
考察抗战时期活跃在昆明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和文学团体,以及昆明的政治环境、文化场域、社团机构等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影响,分析抗战时期居住在“大后方”城市昆明的作家文化心态调适、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风格变化,探究昆明城市文化内涵与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美学蕴含之间的潜在关联,能够彰显昆明抗战文学研究的个性与特色,突出昆明文学生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维度的研究,还可以证实“大后方”城市文化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中留下了一定的历史印痕,藉此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化空间和内部机制等问题。
二、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映像与特质
民国时期的昆明城市规模已相当宏伟,抗战时代是昆明发展的重要“台阶”,“昆明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发展规模和城市近代化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昆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昆明“成了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9](P25~27)
有人称赞昆明是“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10]有人感叹昆明“现代化”设施之齐备,如旅行社、大酒店、巴黎理发室、温泉沐浴室等,“都是最高等、最摩登,而且最舒适”。[11]也有人惊讶于昆明“文化的水准也相当地提高了,报馆,书店业已改换了旧时面目,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成了昆明的文化街,所有生活,北新,上海杂志公司……等新兴书店,都集结在附近一带”。[12]还有人记录了昆明市民的娱乐活动:“昆明大戏院,南屏大戏院,大逸乐电影院,相继以最新姿态出现于东南城角,华灯初起,南屏道上,衣香鬓影,车水马龙,诚为昆明生色不少”;[13]“每晚只见满街行人,尤以外宾为甚,繁荣的市面,够令人兴奋的”。[14]那时的昆明在人口密度、经济规模、设施水平、文化氛围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大都市相比并不逊色,不愧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城”。
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又自有其特点,自由、疏放可谓其文化特质,它既不同于“陪都重庆文化的发展自由受到执政者的直接行政限制”,[15](P21)又不像战时的桂林文化那样呈现出“解放区‘面向国统区’”的“半开放”形态。[8]从昆明文化场域的权力机制来看,国民党的中央政权与龙云的地方政权之间有较大的缝隙,此外还有美国势力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力量的存在。相对宽松的权力场域为昆明的学者和文人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外省知识分子迁至昆明以后“能够享有高度的学校自治和政治自由”,像西南联大这样的文化团体在“半独立”的云南地方权力保护下“免受国民党的压迫”。[16]何兆武回忆说:“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的事……”[17](P96)很多外省人奔赴“可以自由呼吸的昆明”,[18]冰心也夸赞昆明的城市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19]在抗战烽火映照中国大地的时候,像昆明这般自由、活跃的城市文化场域实在难觅。
昆明城市文化的“自由”精神也与昆明文化传统和自然条件有关。古代昆明不断发生文化“杂交”现象,“移民城市”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昆明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既时尚又保守”的市民个性,“工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长期并存,使昆明城市文化充满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城市生活以慢为节奏”。[20]开放包容与古朴安闲,看似冲突,却真正反映了昆明城市文化的“自由”内质,尽管这种“自由”也可能流变为“散漫”。
昆明的城市环境对于“自由”精神的塑造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昆明被誉为“城市山林”,[21]有山有水,风景极佳,易使人养成怡然自得、从容不迫的精神品性。汪曾祺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冲淡了“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给予昆明人“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22](P362)他还怀念西南联大校舍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上的茶馆,肯定“泡茶馆”有助于乱世书生“养其浩然之气”,也便于发奋“读书”、“接触社会”。[22](P368~375)“山林”城市昆明的市区与城郊具有天然的连绵性和贯通性,西山、滇池、黑龙潭、大观楼等名胜景点便是座落在郊外,而茶馆遍布“城里城外,从最繁盛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23]昆明市民为躲避敌机空袭可以随时“疏散”到四郊乡村,又能够自由地返回城内,展现了“田园”城市的文化风姿。在城市景观方面,“昆市日见趋向现代都市化,而民间住屋,仍多画栋凋梁……依然不失为一古色古香之古城,或云昆居颇有古都风光也”;[24]有人还发现昆明普通市民的生活习惯依然“保持十足中国古老的气味”。[25]就恬静古朴、迂缓内敛的文化内质而言,昆明确实有点类似于北平。
“半独立”的权力机制、“山林”式的城市空间、新旧参差的观念形态,酝酿了昆明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特质,这种文化风格有可能使抗战时代的昆明市民受到过于“平时化”的批评,[26]但它确实为在滇文人助长了文化开拓的信念与激情。不过,也要看到部分昆明人“乡土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失衡现象,[27]当地人与外省人的意识冲突偶有发生,是战时昆明城市文化的不和谐斑点。
三、抗战时期昆明文化与文学生态的关系
1937年之后,云南大学聘请了施蛰存、李长之、吴晗、林同济等人,他们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第四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当中包括沈从文、杨振声等著名作家。[28](P313)抗战时期到过昆明的外省作家还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田汉、穆木天、冰心、林徽因等人,加上滇籍作家白平阶、楚图南、李乔、罗铁鹰、马子华、梅绍农、彭桂萼、徐嘉瑞等,构成了庞大的作家群落。
敌机轰炸前,多数作家穿梭于昆明城的西北角,他们散居在翠湖旁边的凤翥街、文林街、青云街、文化巷、柿花巷等街巷。日寇空袭昆明之后,文人疏散到昆明城郊以及昆明附近的呈贡、宜良等地。昆明相继产生多个零散的文化—文学中心:城内的靛花巷是作家老舍、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卞之琳、陈梦家、川岛等人的“文艺之家”,[29](P81)文林街的沈从文寓所是施蛰存、杨振声、林徽因等人与沈从文共建的“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28](P313)昆明郊区又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分别为东郊区的“龙泉镇”和西郊区的“大普吉”;[30](P88)稍远处的呈贡也是“人文荟萃,俊彦云集”之地,[31](P8)冰心、沈从文、李广田、费孝通等人曾经居住于此。昆明的文化—文学中心在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社会文化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未能有效地发挥整合作用:因作家经常流动,“文协”昆明分会从皖南事变到1944年8月很少活动,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协”保持远离姿态;“十一学会”竟然“还不到一年,也就随着政治上的分化而烟消云散”;[31](P25)“九老会”和“西南文化研究会”采取不定期的活动方式,成员之间经常发生“认识分歧和思想交锋”,[29](P116)何况后三者都不是文学社团。昆明的文学生态圈非常松散,冯至可以归入西南联大作家群,但他移居于昆明市区与郊区之间,他在杨家山的临时寓所成为昆明作家的“山野沙龙”,[31](P19)足见昆明文学生态的散落表征。
1939年的《良友》杂志展示了昆明作家队伍,包括沈从文、冰心、林徽因、施蛰存、穆木天、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钱歌川等人。[32]蒙树宏认为云南作家“在抗战以后,除本省作家外,还有西南联合大学作家群,他们分别以闻一多为首(包括李广田)、以沈从文为首(包括汪曾祺、卢静等)或以《战国策》为中心(如陈铨等)”。[33]昆明作家数量庞杂、类型多样:穆木天、光未然、楚图南、雷溅波、马子华等人曾是左翼文艺战士,闻一多、罗隆基、陈梦家、沈从文、林徽因、潘光旦等人是旧时的新月派文人,施蛰存迁滇之前被称为“新感觉派”作家,吴宓是昔日的“学衡派”中坚分子,陈铨是“战国策派”成员,陈蝶仙是民国通俗文学作家……战时昆明的文学生态既蓬勃旺盛又色彩斑斓。本地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对昆明文学生态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多数昆明人确实像冯至感受到的那样热情好客,但亦有一些本地人缺乏尊重外省文化人的“雅量”,不利于“增强抗战期间文化阵线的实力”。[7](P169~174)李长之与本地人发生误会而离开昆明,有的外省文人竟然“溜回老家去”,[34]茅盾和楚图南对此问题都予以纠偏。
抗战促进了昆明的书刊出版,人们看到“昆明的大小书店里整天挤满着翻杂志、看画报的学生”。[35]昆明很多报纸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但是这些副刊“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者“影响不大”,少数副刊积极培养文艺青年,而“有希望的作者不多,成长不快”。[2](P24~32)昆明的文学期刊数量少、寿命短,凤子叹息:“在昆明,经常有一两个期刊出版,一是《战国策》,一是最近两月才筹备并已出刊了一期的《当代评论》……《中央日报》有一角副刊,然终以商业第一的关系,如遇广告挤,副刊的位置随时可以取而代之的。因之,像《战国策》一类的刊物应该是当地青年们仅有的读物了。”[36]也有人指出昆明“纯文艺的刊物除了西南联合大学文聚社所编的‘文聚月刊’外,就找不出第二种来了”。[37]文学传播途径对于文学生态形成冲击。施蛰存、沈从文、闻一多、陈梦家、杨振声等“老”作家在昆明较少从事个体创作,而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学队伍甚是耀眼,拥有一大批年轻作者,开辟了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大约“一百多个社团”,[38](P2)以壁报和文艺刊物为载体发表大量文学作品,支撑了昆明大半个文坛。
昆明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精神也波及到昆明的文学样式和风格。抗战时期昆明“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2](P54)其文化场域本来就是包容、分散的。昆明文坛的诗歌与散文取得了较大丰收,描写地方风土人情的游记和报告文学数量甚多,小说和剧本的创作势头相对低落……昆明优美宁静的地理环境、自由浪漫的文化氛围十分有利于作家主体心灵的诗意徜徉,与反映矛盾和冲突见长的文学样式似乎不太相宜。
四、结语
海外学者李欧梵论述战时中国文艺活动中心之转移时,介绍了武汉、广州、重庆、香港和桂林,唯独没有提到昆明。[39](P304)分析抗战文坛情势的国内学者称道重庆的出版功绩,重视桂林、香港、广州的华南作家群,对于昆明的文学活动情状略作陈述。[40](P836~837)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敞亮昆明文化镜像。本文探讨了昆明的“山林城市”空间、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精神与昆明抗战文学生态的关系。从多维视野中观照昆明的文学史镜像,应当成为更多研究者的自觉努力!
[1]秦弓.抗战文学研究的概括与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2007,(4).
[2]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高兴.比较视阈与文化之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4]秦弓.重庆抗战文学研究要有个性[J].涪陵师专学报,1999,(2).
[5]靳明全.深化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我见[J].文学评论,2009,(5).
[6]高兴.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7]楚图南.楚图南集(第1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
[8]高兴.桂林“文化城”的文人映像及文学生态[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9]谢本书,李江.昆明城市史(第1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麦浪.昆明画像[J].半月文萃,第1卷第9-10期,1943-03.
[11]予矛.后方的昆明[J].文艺阵地,第2卷第3期,1938-11-16.
[12]直田.昆明点滴[J].国风,第1卷第3期,1939-09-15.
[13]黄卓秋.昆明印象记[J].旅行杂志,第15卷第12号,1941-12.
[14]林希英.昆明寄语[J].春秋,第1卷第5期,1944.
[15]靳明全.重庆抗战文学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16][美]易社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J].抗日战争研究,1997,(1).
[17]何兆武,文靖.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8]光弟.由北平到昆明[M].察省青年,第3期,1940.
[19]冰心.从昆明到重庆[J].文摘月报,第1卷第3期,1941-05-25.
[20]张祖林.昆明文化——城市发展驱动力[J].光明日报,2010-09-09.
[21]公奇.“城市山林”的昆明市[J].市政评论,第3卷第12期,1935-06-16.
[2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3]班公.昆明的茶馆[J].旅行杂志,第13卷第7期,1939-07-01.
[24]帅雨苍.昆明漫记[J].旅行杂志,第13卷第8号,1939-08-01.
[25]绿蒂.昆明琐谈[J].上海妇女,第2卷第3期,1938-11-20.
[26]浩生.昆明杂写[J].国讯旬刊,第250期,1940-10-15.
[27]高山.昆明—後方冒险家的乐园[J].改进,第2卷第5期,1939-12-01.
[28]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29]余斌.学人与学府[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30]冯友兰.冯友兰自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1]余斌.文人与文坛[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32]杨立达.在昆明的作家[J].良友,第146期,1939-09.
[33]蒙树宏.云南现代文学史话四题[J].楚雄师专学报,2000,(5).
[34]高山.昆明青年的没落与生长[J].学生月刊,第1卷第7期,1940-07-15.
[35]毛文贤.昆明学府近影[J].青年月刊,第8卷第3期,1939-09-15.
[36]凤子.昆明点滴[J].笔谈,第2期,1941-09-16.
[37]文凤之.昆明出版物现状[J].读书通讯,第64期,1943.
[38]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9]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0]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