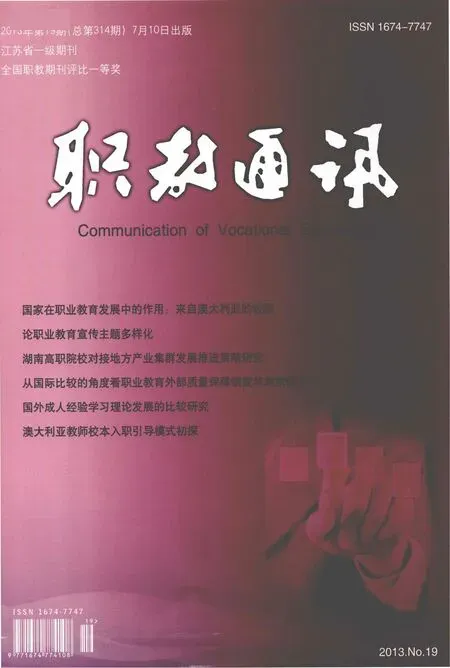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
臧志军
说到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人们会自然想起亚当·斯密的那段名言:
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一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隐喻被斯密用来形容充分运作时的价格机制,在价格机制充分运作下,自由市场里的供给和需求将会自然而然达到均衡。后人对这只手有各种引述和发展。有人就认为,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与政府的干预机制分别代表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于是产生了很多需不需要看得见的手的争论。在职业教育领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职业教育中的哪些行为只是私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而不需要政府参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应该伸多长?
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试图承担全部的职业教育责任,事实上这也不可能做到。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国家与地方责任共担的问题。国家与地方究竟应该在哪里划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呢?也许这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以下将通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说明。
一、地方自发的职业教育
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因为早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英国移民,英国只是在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时候才会允许技能型人才来到澳大利亚,所以早期澳大利亚人口中士兵与囚犯占了很大的比例。[1]默里-史密斯注意到,劳动力短缺对澳大利亚技能形成的影响: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直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不仅加强了技术工人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消磨了其他国家非常普遍的技术与非技术之间的广泛的鸿沟”。[2]默里-史密斯所谓的“劳动力短缺”是指澳大利亚早期历史基本是一些流放犯人和军人的移民史,数量少、技术低,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人口总数才达367万。[3]至于所谓的“消磨鸿沟”是指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形成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明显界限,技术工人有专门的成长通道,非技术工人难以进入到技术工人队伍中,但在澳大利亚,由于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这一界限被模糊了。
默里-史密斯还注意到了劳动力短缺的另一个影响:澳大利亚的行政当局形成了介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传统。从19世纪开始,政府就开始对私立或社区的职业教育提供资助。[4]默里-史密斯举了个具体的事例:“澳大利亚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的创立应归功于金(King)总督。在他1800年创办的女子孤儿学校,女孩们学习家政,在马卡里(Macquarie)创办的男子孤儿学校,男孩们学习各种手艺”。[5]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会开始壮大起来,技术教育在澳大利亚的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6]同时期,各殖民地政府开始采取一种布特林所称的“政府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施政策略,各殖民地政府开始与各类工会结成联盟关系以达到一系列社会目标。[7]这些合作催生了每个殖民地中的城市技术学院,也促使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的转向,从单独地对职业教育进行公共资金的资助转变为对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职业教育进行控制与管理。在世纪之交,各殖民地都成立了教育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统一管理。[8]至此,在对技术型劳动力的渴求下,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各殖民地都形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政府干预与管理。
二、走向国家制度的构建
在职业教育史的研究中,有一种理论认为,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不过这种理论在澳大利亚却并不完全适应。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1901年成立,照理应该延续之前100年由政府干预职业教育发展的传统与趋势,发展出一种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管理,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这里需要指出是,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重视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高质量教育的渴望,而不一定完全出于对职业教育的特别偏好。当时的技术学院不仅教授有关工业的科目,也大量传授古典和艺术课程。默里-史密斯甚至把这些学校称作“穷人的文法学校”。所以对技术学院的支持并不完全出于经济目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联邦政府在成立之初并不觉得有统一全国职业教育管理的需求。因此,建立一个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并不是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的澳大利亚人的当务之急。技术学院原来的“穷人的文法学校”的色彩有所减弱,开始专心开展职业教育,甚至开始把教学活动限制在向在职人员提供培训。这样一来,职业教育逐渐不再引起公众的兴趣。[9]所以,尽管也有一些人士提出把职业教育纳入联邦事务的诉求,但始终未得到足够的响应。
联邦宪法的第51条对联邦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包括国防、人口普查、货币发行、邮政等,明确表示联邦只能从事州际工商业权力、外部事务权力、征税权力等。联邦政府成立后严格区分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责任分担。有一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州政府曾经向成立之初的联邦政府寻求一些州事务的财政支持,维多利亚州的教育部长福兰克将之看作“不负责任的管理者”所为,而且“各州应拒绝联邦活动的任何扩张”。[10]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澳大利亚在20世纪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在这三次重大危机中,职业教育的作用重新得到评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职业教育被联邦政府作为了战后重建的一种手段。当时的主要理论是,通过职业教育可以对受到危机影响的人士给予一定的补偿。比如对于在战争中受伤的、学徒生涯被战争打断的人和老兵。
尽管联邦政府在介入像职业教育这样的各州事务上扭扭捏捏,政策环境上的变化还是发生了。通过像联合工程师协会诉阿德莱德轮船公司等案的审理①,人们逐渐认识到,联邦进入州内事务并不是一件坏事,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宪法96条帮助各州政策。②
联邦政府开始受到各州的压力,要求增加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20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教育厅长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就大力呼吁过联邦政府加强对全国教育的领导。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教育沟通交流的趋势。尽管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在20世纪的头30年还是成立一些全国性组织,如1916年成立的教育局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Directors Generalof Education)、192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Australian Vice Chancellors Committee)、193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Research)等。
这些来自全国教育界的压力使联邦政府逐渐改变对自身在教育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认知。同时,根据澳大利亚宪法,联邦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权利比较大,收入税、资本所得税等主要由联邦政府收取,随着联邦财政状况的改善,联邦政府开始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资助各州的发展,自然会产生关于联邦角色的新讨论。联邦政府开始直接参与教育活动,于1923年在堪培拉直接建立了一所学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联邦政府承担起了诸多以前不愿承担的责任。为了扶持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联邦政府在设备使用与人员培训方面广泛介入,此时联邦政府与职业技术教育已经无法分开了。在战后重建中,技术教育在老兵的退伍培训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对相关培训进行了大量财政资助。以这些方式,联邦政府的大笔经费开始进入原先被忽视的技术教育院校。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认识到,对职业教育进行全国统一管理的重要性。一战后的重建部就开始负责职业教育事务,新南威尔士技术教育主管被任命为全国的退伍转业培训办公室主任,这是第一个负责职业教育事务的联邦机构。到二战期间,在战争工业组织部(Department of the War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的下面设置了工业培训办公室,战争结束后,这一部分划归劳动和国家服务部(Department of Labor and National Service),每个州的技术教育主管都被任命为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些主任和副主任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全国职业教育问题,这一机制成为后来TAFE董事长会议(Australian Conference of TAFE Directors)的先声。这样,全国的职业教育人士团结起来,为后来发出更大声音奠定了基础。
战后,联邦政府开始加强对工业发展的领导,并且开始发展工业仲裁法律体系,这最终导致1956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学徒制顾问委员会(AAAC,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Advisory Committee)。顾问委员会的成立至少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把全国各州的学徒制负责人和技术教育界人士产生了联系,二是促使技术教育办公室的主任们开始正常会议。学徒制顾问委员包括联邦劳工部的代表和各州的官员,应被看作是第一个协调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
学徒制顾问委员会和早先的技术教育处长会议均反映了政策气候,即联邦政府只需承担最小的职业教育责任,同时,职业教育只被限定在其最狭义的范围内,在学徒制框架内执行。之后成立的全国培训委员会(National Training Council)继续认为,就国家利益而言,技术教育应被限制为提高工业生产力,在教育者与培训者之间进行很好的角色划分。
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教育政策重心是加强对学校的联邦资助力度,作为这一政策的成果之一,联邦政府也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由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澳大利亚政策也开始重视对科技的投入,1964年,通过州拨款法案中的科学实验与技术培训条款,联邦拨款开始资助技术教育,随后更是通过了专门的技术培训条款,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20世纪70年代,惠特兰姆(Whitlam)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他相信经济繁荣与教育进步是当时时代的两大支柱,他和工党的政治信条崇尚国家权力和中央政府的作用,鼓吹对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进行政府干预。[11]他曾宣称要利用宪法96条的拨款机制作为建立“ 公共企业的特许状”。[12]在这种政治风气下,联邦对职业教育的统一管理逐渐展开。
整个80年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在增加。1987年,联邦政府再次进行重组,把原来的就业与劳动关系部合并,成立了新的就业、教育与培训部。这个新部门打通了教育、培训与就业的关系。它成立的第二年就通过了国家工资的规定,把工资收益与技能水平联系起来,是国家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干预的标志之一。
20世纪90年代,可以看作是职业教育决策管理结构完善的10年,有两个标志性的机构说明澳大利亚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管理方式。首先是职业教育、就业与培训部长联席会议的成立。这个会议是各州部长讨论国家职业教育决策的定期机制,在这个会议之下还专门成立了常设的顾问委员会,对各州部长提出建议。1994年,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了全国培训局(ANTA),这是对全国的职业教育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成立后迅速承担起扩张职业教育市场的责任。全国培训局有六个目标:(1)建立全国培训体系;(2)鼓励行业参与职业教育;(3)建成高效培训市场;(4)形成高效的职业教育机构网络;(5)增加培训机会,提高培训质量;(6)增强跨部门联系(Taylor1996)。
从这些目标来看,全国培训局已经成为代表国家进行全国统一职业教育管理的重要机构,这个局的成立也标志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建立。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
(一)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注册培训机构”的平等待遇构建国家职业教育市场
企业、公立培训机构、私立培训机构、集体培训机构、中学、技术与继续教学学院、大学都可以成为国家认可的注册培训机构。国家并不需要扶持每一个培训机构的发展,国家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职业教育市场
中学阶段的校内职业教育、中学后阶段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和面向非在校生的学徒教育为主要框架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节点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在纵向上,中学生可以在校内学习职业教育课程,并可平滑过渡到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可以平滑过渡到大学学习;在横向上,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和参加学徒制的学徒可以相互渗透,在这个体系中,三者之间有相互渗透的趋势,其中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是职业教育的主体。
(二)澳大利亚通过联邦与州的协商机制规定了联邦与州的权限划分,联邦主要负责决策和质量保障,州主要负责经费使用和日常管理
从法律上来讲,澳大利亚政府间有两种授权方式:一种是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授权,把一些本来由州负责的事务交由联邦;另一种是联邦政府向领地政府授权,允许他们实施某种本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管理。这是由澳大利亚联邦特殊的地位决定的,1901年,原有的六个殖民地同意成立澳大利亚联邦,以宪法的形式规定的联邦与州的权力分配。但同时,澳大利亚大陆上还有大片土地在这六个州之外,就成为联邦的两个领地,联邦对这两个领地有管辖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干预领地的事务。但在实际操作中,联邦与领地仍然采取协商制,领地也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台面上的协商制度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决策系统的一个特色。
(三)澳大利亚通过政府间协议规定联邦与州政府按1:2 的比例进入职业教育日常经费投入,联邦教育部与州教育部门是日常经费的主要管理者
这种职业教育投入上的责任划分表明,州政府仍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人,国家的角色不仅是职业教育的投资人,更是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引导者。国家所投入的1/3的资金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或者说国家仅用1/3的资金就橇动了整个职业教育市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多数采用了中央和地方税收分账的方式,国家的投入到底起什么作用是一个许多国家都要研究的课题。
(四)国家通过财政专项的转移支付方式鼓励个人和雇主参与职业教育
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有三种资助方式,资金最大的日常性经费支出用于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等机构的基本建设和日常运行。而对于个人和雇主的资助则通过财政专项下拨专门资金,由个人和雇主申请。采用专项的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经常性调控进入职业教育市场的人数以满足国家技能目标的要求。
(五)国家通过认证、资助与授权等方式鼓励行业参与职业教育
认证是指行业组织不一定由国家组建,而可能是自发形成,国家通过某种方式认可其权利;资助是指国家拨付资金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授权是指政府把一些权力授予行业组织,如课程标准的制订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鼓励行业组织的发展,也可以形成行业组织之间的竞争,使行业的参与更加专业。
(六)国家通过全国统一的资格框架和全国统一的管理系统规范教育成效
国家管理系统不介入职业教育机构的内部运作和日常教学,它以资格框架和培训包为依据实行结果导向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的特点是国家管理出口和入口,教育培训机构管过程。这样一方面确保最终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保护教育培训机构的创新冲动。
(七)国家通过介入雇员的工资率规定技能的市场价值
国家以确定技能培训的回报率为目的提供一个制度框架,要求企业提供为不同技能提供恰当的回报。这里的回报不仅是工资水平的提升,也包括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等条件,是一种综合回报。
可以说,澳大利亚形成了以质量标准为中心节点的国家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国家通过统一的资格框架调节对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力度,确保教育部门按照大致相同的标准组织教学,生产部门、劳动部门也围绕资格框架进行人员配备和福利供给。在国家不出台教育计划的前提下,通过利益杠杆基本使职业教育发展达到了国家发展目标。我国的国情与澳大利亚有很大差异,但以上的这些做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国家管理策略。
注释:
①联合工程师协会诉阿德莱德轮船公司案:1920,联合工程师协会准备向它的成员颁奖,这些成员是包括阿德莱德轮船公司在内的843个企业的雇员,由于这些公司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州,因此,就出现了各州是否承认这些奖项的问题。其中的法律难题是:1904年通过的联邦协商与仲裁法案是否对各州有约束力。通过本案的审理,法庭支持了联邦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权力。——Booker,Keven;Glass,Arthur and Watt,Rob(1998).?Federal Constitutional Law:An Introduction?(2nd ed.).Sydney:Federation Press.
②宪法96条:宪法96条规定联邦政府“可根据本条款在各州认可的情况下向各州提供财政支持”。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Christian,C.K.,etal.(2006).A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breast reconstruction:A study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Annals of Surgery,243(2),241-249.
[2]Ostrom,Elinor(1994).“Neither Market Nor State: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ecture presented June 1,1994,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3]JACKSON,G.and DEEG,R.(2006-lastupdate).How many varieties of capitalism?Comparing the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es of capitalist diversity.http://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9930/1/dp06-2.pdf[Nov.21,2012].
[4]DFID(2005).Tools for Institutional,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TOPPSISOU/Resources/Volume201Tools-Sourcebook.pdf
[5]Hans Keman Federalism and Policy Performance——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from Federalism and Policy Performance edited by Ute Wachendorfer-Schmidt,Routledge|ECPR Studies in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Routledge2000,P202-205.
[6]Kingombe,Chirstian(2012).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Experience with Technical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IGC.
[7]Ostrom,Elinor.“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In PaulA.Sabatier(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M].Boulder,CO:West view Press.2007.
[8]Basurto etc.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IN STITU-TIONAL ANALYSIS:APPLYING CRAWFORD AND OSTROM’S GRAMMATICAL SYNTAX [M].London:Oxford press,2001.
[9]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Martina Krause&Christian Woll.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Germany 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M].Berlin:CEDEFOP,2007.
[11]Paul Geoff.Australia Facing New Skills Shortage,[EB/OL]http://ezinearticles.com/?Australia-Facing-New-Skills-Shortage&id=5210804.
[12]Greinert,Wolf-Dietrich,European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In Cedefop Panorama series:Towards a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in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