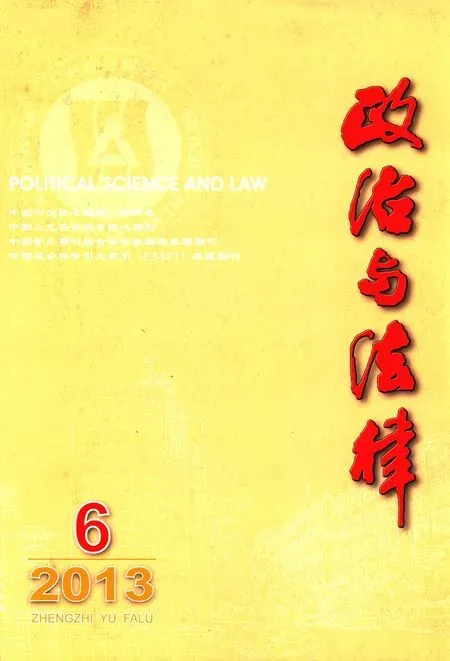论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以《侵权责任法》第79条为分析对象
张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论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以《侵权责任法》第79条为分析对象
张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依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现有的有关“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体系内,可将第79条视作一种转化情形。基于是否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这一客观评判点,实现对饲养动物责任的灵活归责。从体系解释和利益衡量等视野出发可发现,在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而致害时,其不得主张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免除或减轻责任;在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时,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可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减免责任。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管理规定;安全措施;体系解释;利益衡量;侵权责任法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针对“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所确立的归责体系中,第79条(即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条款)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如果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已经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在动物致害的情形下,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其是否可以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免除或减轻责任;在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下,其是否可以主张因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减轻或免除责任。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拟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对《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内涵进行阐释。
一、《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制度价值
(一)《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立法溯源
《侵权责任法》历经四次审议,第10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条文数量从少到多,对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在不同情形下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和程度加以分别,最终形成多层次的归责体系。1就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而言,其在第一次审议稿中并未出现。第二次审议过程中,原第79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饲养烈性犬等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次审议才出现了现第79条的规定。可见,《侵权责任法》第79条所作的规定实际上是从第二次审议稿中的第79条演化而来的,同时,第二次审议稿中的第79条分化为《侵权责任法》第79条和第80条的规定。
立法者之所以作此修订,是因为第二次审议稿第79条所规定的“违反管理规定饲养烈性犬等动物”,可作以下两种理解:一为法律法规禁止饲养烈性犬等动物,但饲养人违反该规定进行饲养,二为饲养人饲养烈性犬等动物虽为法律所许可,但其饲养方法和条件或对该动物采取的安全措施却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在这两种情形下,动物饲养行为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的不同,行为的潜在危险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和“依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之间的主观可非难性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区别,无论是对于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还是受害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且有悖于《侵权责任法》所具有的预防惩戒之功能。而“违反管理规定饲养”的不当用语却会导致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同样的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上述两种情形确实存在。因此,立法者对“未依据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和“禁止饲养的动物”加以区分。
未依据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一些具备高度危险性的动物,一般情形下被禁止饲养,但在一些特殊情境和特殊需要之下,其饲养为法律所允许,如因警用、军用、海关检验等执行公务所需或为进行实验等而被允许饲养或管理。以饲养烈性犬为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0条的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在现实中,烈性犬的饲养也并非总是为法律所禁止,在特定地域空间,烈性犬亦可被饲养或管理。例如,《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3年9月)第10条规定:“在重点管理区内,每户只准养一只犬,不得养烈性犬、大型犬”,同时《规定》第7条对一般管理区和重点管理区进行了划分。而依据《规定》第17条,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可以在一般管理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等动物,但应对其采取拴养或者圈养等安全措施。2由此可见,即使是烈性犬等动物,也存在法定允许饲养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当“依据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并不仅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0条所规定的一般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动物,而是还包括有相关管理规定就饲养作出专门规定的动物。例如,普通的犬类3、实验动物以及可以驯养的野生动物4。对于此类动物的饲养和管理一般也会存在专门性规定。在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其采取安全措施而致害时,则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规定。
(二)《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规范意义
法律用语所体现的是一种规范导向。显然,“禁止饲养的动物”表明的是,此种动物的饲养与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相悖。而“须对其饲养或管理采取安全措施”表明,此种动物的饲养为法律所允许。至于某种动物为何被允许饲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看,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动物的危险性较弱。而即使是同一动物,采取不同的安全措施,或是在不同区域内进行饲养,其危险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闹市区饲养大型犬和在空旷无人的草原地带饲养大型犬,就明显不同。二是基于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的考虑。例如,海关为稽查毒品等走私物品而饲养某警用动物。诚然,不管何种动物都具有一定危险性,但此种危险性实际上是抽象危险性。基于此种抽象危险性,法律将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设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然而,动物种类的不同以及动物饲养地域的不同则可能导致各种动物的具体危险性(或内在危险性)产生差异。在不同情形下,同样动物所存在的具体危险性是不同的,政策导向性也应存在相应的区别。就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而言,其规范意义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利于区分“禁止饲养的动物”和“须对其饲养或管理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之
间的具体危险性。一方面,在禁止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时,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未对他人利益尽到最低限度的照顾和注意义务。在此情形下,此类动物的饲养或管理已经为法律所明确禁止,饲养人或管理人只需对此禁令保持遵守,对其行为予以克制,即可满足有关要求。从主观可归责性出发,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饲养禁止饲养的动物,可谓是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的罔顾或蔑视。因此,由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最为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有利于惩戒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从法律用语来看,须“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就表明立法者对此类动物的饲养或管理持肯定态度。如前所述,即使管理人或饲养人保有烈性犬等动物,也并非总是为法律所禁止。允许管理人或饲养人保有此类动物,实际上是法律在风险与利益二者之间进行衡量之后做出的抉择。对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进行专门规定,既是考虑到动物整体的抽象危险性,也是充分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针对特定动物的饲养或管理而做出的区分规定。在尊重此类管理规定所保护的特定利益的同时,也可实现对受害人遭受损害的特定利益的兼顾。
第二,有利于促使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更好地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在动物的饲养或管理为法律所允许时,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因保有动物的行为而获有利益,要求其对动物致害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符合“利益之所归,损害之所属”这一原则的内在要求。同时,这也有利于实现风险控制成本的内部化。此类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作为危险的控制者,能够以最低成本管理此类动物。对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课以程度相对较高的无过错责任,不仅是公平合理的,且可以有效地发挥行为指引的功能,5引导人们遵守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从而抑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9条,与作为一般条款的第78条规定之间并不冲突,反而有助于实现归责体系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该条款可以在现有的归责体系中拉开梯度,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这也正是《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制度价值之所在。
二、体系解释视野下的《侵权责任法》第79条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适用多层次的归责体系,所以,针对《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疑问,应以体系解释的方法进行阐明,结合该条款在特定归责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加以解释。
其一,就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而言,饲养人或管理人是否可以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承担或减轻责任?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明示其一,排斥其他”的解释规则,《侵权责任法》第79条没有明确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以导致责任的减轻或免除,所以,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都不可能影响责任的承担。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公平原则考虑,受害人对因其自己原因导致的损害应自行承受,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可以减轻或免除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责任。7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总则性”的规定,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动物致害责任。8但是,当述及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时,同样是法律条文未就免责事由作出规定,却可推导出《侵权责任法》第80条规定适用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不允许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因被侵权人或重大过失而免责。这其中的逻辑转换难免令人生疑。
在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的情形下,饲养人或管理人之所以不能免责,是因为其所承担的是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而之所以从《侵权责任法》第80条解释出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无非是基于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的危险性。就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与管理规定允许饲养的动物而言,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讲,此二者的危险性确有明显差异。但禁止饲
养的动物与违反管理规定而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之间,其危险性的差异究竟该如何评判,却不得而知。尤其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例如,被侵权人故意挑逗动物,禁止饲养的动物与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哪一个更容易侵害他人,是无法判断的。法律条文的设计所应考察的是在设定具体义务之后,行为人是否遵从义务,而并不在于对客观存在进行探索。在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违反了法定义务,而将其以外的第三人置于动物的“本性”之下。动物的本性主要表现为其具有非理性,其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9在此情形下,各种动物之间的本性可能存在差别,但对此的界定不应是《侵权责任法》的工作和任务。侵权责任法应以救济受害人为首要目标,并对个人行为的自由与社会集体安全予以兼顾。10在行政管理规定对允许饲养的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设定了自由的规范和界限后,如果其未遵循此规范,应从维护社会集体安全的价值角度出发,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
此外,在饲养人或管理人未按照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下,如果允许其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免除或减轻责任,则意味着作为免责事由的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对于应按照管理规定而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此一来,在应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时,责任的承担则会出现如下情形。首先,因为《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属于一般条款,不论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是否采取安全措施,在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时,其都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其次,如果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免除责任。由此,《侵权责任法》第79条就没有必要针对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而专门作出规定,否则只会产生立法的重复。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否按照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都将与《侵权责任法》第78条无异。但是,从《侵权责任法》的现有规定来看,第79条是作为单独的一条而对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进行规定。据此,应当认为该条规定是立法者有意为之。从上文对《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历史溯源来看,更可证明立法者将此种责任进行独立规定是独具匠心的。在体系化视野下,《侵权责任法》第79条所确立的责任构成要件不同于第80条,第78条所确立的“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免责事由对其也无法适用。如此,才可证成该条规定的合逻辑性以及合理性。因此,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中,饲养人或管理人不得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承担或减轻责任。
其二,即使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依据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在该动物致人损害时,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侵权责任法》第78条是作为“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而存在的。因此,在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已遵守管理规定并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下,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不因此免责。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背景下,如出现前述情形,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8条所确定的无过错责任。
三、利益衡量视野下的《侵权责任法》第79条
对于《侵权责任法》第79条所规定的依据管理规定而被允许饲养的动物,无论是基于特殊的公务需要或因动物自身的危险性减弱而被允许饲养,皆为对不同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但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采取某些行动的人将在行动中以应有的注意不给其他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危险。动物的饲养将导致危险源的产生,饲养人或管理人作为危险源的开启者,有义务对该危险源加以控制。
如前所述,之所以产生允许饲养的动物与禁止饲养的动物的区别,是因为有动物的危险性不同之分。我国《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与行政管理法采纳同一分类标准,即某一动物是否可以进行饲养,是基于该动物所具有的危险本性。11在实践中,某类动物是否属于危险动物通常是由公安机关与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确定的。12法律上允许对某类动物进行饲养,实际上是基于对此类动物所具有的危险性的信任,并基于对自身的管理制度的强制性以及可行性的自信,即相信饲养人或管理人会按照管理规定而对该动物采取安全措施,以及对动物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安全措施会避免危险的实际发生,而容忍此种风险的存在。但是,此种风险(或危险)的存在势必会扩大普通民众的注意范围,加重其注意程度,而对其自由构成威胁和限制。因此,应对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致害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将损害承担转移至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从而实现利益的平衡。对于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而言,其作为潜在的加害人,可以采取诸如订立赔偿义务保险合同等特殊预防措施,来应对饲养动物带来的风险。13
在此情形下,如果饲养人或管理人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其作为危险的开启人、控制人和受益人而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却可因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免责,实际上是将此种风险成本转移到受害人的身上。对此,或许存在质疑,即认为如果受害人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那么即使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损害也不会发生或得以减轻。就此疑问而言,以同样的逻辑进行反问即可消解:如果饲养人或管理人未从事动物饲养行为,那么即使受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责任也无从发生。虽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赋予此种饲养行为以合法性,但该合法性是建立在动物自身危险性较弱以及饲养人或管理人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会产生实际的防免效果这二者之上的。就此而言,可以将此种合法性理解为“附生效条件”的合法性,即只有动物自身的危险性以及饲养、管理行为满足法定条件,才可获致其合法性。如果饲养人或管理人未采取安全措施,其饲养行为将丧失合法性。同时,允许此情形下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因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免除或减轻责任,也会不适当地扩大受害人的注意程度。如果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普通民众仍应尽到注意义务,无疑是将自由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张。但在目前,针对此种扩张的正当性却是存在争议的。因而,应坚持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即不得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的立场。14在此意义上,以受害人的注意义务的履行程度作为饲养人或管理人对自身过错的免责理由,是不妥当的。
此外,在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已按照管理规定,对所饲养的动物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下,仍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即使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也无法避免发生的损害及风险承担责任。15这是由危险责任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危险责任的情形下,责任人是否应承担责任仅取决于由其掌控的危险是否变成事实。16同时,即使已按照管理规定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该动物自身所存在的危险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有助于降低其风险)。从我国现有规定来看,行政管理规定针对动物饲养所设定的安全措施都较为简单,且通常并未依据动物自身危险性的不同而规定相应的安全措施。这就可能导致行政管理规定所设定的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因动物自身的危险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某些情形中,动物可能会存在危险性倾向。例如,某动物曾无征兆地咬伤人,而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对此知晓,其只有在管理规定所设定的安全措施之外,对其所饲养或管理的动物采取附加的安全措施,才能实现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如果以“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而使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免除或减轻责任,可能无法实现对第三人的利益的有效保护,同时也会导致动
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因此,基于动物自身的有用性、动物的自主移动能力及其危险本性,由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负担最低限度的保护公众的义务是正当的。17在动物致人损害时,即使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已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其仍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8条的规定承担责任,而非依照“不幸事件只能由被击中者承担”的精神由受害人自己对损害承担责任。但是,因为危险责任是在寻求“对允许从事危险行为的一种合理的平衡”,18在对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应允许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在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时不承担或减轻责任。
四、结语
鉴于《侵权责任法》第79条所具有的制度价值,应将其理解为一种转化情形,转化的关键在于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是否已经按照管理规定采取安全措施。换言之,如果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违反管理要求未采取安全措施,其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类似于《侵权责任法》第80条所规定的严格无过错责任,其所负担的注意义务和责任不应因被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减免。反之,则表明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已经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其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类似于《侵权责任法》第78条所规定的较低程度的无过错责任,但其可以因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减免自身所承担的责任。
注:
1参见杨立新:《三高危险责任:退两步还是退一步》,《方圆杂志》2009年第4期。
2《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养犬人对烈性犬、大型犬实行拴养或者圈养,不得出户遛犬;因登记、年检、免疫、诊疗等出户的,应当将犬装入犬笼或者为犬戴嘴套、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
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4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页。
5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718页。
6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刘智慧主编:《中国侵权责任法释解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
7参见邓鹤:《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研究》,《河北法学》2001年第3期。
8参见周友军:《我国动物致害责任的解释论》,《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
9参见李金招:《动物致人损害归责原则研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0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187页。
11参见兰仁迅:《动物损害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变迁》,《法治研究》2011年第7期。
12参见江平、费安玲主编:《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
13Vgl.MüKo-Wagner833 Rn.2.
14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载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版,第48页。
15Vgl Kurt Schellhammer,Schuldrecht nach Anspruchsgrundlagen samt BGB Allgemeiner Teil,4. Aufl.,Heidelberg 2002,S.492.
16、18[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5版),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17参见杨立新:《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24页。
(责任编辑:陈历幸)
D F522
A
1005-9512(2013)06-0035-06
张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