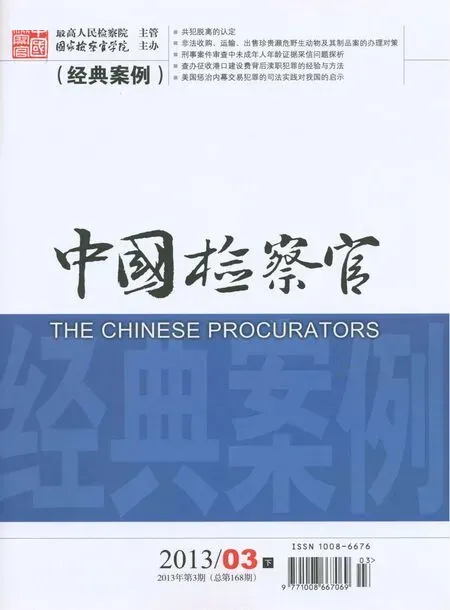以涉案财产的归属性区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界限
文◎史春衡 刘涛涛
以涉案财产的归属性区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界限
文◎史春衡*刘涛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400711]
案名:张某、王某受贿罪案
【基本案情】
2003年底至2010年,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原副主任张某在其担任广告部业务科华南片区经理、业务科副科长、科长及广告部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接受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负责人赵某某关照其广告公司业务并承诺事成后会给予“感谢”的请托,伙同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业务员王某找到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总裁李某,以在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要提价,通过广告公司代理其广告业务可以获得优惠的广告价格(即少提价),而且其本人还可以从广告代理公司获取“好处费”为条件,最终促成李某同意其药业公司由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在西南某地电视台代理投放广告。本案具体的代理情况是:张某先授意其业务员王某与李某所安排的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广告业务经办人员商定一个较高的广告价格,张某再授意赵某某安排其经营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派业务员按前述张某、王某与之已商定的较高的广告价格直接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签订广告代理合同,并安排王某联系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通过冒用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名义与西南某地电视台签订与前述广告代理合同内容相同但广告价格较低的虚假广告合同。最终,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以前述较高的广告价格支付广告业务款给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则以前述较低的广告价格支付广告款给西南某地电视台。在前后7年左右的时间里,前述几方人员采取相同的方式先后7次将“一高一低”广告合同价格下的差价款总计726.355万元据为己有。其中,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从中获得286.355万元,并将其余440万元的合同差价款拿与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张某,张某从中获得205万元,并将其余部分拿与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业务员王某及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总裁李某,王某从中获得150万元,李某从中也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合同差价款。
【判决结果】
本案的最终处理情况是,本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张某、王某、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总裁李某涉嫌犯(共同)受贿罪,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及其负责人赵某某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公诉机关以前述张某、王某、赵某某涉嫌犯(共同)贪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与此同时,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总裁李某因客观原因致使证据收集不足,被公诉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最终认定被告人张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0万元,违法所得赃款910万元[1]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认定被告人王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对其违法所得150万元予以追缴;认定被告人赵某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2]。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一)公诉机关对本案以“贪污罪”定性理由的分析
本案中,公诉机关以“贪污罪”为本案事实定性,笔者分析其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请托”的形式性。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负责人赵某某当时找到其 “业务熟人”——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时任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部业务科华南片区经理)张某帮忙介绍广告业务,此种“请托”应视为广告行业内的一种“概括性”请托,因为在赵某某找到张某帮忙时,并没有提出针对特定的广告客户进行广告业务代理,更没有提出之后如本案中那般如此“复杂”的操作方式与方法,对于自己“请托”的成功与否更是一个未知数。相反,赵某某的广告公司最终会与哪家广告客户合作,是采用签订“一高一低”价格的广告合同来代理的方式还是其他什么代理方式,甚至于“操作”利益(“一高一低”广告合同差价款)采取哪种分成办法均是由张某在主导、提出与安排的。二是“行为”的实质性。从形式上看,张某除了最初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出面商谈,其他事务基本上都是由其业务员王某在协调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方面的相关事务及与赵某某所安排的其广告公司业务员具体接洽。但王某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商定的较高的广告价格是张某提出与确定的,王某为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拟定的较低的广告价格也是张某提出与确定的,包括王某安排赵某某的广告公司业务员伪造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广告合同业务专用章等行为均是为实现 “操作谋利”的目的而实施的具体行为,并未超出张某的主观掌控范围。三是本案存在一定的“机巧性”。其一,对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而言,张某向李某提出通过广告公司代理其广告业务时,正值国家出台相关广告业务价格要大幅上涨的政策,而通过广告公司代理的方式就可以钻当时政策的一些漏洞,使其可以少涨价而获得价格上的一定优惠。作为广告客户的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其并不关心国家的相关政策会致使电视台的广告经营是会多收益还是少获利,只要其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就可以。因此,李某就同意了张某等提出的上述“操作”方案。其二,对于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而言,其广告公司当时的业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对于一直就在西南某地电视台直接投放广告的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只需要 “倒手一下合同,过一下广告账款”,也不需要承担广告制作等过多的业务成本,其只要求保证一定业务成本基础上的一定利润。对于张某提出的分成方案以及“一高一低”的合同差价利益在张某、王某、李某之间具体如何分配等事项,赵某某是不关心也不过问的。因此,赵某某也并不反对张某授意的“操作”方式及合同差价利益的分配“安排”。四是张某具备了客观的行为条件。张某作为西南某地电视台广告业务方面的“实质性”负责人,其具备协调各方、安排调剂及灵活掌控政策与变通执行的便利机会与条件。站在张某的角度而言,无论哪种操作方式,均满足了不同政策的基本要求,只是在不同政策的执行下,获得利益的主体及获得利益的多少会有所差异而已。五是客观方面“骗取”手段的典型性。张某虽然形式上授意、安排直接以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名义直接与西南某地电视台签订广告合同,但其是通过授意、安排王某与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联系伪造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广告合同专用印章进而伪造以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与西南某地电视台作为合同双方主体的广告合同的方式来实现的,对于西南某地电视台这一单位主体而言,其对于张某“操作”本案业务的真实情况是不知道的,因此其具有构成贪污罪客观行为方面所实施的典型的“骗取”手段。六是“一高一低”的合同差价款应当被视为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得而未得到的公共财产。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本身就多年来一直直接与西南某地电视台签订广告合同,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支付广告款,即便是依据当时要求涨价的广告政策,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如果仍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需要基于更高的广告价格支付更多的广告价款,其更多的广告价款本身就是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当收益的公共财产;反之而言,如果没有张某等的“操作”行为,西南某地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公共收益,正是张某、王某、李某、赵某某四人共同“贪污”了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得而未得到的国家公共财产。
(二)审判机关对本案以“受贿罪”定性理由的分析
本案中,审判机关以“受贿罪”为本案事实定性,笔者分析其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请托”的实质性。无论赵某某当时请张某帮忙介绍广告业务的目的最终能否实现,也无论采取如何的“操作”方式及利益如何分配,在本案之初,确实是赵某某代表其广告公司向张某提出了“请托”,并许诺给予其“好处费”。这应当被视为一种实质性的“请托”。二是,“行为”的目的性。张某在本案的“操作”中无论是亲力亲为,还是授意安排,均应被视为其是为了达到收受贿赂的目的而为行贿主体实施的实现“请托”事项,既而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三是“市场行为”的自主性。无论是公主体,还是私主体,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应当处于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获取可得的竞争利益,并承担相与对应的市场风险。对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及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而言,他们各自的负责人李某与赵某某所作出的“只要本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其他与其不相关”的处断正是平等市场主体之特有主观状态的反映。也就是无论获益还是利亏,只要是市场主体自主作出的选择,他人就无权非议。由此,即便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先前一直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如今却选择通过中介方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代理来与西南某地电视台间接开展广告业务,这都在其自主权限范围之内,自主可行。四是“政策”选择的主观性。各种政策的制定皆有其当初制定的意旨与目的,但交叉边界与模糊地带难以避免,为了特定政策的“实惠”而创造条件以符合特定政策的特殊要求之“变通”做法更难以对错评价。本案中,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按照既有方式直接投放广告就需要大幅涨价既而支付更多成本,如通过第三方的广告公司代理则可以少涨价而相对减少成本支出,加上张某在贿赂利益驱使下创造条件以选择特定政策予以适用,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一定意义上国家不受损失前提下的几方“利益均沾”。如此主观性的“选择”适用政策难以断言其是贪污背景下的违法之举。五是客观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典型性。张某在得到了赵某某许诺给予“感谢”的承诺后,通过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的业务“操作”,最终现实性的为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谋取了286.355万元的不正当利益。张某等的行为在本案中属于典型的收受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六是“一高一低”广告合同的差价款应当被视为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不应得而得到的非公财产。赵某某的广告公司既然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签订了广告业务代理合同,从法律上讲其确实成为了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广告代理公司。赵某某的广告公司基于一定的成本与利润测算,在直接代理与间接投放之间所形成的一定数额的广告款差额应当被视为是其广告公司的经营收益,其收益所有权理应为其广告公司所有。只是因为这是在其向张某、王某等进行单位行贿的前提下,在张某、王某的安排、操作下才实现的,所以说这是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所得到的本不应得到的不正当利益。但仅考察该收益本身的所有权性质,理应视为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完全所有。就本案而言,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获得的上述收益当然属于不正当利益,其从中分与张某、王某等的钱款当然属于单位行贿的贿赂;相对应的,张某、王某等收受该贿赂当然属于“受贿”犯罪。
(三)司法机关对本案不同定性理由的比较分析
基于刑法理论之犯罪四大构成要件说,本案在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中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犯罪的客观方面实施了哪些具体行为等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疑义,唯独在犯罪客体之涉案财产(“一高一低”的广告合同总差价款)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即从财产所有权归属上分析,“一高一低”的合同总差价款726.355万元究竟属于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得而未得到的公共财产,还是属于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不应得而得到的非公财产?针对本案而言,上述财产的所有权划分直接决定着本案事实的定性。如果欲对本案涉案财产的归属予以准确划分,可能需要着重研讨如下几个相关方面的内容:
一是认定犯罪性质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主客观相一致”是刑法理论中认定犯罪的基本要求。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定罪必须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上综合判断。结合本案而言,涉案人员于本案中的各个涉案行为皆是较为明确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通过其客观行为来认定其主观状态,既而在确定的主观状态下来分析其客观行为的性质。例如,“请托”介绍广告业务的行为究竟属于行受贿的“指标”行为,还是仅为致使贪污的形式诱因行为;又如,张某的授意、安排行为究竟属于为达到受贿目的而为他人谋利的行为,还是仅为实施贪污的实质性方式、方法。笔者认为,本案中张某自始至终授意、指挥、协调、安排了本案绝大部分(或曰起核心作用)的行为,结合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的被动谋利状态,王某的依指挥执行行为,以及李某的“事不关己,任其所为”的实际状况,加之张某的职务、地位的恰当与适宜,还有相关广告业务政策出台的适时性等相关因素,本案张某贪污的主观故意似乎更胜一筹。
二是政策选择的正当性问题。前文已述,依据新出台的广告业务政策,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如果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就要付出更多的广告成本;相反,如果通过广告代理公司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则可以利用一定的优惠政策而减少自身的广告支出成本。从形式上进行相关利益的权衡与取舍,答案是显而易见,但具体就本案而言则有其特殊情况:其一,张某所谓的只有通过广告代理公司来开展广告业务才能获得较低的或曰涨幅较小的广告价格纯粹是虚构的,只不过是以此来蒙蔽李某,将其作为“要挟”李某同意通过广告代理公司来代理其广告业务的所谓“客观形势”条件。其二,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本身具备或者说其可以通过答应“改变”其广告的播出方式而继续直接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同时也可以享受此种“改变”下的广告价格优惠政策;也就是说,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并非必须通过广告代理公司向西南某地电视台投放广告才能享受到后来完全一样的优惠政策。其三,站在西南某地电视台这一单位主体的角度来看,其主观上认为自身与以往相同,仍然是由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直接向自身投放广告的。因为在张某的安排下,赵某某安排自己的广告公司伪造了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广告业务合同印章,而以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的名义直接与西南某地电视台签订的广告合同,西南某地电视台本身是不知道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与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还存在另外的广告代理合同(即价高、真实的广告合同)。就此而言,张某是利用了政策的可选择性,或者说是通过“安排”创造条件(如说服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同意改变其广告播出方式等)以满足政策要求,既而从中掘取非法利益。也可以说,对于东南地区某制药公司这样的优质广告客户的一贯广告合作方式,人为、主观的进行了既定合作模式的改变,应当正常方式投播广告,依政策正常大幅涨价,却改变既有的广告投播方式,规避大幅涨价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从当时相关广告政策出台的背景及意旨来考察,张某对相关政策的选择适用更应偏向被认定为不具正当性。
三是刑法所保护利益的时代性问题。这里就要谈到本节开头所提及的本案涉案财产归属的准确划分问题。基于前文所论,“一高一低”的广告合同差价款如果被认定为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得而未得的公共收益,当然对张某等人认定“贪污罪”准确无疑;相反,其如果被认定为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不应得而得到的非公财产(不正当利益),当然应以“行受贿”犯罪来为本案定性。在前述认定本案“受贿”犯罪的定性理由中,审判机关有一条核心的“分界”理由——“西南某地电视台并未受到经济损失”。关于该理由,笔者有几点思考:其一,政府相关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损益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笔者赞同公平市场竞争下的正常损益状况之理性认可。其二,在非公主体与公主体的市场活动收益“分配”中,笔者赞同“让利于民”。其三,单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本来在正常情况下言之“西南某地电视台并未受到经济损失”却也无可厚非,但就是因为该种状态的形成是公主体之执行个体主观“操作”而人为“炮制”的结果,所以笔者更赞同“一高一低”的广告合同差价款属于西南某地电视台应得而未得到的公共收益,本身具有公共财产之属性。也既此而言,本案被告人张某、王某、赵某某等人似乎应以“贪污罪”予以定性更为准确、适当。
注释:
[1]本案被告人张某另犯两宗(单独)受贿罪,在此两宗受贿案中张某收受贿赂共计705万元。
[2]因公诉机关对赵某某的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未予指控单位犯罪,虽然其本应构成单位行贿罪,但基于不告不理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西南地区某广告公司的相关刑事责任不能追究。